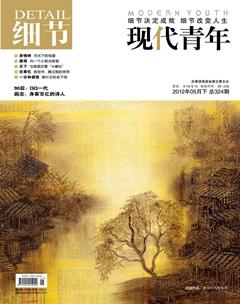美,看不見的競爭力(二)
蔣勛
最微小的努力可能是最大額救贖
中國人有很多美的實踐,但無可否認,最早讓美成為一門學問的是西方人。“美學”這個詞是后來日本人翻譯的,翻譯產生了很大的問題,仿佛美學就是研究美和丑的學問。然而事實上,美學的拉丁文原意是“感覺學”。
也許我們可以閉起眼睛,感覺一下自己的口腔里有多少味覺的記憶,自己的鼻腔里有多少嗅覺的記憶?
我曾把學生帶到菜市場,臺灣的菜市場收工之后,會打掃得很干凈。我拿布蒙住學生的眼睛,讓他們猜白天哪一個攤賣什么。結果他們很快就找到了賣魚、賣蔥、賣姜、賣牛羊肉的攤子。
那么,氣味到底是什么?它是肉體生命已經不在了,還在空氣里流動著的東西。
母親過世以后,我常常聞到她的味道,我一直覺得是我的幻想,因為我跟她太親。做了菜市場的實驗,我才發現:鼻腔的記憶體是這么靈敏,最愛你的人已經離你而去,她的味道卻揮之不去。
幾年前,發現鼻腔里記憶腺體的科學家已經得了諾貝爾獎,他發現人能分辨一萬多種嗅覺。你能聞出這么多的味道嗎?你是否記得春天從北方吹過來的風沙的味道?去香山的時候,你是否聞到過松樹的清香和苔蘚的潮濕?收割后的田野、大汗淋漓的愛人,是否在你的鼻腔里留下記憶?
年輕的時候,我在巴黎讀書,讀到第四年突然很想家。在香榭麗舍華麗的街道上,驀然覺得秋天的荒涼。忽然,我的鼻腔釋放了一種味道,讓我一下子熱淚盈眶。那是臺灣夏天七八月間,太陽曬了一整天,曬到土都發燙,忽然來了一陣暴雨,土壤泛起的味道。我才發現鄉愁是氣味。你想家的時候,想的可能是某種奇怪的小吃,它一下子把你底層所有的東西都喚起。
你的眼睛能看到多少種顏色?科學家說,我們的視網膜能分辨兩千多種顏色。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奇怪,有那么多嗎?紅、藍、紫……你數幾個就數不下去。
剛才我們講到,汝窯是世界第一瓷器品牌,有名“雨過天青”,最早是五代后周世宗創造的。別人問世宗:你喝茶的茶杯是要藍色的還是綠色的。他看著天說:給我燒一個雨過天晴的顏色。工匠很犯難,因為他要等下雨,等雨停,要看天空很久,觀察到天光在藍跟綠之間變幻,其間又透露出太陽將要出來的淡淡的粉紅色。聰明的皇帝宋徽宗把它沿用下來了。康德說“美的判斷力”,把這樣的色彩固定在瓷器上,需要多么高超的“美的判斷力”!
我們在作美的判斷的時候,視覺通道打開了、聽覺通道也打開了。
聽覺并不只是聽貝多芬、巴赫。今天是寒露,入夜以后,如果你仔細聽,應該可以聽到樹葉的沙沙的聲音,伴隨秋天最早到來的是聲音。我們的古人寫過多少關于“秋聲”的詩,古代文學里有多么好的敏感度!如果我們只知道讓孩子背唐詩宋詞,而忘了讓他聆聽秋天的聲音,那沒有太大意義。
秋聲一來,過不了幾天,香山滿山的銀杏都會變黃,灑落一地。
今天我們講競爭力,掉了還有什么競爭力?因為接下來的季節是一個艱難的季節,在緯度這么高的地方入秋入冬養分是不高的,只能把部分肌體犧牲掉,保存最好的水分和養分,來年春天重新發芽。如果你看到了秋天凋零的悲哀,那你恐怕不懂什么叫“看不見的競爭力”。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每一天都在做美的功課,可是他不講話。
我最敬佩的老師佛陀,沒有寫過一本書,我們今天看到的很多佛經,不過是他學生的筆記,所以開頭總是說“如是我聞”。有一天佛陀不想講課了,就拿一朵花給大家看。他的意思是說:我一生講的經,就在那朵花里,你懂得了那朵花,就懂得了生命本身。
回到生命的原點,才能看到美。美最大的敵人是“忙”,忙其實是心靈死亡,對周遭沒有感覺的意思。我們說“忙里偷閑”,“閑”按照繁體字的寫法,就是在家門口忽然看到月亮。周遭所有最微小的,看起來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可能是我們最大的拯救。我不覺得,今天在這個城市里,我們講任何大道理對人生有什么拯救,我們能做的是許許多多微不足道的小事,一點點像女媧補天一樣,把我們的荒涼感彌補起來。
看到大,也關心小
這個城市有多少被你遺忘的角落?
大家都知道《清明上河圖》,一個畫家受命去畫他的城市,表現其中的繁華。畫家畫了一千六百多個人,各式各樣的場景。其中有一個場景是:官家的轎子出來,前面有人舉著“肅靜回避”,一個小孩在路中間玩,他媽媽怕他被馬踩到,驚惶地把他抱起。如果是你受命拍一個關于北京的紀錄片,你能不能拍出這個畫面?
還有一個畫面,出現在畫卷快結束的地方。一個做大官的人進城,前有開道車,后有隨護。城門口有一群叫花子,其中有一個沒有腿,做官的人回頭看了他一眼。看到這個地方,我覺得這個畫家真了不起。我的學生問我:你覺得那個做官的人后來給乞丐錢了嗎,我說我不知道,我覺得一個畫家能畫出大官跟乞丐的對視就很了不起了。
好幾年前,我路過天安門廣場,在長安街上看到一個畫面:那一定是一個鄉下來的婦人,因為只有下田勞動的人才會有那么粗壯的骨骼。她喂孩子吃奶,毫不遮掩,孩子吃飽了,奶汁還很多,她就讓奶滴到長安街上。我覺得那個身體好動人:她跟那個土地是在一起的。我問自己:T臺上的美跟這個婦人的美,哪一個能讓我記憶更久?
美不僅僅是華服名模,甚至不僅僅清風明月、巴赫貝多芬,要看到美,我們首先要看到生命存活的艱難。
唐朝人喜歡畫牡丹。我曾在二月間到日本皇宮里看過牡丹,全部用草圍著,上面還撐一把傘,因為牡丹有一點風吹雨打就會凋零。宋朝以后發現牡丹的美不能體現生命頑強的競爭力,就開始畫梅花。王冕的《南枝春早》成了傳世名作。如果說唐朝創造了牡丹的美,宋朝發現梅花的美,我們這個時代用花來象征,可以找到什么?
上海世博會的中國館使用漢朝斗拱的造型,堆砌出一個倒三角形的飛檐式建筑。我看了很辛酸。因為我看到它強大背后,是幾乎要被世界列強瓜分殆盡的屈辱記憶。所以它的強是一定要撐出來。可是我看到英國館,輕輕松松就做出一個好漂亮的東西。當時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大國崛起,必須有最篤定的自信,不去做場面上的東西,而是回到最小的事情,慢慢做,不一定要那么快。現在的強有一點用力,并且用得好辛苦,我害怕它變成煙火,那么絢爛華麗,可是一下沒有了。
唐的文化、宋的文化為什么有厚度?因為它看到大的,也關心小的。杜甫擠在難民里面逃難,寫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如果這十個字變成千古絕唱,我覺得不是詩的技巧,而是詩人心靈上動人的東西:他看到了人。同樣那捧白骨,很多人走過去都沒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