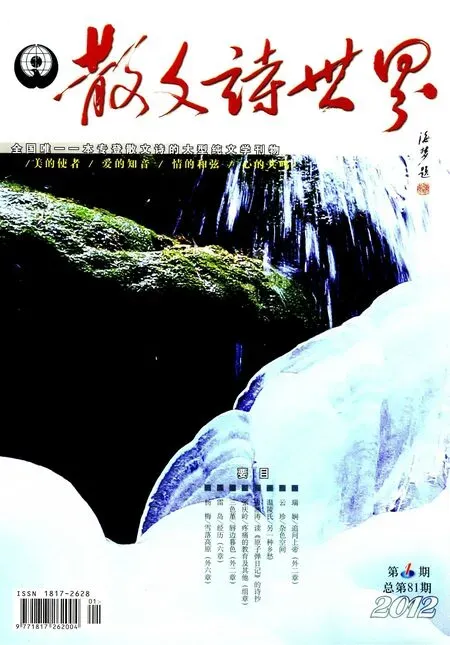河以西的游牧方式(組章)
青海 才 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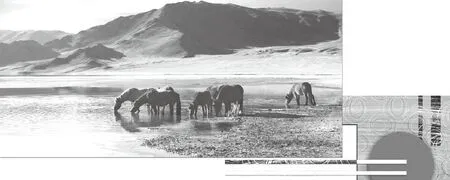
轉 場
托勒南山的牧草泛青的時候,最不安分的要數那些野性的牦牛。一個冬天的圈養,使它們看起來焦躁不安,原本黑亮的皮毛粘上了枯草和糞便,而眼睛里傲慢、野性的光澤卻一點也沒有改變。
的確到了轉場的時候了。天邊沉悶的雷聲和消融的溪流都在暗示著這一切。
于是,漢子們玩轉了剪刀,讓大片的白云堆積起來。必須要在轉場之前,先讓羊們脫去棉衣,好給心愛的女人添置一些珊瑚之類的飾品,讓她成為轉場人群中的亮點。因為,她是這片草原驕傲的女主人。
對于逐水草而動的牧民來說,全部的家當和牛羊頂不過女主人的一套服飾。在這里,女人是花,是頂著露珠、晶瑩剔透、散發著草香的野花。
是到了該轉場的時候了。阿格日山下濃濃的綠意和鐵青馬舒展的四蹄告訴牧人,一個浪漫的草原之夏又將開始。
不久,托勒南山將會在薄霧里延伸,清純的泉水漫過熬了一個冬天后完全蘇醒的土地,牛羊點綴山河的靈動。駐牧于山根的點點帳篷上,會升起一縷縷達玉部落后人的煙火。
雪線下緞子一樣的新綠,讓初來乍到的牧人興奮不已。逐草的牛羊,在這奇異的沼澤地上撒歡,水晶花漂染過的蹄子,如妙齡女胭脂的唇,散發著清香。
轉場,對于牧人來說,是全新的修復和放松,是游牧者的一個新起點。
駿 馬
我匆匆走在山梁上,趕赴一場關于親情的約會。
在夏季草場,一片片白云,在天邊開出憂郁的花朵。就在此時,我打馬走過草原。草原已經很蒼老了,如我的老人一樣。
此時,只有托勒南山的粗線條、倔犟的四季風、大氣的牧人,輪回不息。
面對古老的草原,我輕輕地問一聲胯下的駿馬,你能否守得住最后的一片蔚藍,坐擁你足下的無疆?
駿馬漠然。在一聲長長的嘶鳴后,竟揚起四蹄飛奔起來,在風中,我身上的衣服成了一些花花綠綠的旗子。
我知道,夏季的空氣從此揉進豪放和奶香的氣息,駿馬和挾持的牧歌仍將席卷草原。
星 星
黑牛毛帳篷的天窗打開了,夜晚,我在“它夸”上煮著一鍋星星。
夜很靜,靜到我心頭的詩歌一句一句往外蹦,如置于炒鍋里的豆子,攔也攔不住。看那搖曳的火苗舔著鍋底的樣子,就像草原前世的一個夢,無法睡醒。我想,我是屬于夜的,屬于夜的草原。燈火闌珊的城市,有多少無依的心靈,有多少無奈的冷寂?漫步在浩河邊上,人來車往,燈火闌珊,卻常常暗自傷懷。
此刻,我有了自己的夜,擁有自己的寂寞。沒有雷,沒有風,也沒有其他的念想,只有犬吠聲一高一低地傳來,在靜寂中傳達詩情畫意。
而星星并不在乎我的注視。不在乎高于她的天和低于她的山,是怎樣地將她包圍,甚至吞噬。
這些星星,它們只存在于夜晚,笑臉都那么燦爛。她仿佛就是一些女子,初裝待嫁,羞澀地眨巴著眼睛……
夜深了,我卻在黑牛毛帳篷里的“它夸”上,煮著星星。
饅頭花
盛夏的草原被饅頭花覆蓋著,煞是好看。
饅頭花,又名狼毒花。藥典《別錄》中說:“有大毒。”
從我知道花的時候起,我就熟悉饅頭花,草原上到處都是。折斷了它,就有像奶子一樣的液體流出來,沾滿一手,很好玩。
我一直欣賞草原的廣袤,一直固執地喜歡那紅白相間略顯寂寞的饅頭花。喜歡它的硬氣,更喜歡它明明白白、無所掩飾的本真。雖然有毒,但不虛偽。
在山岡上,真讓人有一種“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感覺。轉過幾道山梁,在那綠海一樣的草地上,一簇簇紅色的花蕾在招搖,一捧捧白色的花朵在綻放,像是織錦的帕子。
但其實,在草原上,狼毒花的出現,已被視為草原的一種災難性警示,一種生態趨于惡化的潛在指標。
然而,我對有些人事,從心里喜歡她,也就會心甘情愿地親近她,甚至中毒,也無怨無悔,永不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