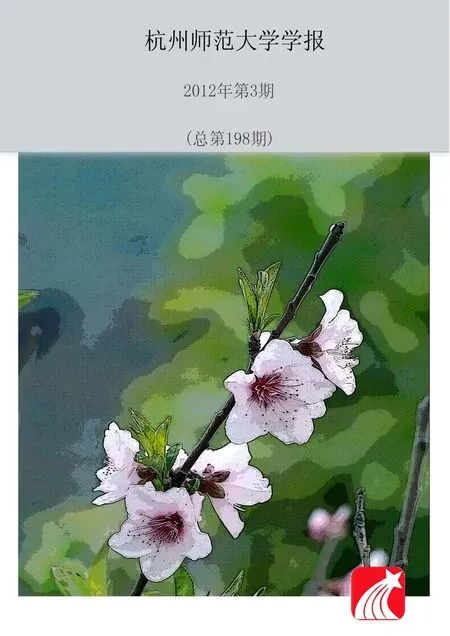“電影雙重本性”視域中的紀錄片
王志敏,趙 斌
(1.北京電影學院 電影學系,北京 100088;2.北京工業大學 人文社科學院,北京 100022)
影視藝術研究
“電影雙重本性”視域中的紀錄片
王志敏1,趙 斌2
(1.北京電影學院 電影學系,北京 100088;2.北京工業大學 人文社科學院,北京 100022)
電影是以鏡頭形式呈現、可以配有聲音效果的雙頻活動影像,一種對表面現象進行制造(紀錄或合成)的綜合媒介。在這一全新的電影概念之上,電影媒介具有雙重本性——“紀錄”與“合成”。在這一前提下,傳統的“紀錄片”可以稱作是“資料片”。以重新命名為契機,對電影合成的媒介功能、紀錄與歷史、紀錄與合成的關系等問題可以作出新的理論剖析。
電影;數字技術;合成;紀錄
電影有四大片種的說法:故事片、紀錄片、動畫片和科教片。事實上,這種分類方法明顯存在著重疊的問題。動畫片和其他三個片種差異性的界定依據一個原則,其他片種之間的界定則依賴另外的原則。麻煩在于,大部分動畫片都是“故事片”,而且現在又出現了“動畫紀錄片”,所以,故事片和動畫片的關系,仍未界定清楚。到目前為止,對于分類,人們仍然提不出更好的方案,只能姑且遵從約定俗成的習慣。
但我們必須認識到現有分類方法的弊端。例如,對故事片和紀錄片之關系的模糊認知,直接影響了紀錄片的創作和發展。目前,這方面的研究非常之少,沒有根本的理論推進,其主要的原因是電影理論的研究水平和發展程度不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電影理論應該進行根本性改造。我們在這里提倡的是,要解決問題就必須回歸電影的本性:從電影的全新定義和全新理念開始,在“紀錄片與故事片”問題上嘗試這一做法,是梳理和推進整體性電影學研究的系統策略的一部分。
基于廣義電影及其媒介屬性,我們把電影定義為:以鏡頭形式呈現的,可以配有聲音效果,并具有畫面性質和深度感或立體感的活動影像,它是一種專門紀錄或合成表面現象(現實表象和意識表象)的異質綜合性媒介。也就是說,是一種具有紀錄與合成雙重屬性的現代化媒介。
在這一定義中,我們首先強調的是鏡頭的性質,這一點把電影與其他媒介做了區分;而重要的是,這一定義強調了電影的雙重本性——紀錄與合成。關于電影的本性,或者巴贊意義上的電影本體論問題,由于計算機和擬像技術的介入,在今天又一次變成了爭論的焦點。重溫巴贊的論述,有必要理解巴贊的電影本體論思想的兩個要點:
第一要點是“完整電影”,或者說是“完整神話”。第二個關鍵在于照相性,即電影的媒介屬性。電影在紀錄方面的獨特性源于攝影術,它是電影能夠完成“完整神話”這一任務所必需的媒介保證,這一保證是歷史性的,但不是邏輯性的。巴贊敏銳地指出,照相性只是完成“完整神話”的偶然的工具,電影與照相術結盟純屬歷史巧合。或者說,電影僅僅是偶然間遇到了最能展現其完整神話的物質性媒介——攝影術;反而是木乃伊情結(人類希望在虛構世界中找到現實的對應物并將其存在的時間永久封存)的存在,攝影術才偶然充當了承載這一內在情結的媒介。這就好比伊卡洛斯的古老神話要等到內燃機發明以后才能走向柏拉圖的天國。[1](P.17)
關于電影的完整神話,巴贊在《電影是什么》一書的開篇就進行了基礎性的論述。也就是說,他非常明確地承認了電影的想象性(或幻覺性),甚至比“精神分析”的電影理論更早地介入了對戲劇與電影的比較。他預見性地指出,關于“在場性”和“認同”的解釋并不能厘清電影和戲劇的差異,也不能分別達致兩者的最高本質。[1](P.154)這些問題最終還是由電影精神分析語言學理論給出了完滿的答案。
符號學家艾柯較早引入了對攝影圖像的語言學分析,特別是對大量基于攝影的廣告圖像的分析,第一次用“分層(分節)理論”對 “合成” 的圖像進行了表意分析。如果我們再考察電影精神分析語言學理論的要義,對電影本性的理解就會更加明確:電影語言學首先承認照相性這一事實,麥茨在《電影的意義》開篇即用萬字表述了這一前提;但隨后即把目光轉向了基于活動照相性的鏡頭組合理論——電影的語言(敘事和修辭)。麥茨觸及了兩個基本的緯度——一個是現象學的、具備印象真實感的“攝影圖像”(紀錄),二是對想象的能指(組合連接的、分層合成的*麥茨并沒有給出合成這個概念,相關的討論主要針對的是歷時組合的蒙太奇鏡頭,這由特定歷史時期所能提供的案例所決定,但在麥茨理論中,能指操作的對象已經包含了疊化而產生的新圖像。紀錄與合成是電影的雙重本性,本文在行文中涉及的合成,指的是電影基本意義單元(鏡頭)內部的合成問題,因而與蒙太奇、長鏡頭和意識流鏡頭三者并立。)的語言學操作。
因此,我們把電影的本性定義為紀錄與合成,對應并發展了巴贊所說的電影的本體論意義上的新“地形學”理念;其有效性為電影本體論的第四個里程碑,即在蒙太奇、長鏡頭、意識流之后出現的合成鏡頭所支持。計算機數字技術和動畫技術,都是合成鏡頭的重要技術手段。當下,正是電影合成鏡頭大行其道的發展階段。關于這一點,只要我們稍加注意就不難發現。美國影片《阿凡達》(2009)、《2012》(2009)和《美國隊長》(2011)等一系列影片都是杰出的例證。
新的概念一定會導致產生新的版圖,即巴贊所說的電影的新“地形學”。我們把新版圖內的電影分成七大類*關于這一分類的最初理論表述,參見王志敏《電影形態學》“緒論”部分,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1.故事片(feature):運用雙頻手段表現故事;2.資料片(documentary):運用雙頻手段描述事實;3.節目片(program):運用雙頻手段安排事項;4.廣告片(advertisement):運用雙頻手段推介產品;5.論述片(discourse):運用雙頻手段探討問題;6.抒情片(Lyrical):運用雙頻手段抒發情感;7.虛擬片(virtual reality):運用雙頻手段呈現情境。
這七種電影形態,并非依據“內容”而定,而是依據使用雙頻手段的方式和目的,特別是混合“紀錄”與“合成”的方式和目的來劃分的。
這里我們對涉及紀錄片這一片種進行相關的理論探討。
首先,來看與紀錄片相對應的故事片,即虛構敘事性電影。故事片是電影在影院銀幕和電視屏幕上發展得最為充分的一個種類。電視(廣義電影的形式之一)的出現以及隨后計算機網絡的出現使得故事片不斷突破原有的疆域,包括呈現空間和藝術形態,例如,電視劇、電視電影、網絡電影、網絡劇等,最終演變成整個電子媒介產業鏈條中最有活力的組成部分之一。它的傳播與接收具有多元化和跨媒介特征,即不局限于特定的方式、媒介載體和空間場所。
資料片就是原來我們稱之為紀錄片(documentary)的主體部分,是指運用雙頻手段描述(紀錄或呈現)歷史及現實的類型。其主要的功能是,提供知覺和感受歷史及現實的資料。
我們曾強烈建議將中文的“紀錄片”這一沿用很久的稱謂改為資料片,即把“故事片/資料片”,而不是把“故事片/紀錄片”作為對立項。當然,這一提議肯定會遭到紀錄片創作者乃至某些研究者的強烈反對。原因首先在于,他們并不了解,“紀錄表象”并不只是“紀錄片”的手段,而是包括故事片在內大部分電影的手段之一。“紀錄片”這一稱謂大有混淆紀錄這種“非專門屬性”和“專門屬性”之關系的勢頭。另一個原因在于,他們不了解歷史和現實不僅是不可復制的,也是不可紀錄的,更談不上虛構;可以紀錄的只是歷史或現實的部分表象,即便是這些被有選擇地截取下來的表象,有時也不得不借助合成手段,才能發揮幫助我們了解和認定歷史及現實的資料呈現功能。歷史瞬間即逝,紀錄片工作者并不總能當場捕捉其表象。即便如此,考慮到電影的雙重本性,運用計算機數字技術,還能通過“合成”的方式重新把它呈現出來,并且方便地傳遞出去——這對于電影、語言、思維乃至歷史與文化而言,都將具有偉大的劃時代意義。因此,合成是一種相當偉大的功能,絲毫沒有貶低紀錄片之意。
這一界定的意義還在于徹底打破過去強加在“紀錄片”和“歷史及現實”關系之上的一切不實之詞。毫不夸張地說,如今大部分涉及紀錄片的理論,都與此問題相關,都是這一問題的延伸。例如,“紀錄與語言(特別是修辭)的問題”——西方電影理論界圍繞近些年流行的紀錄劇或偽紀錄片而展開的混戰*這一爭論可參考孫紅云《真實與虛構最有爭議的混合:紀錄劇》,《電影藝術》,2009年第1期.便是這一問題的反映;還有“紀錄片與真實的問題”——這一問題是國內外紀錄片研究領域長久的爭論焦點。
“真實”的概念,在西方延承自一個源遠流長的邏各斯傳統,即將“真實之實在”與“純粹之表象”對立起來,這一傳統在黑格爾那里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德國16世紀神學家塞巴斯第安·弗蘭克形象地指出,凡事都有對立之兩面,由于上帝決定要以人世的對立面自居,因此他將事物的表象留給人世,而將真理及事物的本質留給了自己。*http://www.ylib.com/search/qus_show.asp?BookNo=R1047.中國古人并不常使用“真實”這一抽象詞匯,也不相信善變的表象,而熱衷于探索永恒之“道”。在今天,道的理論及其概念在語言及歷史中變得模糊和復雜起來,遮蔽了形象而樸素的原貌。
關于“道”的話題,我們不妨引入兩個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學術公案,一是關于道的話題,二是關于邏各斯的話題。
老子的《道德經》包括題目在內,道字出現了80次,《論語》中道字出現了86次。最著名的是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含義相當玄奧,究竟何解,歷來都莫衷一是,難有定解。簡單而樸素的思想為何變得復雜起來,理論領域中的玄奧究竟來自何方?據說甲骨文中沒有道這個字,只在金文中才有,字形如下。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會意字。會意為六書之一。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對“六書”中的“會意”做了說明,“會意:比類合誼,以見指,武,信是也”。許氏對“道”字的意思也作了明確的解釋:一,所行道也;二,達謂之道。因此,道字今天仍有兩個含義,道路和說出。那么,這兩個意思怎么聯系到一起的呢?從字形上看,走針偏旁加上一個首字,首字含一個目字,也就是眼睛的意思。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在地形復雜之處,當有人“問道”的時候,那個知道“道”的人,也就是走過和見過“道”的人,當他想說出來的時候突然發生了困惑,不知從何說起。這不正是一種“說出道”的困惑嗎?道字的造字之初不正是描繪了這一場景嗎?更令我們驚喜的是,這不正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所要說的意思嗎?“道”一旦被能說,就已經不是我想告訴你和你要知道的“道”了。
最有意思的是,中國古代“道”字含義變遷的情況,在西方大體上也是差不多的,甚至可以說是如出一轍。中國古人所謂的“道”,就是古希臘的“邏各斯”。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最早在哲學中使用了“邏各斯”這個概念,認為“邏各斯”是一種神秘的規律,是世間萬物變化的微妙尺度和準則,是宇宙事物的理性和規則。它沖塞于天地之間,彌漫無形。此時的邏各斯已經被神秘化、“玄奧化”了。古希臘的邏各斯的原始含義同樣是清晰、樸素而具體的,它指的是“用語言來說明”,特別是指“對事物的比例、尺度的描述”。只是后來,邏各斯被形態、規律、機制、機理之類的概念代替,遭棄用后反而升華,變成了高深莫測的東西,其自身反倒成了絕對真理的化身。
關于道,《莊子·田子方》有另一段銘文:“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王先謙集解引宣穎曰:“目觸之而知道在其身,復何所容其言說邪?”
“目擊而道存”說的是一個人具有敏銳的領悟力和深厚的修養,只在略一顧瞻之中便能感受得到。但最重要的是這句話說出了眼睛和“道”的關系。對莊子來說,要了解“道”,只要看一眼就夠了,但要用語言說出來,那就麻煩了。
中國古人在對言和意關系的理解上和西方大相徑庭,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相信“語言”是表意的精確而可靠的方式,但中國古人追求“舍筏登岸,見月忽指”的“忘言”境界,信賴通過建立在直觀之上的“悟道”而直接獲取意義。
莊子的時代只能“目擊道存”,而不能“目擊道傳”,但是現在不一樣了,因為我們有了維爾托夫所說的“電影眼睛”——攝影機。
1922年,維爾托夫發表了“電影眼睛派”宣言,提出了電影“眼睛”理論。攝影機就像人的眼睛一樣,但是又跟人的眼睛不一樣,維爾托夫意在挖掘其不一樣之處,即優越之處。影片《電影眼睛》(1923)和《帶攝影機的人》(1929),便是實踐其理論的經典作品。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帶眼睛的人”,同時也是“帶語言的人”,現在我們還可能成為“帶攝影機的人”。人眼與攝影機的差別,意味著我們可以從“目擊道存”升級為“目擊道傳”。這意味著,人類在語言的語言、文字的語言之后,又有了一種“眼睛的語言”,回顧西方現代哲學對語音的糾結與反思,“眼睛的語言”的存在價值就不言而喻了:“帶攝影機的人”不僅能使人用看到的進行思考(目擊道存),還可能使人把看到的以直觀影像的方式傳遞出去(目擊道傳);“帶語言”,使人具有思考的能力,“帶攝影機”使“眼睛的語言”在兩個方面向語言看齊,既具有思考的能力,又有表達的能力,而且這一表達是一種不同于語言的更加“完整的表達”。
維爾托夫“電影眼睛派”理論與實踐的目的就是要把電影提升到語言的功能:電影工作者手持攝影機,就像人的眼睛一樣,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同時運用直觀畫面賦予捕捉到的以意義。維爾托夫對后來法國的“真實電影”、法國新浪潮的分支“真理電影”以及美國的“直接電影”產生了直接影響。真實電影、真理電影和直接電影這三者是一脈相承的,其代表人物有法國的讓·魯什、美國的戴維·梅斯爾斯和阿爾倍特·梅斯爾斯兄弟等。真實電影的倡導者宣稱他們的靈感主要來自維爾托夫的“電影眼睛派”。*維爾托夫把自己在1920年代拍攝的一系列生活片段組成了新聞片,并稱之為‘電影真理報’(kino-pravda),真實電影實際上就是這一俄文詞匯的法譯。現在我們可以理解,這種理論一脈相承的根本目的,就是運用電影視聽手段持續不斷地對現實展開“在捕捉中思考”的不懈努力。
對于維爾托夫來說,他擁有的是“電影眼睛”;但到了20世紀50年代以后,我們擁有的則是“電影眼睛+電影耳朵”了,單一視覺擴展為了視聽雙頻媒介的綜合運用。美國“直接電影”觀念的核心之一就是強調設備的可攜帶性,即便攜攝影機和同步錄音技術,正像維爾托夫當年強調攝影機的可攜帶性一樣。莊子的“目擊而道存,亦不可以容聲也”,仿佛是在說維爾托夫——通過視覺來接近真理;而在今天,我們可以將其改為“視聽而道存,必須容聲也”——直接通過視聽手段去接近、捕捉和思考真理。
國內外學術界一直把紀錄片的根本特征界定為非虛構(non-fiction),這是非常正確的。但長期以來,對紀錄片類別屬性的錯誤理解產生了不少畫蛇添足式的定義,*如這樣的電視紀錄片的定義:“運用現代電子、數字技術手段,通過非虛構的藝術手法,真實地記錄人類社會生活,以現實生活的原始內容為基本素材,經過創作者的選擇、重組、集中、強化,結構而成的一種完整的紀實性電視節目形態。”造成了紀錄片的創作和研究上的模糊認識。甚至不斷有人試圖以創新的名義對這一界定提出質疑,以便使紀錄片的外延無限擴大,結果導致了很多問題論述不清,并使這些問題在無意義的爭論中被擱置起來,最終以紀錄片的名義幾乎可以做任何事情。
近年來西方出現了各種所謂的“新紀錄片”,竟然去探討和發展紀錄片的虛構特點。*關于新紀錄片,典型案例可參考斯泰拉·布魯齊《英國新觀察式紀錄片:紀錄肥皂劇》,載《世界電影》2011年第2-4期。國內也有人出版了一本專門討論紀錄片虛構問題的著作《紀錄片的虛構》,書中把虛構視為紀錄片可以使用的藝術手法之一。[2]還有人以《北方的納努克》(弗拉哈迪,1922)中的搬演為例,來說明紀錄片誕生之初便存在虛構要素,*對這一例子的錯誤征用隨處可見,范慧琨《搬演:再現真實的尷尬舞者——淺論紀錄片的表現手法》,《南方電視學刊》2009年第3期。這種做法顯然混淆了概念。有兩點特別需要明確,一是紀錄排斥虛構,二是搬演絕不是虛構,而只是通過“表象再造”接近事實、保留事實,而虛構則意味著運用媒介而展開“想象”并以此對“意義”進行修辭性表述。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與故事片的虛構本質相反,資料片的本質就是“挽留事實”。當然,我們在片中看到的實際上都只是可供我們參考事實、挽留事實或確認事實的資料。尼克爾斯曾說過,一切電影都是紀錄片。如果說這一斷言曾經是正確的話,這句話的正確性在今天從根本上被撼動了——合成鏡頭的出現,使得很多電影不再是“紀錄片”。同時,基于我們對合成鏡頭功能和價值的理解,傳統意義上被定義為“紀錄片”的部分影片,完全可以分享(事實上,已經在分享了)紀錄和合成這兩種手段。所以,把Documentary的中譯詞由原來的“紀錄片”改譯成“資料片”是恰如其分的。這一改譯,意味著概念外延的收縮,即,只有那些致力于紀錄(捕捉、收集和整理)事實資料的影片,才是資料片;而另有部分冠以紀錄片之名的影片,因其虛構性或對合成手段的大量運用,則完全可以被劃進論述片等其它片種的范疇。*例如影片《圓明園》,大量借助三維動畫還原圓明園的空間場景,其重點主要不在于對歷史資料的發掘,而在于通過混合各種敘事手段,將視覺化的圓明園處理為近代中國的象征,以此完成對某種特定歷史觀的論證,故此類被稱為“紀錄片”的影片,實為論述之片。尼克爾斯還說過“一切電影都是虛構的”話,或許比前一句話的正確性更多一些。尼克爾斯雖然指出了紀錄片的虛構和故事的虛構是不同的,但他也沒有說清楚到底是什么不同。這里順便指出,不過是歷史和現實本身包含的虛構成分和藝術虛構的區別。對此做具體的論述已經超出了本文的范圍。
這不僅僅是關乎“名份”的問題,現譯(紀錄片一詞)涉及到了基本的電影觀,并且犯了一個已經造成了嚴重影響的歷史性錯誤。并不是每個創作者都愿意理會電影觀的問題,但電影觀卻會毫不商量地左右著每一部電影作品的深度和價值。對于理論研究者來說,確立“資料片”這一嚴謹概念,意味著需要把近20年來相當一部分圍繞所謂紀錄的新觀念(如紀錄劇,甚至偽紀錄片)展開的理論爭論安放到別處。這里并不是說要把它們粗暴地扔進虛構電影或論述片的領地草草了事,也不是要否認這些爭論的理論意義,而是希望能提醒人們,大部分爭論都在基本概念上存在著問題。這些爭論真正應當深入思考的關鍵點在于:所謂紀錄的各式新觀念,連同更宏大的現實主義傳統,并非對現實的全然反應,藝術或媒介意義的現實主義與現象素材之間的構成性關系,與浪漫主義、形式主義甚至新堪普主義與現象素材間的關系一樣,復雜而隱秘,我們對此還從未有過認真的思考——此類話題只能借由現象學和精神分析理論得以清晰闡釋。目前這些爭論,在錯誤的概念起點上推錯了理、表錯了意,最終陷入了由(包括概念在內的)語言和邏輯制造的泥潭。正如羅素善意地說的那樣,我們常常不是對所論對象不夠了解,而是對論述的邏輯所知太少。而概念,恰恰位于邏輯的起點位置。
克拉考爾和巴贊的理論都強調了電影的紀錄功能,不約而同地指出了電影表現現實的巨大優勢。從這個角度來看,得到長足發展的應該是紀錄片,而不是故事片。但歷史并不是這樣書寫的,它非常殘酷地決定把大部分紀錄片從影院電影中淘汰出局。嚴格意義上的紀錄片(資料片)排斥虛構,這就決定了它缺少那種既集中又強烈的戲劇性,從而影響了電影在人們工作之余所需要的那種娛樂性。電影誕生百余年來,正是故事片在我們的身邊創造了一個相當龐大的逼真而又虛幻的世界;這個世界加入到我們的生活之中,使生活流光溢彩,姿態萬千,無可比擬地讓人迷戀。但是,我們相信,資料片一定會在新的界定和新的分類體系中找到自己的準確定位,并且發揮出前所未有的挽留和保存事實的偉大功能。我們還相信,不僅故事片有思考性,資料片同樣也有思考性,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思考更加完整,更加沉重和深邃。
[1][法]安德烈·巴贊.電影是什么[M].崔君衍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2]劉潔.紀錄片的虛構[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
DocumentaryFilmintheLightofIts“DualCharacter”
WANG Zhi-min1, ZHAO Bin2
(1.Department of Film Studies, Beijing Film Academy, Beijing 100088, China; 2.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2, China)
A film is a series of dual-frequency moving and talking images which are produced by cameras and through visual effects. It is a comprehensive medium that makes up (by recording or synthesizing) surface phenomena. With this new concept of film, the medium of film has dual character—“recording” and “synthesizing”. This means that a traditional “documentary film” can be seen as a “documentary”. In discussing film’s medium function of synthesizing, this paper also m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ording and history, and recording and synthesizing.
film; digital technology; synthesizing; recording
2012-04-26
王志敏(1948-),男,天津寶坻人,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重慶大學美視電影學院特聘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電影美學、電影理論方面的研究;趙斌(1980-),男,山東淄博人,電影學博士,北京工業大學人文社科學院講師。
J902
A
1674-2338(2012)03-0053-06
(責任編輯:山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