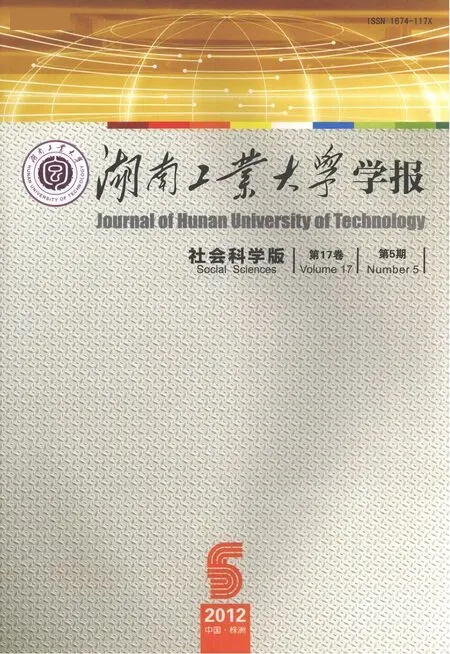《水滸傳》英譯本的歷時描寫研究
高 磊
(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南 長沙410083)
霍姆斯(J.Holmes)最早于1972年提出描寫翻譯學的理論,認為翻譯學由純理論研究和應用翻譯研究組成。而純理論研究又可分為兩個分支:描寫翻譯研究和翻譯理論研究。繼霍姆斯之后,圖里(G.Toury)對該框架作了進一步的闡釋。在他看來,翻譯是“眾多變量因素綜合作用最終形成的產物:原著不是翻譯過程中唯一的中心,對翻譯有著重大的影響的包括有譯者、讀者、社會歷史文化等諸多因素。”[1]21該理論主張探討諸多的翻譯現象應該采用描寫研究的方法:以現實的翻譯現象(包括翻譯行為、翻譯作品)為研究對象,通過客觀描寫與分析,探究譯者的翻譯目的與翻譯策略,探討譯本在譯入語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并歸納出特定歷史時期與文化系統中制約與影響翻譯的因素。翻譯描寫可從共時性與歷時性兩個不同的視角展開。其中后者適用于對同一原著在不同時期產生的多個譯本進行研究。《水滸傳》的譯介歷時百余年,出現了10余種的英文節譯、全譯本,其適合采用歷時性描寫方法來進行研究。
一 對《水滸傳》英譯本進行歷時性研究的必要性
《水滸傳》又名《忠義水滸傳》,是中國四大名著之一,它的問世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其思想性和文學性在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當今世界上最知名、最權威的三大百科全書之一的《不列顛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ca)》(又稱《大英百科全書》)中有專門章節重點介紹,并對其文學性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英譯家杰克遜說:“《水滸傳》體現的不可征服的、向上的、不朽的精神貫穿著世界各地的人類歷史。”[2]31目前,它已有英、法、德、俄、日、韓、泰、及拉丁等文字的數十種譯本。本文試圖梳理百余年間出現十余種《水滸傳》英譯本,根據歷史階段進行劃分,探尋特定歷史背景下譯者的意圖,總結各個階段譯本的共性,再現原著的譯介軌跡及其影響,論證翻譯作為一種文化事實的存在。
二 《水滸傳》英譯本的歷時描寫及特征
(一)《水滸傳》英譯本的歷史分段描寫
我們將《水滸傳》英譯歷程分為四個階段,并對各階段中最具代表性的譯本加以考證和研究。
第一階段:1840年鴉片戰爭后的晚清時期
這一時期《水滸傳》的英文譯介數量很少,地域僅限于當時的香港英租界。1872年香港的一部重要的漢學期刊《中國評論》第一卷載有《一個英雄的故事》,是由一個署名H.S.的譯者節譯的。這是有關《水滸傳》英譯的最早記載。其內容為《水滸傳》前十九回關于林沖的故事。這些節選譯文只圍繞特定人物的事跡展開,編選重要情節,未及全書。
為何《水滸傳》的英文譯本大陸內地不見,而在香港可見呢?這得從《中國評論》這一刊物的性質說起。《中國評論》,又名《遠東釋疑》,是一份主要刊登英文漢學評論的刊物。主要撰稿人和讀者均由英美來華傳教士、漢學家、外交官、公務員、商人、報刊記者等組成。他們這一群體大多生活和工作在中國的沿海港口城市,比較愛好和仰慕中華文化,他們感興趣的是中國社會與歷史文化的變遷,同時還積極向海外譯介中國。19世紀后半期,西方漢學正經歷著迅猛的發展,而這一時期的漢學研究也正由業余向職業化轉型和過渡。這一時期的西方漢學領域所發生的重大變化,《中國評論》都有親自見證。作為研究西方漢學史(特別是中國19世紀后期)的一份珍貴的歷史文獻,《中國評論》完整地記錄了漢學研究的歷史進程及學術面貌在西方(尤其是歐洲)所取得的進展。該刊物逐漸成為了譯介中國文學的主要窗口,向外譯介的包括有中國小說、詩歌、民間文學等等。它還刊載有當時一些主要漢學家們對中國文學文本的閱讀闡釋,既包括傳統經典文學文本,又包括豐富浩繁的民間文學文本。英語成為了當時漢學家們投稿《中國評論》使用的主要語種,而追溯到18世紀、19世紀上半期,西方漢學及東方學的研究主要使用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德國等歐洲大陸的語言,因為在那時這些國家的漢學研究更為發達。這一變化昭示著歐洲漢學研究的中心,已經轉移到英國和正在逐漸崛起的美國,不再局限于歐洲大陸了,這一過程是從19世紀下半期開始的。《中國評論》上所刊載的《水滸傳》部分章回的譯文,較為客觀地審視、考察了中國文學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民族性與人性方面的特征,基本采用對華中立、宣揚普世價值觀的立場。英國文明和中華文化的碰撞、交匯和融合在譯者身上有著較為明顯的體現:譯者具有著雙重的矛盾身份:他們是仰慕中華文化的,同時又執行著西方的炮艦政策;他們在文藝復興以后積極向東方移植著人文精神,又在中華文化向外流播的空地上拓荒。而19世紀下半期以來中國文學的“西漸”過程和中西文化的對話,由《水滸傳》的初步譯介也可見端倪。
總的說來,“緩慢”是這一時期的《水滸傳》英譯歷程較為突出的特點。與這一現象有著很密切關系的自然是當時的晚清政府奉行的閉關鎖國政策。除此之外,在歷代專制王朝的眼里,《水滸傳》均被斥為“誨盜”之書,在國內(除香港、澳門外)都屢次查禁《水滸傳》的中文原著,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水滸傳》的譯介過程是從香港開始,而非大陸境內。
與當時腐敗落后的“天朝”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列強在鴉片戰爭以后,用槍炮洞開了中華封建帝國的大門。在香港的第一個漢學研究中心正是由當時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建立。聯翩渡海來華的有各國的殖民者、傳教士、冒險家、商人、旅行者等,他們都有著自身的政治、宗教和商業利益的需要。這也客觀上加快了中國古代典籍、文學作品、風俗習慣在西方的傳播。香港是當時大英帝國在華的租界,相對比內地,有著更為濃厚和寬松的學術氛圍,《水滸傳》的譯介活動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得以展開。當然,從主觀上來講,對漢學展開研究,對中華文化經典進行闡釋是當時《水滸傳》得以向外譯介的更為直接的目的。這一階段的《水滸傳》譯介,基本采用的是以歸化和直譯為主的翻譯策略,譯者盡量做到還原原著的全貌。而在選材方面,只節譯了《水滸傳》原著中家喻戶曉的典型英雄人物的事跡,因其性格特征較為鮮明且為大眾熟知,也更利于國外讀者對中華文化的內涵及國民性格特征的認識和了解。
第二階段:20世紀30、40年代
這一時期是《水滸傳》譯介的重要時期。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許多明清小說得以全面開禁,大量流傳。加之五四運動提倡白話文,很多白話小說便被捧上了正宗文學的寶座。顯然,這樣的時代背景也為《水滸傳》的譯介掃清了障礙。
據著名史學家史式教授統計,20世紀30、40年代,《水滸傳》的印數最多,讀者最廣,居于四大古典小說之首。與此同時,《水滸傳》的譯介也進入了活躍時期。一戰后的美國迅速崛起,隨著其軍事和經濟實力向亞洲擴展,中國及亞洲研究領域也逐漸得到美國學術界的重視,在漢學研究上得到了長足的進展,尤其是在1920~1938年間最為明顯。1923年翟理思(H.A.Giles)的譯著《中國文學史》在美國紐迪·阿普爾頓出版社得以出版,其中刊載有《水滸傳》的一段譯文,“魯智深大鬧五臺山”為其主要內容。雖然這只是一段節譯,卻是作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傳》首次在境外被譯介。此外,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三個較為重要的譯本:(1)1929年英國倫敦豪公司和美國紐約A.A.諾夫公司分別出版了《水滸傳》七十回本的英文節譯本,書名為《強盜與士兵》,是英國漢學家杰弗里·鄧洛普(Geoffrey Dunlop)經埃倫施泰因的德文本的轉譯本(以下簡稱“杰譯本”)。該譯本采用的是金圣嘆的70回本,在思想上、內容上已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并且在國、內外影響較大,是第一部英文全譯本。(2)1933年由紐約約翰·載公司及倫敦梅休安出版社分別出版的《水滸傳》的英譯本,由美國女作家賽珍珠(Pearl.S.Buck)根據金圣嘆的70回本《水滸傳》翻譯而來,書名為《四海之內皆兄弟》。[3](3)1937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英文70回節譯本《水滸》,[2]45由英國學者杰克遜(J.H.Jackson)翻譯,方樂天編輯。
這里需要特別提出的是譯者之一的賽珍珠。她本人有著很強的中國情結,是一名中國通,在中國度過了整整40年的時光。她正在金陵大學(現南京大學)任教(1919~1934),期間于1927~1932年完成了《水滸傳》70回的英文全譯本,前面附有林語堂寫的導言,該翻譯過程歷時4年多。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內憂外患、戰火紛飛、動蕩不安,中國各知識階層奮起救國圖強、為民請愿。當時幾乎所有的中國知識分子都被卷入到“五四”運動前后的“中西文化論戰”之中。作為一名生活在中國國土上的公民,一名從事高等教育多年的美國學者,賽珍珠親歷了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變革,對“五四”運動后中國文化思潮的涌動可謂身臨其境,深有感觸。然而,賽珍珠畢竟是一個特殊人物:具有雙重身份背景和雙重文化情結。一方面,她對中國社會給予關注,對中國社會的混亂和人民的命運給予同情;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顧及美國主流文化的影響和制約。[4]61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不斷發展,當時的美國社會各階層的競爭也隨之愈演愈烈,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社會矛盾日趨尖銳,“鍍金時代”的大潮將“黃金時代”的“美國夢”沖洗得蕩然無存。此時的美國學界,深受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進化論的影響,很多文學作家,尤其是那些出身貧寒、親歷苦難的作家們,開始對美國的社會進行深刻反思。他們采用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創作手法,對當時的社會黑暗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傳》采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對底層社會的現實進行了細致入微的描寫,為美國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文學的創新和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也滿足當時美國社會急于吸收外來文化,消除其文化貧弱,進而實現文化獨立的現實需要。賽珍珠選取了《水滸傳》70回原著,在她看來,《水滸傳》70回本“出色地刻畫了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它描述的不僅是中國的過去,更是現在。小說不僅是對過去人民的寫照,也是對當今社會的寫照”,[3]48這就使得小說“去掉了小說的革命文學的立場,轉而成為迎合統治階級需要的道德說教。”[3]50它“自始至終貫穿著與官府反抗到底的思想”;而120回本的“結尾大多是好漢們被朝廷招安”[3]15。從翻譯策略來看,賽珍珠譯本總體采用直譯,盡量保留原作的意義和風格,保留漢語特有的表達方式。她甚至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一些即使是中文讀者也不很感興趣的內容。對原文中那些質量不高的打油詩照樣譯成了打油詩,譯后又和中國的朋友一起通讀了譯本,逐字對比了譯本與原本。賽珍珠翻譯《水滸傳》的初衷就是想把它忠實地介紹給西方讀者,因而在中文語言、表達方式、行文特點方面多加保留。為了讓國外讀者既能領略到美妙的民間傳說,又能吸收原作的內容及寫作風格,在譯文中她主要采取異化的翻譯方法。賽珍珠選取了孔子的一句名言(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進而將書譯為All Men Are Brothers,非常深刻地體現出書中眾多綠林好漢的俠義精神。1933年出版的《中華月報》評論說,賽珍珠譯本“忠實地譯成英文”,“真是不易多得的杰作”,譯作中的“人物頗與英國的羅賓漢等綠林豪杰相似,合西洋人口味。”[5]此譯本一出,深受廣大歐美讀者的推崇與喜愛,至今在國外亞馬遜等網上書店,仍可看到該譯本的一版再版和熱銷情況。
杰譯本《水滸傳》與賽譯本產生于同一時代。杰弗里·鄧洛普是英國有名的漢學家,他所處的年代,英國剛經歷一戰,經濟發展相對滯后,政治上逐漸失去“日不落帝國”昔日的輝煌,而文學創作也日漸削弱。英國文學界積極行動起來,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文學。在文學體裁中則“出現了與努力使藝術接近廣大人民階層有關的”,“更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的形象”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6]880這些作品刻畫的是值得同情的“受苦受難、顛沛流離的小人物”[6]880,在人物描寫上與《水滸傳》如出一轍。當時的衰退英國文學急需外部文學的給養和輸血,而《水滸傳》在體裁和內容上正迎合了這種需要。由此可見,杰克遜本人是肯定了《水滸傳》的人文精神和歷史價值的。當然,杰譯本中出現了大量任意的刪節和改寫,就價值觀念而言,譯作帶有明顯的西方文學形式規范中心論思想傾向,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普遍文化”意志和權力對原語文化的蔑視和侵犯。
這一時期的《水滸傳》英譯本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原著均采用民國初年流行的金圣嘆腰斬本(七十回)。自始至終貫穿著梁山好漢與官府反抗到底的思想,并省去了招安等情節。由此可見,譯者在選取原著版本的時候受到很大的時代因素的限制。20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革命是時代的主流,體現出革命者與當時的當權派勢不兩立的革命姿態。因而身處革命浪潮之中的譯者,受到當時風起云涌的革命氣候的浸染,在選材方面舍棄了“革命者向當權派妥協”[4]58的招安情節,保留徹底的革命精神而非達成妥協。無論是賽譯本還是杰譯本,其翻譯的目的,更多的是從中借鑒《水滸傳》批判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推動本國文學的創新和發展,為其輸入新的血液。而“并不試圖從學術上作什么探討,也不在解釋和考證方面過多下功夫。”[7]
第三階段:二戰后至文化大革命后期
因其獨特的歷史原因,這一時期的《水滸傳》譯介活動受到了嚴重的影響。二戰以后,特別是文革期間,大陸內地《水滸傳》的譯介工作基本處于停滯狀態。與此同時,在國外,1947年耶魯大學紐黑文出版、由小詹姆斯.I.克倫普翻譯的《水滸傳:選錄》英文選譯本。這一時期的的譯者活動主要集中于對已有譯本進行修改、補充、重譯。根據《中國翻譯詞典》介紹,賽譯本是當時在西方影響較大的一個譯本,于1948、1957年在英美一版再版。而在1963年,杰克遜也對其以前的譯本進行了加工、修改、重譯,整理完后在香港繼續出版。此后該譯本又于1976年分別由紐約帕拉貢圖書重印公司和劍橋C.&T.公司再版。
這一時期值得關注的是著名美裔翻譯家沙博理(Sidney Shapiro),他一直在中國對外文化聯絡局做翻譯,并于1963年加入了中國國籍。他的《水滸傳》100回全譯本(譯名為《沼澤地邊的不法之徒》或《亡命水泊》)[8]22于 1980 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雖然該英譯本是20世紀80年代初出版的,但該書的翻譯活動卻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文革”晚期)展開的。在“文革”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沙博理當初在選擇原著版本時,似乎也顯得身不由己,費盡心思。“100回版本更接近于那個方針的要求”,因為“70回版本結束時,盜寇仍在被追捕中,而100回版本則讓這些盜寇歸順了皇帝。”[8]30由此可見,譯入語的時代背景極大地左右著譯者在選材方面的抉擇。與別的英文譯本不同的是,在翻譯過程中,沙博理采用的是歸化、異化相結合的翻譯策略,盡量做到靈活處理原文的信息。在他的譯本中,他努力克服直譯的“困難”和意譯的“不準確”,力求達到最佳的效果。不過,沙譯本對原文的內容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刪節,凡涉及詩詞的部分均未譯出。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著壓抑和消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狀況。
這一時期《水滸傳》的譯介特點是選譯、節譯、重譯現象比較普遍。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官方的主流思想是反水滸的,并由此經歷了一場舉世矚目的“評水滸運動”。在這樣復雜的時代背景下,加之譯者特殊的公民身份及其從事的工作性質,使得他們一方面需考慮當時政治批判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滿足西方讀者對異域古典作品譯本的期待:即“對生活在遙遠國度里一個古代民族的一種‘感受’,對原著風格的一種感覺”[9]35。這一時期《水滸傳》原著選材方面,譯者更顯謹慎,能清楚地看出意識形態、贊助人操縱翻譯過程的身影。
第四階段:冷戰結束至今
這一時期經歷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政治格局極度動蕩不安。而與此同時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并取得豐碩成果,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經濟實體,正逐漸融入到國際社會之中。冷戰結束后的世界呈現出美國“一超獨大”的格局。經濟全球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樣化的呼聲連綿不斷,意識形態對立表面似乎得以消解。《水滸傳》的譯介活動仍在持續:1994~2002年間,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分四次陸續出版完約翰.登特-楊和阿萊克斯.登特-楊(John and Alex Dent-Young)父子合譯而成的五卷本英譯《水滸傳》,該譯本的翻譯過程前后耗時8年,書名定為《水泊梁山》。[9]57這無疑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是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英譯的又一重大成果。全書共2 229頁,93萬6千多字,是迄今為止《水滸傳》英文全譯本中內容最全、篇幅最長(120回)、參考版本范圍最廣的,是世紀之交《水滸傳》的英譯典范。約翰.登特-楊為英國學者,曾在香港任教。他的夫人是一位華人,兒子畢業于倫敦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因而都深諳中西語言文化。而《水滸傳》的翻譯計劃是在John Minford(閔福德)和Sean Golden的建議和支持下實施的;Joseph Lau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并且還為譯本作了頗具價值的評論;香港學者朱志瑜在詩歌翻譯方面提供了極大的幫助;David Polland,Eva Lau和John Deeney對譯稿進行了多次閱讀并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建議;David Boothby和其他學者對譯本的可讀性進行了探討和評論;而該英譯本重譯時所參照的藍本即為Sidney Shapiro的英譯本和Jacques Dars的法譯本。由此可見,該譯本并非某一人一己之力的結晶,而是眾多“合作者”共同努力的結果。登譯《水滸傳》的翻譯全過程采取了合作的方式,有時候甚至是全家上陣。主要譯者為John and Alex Dent-Young父子,但身為妻子和母親的Maria Tao也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也正因此,登特-楊父子將譯本的第4-5卷題獻給她。此外,在體制方面,登譯《水滸傳》模仿霍譯《紅樓夢》采取獨特的分卷方式,即根據各卷內容和核心主題為各卷分別分別冠以總名,起到提綱挈領,綱舉目張的作用,使讀者對作品內容一目了然。
登氏父子在譯者序中對于關于該譯本所采用的翻譯策略有著明確的陳述:“所有的翻譯都有妥協的成分。我們就是要使我們的英語譯本具較強的有可讀性。盡力避免使用在英語中可能造成不當意義或聯想的表達法,我們也不允許出現任何與譯入語境意義不符的東西……在詞序和句長上很下工夫,力圖保持英語行文規范的連貫、重心和節奏。”[9]3譯者在前言中寫道,“本譯文必須盡量具有最大的可讀性,我們一方面要保留中國古代的文化內涵,另一方面對于中國的方言及成語用最流暢的英語表達。”[9]4由此不難看出,登氏很關注《水滸傳》自身所具有的獨特的文體特征和藝術價值。在翻譯策略采取的是歸化與意譯,強調廣大讀眾的接受程度。
當然,我們也應該從譯者序中看到該譯本帶有明顯的政治文化傾向。登氏以自己所解讀到的信息向西方讀者展示他心目中的“中國國民性”:即反叛、暴力、淫穢、報復、欺騙、殘忍等。與之相對的,對書中英雄人物忠誠、寬仁、仗義、誠實的一面卻較少關注,其后殖民主義的翻譯價值取向是非常明顯的。
總結起來,本階段《水滸傳》的英譯現象有別于以往任何階段,呈現出多維度、多層次、多元化的特征:
(1)譯者選擇原文版本多渠道化,雜交化,各版本間有著明顯的互文性;
(2)翻譯過程不再局限于個人行為,逐漸形成譯者、同行、友人、家人、評論家等共謀的局面;
(3)原著的文體特征和藝術價值得到更大關注;
(4)意識形態和話語權力得以體現,西方的核心價值觀得以張揚,而原語文化得以操縱、改寫、壓抑、曲解;
(5)歸化翻譯(流暢地道的目的語翻譯;目的語文化價值觀取代原語文化價值觀)仍是很多英美譯者的自覺選擇。
(二)《水滸傳》英譯本的歷時特征詳述
通過對不同歷史時期《水滸傳》英譯本的全面歷時性描寫,我們描繪出《水滸傳》在英語世界傳播的大致面貌。這一歷程跨越140年,涵蓋10多個不同的節譯本、選譯本、轉譯本和全譯本。其發展脈絡可以概括為下表所示的7個方面(參見表1)。

表一 《水滸傳》英譯本的歷時特征詳述
表1顯示,近一個半世紀以來,因為譯者各自所處的時代和身份不同,翻譯目的與策略選擇也存在差異,這使得《水滸傳》英譯本呈現出逐步變遷、日益開放的局面。在這一漫長演變過程中,社會歷史文化因素的變化影響著譯者的翻譯目的、翻譯策略、翻譯方式的變化,不同的英譯本從不同的角度解讀和闡釋著中華文化和國民性格特點。而整個翻譯的過程也從客觀上反映出翻譯作為一種文化事實的所具有的復雜性。
本文對跨越近一個半世紀、擁有10余種譯本的《水滸傳》英譯本進行了系統的歷時性描寫,并概括出該過程的發展脈絡。此項研究得出以下五點結論:(1)霍姆斯與圖里建立起來的描寫翻譯學理論,為我國的經典名著英譯研究提供了嶄新的視角。從歷時性角度來考察翻譯現象,將會更為全面與客觀,可以避免傳統譯學研究中的片面化。(2)《水滸傳》英譯歷程的描寫性研究表明,從最初的節譯、選譯方式,到轉譯、重譯,再到全譯、合譯,翻譯作為一種文化事實,對其展開的研究越來越呈現出多元復雜的傾向。(3)在《水滸傳》英譯的歷史長河中,尚沒有由中國裔的譯者翻譯的譯本,對于這樣一部富含中國文化,具有獨特語言特點和敘事結構的中國英雄傳奇文學巨著的對外傳播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華人譯者積極地弘揚中華文化,可以更好地避免文化失真。(4)翻譯目的不僅是譯者個人價值取向、藝術偏好的產物,而且還受到社會歷史文化和政治、意識形態等的多重影響和制約,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該結果也會影響譯者對原作的選擇;(5)由于譯者翻譯目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的不同,譯者都在一定程度上都對原著進行了調整、變通、刪節和改寫,從而在接受了原著的一些內容和形式的同時,也壓抑和排斥了原著的一些內容和形式,表現出譯語與原語既契合又悖離的雙重特征。
[1]Toury,Gideon.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1.
[2]Jackson J H.Water Margin[M].Hong Kong: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63.
[3]Buck,Pearl S.All Men Are Brothers[G].2 vols.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33.
[4]陳 敬.賽珍珠與中國——中西文化沖突與共融[M].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
[5]孫建成.《水滸傳》英譯的語言與文化[D].天津:南開大學.2007:22.
[6]秦 水.英國文學史 (1870-1955)[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7]馬紅軍.為賽珍珠的“誤譯”正名[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3(3).
[8]Shapiro S.Outlaws of the Marsh[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80.
[9]Dent- Young,Alex Dent- Young.The Marshes of Mount Liang[M].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4~2002.
[10]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全傳[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
[11]林煌天.中國翻譯詞典[C].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621-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