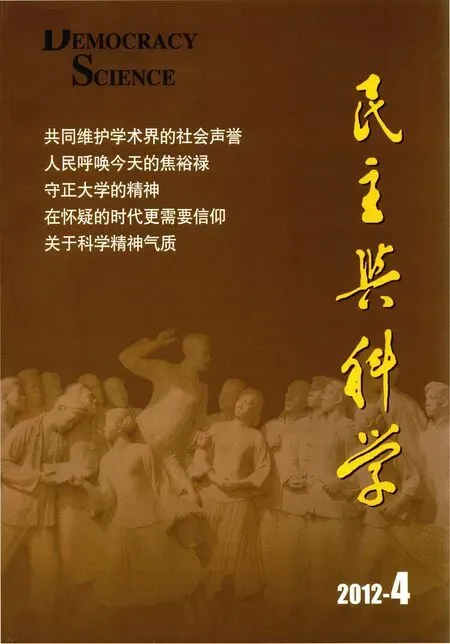從輿論司法走向司法輿論
■余雙彪
從輿論司法走向司法輿論
■余雙彪
社會的轉型期,一切都在變化,司法概莫能外。在開放、透明、信息化的條件下,隨著不同情緒的追逐和發酵,不同聲音的質疑和關注,特別是輿論的深度跟蹤和監督,司法平衡各方利益的難度越來越大,司法公正也日趨成為社會各界高度關注并持續推動的焦點性問題。一些案件、事件發生后,在輿論和各方的高度關注下,司法何去何從,備受關注,備受矚目。
司法與輿論,相互促進,抑或相互抵牾,確實“兩難”,特別是在快速變動的時期,這種關系更是磨礪著司法人員和媒體工作者的內心。一方面,執法司法不公、不廉,甚至貪贓枉法、徇私舞弊等等還依然存在,司法腐敗還比較嚴重,民眾對司法信任度也不是很高,這種情形下,輿論的介入為案件的公正處理提供了極佳的外界助力,也監督著司法人員嚴格公正廉潔高效處理各種糾紛。輿論監督的正面作用牽引著司法走向更加公平公正的道路。另一方面,輿論本身的局限或者一些從業人員的有意為之,在報道時對尚未處理的個案預先定性,有的甚至用“炫目”的標題,煽動民眾本已對司法不信任的脆弱神經,使得案件的處理壓力劇增。特別是先入為主的觀念,使得但凡處理結果與原先形成的大致印象不同,人們就紛紛猜測背后的緣由,腐敗案、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等等,久而久之,可能出現一種奇怪的邏輯,輿論熱議的案件,司法處斷與大家的評判差不多,這樣才能平息“民憤”。于是,在某些案件中,人們寧可相信輿論,也不相信司法,這成就了輿論司法。
輿論的司法,即使有很多益處,但終歸有一點需要明確:輿論該如何監督?換言之,輿論在發揮監督司法重大作用的同時,不免帶來一些值得反思的場景:一些案件發生后,司法尚未有結論,或者說司法的結論還沒來得及作出 (辦案總是需要一定時限的),輿論可能鋪天蓋地。案件的處理是個過程,具體的案情是什么,一開始往往難以說清,或者根據現有的證據只能得出大致的判斷,此時輕下結論操之過急,更不合司法規律。而且,相對于司法辦案來說,輿論可能更加感性,人也是更加同情弱者。民眾的正義心會極度聚集在共同認定的弱勢方,于是長期積累的情緒不知不覺中影響了客觀、中立的判斷,在呼吁真相的同時不免帶上強烈的主觀期待,這種期待和與之一起形成的強大輿論氛圍很難不影響司法人員的處斷。一些國家司法人員在處理重大案件時,尤其是社會高度關注的案件時,不去關注社會上的議論,不與外界接觸,而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本身作出處斷,就有這方面的考慮。
當然,我們也必須強調,輿論客觀報道的要求,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司法權的公正行使。司法和輿論的兩難,不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上,實踐中的博弈更加糾結。沒有輿論的監督,一些司法不公不廉行為確實得不到糾正,尤其是在目前的轉型階段,人們呼吁加大對司法權運行的監督制約,此時即使是“過激”的監督,囿于人們對公正的渴望,也會被理解。換言之,為了“矯枉”,允許“過正”。而且,在司法權相對強勢時,輿論監督受到各種制約還比較多,實踐中發生一些“千里追捕”發帖者和以所謂“誹謗”起訴記者等等光怪陸離的事情,在此大背景下,人們對輿論作用的期望值更高,自然不會重視輿論不客觀報道等等存在的“微小”瑕疵。但瑕疵畢竟是瑕疵,實現司法和輿論的良性互動,不能不忽略這些微小問題的解決,也正是一系列“小”問題的逐漸解決,最終才會形成整體性的和諧和融洽。
輿論的司法,司法受制于壓力,即使想客觀處斷,最終難免受到輿論的影響而偏向大眾的判斷和追求。這并非否認輿論監督的作用,提出問題的關鍵是輿論該如何監督。當漫天的輿論到來之時,司法系統內部的關注度也自然上升,司法一線人員不可能不考慮這個案件處理出來的效果會如何?如果是結合法律、事實等來綜合考量案件的處理,那么這種社會效果的思慮無可厚非,更值得贊賞。但是,不能不引起深思的是,為了迎合輿論的需要,滿足一般觀眾的判斷,司法人員的違心未必就不存在。如果這種壓力變成了案件處理中考慮如何滿足社會觀眾需求的驅動,如何考慮對“上”和對“下”交代,那么,不管如何表揚這種思維方式,總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存在——可能會損害司法真正的公平、公正。平一時民憤,不代表處理就是最合適的,哪怕這種處理也是依法辦事。事實上,輿論司法還是司法輿論,拷問的是制度的完善和司法、媒體從業者的良心。
司法的輿論,就是輿論監督司法時,應建立在尊重和信任司法的基礎上,客觀描述正在發生的事情。輿論在案件還沒有調查清楚之前,不應給案件一個定性,或者對案件的處理進行預測。近年來,在發生一些事件、案件之后,媒體往往進行深度追蹤和報道,有的還采訪法學專家、教授等等,對案件的定性進行評價。受過法科系統訓練或者從事司法實務的人都明白,案件事實往往十分復雜,以濃縮出來的事實為依據進行判斷,有時候與正在偵查的事實之間可能有些出入,過早地下結論顯然不利于后續的司法處理。當結論已下,民意已成,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這些民意自覺不自覺就成為裹挾司法的重要因素。在更為特殊的情況下,有些案件在司法處斷并無不當時,過度的關注也給案件的定性增加了難度。因為,從法律的角度上看,可能前后兩個處理都合適,只是那個處理在那個階段和那種情形之下更合適一些而已。但是,從社會上看,即使前后兩個處理都沒有錯,司法的權威和威信顯然難以為繼了。
司法的輿論,當然不只是為了維護司法的權威。因為司法權威絕不是通過輿論引導和宣傳就能形成的。從根本上說,法律權威來自于法律能夠實現公平和正義,來自于司法的功能和價值得到真正的實現。在司法希望得到輿論衷心支持的同時,如何構建一個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體系更為急迫。相信輿論而不相信司法,其實不是司法和輿論相互抵牾的產物,而是民眾對司法的信任度是否足以抵擋其他方面的沖擊。或者說,當對司法的信任不足以支撐民眾的內心確信,那么任何一種輿論的導向都會使這種動搖朝著更加危險的境界發展。我們與其期望輿論更好地引導民眾,不如在實現司法公正上下功夫。一個公正的司法,即使存在相應的誤導,當最終判決作出時,很多質疑都會煙消云散,這既是司法權威的體現,也是輿論作用的彰顯。
簡言之,轉型期的中國,實現司法和輿論的良性互動,需要在“兩難”中找到平衡。輿論的報道必須客觀,或者更多的是描述已發生的事件,而不能對事件本身定性作過多的猜測和評價。司法在努力走向更加公正的同時,其運行必須克制,不能因為媒體稍有報道,就感到“不爽”,想方設法利用權力影響和干預輿論,有的甚至打擊報復相關人員。從輿論的司法走向司法的輿論,文字含義不同的背后是理念的差異,當法律成為信仰,法治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時,這些問題或許可以不必像今天這樣來探討。
(作者單位:最高人民檢察院)
book=43,ebook=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