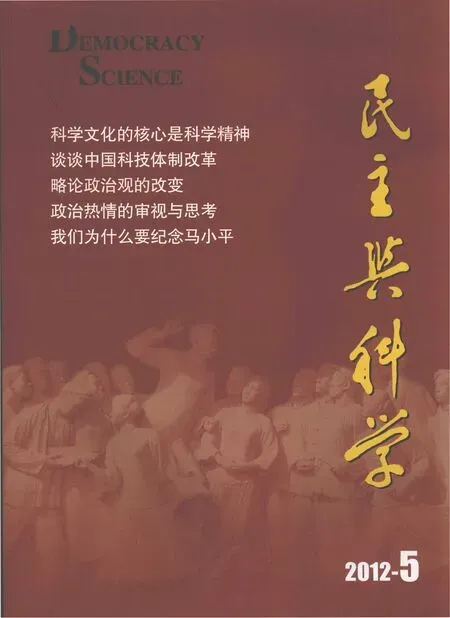政治熱情的審視與思考
■岳慶平
政治熱情的審視與思考
■岳慶平
政治在現代社會是眾人參與之事,雖然人有選擇對政治不熱情的自由,我們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有政治熱情,但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應有以政治擔當和政治理想為支撐的政治熱情。中國歷史的發展有時起伏太大:如果說在數十年前的“文革”時期,某些知識分子身上曾體現出無意識的政治狂熱這一極端的話,那么歷史發展到今天,某些知識分子身上又體現出有意識的政治冷漠這另一極端。上世紀末有人說:“中國人愛談政治,那是十幾年前的老皇歷了,因為那時中國除了政治,沒有別的。現在中國人覺悟了,國內還有誰關心政治,老百姓都忙著去掙錢了,誰也不玩虛招子,都務實了。這叫否極泰來。20世紀中國是世界上最講政治的國家之一,到頭來恰恰是中國人最不關心政治。”總而言之,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某些中國知識分子身上很難體現出不偏不倚和動態平衡的中庸之道,他們往往缺乏以政治擔當和政治理想為支撐的政治熱情。
無論從何種角度審視,知識分子都應有以政治擔當和政治理想為支撐的政治熱情。亞里士多德說:“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意為政治熱情是人的本能和人性。劉易斯·科塞說,知識分子“歸根到底要以服務于政治目標為導向”。錢穆在分析辛亥革命后的知識分子時說:“試問這四十年來的知識分子,哪一個能忘情政治?哪一個肯畢生埋頭在學術界?偶一有之,那是鳳毛麟角。”亞辛斯基說:“不要恐懼你的敵人,他們頂多殺死你;不要恐懼你的朋友,他們頂多出賣你;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關心的人們,只有在他們不作聲的默許下,這個世界才會有殺戮和背叛。”
民主的含義是人民當家作主,“切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特別是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盡量調動人民的政治熱情,積極穩妥地深入研究和科學設計政治體制改革的路線圖、時間表和具體目標,是逐步解決當前許多深層次重大問題的重點。早在1944年,毛澤東與到訪延安的美國代表團談話時就指出:“我黨的奮斗目標,就是推翻獨裁的國民黨反動派,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國人民能享受民主帶來的幸福。”1945年,毛澤東在回答黃炎培如何跳出朝代敗亡的“周期律”時又指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至今近70年過去了,盡管我們推動政治進步的責任不斷增大,但因我們推動政治進步的能力非常有限,推動政治進步的努力又非常不足,所以我們有時只能遺憾地感嘆:毛澤東當年大力倡導的“民主”至今仍有許多問題,某些深層次的政治障礙至今仍巋然不動,唐德剛所謂“歷史三峽”至今仍橫亙我們面前,而我們一代又一代人卻在“不舍晝夜”地迅速衰老。有人認為,雖然政治看不見摸不著,仿佛和我們的生活沒什么聯系,但事實上政治無時無刻不在介入和影響我們的生活。也正因如此,我們才強調政治的民主參與性,才呼吁更多公民尤其是知識分子要有政治熱情。
認真審視目前實際情況,除了不少人體現出熱衷于從政當官、權錢交換、高喊口號、滿口大話、違法亂紀、革命斗爭等方面的不正常政治熱情外,公民尤其是知識分子以政治擔當和政治理想為支撐的政治熱情不容樂觀。不少知識分子出于個人享樂和追逐私利而明哲保身,在安樂窩里過著悶聲致富、沒事偷著樂的“幸福生活”,或假裝清高地說自己對政治不感興趣,或公開宣稱:“我們憑什么要關心政治?就愛拼命賺錢吃喝玩樂怎么了?”有人非常鄙視這些逃避政治的知識分子,認為他們拒絕和放棄了社會和人民賦予的政治責任和時代責任,缺乏“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與“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擔當精神和奉獻精神。因為人都是在占用了國家極其寶貴的教育資源后成為知識分子的,如果都像這些人一樣,在經濟利益和各種待遇方面極力扮演知識分子角色,向國家索取良多,而到了需要他們為國家奉獻時卻縮頭逃避,不肯履行知識分子職責,那么國家的全面現代化將如何實現?據中國人民大學前幾年進行的“北京市居民社會政治文化”的抽樣調查,關心政治者只有65.1%,較10年前下降了21.4%。從年齡上看,青年人比老年人更少關心政治;從職業上看,農民、私營及個體勞動者、企業職工最少關心政治。北京高校同學一向以政治熱情和政治敏感而著稱,但這次的抽樣調查卻將他們歸入了政治冷漠的群體,其中不乏“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與“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或“一心只慮個人事”者。
再據2005年涂序堂先生對南昌市大學生的問卷調查,部分大學生政治熱情不足,對某些政治參與表現出淡漠、消極甚至冷漠。如在回答“您面臨難以克服的困難時,第一求助的是誰”,有69.49%選擇了“同學或親戚朋友”,而謀求政治途徑求助“校方領導”和“班主任”的僅有4.66%;有半數以上的同學表示未參加任何學生社團,有49.79%的同學對“目前大學生的民主參與現狀”不滿意;在評價“目前大學生的入黨動機多是”時,選擇“有利于就業和個人前途”的為73.94%。
又據2011年華中師范大學在全國范圍的問卷調查,農民的政治參與存在8個方面的問題:政治知曉途徑單一、政治參與意識淡薄、政治參與能力不足、區域政治參與不平衡、低收入者參與度低、青年人政治參與度低、務工群體政治參與度低、女性政治參與度低。青年農民的政治參與度低于其他年齡段的農民,甚至比老年人還要低,形成了反常的農村政治參與現象,這與當今世界的主流情況正好相反。30歲以下的農民“不知道怎么反映”和認為“反映了也不會有回應”的比重高達73.3%。
有人提出,真誠地探討政治問題和政治理念,不怕犧牲、一往無前的政治熱情,這些可能永遠屬于上世紀80年代的品質。政治冷漠不但會帶來政治道德滑坡,還暗示著人們一種潛在的離心傾向、不信任感的加劇。針對目前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如果缺乏全社會的參與,“沉默的大多數”太龐大,喪失自下而上的改革沖動與建議,也就喪失了極其寶貴的勇氣、智慧與機遇,有些重大社會問題幾乎永無解決的希望。鑒于所有社會利益群體都休戚相關,所以對保持冷漠的知識分子群體而言,政治冷漠預示著很大風險:如果農民受苦時他們不說,工人下崗時他們不說,弱勢群體求告無門時他們不說,當輪到他們自己時,又會有誰替他們說話?
深入思考上述政治熱情不足的原因,確實多種多樣,這里僅提四點:
一是傳統政治的影響。中國傳統政治是君主專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生殺予奪往往系于君主一人一時的喜怒,而且不乏“道路以目”的政治高壓時期。所以傳統中國只有順從臣民,沒有獨立公民;只有倫理說教,沒有公民教育。像古希臘以公民精神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在傳統中國難以產生。直到清朝末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作為預備立憲的綱領,最后專章“臣民的權利”中,所有的“民”還被稱作臣民,仍要接受三綱五常的約束。顧炎武說:“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意為維護國家政權是帝王將相的職責,與知識分子無關。這使知識分子的依附性、盲從性和奴性空前增強,有時只能“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即便歷史發展到現在,知識分子的公民意識和主人翁意識仍很缺乏。當然也有人質疑,如果政治僅由“肉食者謀之”,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人民可以缺席,則怎么能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
二是歷史教訓的吸取。傳統中國也有一些知識分子受儒家文化影響,具有較重的入世情結,即在傳統政治文化的“超越”與“介入”中選擇了“介入”。但正如李國文先生所說:“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情結,說來也是一種痛苦的自虐。明知是杯苦酒,但一個個卻巴不得地端起來一飲而盡。于是,只要卷入政治漩渦之中,這個文人,縱使滿腹經綸,縱使才高八斗,也就統統付諸東流了。”于是,這些知識分子所深戀著的政治,往往會變成導引他們走向地獄之門的通行證。辛亥革命后,有些知識分子的命運如魯迅所說:“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殺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于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于革命的,或并不當作什么而被殺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新中國建立后,“思想改造”、“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斗爭”、“反右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運動使不少知識分子遭受政治打擊,他們至今對政治仍心有余悸。這些歷史教訓也會影響知識分子的政治熱情。
三是市場經濟的沖擊。市場經濟使個人實現自身利益的途徑多樣化,往往會轉移和替代人們對政治的關心和熱情。誠如達爾所說:“如果你認為同可以期望從其他活動中得到的報酬相比,從政治介入中得到的報酬價值要低,你就不大可能介入政治。”有人認為,市場經濟對個人發展的誘惑太大,而某些因素又使關心政治的成本太高,有些知識分子出于“趨利避害”,選擇追求個人發展和收獲經濟利益而不關心政治甚至完全忘記政治。有人理解在一個關心政治成本太高、追求個人發展和收獲經濟利益動力很大的時代里大多數人的政治冷漠,但不理解為這種政治冷漠而感到的洋洋得意。大學生也深受市場經濟注重物質利益的影響,他們明白政治參與不會馬上帶來實惠的物質利益,所以把更多時間和精力花在考證、考研、考公務員等與個人切身利益相關的事情上,這勢必影響他們的政治熱情。
四是社會責任的淡化。知識分子應有強烈的社會關懷感、社會責任感和社會正義感,應以推動社會公平和社會轉型為己任。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很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和“達則兼濟天下”,如孟子說:“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知識分子應以特有的社會責任和政治理想與祖國共命運,如屈原堅持明君賢臣共興楚國的“美政”理想,“雖九死而猶未悔”;林則徐禁煙抗英,雖遭革職充軍也無悔,“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青年周恩來立誓要“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而當前在各行各業的社會責任和職業道德都不容樂觀的背景下,有些知識分子也在淡化甚至逃避本職業群體承載的“不冷漠”、說真話和與祖國共命運的社會責任和政治理想,從而帶來了政治熱情的不足。
目前有的知識分子既不懂政治學理、政治原則和政治常識,也缺乏政治熱情、政治擔當和政治理想。有人指出,一個社會的知識界如果不了解現代政治科學,恐怕難免影響到這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當《中國人可以說不》、《第三只眼睛看中國》這樣的出版物受到大眾喝采并腐蝕大眾心智時,中國知識界基本在袖手旁觀,這是值得擔憂的。其實如前所述,知識分子應有以政治擔當和政治理想為支撐的政治熱情。吳敬璉先生說,目前有的干部是下定決心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如果也用“擊鼓傳花”一詞,則知識分子應下定決心抱著政治理想擊鼓傳花,應有不怕“鼓停花止”受“懲罰”的奉獻和犧牲精神,這是知識分子的正確政治擔當。只有知識分子引領更多的人下定決心抱著政治理想擊鼓傳花,這種政治理想之花才有可能在若干年或若干代后結出成功之果。
(作者單位:九三學社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