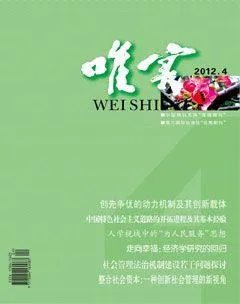康德、福柯啟蒙思想之現代性品格探微
康德、福柯啟蒙思想之現代性品格探微李西澤摘要:康德啟蒙思想的主要旨趣在于揭示人類自由地運用自己天賦的理性對現實予以思考和改造,福柯的啟蒙意旨是在關涉我們自身之歷史性存在的反思中對現代性問題的批判。啟蒙與現代性的交匯指向在于構筑全新的現代知識體系,鼎新現代社會觀念,建構現代社會運行秩序,并用知識代替幻想之意愿的追尋。在社會轉型時期,當代中國進行的啟蒙預構維度,旨在繼續秉持解放思想的理念,重塑理性的本真精神,建構公序良俗的社會規則與秩序。
關鍵詞:啟蒙思想;理性;批判;現代性;中國社會
中圖分類號:B516.32,B561.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1605(2012)04-0037-07
基金項目:201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研究(批準號:11XZX001)的階段性成果;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成果:馬克思社會有機體理論的內在邏輯研究(項目編號:12XNH192)的初步成果。
作者簡介:李西澤(1975- ),男,河南固始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發展理論、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哲學。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發端于歐洲18世紀的啟蒙運動已經成為一座思想的坐標被后人所向往、守望和景仰。當歷史的洪流歸于平靜抑或激流涌蕩之時,啟蒙之本真精神常為后人所論及、深思和重提——對理性致思自覺本然的追尋及理論思維何以在現代性的視域內得以生成并觀照當下的人類生存境遇及社會發展路向。于是,我們又不得不再次回到對啟蒙本源意義的理解和闡揚上去理解啟蒙所涵攝的真實意旨。“也許,當我們重新考慮啟蒙運動自己對‘什么是啟蒙?’這個問題的討論時,在我們對‘啟蒙’進行辯論的時候,這個重新考慮就能夠啟發我們理解那些仍然是至關緊要的問題。”[1]31康德和福柯對“啟蒙”的認識是我們在特定時代場域中真正理解該詞不可跨越的“思想基座”。
一、康德、福柯啟蒙思想的歷史回溯
今天,我們再次回眸啟蒙,不得不提及康德。是他在1784年的《柏林月刊》雜志第4卷第12期上發表了題為《回答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一文,從而將關涉啟蒙的問題凸現為世人所關注。康德啟蒙思想之意旨是批判封建中世紀的宗教神學對人們的精神制約與思想禁錮。康德指出,啟蒙“就是人從他咎由自取的受監護狀態走出……沒有他人的指導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狀態”[2]40。他列舉了人類不成熟的受監護狀態的諸種表現,并指出之所以處于不成熟的狀態,是因為人類自己把各種禁錮強加于自身。在康德的論域中,實現主體自身脫離不成熟狀態的條件是自由的開啟——人類運用自己思想理性的自由。“這種啟蒙所需要的無非是自由;確切地說,是在一切只要能夠叫做自由的東西中最無害的自由,亦即在一切事物中公開地運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2]41并且“對理性的公開運用必須在任何時候都是自由的,而且惟有這種使用能夠在人們中間實現啟蒙”[2]41。可以推知,康德啟蒙思想的核心是人類應該自由地運用自己的天賦理性,勇敢地去面對并沖出各種人為的制度約束和思想禁錮,而這些制約和禁錮的合理性限閾都需要經過理性認知的重新審判——在理性的標尺下對周遭的世界進行再度思考。
在中世紀宗教神學所形成的諸多限制和禁錮面前,康德認為,要運用公開的和私下的兩種不同的理性審判方式打破原有的束縛。“我把對其理性的公開運用理解為某人作為學者在讀者世界的全體公眾面前所作的那種運用。至于他在某個委托給他的公民崗位或者職位上對其理性可以作出的那種運用,我稱之為私人運用。”[2]41-42就此可知,公開運用理性意指人們從人“類”的視角審度和檢視各種規約和限制人們日常行為的合理性;而理性的私下運用即為人們從崗位職責的境遇審視各種限制和規約在特定職業崗位上發揮作用的合理性。可見,康德在理性的運用上特別強調對崗位、職位的相應制約及其限制,這是我們必須服從的,是維護一個個社會共同體有機循環和良性運轉所不可或缺的。身為“世界公民社會的成員”的諸多社會個體,亦具有運用自己的理性反思和批判這些制約、規范之去留的必要的權力。在此,康德認為,“理性在自由方面的實踐應用也導向絕對必然性,但卻僅僅是一個理性存在者本身的行為法則的絕對必然性。如今,我們的理性的一切應用的一個根本原則,就是把它的知識一直推進到對其必然性的意識(因為沒有這種必然性,它就不成其為理性的知識)”[3]。據此,在康德語境下,啟蒙的精神在于對舊有的壓抑人性的、束縛人自由發展的陳規進行批判與反思,在于勇敢地運用自己的理性合理地審視和批判以前的和現在的加載在自由、理性上的諸多限制。
在康德論說啟蒙的語境中,啟蒙不僅是人的一項權利,更是人追求、向往自由生活的象征;而且又是人的一項義務,因為人有義務和稟性去認識、探究事物的真相及其呈現形式。換言之,作為啟蒙主體的我們,可能因為諸種緣由而推遲啟蒙,但不能放棄對啟蒙的熱望。因為放棄啟蒙意味著對人的權利和義務的摒棄,意味著對人或成為人的棄置。“一個人雖然能夠對他個人,而且在這種情況下也只是在若干時間里,在他應該知道的東西上推遲啟蒙;但放棄啟蒙,無論是對他個人,甚或是對于后代,都叫做侵犯和踐踏人的神圣權利。”[2]44由此可知,啟蒙是人的一種存在,與人的自由、權利和義務緊密連結,構成人的一種生存程式或存在際遇。
或許,“啟蒙的每一個進步也許只是邁向黑暗的更進一步,這種感覺彌漫在尼采在20世紀的最忠實的信徒福柯的著作之中”[1]27。福柯以其看似“另類”的視野將其思想以極為犀利的觀點予以綻出,并將康德的啟蒙理論拆成了“碎片”,從這些片斷的邊緣追問啟蒙之要義。福柯關于啟蒙的言說是在對康德關于啟蒙思想的解釋、回應、提升中得以顯現的。福柯認為,康德把啟蒙喻為“出口”和“出路”意在表明啟蒙是一個過程,且“這過程使我們從‘未成年’狀態中解脫出來”[4]530。他指出,人類欲從“未成年”期進入到“成年期”,必須要在提升人類整體認知水平和提高個體素質兩個維度上得以實現。“應當認為‘啟蒙’既是人類集體參與的一種過程,也是個人從事的一種勇敢行為。”[4]530福柯雖然認同康德把啟蒙歸結為理性的使用和對啟蒙中內蘊的所謂的公開理性與私下理性的分類與提法;但在康德關于公開理性與私下理性具體運用的問題上,福柯發現了其中所隱藏著的不協調傾向。“不管怎樣,問題是要弄清楚理性的運用怎樣取得對于它來說是必需的公共形式,追求知識的勇氣怎樣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充分施展而同時又使個人確實地俯首聽命。”[4]532為了達致公共理性與私下理性間的有效協作,實現人的“類”原則與人們現實具體原則的通約、一致,福柯強調:“公共地、自由地使用自主的理性將是對唯命是從的最好保障,其條件是,那個人們必須對其聽命的政治原則自身應符合普遍的理性。”[4]532換言之,一旦社會民眾所尊崇、信守的任何具體的社會原則都是出自民眾自己對公共普遍理性的使用和反思,就可以在社會現實中盡可能有效地求解公共理性與私下理性間的可通約性,并在理性所構建的對社會現實的合法性質疑與合理性批判中推進人類認知水平的提高及人們自身完善度的提升和社會整體的良性躍遷。
在對康德啟蒙思想的析理中,福柯管窺出啟蒙與現代性問題的某些勾連。但令其深思與糾結的是:現代性與啟蒙的關系如何?現代性是啟蒙思想的緣起、接續還是終結?通常意義而言,人們慣常把現代性看作是與“前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相區別的一個時代。而福柯主張現代性不僅是一種態度,更是一種氣質(Ethos),這種態度和氣質所內蘊的是批判的特征。在康德的啟蒙思想里,這種批判精神的指向即為批判哲學氣質的表征。“這種‘氣質’具有對我們的歷史存在作永久批判的特征”,因此,“‘啟蒙’確定了某種哲理探討的方式”[4]536-537。在福柯看來,啟蒙的批判精神即是現代性的氣質和態度。因此,他認為,我們現在所擁有和秉持的現代性態度,并非是要從啟蒙運動中尋找或繼承其中的某些合理性的基本內核,而是要繼承啟蒙的批判精神的實質,并將這種精神“指向它的‘必然性之現在的界限’,也就是指向對于我們自身作為自主主體的建構來說并非必不可少的方面”[4]537。質言之,福柯啟蒙思想中的現代性就是在批判性質疑中對我們自身之歷史性存在的深度反思和對那些并非必不可少的、諸種多余的舊有社會制約與規范的批判——“要讓我們相信科學真理,相信歷史進步和社會公正。”[5]于是,福柯試圖通過對啟蒙思想的批判性繼承來反思各種現時代對理性和自由的限制和界劃,并通過批判來預示、把握、觀照并超越存在的種種可能性。他說:“批判正是對極限的分析和對界限的反思。……在今天,批判的問題應當轉變為更積極的問題……在于把在必然的限制形式中所作的批判轉變為在可能的超越形式中的實際批判。”[4]539因此,啟蒙的批判性一方面是對一定社會既定歷史必然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是對可能現實超越性的反思。“啟蒙所要求的不是一個在其中一切東西都赤裸裸地屹立在光芒之中的世界,而是一個在其中能夠無所畏懼地表達言論的世界。”[1]30
從康德在理性和自由的意蘊下言說啟蒙到福柯對“何為啟蒙”的再度詮釋中,蘊涵著這樣的邏輯脈絡:現代性作為一種態度和哲學生活,是在啟蒙精神的賡續中,以理性自覺為鵠的,以質疑性批判審視現實,以建設性反思引導時代潮流的。“這種批判與反思的對象是人類自身存在的歷史性和必然性制約或限制。”[6]正是在不斷求解啟蒙對時代的“普羅米修斯”式的精神建構和解構中,啟蒙不僅在歷時的境遇中成了時代精神的拓荒者和時弊的針砭者,而且在共時的際遇下,以普照光的形式開啟自身對時代之思的自覺引領和深度反思,并力求達致啟蒙與現代性的深度交匯。
二、啟蒙與現代性的交匯
我們知道:“一個民族要想登上科學的高峰,究竟是不能離開理論思維的。”[7]從傳統意義上講,哲學家及其他思想者往往把整個人類作為思維的對象,在運思其理性致思的時候,他們關涉的不是個體的行為,而是整個人類的特性、命運與福祉。與之相應的是,在現代性視閾下,啟蒙的主要旨趣也不僅僅是個人意識的張揚,而是聚焦于整個人類反對神話的話語霸權,打破迷信和愚昧的牢籠,喚醒主體自我意識,凸顯主體的自我價值,進而建構現代的價值規范與社會秩序。
在詞源學意義上,“啟蒙”一詞在漢語里是由兩個詞構成的。“啟”是動詞,本義是“開、打開”,引申為“啟發、啟導”;“蒙”是名詞,指一種草本植物,即菟絲子,引申為“蒙翳、蒙昧”,在“啟蒙”這個復合詞中,它又進一步引申為蒙童。由此可見,在漢語里,啟蒙一詞的本義就是去除遮蔽物,顯露出被遮蔽的東西,啟蒙概念的核心就是除卻蒙昧而使理智開顯出來。“‘啟蒙’以隱喻的方式被用于多種語言之中,意指敞開心智接收真理。”[8]
在人類發展的宏闊歷史視野中,啟蒙內蘊的精神氣質表征著一種流變、躍遷、提升的演進過程,“通過這一過程,首先在自由的名義下,理性被運用于人類既存現實的各個方面”[9]。在對理性正面效應規制的可能性前提下,啟蒙使人類在主體精神逐漸覺醒、自立的狀態中、從傳統社會的蹣跚步履中移植到現代社會的前臺——從蒙昧邁入文明,從未開化進入到開化,從稚嫩步入成熟,從成熟到新的更高級的成熟。在流動的歷史轉向中,“不成熟,就是聽命于權威的擺布和操縱,需要他人的引導,對先在的假設、教條和理論俯首稱臣,一句話,就是沒有批判性質疑的勇氣和能力。反過來,成熟——這是啟蒙的特點——就是敢于認知,擺脫權威的引導,并富有勇氣地運用自己的理智”[10]——即在勇敢地運用自己理性的境遇下,盡可能地使“人類理性能夠像鏡子一樣反映現實世界的結構”[11],使人類的理性之光普照寰宇。也就是說,啟蒙的根本旨趣是“使人們擺脫恐懼,樹立自主”,“喚醒世界,祛除神話,并用知識替代幻想”[12]。
啟蒙精神所內蘊的“祛魅”品格致使其注定要在社會運行的除舊與納新的互熵與博弈中與傳統相決裂而最終分道揚鑣,其旨意在“消解”傳統、“解構”人們思維和行為中固有的疾疴。因為“舊的秩序到那時已經過時、失效,并將要被一個比它前任脆弱性少一點靈活性又多一點的新秩序所取代”[13]。誠如E·卡西爾所言:“現代人,啟蒙時代的人……他必須而且應該拒絕來自上面的幫助;他必須自己闖出通往真理的道路,只有當他能憑借自己的努力贏得真理,確立真理,他才會占有真理。”[14]125啟蒙正是憑借自身的力量,以潤物無聲的堅強砥礪精神,在社會主流話語權或非主流行為藝術中,伴隨著世界整體信息激增和知識爆炸的大潮一往無前,表現出啟蒙與現代性交匯的品性。
一定意義而言,學界對現代性的論爭一直和“啟蒙”有著種種難以言說的纏結,這不單是因為現代性的批判者往往把矛頭對準啟蒙,也不僅因為人們在日常話語世界中通常把現代性等同于啟蒙,重要的是,我們現在很難脫離啟蒙言說現代性的諸多問題:就問題的產生而言,對現代性的質疑、反思、批評均是在啟蒙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沒有啟蒙,就沒有現代性的問題;就問題的實質而言,啟蒙的價值和理想與現代性的價值和理性有諸多重合之處,啟蒙典型地內蘊了現代性的核心精神。也就是說,現代性是啟蒙的主要結果,啟蒙關涉整個現代社會主體架構的塑造與構建。
概而言之,啟蒙表征了現代人追求的兩個價值維度:獲得永恒真理和達致普遍的人類解放。第一個維度與知識相關——啟蒙之意旨在于獲得關于世界的永恒真理。在18世紀啟蒙高峰期,啟蒙思想家堅信:經由啟蒙,人類能夠洞察人性的秘密、發現自然和宇宙的奧秘并揭示支配歷史發展之規律。牛頓力學體系的建立標志著近代科學的形成。在啟蒙的指引下,人類為了實現獲得永恒真理的偉大理想,三次科技革命相繼展開。于是,現代人擁有了實現自己理想的工具——現代科學技術。與此相伴生的是,現代意義上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應運而生。第二個維度與實踐相關——啟蒙希冀實現普遍的人類解放。在開啟民智、秉持理性和弘揚自由之理念的開啟下,啟蒙吹響了人類解放的號角,并負載在各種各樣的政治理論名號下為人類從必然王國達到自由王國提供指引:“自由主義”的政治理論試圖通過政治民主和工業革命實現其理想,而共產主義的政治理論則試圖通過勞動社會化和財產公有化達到人類的自由和解放。與這兩個維度相契合的是,在啟蒙與現代性的交匯中,昭示啟蒙正向價值的有以下三個面相:
一是構筑全新的現代知識體系。經由上文分析可知,啟蒙的宗旨是基于理性的自覺而重估人的本真價值。在彰顯人的主體價值和重新理解世界的基礎上,啟蒙在新的歷史際遇中產生了全新的現代知識體系。在自然科學領域,伴隨近現代工業化進程,啟蒙引發并促使了近代天文學、力學的建立,產生了具有現代科學意義上的數學、醫學、化學、生物學等學科。就人文科學而言,啟蒙思想創立了具有現代學科意義上的人學、倫理學、美學、政治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學科。同時,在啟蒙思想的影響和感召下,哲學、宗教學、邏輯學、法學等許多傳統學科也相應地發生了現代意義上的轉向。這些都為現代社會龐大知識體系的奠基、發展、演變做了較為充足的學理準備和知識儲備。與新的現代知識相呼應的是,在啟蒙的呼喚下,現代大學教育在歐洲日漸興起,隨后漸趨傳播到世界各地。可以說,正是科學的教育教學方法的推廣,現代社會的基本規制和秩序才得以確立與實現——啟蒙時代的大學是現代社會肇始與發展的搖籃。
二是革新現代社會觀念。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生活的變化必然帶來社會觀念的改變。在啟蒙的導引下,新的社會觀念得以基本確立,建立于基督教文化基礎之上的傳統社會觀念和主流價值日漸被啟蒙精神所創立的一系列全新的社會意識所取代,并引發具有現代風格與氣質的社會觀念的新轉型。在啟蒙思想所內蘊的現代社會觀念維度中,“理性”、“自由”、“平等”、“進步”等不僅在啟蒙思想中起重要作用,同時,也是現代社會價值觀念中的精神內核。在啟蒙對現代社會觀念的架構中,“理性”不獨具思維理性之意,亦有意志理性之內涵,還涵括工具理性和知識方法論之意蘊,并逐漸衍化為人們認知世界、實現自我、創造價值的基本方式。作為啟蒙思想主要意旨之一的“自由”,在當代成為人們的一種基本生活態度和提升人類追求自身解放的原動力。為打破歐洲封建政治等級制度而確立的“平等”觀念,在現代社會架構中日益成為衡量與公度整個社會生活各領域機會均勻、公正和諧、有序發展的基本價值維度;而“進步”則成為標識當代人類行為之正邪、善惡和未來社會發展優劣的終極標準之一。質言之,現代社會價值體系的基本架構皆濫觴于啟蒙所帶來的這些新的社會觀念。
三是建構現代社會運行秩序。啟蒙理性在對傳統社會秩序的反思、批判、詰問中,亦催生并建構了現代社會運行秩序。在政治領域,啟蒙思想經由對教會教規、禮儀的正當性批判、對教會專制合法性的質疑,最終引發了歐洲政教分離運動——在政教分離中的宗教世俗主義的轉向催化了近代民族國家的誕生。其間,在啟蒙精神滋養哺育下的民族國家大多選擇了開明君主制。隨著社會進步和啟蒙思想的日漸深入人心,君主立憲制取代了開明君主制,并最終創生了以民主、分權、制衡等為特征的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在經濟領域,啟蒙凸顯了人的主體價值,使重視人的現實利益的思想漸趨深入人心,而以“重農主義”為基礎的經濟利己主義思路的提出與推行和讓更廣大的民眾獲得更大利益的政策的出現,促進了人們共同利益的可通約性;在摒棄、廢除多種限制貿易自由、交易自主的規定后,市場經濟制度隨之確立起來。在文化領域,啟蒙思想崇尚的思想自由、批判質疑的意識使歐洲社會的言論、出版和思想自由在法律的保護和社會建制的規范下,逐步完善并成為現代人權發展的主要內容和基本價值取向。
當然,在啟蒙精神與現代性的碰撞、交流與匯合中,并非都顯示出啟蒙精神的正向價值。在歷史的長河中,啟蒙理性的擴張和普遍推行也在一定意義上帶來了一些不良后果。諸如:因為理性的盛行,現代社會在整體泛理性化的境遇下流變和衍義,理性視閾之外的鮮活現實內容則被理性的統一目標、普遍要求、秩序規則所遮蔽、宰制、扼殺;從某種意義上講,生活一旦被理性所過分控制,人類日常生活向度中的豐富性維度將漸趨匱乏;理性在破除舊有迷信的歷史回轉中,因“強迫”人們過分迷戀、盲目崇拜它,而達到迷信的程度,理性近乎成為當今世界最大的“宗教”;啟蒙理性制度化、宗教化的蔓延導致當今人與自然的關系在整體上較為緊張,從而產生今天的生態危機。就處于社會轉型期的中國而言,我們仍需在改革開放中呼喚新的啟蒙,并有必要對中國當下的啟蒙進路加以詩性預構。
三、啟蒙在當代中國社會的進路預構
歷史行進在21世紀,在全球化語境和后現代思潮的裹挾下,中國進行改革開放事業已經三十多年,正在由一個前現代社會步入現代社會,社會處于深度的轉型時期。而要使中國社會平穩涉過轉型期的“深水”區而到達成功的“對岸”,我們必須要有較為深刻、徹底的觀念上的變革——這種觀念上、精神上的深度變革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對當下中國社會的再“啟蒙”。立足于中國社會現實,啟蒙精神在中國社會當前境遇下的開啟無疑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啟蒙”既負載著我們一直追求的“立足時代,解放思想,啟迪未來”的理想,也包含了我們對理性精神的呼喚和對批判反思精神的追尋。要在清理既有體制的沉疴、陋習的頑劣、大眾認識的淺薄等諸多社會風氣的同時,建構既體現現代社會發展理念又符合中國國情和當下中國社會發展潮流的社會規則和秩序,就必須理清“啟蒙”在當代中國社會的進路預構。
第一,秉持繼續解放思想的理念。在啟蒙的歷史語境下,解除認識主體的被蒙蔽狀態,達到祛蔽的目的,就要祛除附著在認識主體周遭的陳腐思想和不合時宜的理論羈絆,從而達到思想對現實把捉的澄明之境和理論與實踐的緊密契合。就中國目前的情況而言,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綜合國力與國際威望也隨之提升,但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是,作為后發展國家,我們的工業化之路用半個世紀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用二百多年走完的歷程,因而,西方現代化百年之后出現的現代性問題在中國被壓縮打包,一并出現。因此,中國在進一步走向現代化和步入現代性的進程中,必須繼續秉持解放思想的理念,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用鮮活的實踐檢驗一切與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相關的理論,著力使思想和認識與現實和實踐相契合,自覺地使思想認識從束縛和制約其發展的體制和機制中解放出來,在應對全球化、后現代社會及風險社會的博弈中,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煥發出新的生機。在求解和破解中國社會進一步邁向縱深發展的當下,我們必須秉持繼續改革開放的理念,把新時期解放思想的工作持之以恒地堅守下去。在力求達到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中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在民生問題切實有效的解決中,使發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的社會民眾,在廣大民眾對社會的幸福度的體會和認可中更順暢和自洽地推進整個社會的思想再解放。
第二,重塑理性的本真精神。在康德和福柯對“啟蒙”的言說和表述中,有一個理論的共同結點:啟蒙標示著對既有權威的批判性質疑和懸疑性拷問,將歷史之致思和批判之思考予以邏輯鏈接,并將所有在啟蒙自身語境中能觀照到的事物置于理性的法庭加以審判。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民族從不文明、愚昧、專政、盲從的社會到文明、民主、自由、人權受到普遍尊重的社會,都歷經了“理性”的消化、反芻與吸收。在這一階段,可以把理性“視為一種能力,一種力量,這種能力和力量只有通過他的作用和效力才能充分理解”[14]11。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要重新進行社會“啟蒙”、重塑理性價值真蘊的地位,就必須使理性坦然面對并毅然為破解這些問題提供恰當的致思:資本的話語霸權和消費欲望的膨脹,人們日益增多的焦慮感、不安感、煩躁感,熱望實現自身價值而進行的追逐名利和自我炫耀,貫通在大眾心靈深處的皈依感和歸屬感的慢慢淡去——社會大眾處于欲望的“爆發期”、精神“失戀期”和文明j8y8dsg2tQJULai+FK8EBA==的“斷奶期”,“處于迅速崛起但價值迷茫的狀態”[15]101,社會民眾本已固有的理性的沉穩與平和心態的靜觀已經被資本異化及在資本異化下權力的話語所俘獲、淹沒乃至漸趨沉寂。“啟蒙”理性祛蔽的作用要求我們打破教條主義和他律對理性的破壞性束縛。尤其在以文化自覺、自信、自強為主旨的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當下,中國文化在世界圖景中的挺立、自強和走出國門必須是中國思想以新銳之思、學理的深邃綻出,這恰恰需要以包含中國理性和具有世界話語的形上之思的返本開新為深層底蘊。
第三,建構公序良俗的社會規則與秩序。啟蒙思想在自身的邏輯域中,除了在應然意義上給予世人以理性的開敞和思想境遇的開放和批判性反思外,還在實然意義上具體地構建基于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圓融、自洽自身的社會規則和秩序。行進在當下中國的啟蒙,必須戒除物質主義的神話和資本的話語霸權并建構符合中國國情的公序良俗的社會規則與秩序。在我們當前的社會中,浮躁之風日盛,急功近利之氣流行,攀龍附鳳之行為漸多,“拼爹”現象和“潛規則”事件頻現……這說明,中國的社會現代化作為一種深刻的社會轉型,必然交織著一個不斷激濁揚清、破舊立新、秩序重鑄的過程。在打破既有的社會結構和包括附屬于這一結構的社會規則體系時,在新的社會規則和秩序沒有完全確立和舊的社會規則和秩序沒有最終退出歷史舞臺的間隙中,社會規則意識缺位,違背和破壞規則以贏得“方便”和賺得利益成為習以為常的事情(這些現象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也是常見的)。因此,必須規避規則意識缺位和社會秩序失范帶來的弊端;必須在啟蒙精神的指引下重塑全社會的誠信意識,建立健全完備的法律體系,加大對違法者的懲處力度,擴大社會民眾的教育水平,依法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加大對權力的監督和管控,在體制機制創新中推進社會管理制度的改革。妥善處理好“作為傳統社會基本特征之一的‘熟人社會’向現代社會所要求的‘公民社會’轉變,也是社會現代化和現代社會規則建構過程中必須面對的問題”[16]。如此,“一個具有完善憲政與法治的國家,既可以造就一個普遍法律規范下的市場,同時也會形成一個以溝通理性為主導并與國家能夠實現良性互動的公民社會”[15]164。
啟蒙運動作為一個歷史事件已經成為人類思想史界域中遠逝的風影,但它所蘊涵的啟蒙精神意旨卻依然激勵、鞭策、鼓舞著我們。當代中國社會的再啟蒙是與中國社會蓬勃發展的現實相聯系并有契合之處的,同時,與啟蒙相伴生的是希冀中國社會的良性、有序發展和對國際社會作出的道義擔當和應有貢獻。我們應該明白,啟蒙的境域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在歷史沒有“終結”的情境下,啟蒙一直都是行進在人類致思途中未完成的開敞形態。□
參考文獻:
[1]施密特.啟蒙運動與現代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3]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4]福柯.福柯集[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
[5]歐陽謙.當代法國哲學與新啟蒙運動[J].教學與研究,2007(12):62.
[6]許斗斗.啟蒙、現代性與現代風險社會——對康德、福柯、吉登斯之思想的內在性尋思[J].東南學術,2005(3):124.
[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5.
[8]Burns,Pickard,H.R.歷史哲學:從啟蒙到后現代性[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47.
[9]奧斯本.啟蒙面面觀——社會理論與真理倫理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13.
[10]汪民安.現代性[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84-85.
[11]Gray,J..Enlightenment's Wake[M].London: Routledge,1995:152.
[12]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1.
[13]鮑曼.流動的現代性[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223.
[14]卡西爾.啟蒙哲學[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
[15]資中筠.啟蒙與中國社會轉型[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16]賈高建.拒斥與沖突: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規則建構[J].哲學研究,2011(8):25.
責任編輯: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