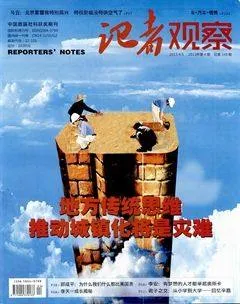沈從文的后半生推開了哪扇“門”
沈從文是現代著名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說代表人物。14歲時,他投身行伍,浪跡湘川黔邊境地區。1924年開始文學創作,抗戰爆發后到西南聯大任教,1931年一1933年在山東大學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
沈從文從事中國紡織服飾考古研究工作的過往,在于沈從文誕辰110周年之際出版的《章服之實》一書中得到了首次披露。
01
1953年,朝鮮的炮火停歇了,23歲的王予予從戰場回到祖國,游覽北京。
他對故宮頗感興趣,一路參觀。走進午門內西朝房時,一個穿著白襯衫的50來歲的人跟在他身后講解。那是個銅鏡展,他講得十分耐心,一個柜子就講了兩三個小時,讓王予予收獲很大,約好了第二天再來。一天又一天,王予予在西朝房待了一個星期。一個星期后,他忍不住說:“非常感謝你花了這么多時間陪我,我一直張不開口問您尊姓大名。”
對方說,他是沈從文。
20年后的1973年,“抓革命促生產”轟轟烈烈,年輕的美工王亞蓉一連幾天泡在圖書館尋找靈感。相鄰閱書的一位清癯長者和她談起來:“我有一位老朋友,有極多的形象資料。如果他愿意,我帶你去拜訪他。”
“您能告訴我他是誰嗎?”“沈從文。”
又過5年,“文革”終于結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正式調入了一個人——沈從文。胡喬木問他有什么困難和要求,他只提了兩條:一,將王子予、王亞蓉調到身邊協助工作;二,集中整理出版周總理囑編的《古代服飾圖錄》。
02
沈從文,這位從湘西走出來的文學家,將自己的后半生投入到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服飾文化悠長千年,針針線線,編織出燦爛云圖。而推開中國服飾文化研究大門的人,當屬沈從文。
學界公認,沈先生既熟悉歷史文獻,又熟悉文物。對于正史、筆記、古今著述,乃至小條注釋,他都處處留心;對于壁畫、雕刻、傳世畫作以及各時代的各色文物,更是過目不忘。考古學家徐秉琨高度評價:“幾十年的研究中,他從文物實證出發,解決了不少學界難題,一些文物落實了歷史上的名稱和用途、用法,一些歷史上的服飾制度也得以從文物上給予_還原,對某些服飾、器物的發展源流、先后演變,他也都作出考釋,為世人勾勒出中國古代服飾發展的輪廓。”
在助手王亞蓉的記憶中,沈先生的腦筋永遠在為他的研究轉動。他的家中堆滿了圖書資料,桌上、墻上總是在不斷添加各種小條:“這個新材料待補充”“這個××有用”……沈先生工作起來廢寢忘食,常備餅干點心充饑,點心過期了就多吃幾片土霉素。難得坐下來好好吃一餐飯,也在談工作,筷子在空中舉了很久,忘記放到嘴里。
沈從文的研究,出入于實物和文獻之中,如魚得水;在歷史長河中考證分析,細致入微。“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這聯詩句如同他的寫照。
03
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先生猝然離世。所幸,他用后半生之力推開的服飾研究之門中,多了幾個身影。
追隨沈先生走上紡織、服飾考古之路的王予予,與先生一樣謙遜、認真。
他主持了全國首件金縷玉衣的復原,在馬王堆漢墓挖掘、法門寺地宮挖掘等考古界大事上,都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然而,他的名字鮮為世人所知。
與老師的研究不同,王予予的工作更側重保護。他的一大創新是發明出絲網保護技術,并用這一技術修復了阿爾巴尼亞的國寶——6世紀和9世紀的兩本殘破的羊皮紙《圣經》。不僅羊皮書,絲紙類軟片文物的保護都可以應用這一技術,功莫大焉。
王予予不僅專業水準高,為人更是謙抑克己,品德高尚。他曾經5次到山西大同萬人坑進行發掘、清理、保護工作,將受害同胞的遺體從幾十米深的坑洞中背出來,身心勞累,種下病根。20年后,他被疾病擊倒,兩三天必須做一次腎臟透析,經濟拮據。此時,由他編寫的《山西煤礦萬人坑發掘記事》在香港出版,出版社支付他兩萬元稿費,希望能幫到他。他卻一分不留,全部捐給了大同萬人坑紀念館。
而在此之前,增訂版《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出版后,王予予本可以繼續自己的研究。但為了使《沈從文全集》順利出版,他毅然抱病整理沈先生的筆記,將大量精力投入這項費時費力而又默默無聞的工作。待到《全集》編成,他的生命也已臨近尾聲。
1997年冬,王予予去世,年僅67歲。
04
沈先生和王予予先生先后過世,令人唏噓。徒留的王亞蓉,依然勤勤勉勉,忙碌在發掘保護的一線。
葉茂臺遼墓、北京老山漢墓、新疆尼雅漢墓以及江西靖安東周多棺大墓等的發掘清理中,都有她的身影。
她說:“唯有不輟與耐煩、合力,方可使今人多少擁有些與千年厚蘊相望的能力。”或烈日炎炎之下,或踏足泥濘之中,華發叢生的纖纖弱質在深深的墓坑中一點一點剝取那些粘附著或疊壓中、甚至糜爛如泥的絲織衣物,一站或一蹲就是幾個小時。
此外,王亞蓉還保存和整理了沈從文先生的講話錄音,形成了《章服之實:從沈從文先生晚年說起》一書。書中,王亞蓉仿若講解者,娓娓道來,并引出沈從文、王予予和自己的口述回憶,展現了中國六十年紡織、服飾考古事業走過的艱難歷程。
這些文字的出版,并不求聞達于世,僅僅因為這段歷史和為這段歷史作出貢獻的人,應該被銘記。
摘自《章服之實:從沈從文先生晚年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