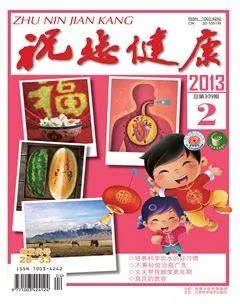莫言的寬容
“他是中國文壇超重量級的作家,他的文學才華、創造力、藝術能量在中國文壇上應該說是舉足輕重、首屈一指的,因此我個人斗膽地說,莫言的高度就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高度。”這是北大中文系教授陳曉明對莫言的評價。57歲的莫言真的沒讓大家失望,獲得了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
上世紀80年代初,莫言在河北的《蓮池》發表了處女作,當時在《花山》當編輯的鐵凝還從自然來稿中編發了他的第一篇散文。1984年莫言考上了解放軍藝術學院,在老師的指導和文學熱潮的刺激下,他悟到很多東西。《紅高粱》、《檀香刑》、《豐乳肥臀》、《酒國》、《生死疲勞》、《蛙》,使莫言名聲大震,走向世界。
盡管作品在世界文壇的影響和聲望足以讓莫言驕傲,他仍然常常懷疑自己配不配得上“作家”這個稱號。除了極高的文學造詣和這種并非偽裝的謙虛,莫言的身上還有特別值得我們學習的寬容。他提出,對新生代作家要持一種寬容的態度。他認為,年輕作家往往積累不夠,沒有相對可以上升到哲學的思想,但是他們確實非常認真嚴肅地進行著文學探討,而且恰恰是他們追求了更多的非世俗的東西。他認為,再過20年,“80后作家”會成為創作主角,更年輕的作家也會發展起來。
這番寬容的話語無疑是給中國文壇的年輕力量注入了興奮劑。在讀書時,莫言同樣有很寬容的心態。他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是不徹底的。我們在讀前人的作品時,往往能看到歷史的局限性,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人的局限性。對前人的局限性,我們大都持一種寬容的態度,但這種寬容里邊似乎還包含著一種惋惜。我們潛意識里想:如果沒有這種局限性,他們會寫出更好的作品。但現在我想,我們這種對人的局限的否定態度,對于文學來說,也許并不一定正確。我的意思是說:一個沒有局限的人,也許不該從事文學;作者的局限,也許是文學的幸事。”
莫言出生在山東一個很荒涼的農村,因為貧困,他輟學回家勞動,正式學歷只有小學五年級。雖然不能上學,但是莫言特別迷戀讀書。沒想到這樣的愛好竟遭到父母的反對,家長反對他看“閑書”,是怕他中了書里的“流毒”,變成個壞人,也怕他因看書耽誤了割草、放羊。有一次,莫言借到一本《青春之歌》,鉆到草垛里,一下午就把整本書讀完了。他從草垛后暈頭漲腦地鉆出來,已是傍晚。由于耽誤了放羊,他心里很恐懼,推測一定會遭到家長的責罵,可沒有想到,母親看看他忐忑的樣子,只是寬容地嘆息一聲,那一刻,莫言心情好得要命。他也因此對寬容感觸尤深。
莫言的寬容,還表現在出版社欠他稿費,他顧著朋友面子不愿去要。一次,他找人裝修房子,錢花了,家里裝修的效果一點不好,他也不抱怨,再找個人來重新弄。莫言都對物質生活沒有什么追求,在他看來吃飽穿暖有地兒住,挺好。
創作至今,莫言的文字也逐漸發生了一些變化。從前的尖銳、反抗漸漸在隱退或是藏在了幕后,而浮出水面的反而是一份平靜下的波濤洶涌、沉思后的人生剖析。面對這樣的變化,莫言自坦言:“年齡越大,我對他人的理解也更寬容了。”
《蛙》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曾獲我國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小說以“姑姑”的一生經歷為主線,她是鄉村醫生,幾十年接生的嬰兒遍布高密東北鄉。而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讓已生育的男人結扎,讓已生育的懷孕婦女流產,則成了姑姑的兩件大事……
在臺灣版《蛙》的序言里,有這么一句話:“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對此莫言解釋說,我們過去都把目光放在別人身上,拿放大鏡尋找別人的罪過,很少有人認識到自己的罪過。“人只要認識到靈魂深處的陰暗面,才能達到對別人的寬容。作為作家,應該對他人抱有同情。哪怕他是十惡不赦的惡棍,哪怕他無中生有地造我的謠言,哪怕他將唾沫啐到我的臉上。因為他本來可以成為好人的,成為惡棍,是他的最大不幸。如果能達到這一高度,才是真正的寬容,才能達到真正的悲憫。”
由此觀之,寬容實為莫言成功的一種智慧。一直以來,我們對中國作家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抱以寬容,在這種寬容的等待下,寬容的莫言終于走上了領獎臺。(編輯湯知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