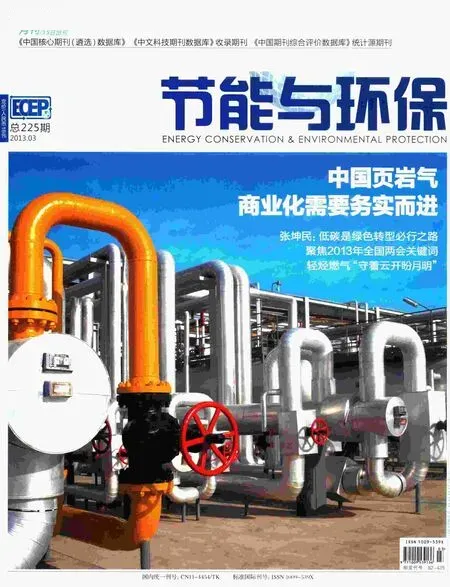張坤民:低碳是綠色轉型必行之路
文 本刊記者 陳向國
2013年中國兩會召開前夕,央視一項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民眾最關注的問題,環境保護位列第一,經濟發展位列第三。
國內外的發展經歷和中國面臨的困局都說明,資源環境支撐經濟增長的能力已日趨嚴峻。褐色經濟必須向綠色經濟轉型,這已逐步成為全球共識。
何謂綠色經濟?聯合國環境署給出的定義是:“可促成提高人類福祉與社會公平、同時顯著降低環境風險與生態稀缺的經濟”,換言之,“綠色經濟可視為一種低碳、資源高效型和社會包容型經濟”。
然而,由于褐色經濟的發展慣性和人類謀取眼前利益的沖動,使得綠色轉型困難重重。
人類的生存環境堪憂,資源能源的支撐能力堪憂。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人類面臨抉擇,中國無可例外:在見證多年經濟增長奇跡之后,窘境正逐漸明顯。以人類生存最基本的需求為例:淡水日益缺乏,且污染嚴重;空氣被PM2.5重度侵入……。
為了探求中國綠色低碳發展的方法、途徑及解決相關問題,本刊采訪了多年來一直致力于推動我國可持續發展發展的先行者之一: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會名譽理事長、原國家環保局第一副局長張坤民教授。

張坤民:
1957年考入清華大學本科,1965年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教。曾任清華大學土木系副系主任、環境系首屆副系主任,中國環境管理干部學院首屆副院長,連任兩屆國家環保局第一副局長,國家環保總局黨組成員兼機關與在京直屬單位黨委書記,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秘書長。現任國家環保部科技委委員,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會名譽理事長兼低碳發展研究學組主任等。
“人類在進化演變過程中,通過無數次成功失敗、生死磨難,經歷了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等階段。盡管曾有過不少閃光的思想乃至法規(如2000多年前的《秦律》),但人類同自然的關系一直處于比較盲目的狀態”。張坤民談到人與自然關系時作如此表述。他說,“特別是人類逐步進入工業文明階段,雖然創造了比以往多得多的物質財富,代價卻是損耗了比以往多得多的地球資源,增加了比以往多得多的環境負荷,使人類飽受發展不平衡、分配不公平、生態難持續的痛苦”。“好在人類正在覺醒,1972年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以‘只有一個地球’敲響了警鐘;20年后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里約峰會,1992年),提出了全球可持續發展綱領《21世紀議程》;又是20年后的聯合國‘里約+20’峰會(2012年),通過《我們希望的未來》,進一步明確了人類面臨的困境、挑戰與希望。”在張坤民看來,中國的希望就是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堅持走可持續發展之路,邁向綠色轉型。
不計代價的單純GDP增長要不得
單純GDP增長并不等于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的目的是要使公眾的物質生活提高、生態系統改善、社會公平公正。而單純GDP增長是建立在生態系統走下坡路的基礎之上的。這種不計代價的做法,是不科學的,肯定不可持續。
“大躍進”的教訓不能忘
記者:國家正在狠抓節能減排,目的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科學發展之路。您親身經歷過新中國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您覺得哪些階段應該認真反思,汲取教訓?
張坤民:1958年“大躍進”年代那種不計代價的發展一定不能要。
記者:是親身經歷過那個時期的。請您根據自己切身經歷談談為什么那種發展不能要?
張坤民:1957年到1958年,“讓高山低頭,要河水讓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天等于二十年”等豪言壯語越來越多,畝產糧食放“衛星”的報道也到處出現。1957年,我國年產鋼只有535萬噸,這確實是太低了。因此,全民動員,“以鋼為綱”,“為1070而戰”,鋼產量一年就要翻一番。1958年9月底,北京抽調了5000名大學生支援全國大煉鋼鐵,我們班60名同學被派往河南省。我和4名同學到鞏縣(現鞏義市)嵩山北麓的夾津口,3個月一直住在山坡的窯洞里,同當地農民以及來自開封、東明、蘭考、尉氏4市縣的5千名基干民兵,晝夜奮戰,直到12月底回京。
記者:這樣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張坤民:希望建成一個小鋼鐵基地。當地確實發現過一些儲量不大的鐵礦和石灰石礦(“雞窩”礦),但遠不足以建成一個鋼鐵基地。后來,我從報上高興地看到,夾津口已從一個小山村發展成為河南的建材生產銷售基地之一,當然這肯定有“大煉鋼鐵”的推動作用。但當年動員了那么多人力、物力,消耗了那么多礦物、燃料,為“大躍進”所付出的學費實在是太高了。科學是老老實實的東西。發展不講科學,難免事與愿違。2010年,我重訪夾津口,沒找到當年住過的窯洞,新建的鎮上見到不少樓房,而當地的空氣污染亟待改善。
改革開放后的高速發展伴隨著嚴重的生態環境被破壞的問題
記者:“大躍進”時代的發展模式不能重來。那如何看待取得令世人矚目成績的改革開放后的發展階段?
張坤民:改革開放初,鄉鎮企業曾風行一時,使城市污染蔓延到鄉村。國家環保局當時花了極大努力,強調政府負責、以法治污、加強規劃、環評與限期治理,2000年前關停了8萬多家嚴重污染企業,盡力遏制環境惡化加劇的趨勢。加入WTO之后,中國抓住發達國家熱衷金融杠桿、加快產業轉移的契機,借助國內大量廉價勞動力,加快了工業化步伐。我們親眼看到,鋼鐵、水泥、化工等產能激增,國民生產總值翻番,逐步躋身到全球經濟總量第二。同時也越來越看清污染轉移、能耗轉移和碳排放轉移等種種弊端。截至2007年,當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四次報告發布和《巴厘路線圖》達成,中國在碳排放方面,已經處于相當困難的境地。這段時間里,有的地方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付出了不小代價。不切實加強環保的發展不是科學發展,必須下決心改變,走可持續的綠色低碳發展之路。
國際壓力與日俱增 生態承載力已經超出
低碳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大勢所趨。然而,由于歷史背景與發展階段的不同,各國的碳排放量和面臨的減排壓力也各不相同。對此,中國要深刻了解自己的處境,為中國的和整個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勇于擔當共同的但有區別的責任,努力有所作為。
形勢嚴峻
記者:中國的節能減排,成果顯著,但碳排放總量仍在上升,人均排放量也不斷達到甚至超過世界人均值。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張坤民:兩句話:成績顯而易見,形勢日益嚴峻。據聯合國發展署(UNDP)的報告,從碳排放的歷史存量看:從工業革命開始到2004年,每10噸CO2中,有7噸是富國排放的。英國和美國人均CO2排放存量達1100噸,而中國人均存量為66噸,相差近2個數量級。按目前流量看,據國際能源機構(IEA)的統計:在2006年,世界燃燒排放的CO2總量為280億噸,中國為56.5億噸,英國為5.4億噸,美國為57億噸;同年世界人均CO2排放量(碳足跡)為4.28噸,中國也是4.28噸,同世界持平,英國為8.86噸,美國為19.00噸。而到2010年,世界燃燒排放的CO2總量為303億噸,中國為73.1億噸,英國為4.8億噸,美國為53.7億噸;同年世界碳足跡略升到4.44噸,中國升到5.43噸(4年間,中國碳足跡比世界人均高出22個百分點),英國略降為7.78噸,美國略降為17.31噸,但他們仍很高。
記者:上面數據說明什么問題?
張坤民:由上述數據可見,相比于已經完成工業化的發達國家,處于工業化中期的中國,盡管“十一五”期間狠抓了節能減排,使碳強度繼續下降了19.1%,但總能耗和碳足跡的絕對量仍在不可避免地上升。這不隨人的主觀意志而改變,而是由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等客觀因素決定的。據多項研究預測,中國要到2030年左右方能達到峰值,然后才會下降。而這個峰值能否提前,要取決于多項政策措施和實際努力的綜合結果。所以說,我們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
對高碳消費方式應理性地說“不!”
記者: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在去年“里約+20”峰會前發布的《地球生命力報告2012》中指出,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需求自1966年以來翻了一番,人類正在使用相當于1.5個地球的資源來維持我們的生活。高收入國家的生態足跡是低收入國家的5倍。按目前的模式預測,到2030年,我們將需要2個地球來滿足我們每年的需求。這對我們走低碳綠色發展之路有何現實意義?
張坤民:上述報告列出了2008年全球生態承載力前十名的情況。其中,巴西生態承載力第一,達世界15.4%,其人口約占世界3%;中國承載力第二,為9.9%,人口約占世界20%;美國承載力9.8%,居三,人口約占世界5%。可見,中國現在就已經明顯超載了。這就告訴我們,必須走低碳綠色之路,而且,刻不容緩。對那些高碳的消費方式應理性地說不。
記者:對于高碳消費和浪費現象,政府正采取各種措施和輿論力量加以引導。如現在興起的“光盤”行動就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高碳生活方式依然很有市場,如對高耗能汽車不遺余力地宣傳等。對此您如何看?
張坤民:你說的不錯。的確,近年來,一些媒體和街頭廣告都在大肆宣揚四輪驅動的大馬力運動型轎車(SUV)。不少國外廠商在華SUV銷量2011年增長了20%以上,他們希望在中國還要有更大的銷售收益。你在機場、高鐵車站或高速公路出入口,很容易見到類似廣告。世界銀行2010年世界發展報告曾以SUV為例講明利害,假設把美國的SUV轎車都全部換成低油耗車,僅此一項所減少的碳排放就幾乎相當于為亞、非、拉16億窮人供電所產生的排放。一半以上石油要靠進口的中國,我們實在不應該盲目地步美國的后塵。
記者:上述數據是如何得到的?
張坤民:計算是基于美國4000萬輛SUV,每年共行駛4800億英里(假設每輛車行駛12000英里)。SUV車的平均油耗為18英里/加侖,4000萬輛車每年消耗270億加侖汽油,每加侖汽油排放2421克碳。歐盟市場上銷售的新型節能轎車的平均油耗為45英里/加侖,每年可減少1.42億噸CO2。發展中國家貧困家庭平均每人每年用電170千瓦時,電力碳排放因子取世界平均水平160克碳/千瓦時。
記者:SUV現在的確很時尚,也很有市場。應該如何引導SUV的消費?
張坤民:我的看法是一分為二。首先,如果生活、工作在山區,需要經常爬坡,或路況坎坷或執行特殊任務,那需要用它;如果你工作與生活在道路平坦的市區,只是為了時尚,甚至為了炫耀,那就完全沒有必要。要知道,我們現在近60%的石油要靠進口啊!

張坤民主要著譯
同原國家環保局、原國家計委、聯合國開發署、世界銀行等專家于1994年完成全球環境基金資助的總報告《中國溫室氣體排放控制:問題與對策》;
主筆《可持續發展論》;
主編《中國環境保護行政二十年》、《低碳經濟論》、《低碳發展論》、《低碳創新論》等;
主譯審《美國環境百科全書》、《環境經濟學新論》等;撰寫專著《關于中國可持續發展的政策與行動》、《低碳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挑戰與機遇》等。
低碳發展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低碳是綠色發展的重要內涵之一。低碳發展就是推進綠色經濟、踐行科學發展觀、走可持續發展之路。現實決定了中國必須走低碳之路,但低碳之路不平坦,面臨挑戰巨大。
發展低碳經濟是中國的內在需求
記者:我國是發展中大國,能源結構以煤為主,產業結構以重化工為主,導致碳排放在近十年多來劇增,面臨巨大的國際壓力。除了外力推動,中國的內在需求體現在哪些方面?
張坤民:我國低碳發展除了應對氣候變化等外部壓力外,至少還有5個方面的內在要求。

張坤民應邀赴日講學時同日本前首相村山富治交談。
一是我國人均化石能源資源擁有量不高,探明量僅相當于世界人均水平的51%。特別是能源結構以煤為主,這在碳排放方面特別不利。而且化石能源的預測支撐年限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使最“富有”的煤也只能支撐80年,而世界保證程度是230年;石油,世界是45年,中國是15年;天然氣,世界是60年,中國是30年,中國的可采量分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或1/2。
二是碳排放總量突出。按照聯合國通用公式計算,碳排放總量實際上是4個因素的乘積:人口數量、人均GDP、單位GDP的能耗量(能源強度)、單位能耗產生的碳排放(碳強度)。我國人口多,經濟增長快,能源消耗大,碳排放總量不可避免地逐年增大,其中還包含著出口產品中大量的“隱含能源”。我們靠高碳途徑生產廉價產品出口,卻背上了碳排放總量大的“黑鍋”。據多項研究,中國碳排放中約1/4(也有說1/3)是出口產品造成的。這種輸出實質上是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性被迫輸出。
三是“鎖定效應”的影響。這幾年,為了節能減排,各地把一些小型燃煤電廠淘汰了,改成大型的或新型高效煤電廠。這些被炸掉的小電廠實際上也是一筆不小的損失。國際能源機構2007年曾預測說,如果按目前趨勢不做改變,中國和印度15年內用現有技術新建的燃煤電廠,由于大型基礎設施的鎖定效應,其碳排放可能影響到2070年。這個包袱就更大了。
四是生產的邊際成本不斷提高。碳減排客觀上存在著邊際成本與減排難度隨減排量增加而增加的趨勢。1980~1999年的19年間,我國能源強度年均降低了5.22%;而1980~2006年的26年間的年均降低率則為3.9%。兩者之差,隱含著邊際成本日趨提高的事實。到目前,成本低的節能減排措施有不少已經被采用了,面臨的將是越來越難和代價越來越高的項目。也就是說,現在節能難度在增大,邊際成本在增加。因此,必須從全球低碳發展大趨勢著眼,通過轉方式和調結構,把寶貴的資金及早地有序地投入到未來有競爭力的低碳經濟方面。
記者:還有第五個內在因素是什么?
張坤民:第五個內在因素是碳排放空間有限。發達國家歷史上人均千余噸的二氧化碳排放存量,大大擠壓了發展中國家當今的排放空間。我們完全有理由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要求發達國家履行公約規定的義務,率先減排。據國際能源機構統計,2010年,我國的人均用電量為2958度,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892度),約為經合組織國家的1/3左右,美國的1/5左右。但一次性能源用量已占世界的19.1%,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占世界的24.1%。這表明,我國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碳排放強度偏高,而一段時間內化石能源用量還將繼續增長,碳排放空間不會很大,所以應該積極發展低碳經濟。
積極有效應對新的復雜形勢
記者: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發達國家扮演了兩種角色,開始曾是積極的正面角色,自2007年后轉變為推卸責任的消極角色。這種變化對我國發展有哪些不利影響?
張坤民:2007年是全球關注氣候變化空前高漲的一年。年初,IPCC發表第四次評估報告;年末,全球氣候大會達成《巴厘島路線圖》,各大媒體都聚焦到這一關系人類命運的大事上。主要發達國家按照《京都議定書》第一階段減排義務的規定,原本應于2008至2012年將其排放量從1990年水平降低6%至8%,實際上非但未減還增排了10%左右。而經合組織的國際能源機構2007年的《世界能源展望》特意把探照燈瞄準中國和印度的能源增長。
記者:在探照燈瞄準中、印等國能源增長的情況下,形勢發生了哪些變化?
張坤民:我感到,同一、二十年前相比,形勢有了顯著變化。一是體現在南北關系上,過去發達國家為了達成氣候協議,口頭上還多少承認歷史事實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并表示要率先減排,現在卻盯著主要發展中國家近年來從很低起點出發的能源需求高速增長,似乎找到了借口,想從道德制高點上逼我們承擔義務;二是體現在經濟增長速度與方式上,發達國家已經完成了工業化的階段,有條件向低碳轉型,我們接受的則是全球化產業結構的被動轉移,仍在拼資源、拼人力、制造廉價商品出口,而現有的能源資源顯然不可能持續支持下去;三是體現在未來的國際競爭力方面,發達國家已擺開陣勢要搞低碳轉型、建低碳社會、抓新能源技術,迎接新一輪產業革命,同時,設置不同壁壘,阻我中華振興。
記者:我們應該如何應對這樣復雜的變化?
張坤民:應該認清形勢,冷靜思考,積極籌劃,落實行動。要深刻意識到可持續發展道路并不平坦。我每天在電腦前瀏覽或思考時,總是喜憂交加。“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的聲音不絕于耳,圍追堵截的身影隨處可見。對手們明知我國“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冷靜觀察、沉著應對、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科學發展”、“和諧社會”、“生態文明”等一系列方略,就是不情愿看到中國國力強盛,影響他們的戰略利益。中國本身的能源資源稟賦、經濟發展階段和科技教育水平也亟待提高。面對氣候變化、能源安全、新的產業革命,保持一個發展中大國的清醒與自覺十分必要。既不能見事遲、行動慢,也不能情況不明決心大,需要的是及早部署、統籌規劃,抓好國內國際、長期短期相協調的兩個大局。
共識!行動!及時行動!高效行動!
“2012年,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報告再次明確指出 ,‘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這表明了中國對于綠色低碳發展的高度重視和決心。”在張坤民看來,綠色低碳發展需要更及時、更高效的行動。
必須凝聚共識
記者:中國作為全球人口總量第一、經濟總量第二和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第一的大國,正處于環境庫茲涅茲曲線的上升時期。為了人類命運和國家前途,我們必須明確選擇并及早行動。在行動之前必須凝聚共識。在這方面我們準備好了嗎?
張坤民:首先可以肯定地說,中國是承擔國際責任、應對氣候變化、踐行綠色發展最積極、最有成效的發展中國家,努力和成績有目共睹。面對新形勢,我們還需要不斷增加共識、并落實到更積極有效的行動中。達成共識,這是一個逐漸凝聚的過程。從2007年到2011年,我們曾目睹一些專家和個別負責人對于低碳發展一時的不解和疑慮,擔心是不是“陰謀”和“陷阱”。隨著從中央到地方,更多同志的努力推動,《“十二五”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綱要》以極其精煉和明確的語句,統一了思想,指明了方向:“面對日趨強化的資源環境約束,必須增強危機意識,樹立綠色、低碳發展理念,以節能減排為重點,健全激勵與約束機制,加快構建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提高生態文明水平”。凝聚共識是漸進的過程。從共識到行動也需要時間。一打宣言不如一項有效行動。
記者:您覺得公眾在踐行綠色低碳發展過程中能夠有哪些作為?
張坤民: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盡管我們強調政府從規劃到落實中的主導作用,但離不開所有企業的主體作用,因為綠色低碳需要創新,而企業是實現有關創新的主要力量。至于每個社會成員,無論生產、生活,經濟、社會,環境、生態,都同每個人休戚相關。人們常說,群眾掌握了真理,便會有無窮的創造力。經濟轉型、低碳生活,任何有心人都可以大有作為。拿綠色消費來說,每個人都需要了解什么是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這樣就會自覺地交通選公交,汽車選擇低油耗或電動汽車;傳統節日不一定要去放鞭炮,等等。此外,也會自覺地節水節電,關注污染,監督企業,支持政府,實現全社會的低碳轉型。
要抓住低碳城市與低碳社區這個根本
記者:在您的論著中多次提到建設低碳城市與低碳社區在踐行綠色低碳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請問強調建設低碳城市與低碳社區的緣由何在?
張坤民:原因有兩個。一是現在全世界包括中國都有一半人居住在城鎮,中國的城鎮化還在加速發展。城市是人口、建筑、交通、工業、物流的集中地,是能源消耗的高度集中地區,必然也是溫室氣體排放的熱點和重點地區。國際能源機構測算認為,2006年,城市消費了全球67%的能源,城市能源活動排放的CO2占全球排放的71%。城市是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上升的重要原因。聯合國人居中心(UNHABITAT)在《全球人居報告2011》中指出,基于生產端計算的城市溫室氣體排放(直接排放)占全球總排放比例在40%~70%之間,基于消費端計算的城市溫室氣體排放(直接排放+間接排放),其比例為60%至70%。可以說,城市二氧化碳及其減排效果將直接決定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控制的成效和低碳發展的成敗。因此城市、社區低碳化意義重大。
記者:第二個原因是什么?
張坤民:城市不僅是溫室氣體排放的關鍵來源和絕對主體,本身也是全球氣候變化影響的嚴重受害者。氣候變化最不利影響很可能出現在城市,因為城市的人口、資源和基礎設施相對集中。城市又是創新與技術的熱點,也是制定解決世界性難題的地方,城市應該擔當碳減排的領導者。同時,由于城市人口密集、經濟發達,因而城市的碳減排措施會有很強的示范效應。對于中國而言,“十二五”期間,城市化率還將繼續提高,各項公共服務的完善,將造成能源、供水、交通和垃圾處理等更大的壓力。因此,建設低碳城市和低碳社區,對我國有非常現實的意義。我們在各地現場調研中看到,不少城市已經意識到這些,正在積極行動。
節能是實現低碳經濟的重要手段之一
記者:您在《低碳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挑戰與機遇》專著中,強調了節能在踐行低碳發展中的作用。請談談強調節能作用的原因。
張坤民:節能是在盡可能減少能源消耗量的前提下,取得同原來等效的經濟產出;或者是以原來等同的能源耗量,獲得更高的經濟產出。不少有識之士認為,節能是實現遏制全球氣候變暖目標最為有效而成本最低的方法,在我們的能源未來中,傳統化石能源和新能源都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而節能的核心地位卻是唯一可以確定的。這都說明了節能在低碳發展中實實在在的重要作用。
記者:有沒有相關的數據支持說明節能的作用?
張坤民:有。據國際能源結構預測,如果政策合理,會有良好效果:中國僅靠對空調、冰箱實施嚴格的能效標準,則2020年前所節約的電量將相當于一座三峽電站;由于提高能效、轉換燃料和改善經濟結構,2030年中國的一次能源需求有可能降低15%;若用燃料效率更高的汽車,2030年有可能每天削減交通用油210萬桶;旨在加強能源安全及減排二氧化碳的政策也有助于減輕局地污染,如硫化物、氮氧化物和微細顆粒物等,這對減輕霧霾具有良好的協同作用。對于中國而言,節能還是緩解資源、能源約束的現實選擇。
綠色低碳發展需要創新并采用新的衡量辦法
記者:眾所周知,盡管綠色低碳發展成為全球共識,但對于全球而言,并沒有成熟的經驗和模式可以借鑒。我們應當如何做?
張坤民:的確,走綠色低碳之路可謂前無古人,但又不得不走,那就只能奮力闖出一條新路。創新是必須的。關于創新,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教授認為,綠色發展是一條全新的道路,沒有現成模式,沒有成熟經驗,需要自主創新、科學創新。至少需要3方面創新:一是國家創新。制定發展規劃,確定發展戰略,設計綠色藍圖,指導全國綠色發展創新;二是地方創新。根據本地條件創新不同的模式,實現當地經濟、社會、環境的三大目標;三是企業創新。根據國內外市場競爭,創新綠色技術,開發綠色產品,開拓綠色市場。
記者:應當如何衡量綠色低碳模式下的經濟發展?
張坤民:如何衡量問題,聯合國20多年前就開始研究了。現在有一種比較可行的方法是核算“真實儲蓄率”,而不是看單純GDP。真實儲蓄率其實就是綠色GDP的一種表達:在傳統GDP的基礎上要扣除環境污染的損失,包括因污染使人生病、喪失勞動能力、提早死亡的經濟代價;還要扣除生態破壞的代價。這種衡量方法還在完善之中,難度在于諸如生態損失的價值有的難于直接以貨幣來衡量。這方面需要創新并試行。去年我在山西考察,驚喜地發現在傳統的產煤大省居然有一個縣搞起了綠色GDP核算。雖然剛剛開始,但意義重大。可以說,綠色低碳發展之路絕不會一帆風順,但只要我們堅定踐行科學發展觀,堅持創新探索,那么,綠色經濟一定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