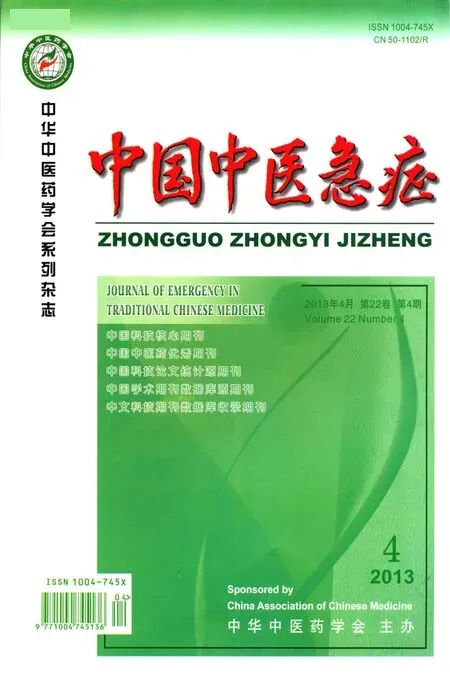《醫貫》喘論解析
丁紅生 劉 杰 陸樹萍
(浙江中醫藥大學附屬嘉興市中醫院,浙江 嘉興 314001)
趙獻可,字養葵,自號醫巫閭子,是明代研究“命門”學說卓有成就的醫家。趙氏學說立意于先天水火而尤重于命門之火,在治療上反對濫用苦寒克伐。他認為先天水火乃人生立命之本,養生、治病莫不以此理“一以貫之”,因撰書名曰《醫貫》[1]。《醫貫》是趙氏僅存于世的兩部醫著之一,較全面地闡述了作者的醫學理論、治病原則及遣方用藥,是一部集中反映其學術思想的最具價值之作[2]。《醫貫·喘論》在繼承張仲景、李東垣、朱丹溪等人學術觀點的基礎上加以發揮,著重點在于闡述虛喘致病的病機及治法。在喘論中,他首先辨別喘與短氣之不同,對于朱丹溪所云“久病是氣虛,宜補之;新病是氣實,宜瀉之”提出不同觀點,認為“喘與短氣分,則短氣是虛,喘是實,然而喘多有不足者,短氣間亦有有余者,新病亦有本虛者,不可執論”。對于外感致喘,認同張仲景的觀點;對于內傷致喘,認同李東垣的觀點,并有進一步的發揮。外感致喘的病機上,他認為“風寒暑濕所侵”,皆可致“肺氣脹滿而為喘”,治法上“真知其風寒也,則用仲景青龍湯;真知其暑也,則用白虎湯;真知其濕也,則用勝濕湯”。對于內傷致喘,分辨為陰虛致喘、陽虛致喘、七情郁結致喘。
1 陰虛致喘——壯水之主,則水升火降,而喘自定矣
前人論及喘證,一般認為屬氣有余之證。而趙氏認為“當屬火之有余,水之不足;陽之有余,陰之不足也”。對于《內經》所云諸逆沖上之火,認為“皆下焦沖任相火,出于肝腎也,故曰沖逆。腎水虛衰,相火偏勝,壯火食氣,銷鑠肺金,烏得而不喘焉?”力辨陰虛為腎中之真陰虛,非丹溪所謂陰血虛。因此治療當用六味丸加麥門冬、五味子等,壯水之主,使水升火降,喘息自定,不宜使用四物湯類加減治喘。對于腎陰虛喘證夾痰者,他認為“陰水虛故有火,有火則有痰”。對于此類痰,趙氏在《醫貫·痰論》中主張“不治痰之標,而治痰之本”,“先以六味壯水之主,復以四君或六君,補脾以制水,子母互相生克,而于治痰之道,其庶幾矣”。
2 陽虛致喘——益火之源,助元返本
對于癥見呼吸氣促,其癥似喘非喘,外見四肢厥逆,面赤煩躁,脈象兩寸浮大而散,兩尺微而無力。引《內經》曰“少陰所謂嘔咳上氣喘者,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諸陽氣浮,無所歸依,故上氣喘也”。認為此癥病機為“真元虧耗,喘出于腎氣上奔,氣不歸元”。治療主張“善治者,能求其緒,而以助元接真鎮墜之藥,俾其返本歸原,或可回生,然亦不可峻驟也。且先以八味丸、安腎丸、養正丹之類,煎人參生脈散送下,覺氣苦稍定,然后以大劑參、芪補劑,加破故紙、阿膠、牛膝等,以鎮于下;又以八味丸加河車為丸,日夜遇饑則吞服方可”。強調益火之源、助元返本。
3 郁證致喘——五郁皆能致喘,治之疏散,然不忘滋腎水
趙氏認為“木郁、火郁、土郁、金郁、水郁,皆能致喘,俱屬有余之證”。郁證致喘病機在于“七情內傷,郁而生痰”。并在《醫貫·郁病論》中認為“木郁則火亦郁,火郁則土自郁,土郁則金亦郁,金郁則水亦郁,五行相因,自然之理”。治之“予逍遙散治木郁,而諸郁皆因而愈”,可見郁證致喘治法以疏散為主。然“一服之后,繼用六味地黃加柴胡、芍藥服之,以滋腎水,俾水能生木”。并且在《醫貫·喘論》中特別指出火郁致喘“為蓄郁已久,陽氣拂遏,不能營運于表,以致身冷脈微而悶亂喘急。當此之時,不可以寒藥下之,又不可熱藥投之,惟逍遙散加茱連之類,宣散蓄熱,得汗而愈。愈后仍以六味地黃,養陰和陰方佳。”總之,趙氏郁證治療立法疏散然不忘滋命門真水。
綜觀趙獻可《醫貫·喘論》對于喘證的認識,其繼承了張仲景、李東垣等人治喘的觀點。對于喘證屬虛者,著重于從腎命水火治療。認為郁證屬實喘,疏散中仍不忘滋命門真水,可見其重視腎命的觀點。《醫貫·喘論》豐富了中醫學對內傷致喘的認識,特別是虛喘的病機治法,影響了后世醫家對于喘證的認識。其后清代葉天士提出“在肺為實,在腎為虛”,來說明喘證肺腎兩臟的病機重點。林佩琴在《類證治裁·喘癥》中提出“喘由外感者治肺,有內傷者治腎”的治療原則。這些觀點對于指導喘證的臨床治療具有重要意義。當然,趙氏為了糾正當時寒涼時弊,治療上著意于命門水火,以六味、八味統治諸癥,亦不無偏頗。今天臨癥時仍需詳查喘之虛實新久、外感內傷,辨證論治,不可拘泥于一家之言。
[1]任應秋.中醫各家學說[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116.
[2]劉玉瑋.趙獻可《醫貫》醫學理論特色辨析[J].中醫文獻雜志,200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