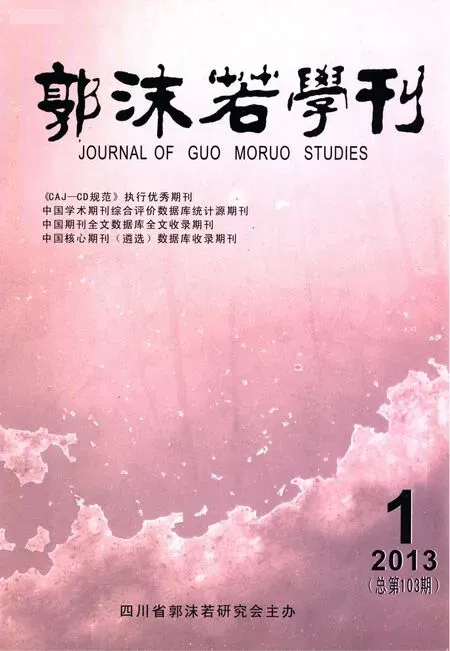關于《南無·鄒李聞陶》
王 靜
(中國社會科學院 郭沫若紀念館,北京 100009)
新中國成立之前,郭沫若與中國民主同盟的交往密切,與其中多位盟員保持了深厚的友誼。在鄒韜奮和陶行知分別于1944年、1946年因病逝世后,郭沫若曾撰文紀念。1946年李公樸和聞一多遇刺后,他寫作了多篇文章聲討暴行。在1948年7月16日出版的《光明報》新1卷第10期上,郭沫若還曾發表一篇題為《南無·鄒李聞陶》的文章,來紀念以上四位先生,現錄于下:
人是很脆弱的。特別處在狂風暴雨的時代,一個人就像一株孤立無輔的樹木一樣,容易拔倒。這樹木不怕就是磐磐大木,也有和根拔倒的時候。并不是風雨的狂暴真是無可抵抗,而是這樹木太孤立了。這樹木并不是倒于風雨的狂暴而是倒于自己的孤立。
我這一寫起頭,讀者或許會驚訝,以為我感傷得有點脫軌,而且有點輕侮鄒李聞陶四先生。好像在說,四先生太脆弱了,太孤立了,那么容易被拔倒。而且風雨無罪,狂暴無罪,脆弱其罪,孤立其罪,這簡直有點近于反動了。
不錯,我自己一面寫,一面就在擔心:會引起性急的朋友們這樣的憂慮。我應該趕快把我的本意說出來。我認為鄒李聞陶四先生是并沒有倒的,他們是永遠存在。他們不僅不脆弱,而且超度的堅強。他們不僅不孤立,而且永遠不愿讓明友們孤立。風雨的狂暴真把他們拔倒了嗎?那才是錯覺呢!
古人已經說過:“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今天我們更可以說,生理上的死(即所謂“身死”)并不能算是死,要精神上的死(即所謂“心死”)才算是真正的死了。有的人,生理上并沒有死,而精神早墮落了,或者成為走肉行尸,或者成為兇神惡煞,你說他是活著的嗎?
但像四先生這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雖然或死于耳癌,或死于無聲手槍,或死于腦充血,但我們能夠說他們是死了嗎?不!他們并沒有死,永遠也不會死!像四先生這樣的人,他們是超過了死亡線,而達到了永生的疆域了。
我們要問:四先生何以能夠做到這樣?這應該是最基本的一問:因為我們如要學習四先生,我們就要探得了他們的精神根源,向那根源處學習才有著落。他們的精神根源是在什么地方呢?據我看來,可歸納成重要的三點。
一、緊緊依靠人民,毫無保留地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替人民大眾服務。
二、發揮超度的自我犧牲的精神,看輕了生死,因而也看輕一切了富貴利祿,暴力淫威,貧困艱難,超過了一切的誘惑和脅迫。
三、知道了不算本事,要身體力行,不作空頭的人民八股家,不作偽善的口頭先鋒隊。表里通達,不作陰一套而陽一套的兩面人。
這樣的人是絕對不會孤立的,他雖然泯卻了自我,但他是以人民大眾為自我。誰能夠把人民大眾消滅?任何狂烈的風暴,不曾聽見說過能拔倒一座山林。
靠著一個人或少數人的力量,自以為了不起的人并不一定了不起,自以為可以保險的人并不一定可以保險,自以為頂天立地而獨立,事實上是跼天蹐地而孤立。
希特拉、墨索里尼、東條英機的例子可以不用舉了,像托羅茨基在十月革命的當年,與列寧齊名,煊赫得夠可觀了,然而后來怎樣了呢?
鄭孝胥、汪精衛、周作人的例子可以不用舉了,胡適被人稱為“圣人”,他自己也當仁不讓是以“今圣”自居的。他的準備也未嘗不周到,學生時代的《留學日記》已經出版行世了,他每天還在用毛筆寫著日記,準備在生前或死后好用珂羅版印行。那些太約也就是“行成于內而名立于后世”的圣人之言了。他今天雖然還沒有死,但我敢于保證,他的確已經成了“圣人”了。
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都曾經做過共產黨的領袖。當了共產黨,當了共產黨的領袖,可謂進步了,進步到極端了,然而也并不能保證他們的將來。
人的確是很脆弱的,在沒有把死亡線通過之前,地位愈高,名聲愈大,實在是危險愈多。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倒老實是古人的經驗之談呵。
自己就是一個最大的陷穽,看不破,丟不下,自己就會把自己打倒。一個人的倒下去,自然我是說精神上倒下去,的確不是由于外在的風暴,而是由于自己的脆弱。看不破,丟不下,自己的包袱背得太多也就是自倒的原因,更不必等到風暴。
名氣夠大了,還要貪圖無實的名聲。財產夠多了,卻不肯率先的博施濟眾。一點芝麻大的虛榮都不肯讓人,一點芝麻大的小利都不肯放棄。這樣空頭的革命家,不怕今天就處在“領袖”的地位,即所謂磐磐大木,事實上也是孤立無輔的,頂頂危險的。
人誰不為自己打算呢?就請朝長遠處為自己打算吧。要想自己偉大,就請把自己的小我化為人民,那就再偉大也沒有了。要想自己富有,就請把自己的財產化為人民的財產,那就再富有也沒有了。這樣的財產會被永遠保持下去,絕不損失。要想自己的聲聞不滅吧,最好讓人民寫在他們的心里。
當然最好不要為自己打算。誰夠為人民丟掉自己的,自己也就有了。誰能夠為人民看小自己的,自己也就大了。人民是絕不會辜負為大眾而犧牲自我者的,請看,鄒李聞陶不正是我們的好榜樣嗎?
我愿意學習鄒李聞陶,切實使自己落根在人民的土壤當中。我愿意把鄒李聞陶作為我的四大精神支柱。我自己也就是一個脆弱者,在我未超過死亡線之前,我自己究竟是成為鄭汪周胡,還是鄒李聞陶,我自己也不敢保證。
我自己很愿意走自力本愿的路,努力策勵自己,但也不敢輕視他力本愿的路,禮請一些精神不死者來支撐著自己。我愿意學和尚念佛,遇著有什么誘惑威逼或自己看不破,丟不下的時候,便這樣連連的念,連連的念:
南無·鄒李聞陶!南無·鄒李聞陶!南無·鄒李聞陶!南無·鄒李聞陶!南無·鄒李聞陶!南無·鄒李聞陶!……(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
郭沫若與《光明報》有著不小的聯系。他于1947年11月16日由滬抵港,1948年3月《光明報》復刊后,他曾在新1卷第1期上發表了《駁胡適〈國際形勢里的兩個問題〉》,而后又作《屈原·蘇武·陰慶》發表于1948年3月15日《光明報》新1卷第2期,以及《歷史是進化的》發表于1948年4月17日《光明報》新1卷第4期。
上面這篇佚文是該期《光明報》“悼念本盟先烈李聞陶杜特輯”中的六篇文章之一,其中“杜”指杜斌丞,他于1947年3月20日在西安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同年10月7日就義。《光明報》該期社論指出,這四位先生或直接倒于反動派當局的槍口下,或間接死于其恐怖與威脅之下,此時的任務是“展開新政協運動,擴大并鞏固民主的統一戰線,與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與一切社會先進,緊緊的攜手,共同為結束獨裁統治,實現人民的民主新中國”,只要“承繼李,聞,陶,杜諸先烈生前‘和廣大人民站在一起’的光榮傳統,堅定不移,抬頭樂干,我們一定能夠沖破黎明前的‘黑暗’,取得最后勝利”,作為告慰諸先烈的奠儀。
1946年2月10日較場口血案發生時,郭沫若與李公樸同在“慶祝政協成功大會”會場,共同面對特務的襲擊,可謂擁有戰斗之誼。而郭沫若與聞一多的友誼也頗深,李聞遇刺后他將聲討與哀悼訴諸筆端,寫出了多篇文章,學界對它們的研究可觀,在此不作多述。
郭沫若與陶行知亦是共同戰斗和患難的朋友,陶行知去世后,他寫作了《祭陶行知》《痛失人師》《陶行知挽歌》《讀了陶行知最后一封信》《記不全的一首陶詩》《陶行知先生最值得學習的地方》,1947年作《行知詩歌集》校后記,稱自己將詩集“前后讀了兩遍”,并對其做了校正。他還曾作一曲詞《大哉陶子》,道“以前無陶子,以后萬億陶子”,表達了自己的尊重之情。
然而郭沫若此文所紀念的“鄒李聞陶”四先生與《光明報》特輯所紀念的先烈并不完全相符,他并未提及杜斌丞,而是加入了鄒韜奮。這或有兩個原因:其一,“鄒李聞陶”作為一個整體而被紀念已有先例,《光明報》1947年7月19日新22號曾作“鄒李聞陶四先烈紀念特輯”,郭沫若將之一起紀念并不出奇;其二,更直接的原因可能是,郭沫若與鄒韜奮有所交往,情之所至自然成文。
鄒韜奮病逝后,1944年10月1日重慶舉辦“鄒韜奮先生追悼大會”,郭沫若為主祭人之一,在會上發表了悼詞。1947年,他在《韜奮先生印象》一文中回憶了與鄒韜奮在1937年11月27日的相識,當時他們一起坐船從上海撤退。這次“邂逅”給郭沫若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在他心目中鄒韜奮“始終顯得是一位青年。不僅他的精神是那么年青,就是他的面貌、風度,也總是那么年青。”他提到二人在船上的談話:“在開船后,韜奮先生和我在二層的甲板上品排著走來走去,一面走一面談,談了將近有一個鐘頭的光景。”盡管后來二人同在武漢,后又在重慶聚會過,這“同韜奮先生最親密地談話的第一次,而且也是唯一的一次”的深談,“留在我的腦里最深”。1944年郭沫若為鄒韜奮作一挽聯:“瀛談百代傳鄒子,信史千秋哭賈生”,其中的“瀛談”便指這次初遇之談。
而杜斌丞的革命活動主要集中在陜西,郭沫若在實際中與之并無交往,僅在其回憶錄《洪波曲》中提及一次:“他(侯外廬)說,他很感謝當時做著省政府秘書長而今已被反動派陷害了的杜斌丞,是杜斌丞得到消息勸他走開的,而且還照顧到了他的路費”,這僅有的一句還是轉述侯外廬的話。
這篇文章的內容也很有特點。首先,此文將四先生視為一個統一的精神體,他們達到的一致境界是“超過了死亡線,而達到了永生的疆域”。郭沫若寫作分別紀念各人的文章時,對逝者的回憶是非常細節的,其描寫是具體的,歌頌是熱烈的。而《南無·鄒李聞陶》出于共同紀念的目的,則沒有任何回憶,它所紀念的是一種先烈共同具有的精神。
第二,此文是一篇富有哲理和教育意義的文章。它以“人是脆弱的”為開始,進而稱人是孤立的、人的肉體會滅亡,但四位先生“發揮超度的自我犧牲的精神,看輕了生死”,“毫無保留地做有益于人民的事”,因而不孤立,其精神亦不會滅亡。而后又道:“人的確是很脆弱的”,“自己就是一個最大的陷穽,看不破,丟不下,自己就會把自己打倒”,“人誰不為自己打算呢?”但他認為若是以某種精神來激勵自己,就能夠看破丟下。縱觀1948年郭沫若所作的文章,或為民主而高呼,或在學術上有所建樹,面對反動暴行,他曾寫道:“是浪頭打巖,不是巖頭打浪”,并引用了蘇聯電影《宣誓》中的語句:“我們是屹立在狂濤惡浪中的懸巖,暴風雨不斷地來打擊我們,可是懸巖從不曾被暴風雨打倒過。”表達出一種堅毅剛強的抗爭精神,而在《南無·鄒李聞陶》中,號召人們學習四先生的文句卻是平靜但能深入人心的。
第三,此文還對自我做了檢視,他說“我自己也就是一個脆弱者,在我未超過死亡線之前,我自己究竟是成為鄭汪周胡,還是鄒李聞陶,我自己也不敢保證”,這使得文章更加深刻誠懇。
值得一提的是,在1949年7月15日舉行的民盟殉難烈士紀念會上,郭沫若做了講話,《人民日報》報道稱:“他指出先烈們是超過了個人的死……在全國就要勝利的時候,我們應該感到這是光榮的日子。郭先生說,前年在上海,去年在香港,他很沉痛的流出了滾熱的眼淚。可是今年我們要拿積極進取的精神,自我犧牲,為人民服務,我們沒有了悲痛。郭先生接著說明,人究竟是有弱點的,犧牲自我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情。套上了自私自利的超度的顯微鏡就會把原是渺小的個人看得比宇宙還要大,把一個人看得比四萬萬七千萬還要多。他要求今后大家要學習先烈們的榜樣,把自我看得小一點,再小一點,以便好好地為人民服務”。其中提到了香港,也講到人是脆弱的,因此要放下甚至犧牲自我,可以說與《南無·鄒李聞陶》一文的中心是一脈相承的。


注釋:
①疑似應為“朋友們”。
②疑似應為“看輕了一切”。
③疑似應為“大約”。
④疑似脫落一“能”字。
⑤曲譜《大哉陶子》,郭沫若作詞,《陶行知歌曲集》,陶行知研究會1992年編印,轉引自《重慶陶研文史》,2006年第4期。
[1]含悲忍淚,后繼前仆——敬悼本盟先烈李、聞、陶、杜諸先生[N].光明報,新1卷第10期(1948年7月16日).
[2]郭沫若.《行知詩歌集》校后記[A].行知詩歌集[M].上海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4月.
[3]郭沫若.韜奮先生印象[J].世界知識,第16卷第2期(1947年7月12日).
[4]郭沫若.洪波曲第9章·反推進[A].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5]郭沫若.浪與巖頭[N].香港《華商報》,1948-04-01.
[6]民盟殉難烈士紀念日 隆重紀念李聞諸先烈 李維漢李濟深等均往參加[N].人民日報,1949-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