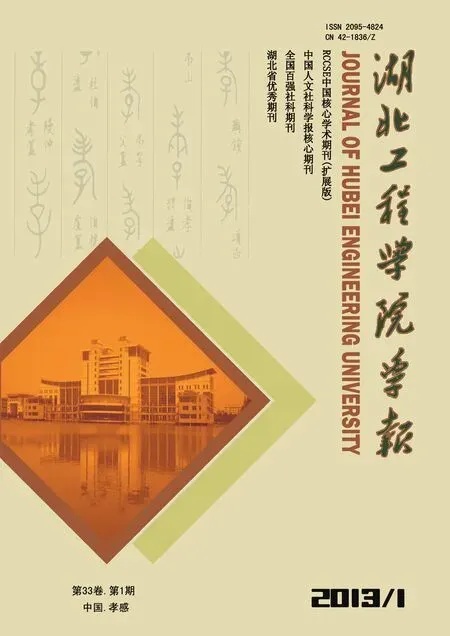上博簡孔子言論修辭初探
常佩雨
(中國科學院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簡稱“上博簡”),是20世紀末出土文獻的重要收獲。這批文獻的出土發表,為研究戰國中期前后的散文創作,提供了可以信據的新材料。陳桐生先生近期提出“七十子后學散文”(即孔子師徒的文章)的概念[1],對于研究上博簡等出土文獻,頗具參考意義。陳氏將“七十子后學散文”中七十子筆錄孔子言行的內容分作四類:一是孔子對眾弟子口述禮儀和闡述禮義;二是孔子答弟子問;三是孔子應對時人;四是孔子語錄與孔門逸事。[注]陳氏將七十子筆錄孔子言行的內容大致分為四類:一是孔子對眾弟子口述禮儀和闡述禮義,這一類內容為七十子所共記。今本《儀禮》、大小戴《禮記》中記載禮儀的篇章以及上博簡《昔者君老》、《內豊(禮)》等文章,絕大部分為孔子所述七十子所記。二是孔子答弟子問,這一類內容多由請教的弟子記載。如《大戴禮記·五帝德》出于宰予,《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上博簡《相邦之道》出于子貢,《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出于子張,《大戴禮記·主言》、《禮記·曾子問》出于曾參,《禮記·禮運》出于子游,《禮記孔子閑居》(上博簡《民之父母》與之內容略同)出于子夏,上博簡《中(仲)弓》出于仲弓,上博簡《子羔》出于子羔,上博簡《君子為禮》出于顏回。上博簡《弟子問》雜錄孔子與宰予、顏回對話以及顏回與子路、子羽與子貢的對答,可能是集纂眾多弟子記錄材料而編成的。三是孔子應對時人,這一類內容多為從游的親歷弟子所記,而未署記錄者姓名。文章多見于大小戴《禮記》、《論語》和上博簡,如《大戴禮記》中的《哀公問五義》以及被稱為“孔子三朝記”的一組文章:《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閑》,《禮記》中的《哀公問》(與《大戴禮記·哀公問于孔子》內容相同)、《儒行》,上博簡《魯邦大旱》、《季庚(康)子問于孔子》等。四是孔子語錄及孔門逸事,這一類文章的原始材料當為孔門眾弟子所記,后由某位孔門后學集纂而成。如《禮記·檀弓》上下篇中記載的孔子師徒幾十個禮學故事,大小戴《禮記》中那些只有“子曰”、“孔子曰”而未出現弟子姓名的篇章(見陳桐生《七十子后學散文研究》,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64-165頁)。本文討論的“上博簡孔子言論”,大體屬于陳氏所劃分的第二、三類中的部分文獻,即上博簡所保存的,孔子答弟子問及孔子應對時人的文章(語言標志是“孔子曰”、“子曰”、“夫子曰”、“聞之曰”等),包括以下各篇:上博簡(一)《孔子詩論》、《緇衣》,上博簡(二)《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從政》,上博簡(三)《中(仲)弓》,上博簡(四)《相邦之道》,上博簡(五)《季庚(康)子問于孔子》、《君子為禮》、《弟子問》,上博簡(六)《孔子見季桓子》,上博簡(八)《顏淵問于孔子》,等等。
上博簡保存的孔子言論,具有多方面的文學價值。現僅對上博簡孔子言論的修辭使用(包括比喻、夸張、對偶、排比、反詰、重言、警句等典型修辭手法)試作論述,以就教于專家學者。
《易·系辭上·乾》云:“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這里把修辭看作是建功立業的基本手段,認為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2]言辭與國家之亂息息相關。先秦人們強調“慎言”,如《詩·小雅·巷伯》云:“慎而言也。”孔子也強調“慎于言”(《論語·學而》),認為“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子路》)。然而,“慎言”并非反對修辭。上博簡孔子言論雖為儒家學術論文,卻隨處可見對于各種修辭手法的嫻熟運用。
一、多種比喻交相輝映
比喻是上博簡孔子言論文獻常用的修辭方式,所用比喻新奇生動,形象貼切,不落俗套,充分表現了孔子及其后學駕馭語言的嫻熟技能。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下》云,戰國時人的文章“長于諷喻”、“深于比興”。比喻包括明喻和暗喻。明喻即本體、喻體皆出現于言辭中,且兩體界限清晰,中間用“象”、“如”、“若”連接;暗喻即“甲是乙”的比喻形式,也即是借助附加、并列、同位等形式把本體、喻體融合在一起,使兩體的關系更為密切。如:
(1)(孔子)曰:詩其猶平門。(上博簡一《孔子詩論》)[3][4]542
(2)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索,其出如[紼]。”(上博簡一《緇衣》)[4]546
將《詩》直接比作可規范其他詩歌的四方之門,將王言比作細絲與大繩,顯然是明喻(后者還帶有對偶與對比的意味)。
(3)子貢曰:“否也。吾子若重名其與?若夫正刑與德,以事上天,此是哉!若夫毋愛珪璧幣帛于山川,毋乃不可。夫山,石以為膚,木以為民,如天不雨,石將焦,木將死,其欲雨,或甚于我,或必待吾名(禜)乎?夫川,水以為膚,魚以為民,如天不雨,水將涸,魚將死,其欲雨,或甚于我,或必待乎名(禜)乎?”孔子曰:“于乎!……公豈不飽粱食肉哉也!無如庶民何?”(上博簡二《魯邦大旱》)[4]553
(4)仲尼:“山有崩,川有竭,日月星辰猶差,民亡不有過。賢者毋自惰也。昔三代之明王,有四海之內,猶來(賚)。”(上博簡三《中(仲)弓》)[4]563
例3為暗喻,例4則帶有類比的意味。比喻使得抽象的事理闡釋得清晰可解,增強了論說的力量。
二、夸張揚厲壯彩增色
夸張亦稱“增語”、“增文”、“夸飾”、“豪句”等。劉勰《文心雕龍·夸飾》云:“壯辭可得喻其真。”[5]徐正英先生譯為“夸大的文辭就可以顯示它的真相”。是說為了很好地表達事物,作者要故意作言過其實的描寫與渲染,給人以深刻印象。夸張是一種積極的修飾方式,在古代詩歌中運用普遍,上博簡孔子言論中亦常使用。如:
(5)孔子曰:“三無乎,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君子以此橫于天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視也,而得氣塞于四海矣,此之謂三無。”(上博簡二《民之父母》)[4]552
(6)顏淵退,數日不出,[門人/弟子問]之曰:“吾子何其瘠也?”曰:“然,吾親聞言于夫子,欲行之不能,欲去之不可,吾是以瘠也。”(上博簡五《君子為禮》)[4]580
此兩節為夸張修辭,前者還是排比;后者簡文記載顏淵因聽到老師教誨而數日不出,竟因苦悶不能履行老師所講善言而形體瘦瘠,顯然采用了夸張的修辭,來表明孔子教誨對弟子影響之巨大,及作為孔門高弟的顏淵履行師道之懇切篤至。
三、對偶工整和諧流暢
對偶即以結構相同、字數相等、意義相關的兩個詞組或句子并列在一起,通過勻稱的句式,表達凝練的內容,充分顯示句式整齊的勻稱美與韻律的和諧美,便于讀者感知、聯想、記憶。對偶是語言成熟的表現。
上博簡孔子言論使用對偶時,從形式看,包括句子的對偶、句中成分對偶和連續對偶等;從內容即語義關系看,包括正對(起句和對句意思相同或相近的對偶,語義互為補充)、反對(起句和對句意思相反或相對)兩種。如:
(7)聞之曰:“侃敏而恭遜,教之勸也;溫良而忠敬,仁之宗也。”(上博簡二《從政乙》)[4]554
(9)子曰:“茍有車,必見其轍。茍有衣,必[見其敝。人茍有言,必聞其聲。茍有行]”必見其成。(上博簡一《緇衣》)[4]546
(10)聞之曰:“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不行。”(上博簡二《從政甲》)[4]554
此四節皆為對偶,首節又引用了格言。
(11)夫行,順柔之一日,一日以善立,所學皆終;一日以不善立,所學皆惡。可不慎乎?”(上博簡三《中(仲)弓》)[4]564
(12)行〈子〉人子羽問於子贛(貢)曰:“仲尼與吾子產孰賢?”子贛(貢)曰:“夫子治十室之邑亦樂,治萬室之邦亦樂,然則壴(矣)”“與禹孰賢?”子贛(貢)曰:“禹治天下之川非以為己名,夫子治詩書□亦以己名,然則賢于禹也。”“與舜……孰賢?”子贛(貢)曰:“舜君天下”(上博簡五《君子為禮》)[4]580
此兩節分別為復句對偶和句內成分對偶。可以看出,對偶的成功使用,使得上博簡孔子言論文字整齊勻稱、節奏鮮明、氣勢充沛、感情激昂、音節鏗鏘、變化多端、表意豐富。這些神奇美妙的對偶句式,是先秦散文形式美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后世韻散結合、多用駢語的散文形式開創了先河。
四、排比使用語勢宏大
排比即連續使用三個或三個以上結構相同、意義相關、語氣一致的句子或句子成分來敘述事件、闡明道理、表達感情的修辭方法。先秦散文有時比喻中包含著排比,有時對偶句中也包含著排比。這種修辭方式極有助于增強文章的論說力量。如:
(13)(聞之曰:)毋暴,毋虐,毋賊,毋貪。不修不武,謂之必成則暴;不教而殺則虐;命無時,事必有期,則賊;為利枉(上博簡二《從政甲》)[4]554
(14)孔子曰:“五至乎,物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君子以正,此之謂五至。”(上博簡二《民之父母》)[4]552

此三節皆為排比。末節每三句構成一組,連續五組一氣呵成,文氣洶涌,如飛瀑直下,氣勢鷹揚,排比效果尤為突出,有力增強了論證力量。
五、強烈反詰表意鮮明
反詰又稱反問,即以反問句的形式來表達思想的一種修辭方式。反詰構成方式有二:一是否定句(謂語前有否定詞)加反問語氣,一是肯定句(謂語前無否定詞)加反問語氣。前者意在肯定,后者意在否定。反詰手法有助于人們更為有力地強調某些觀點,更清楚地說明某種道理,更充分地表達某種感情,從而使語言表達富于變化,豐富多彩,大大增加文章的氣勢與感染力。如:
(16)子曰:“唯君子能好其匹,小人豈能好其匹?”(上博簡一《緇衣》)[4]546
此兩節是反詰修辭,前者同時又包含對比意味在內,表現力極強。
反詰修辭是無疑而問,寓答于問。對反詰的恰當使用,往往能夠吸引讀者(首先是作為聽眾的孔門弟子)的注意力,大大增強先秦散文的氣勢與感染力。
六、重言格言踵事增華
重言即在一句話或一段話中,多次使用某個或某些詞語,具有鮮明的特色和強烈的表達效果。重言的語句內容層層遞進,說理步步深入,能夠深刻揭示事物之間內部的邏輯聯系,闡述道理清晰而有感染力。格言即言簡意賅、富于哲理性與啟示性的簡短語句。格言警句多抑揚頓挫、朗朗上口,節奏明快、音韻和諧,思想深刻豐富,表達生動傳神,韻致含蓄雋永,許多還流傳至今,啟人深思。
上博簡孔子言論中使用的重言如:
為了強調延陵季子(季札)為知禮之人,為天所助,孔子使用了重言“前(延)陵季子,亓(其)天民也(乎)”,并帶有反詰語氣。上博簡重言語句的使用,使得散文內容層層遞進,說理步步深入,深刻揭示了事物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說理、達意明白且具有感染力。上博簡孔子言論中引用格言警句者,如:
(19)(孔子曰:)是故君子玉其言而展其行,敬成其德以臨民,民望其道而服焉。此之謂仁之以德。且管仲有言曰:“君子恭則遂,驕則侮。備言多難。”(上博簡五《季庚(康)子問于孔子》)[4]578
(20)孔子曰:丘聞之孟者吳曰:“夫著書,以書君子之德也。”(上博簡五《季庚(康)子問于孔子》)[4]578
(21)(孔子曰:)丘也聞臧文仲有言曰:“君子強則遺,威則民不道……”(上博簡五《季庚(康)子問于孔子》)[4]578
此三節為引用前賢管仲、孟者吳、臧文仲的名言警句進行說理,增強了論證力量。《論語》中孔子明白引用前代之“言”者至少有6處[注]分別是: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子路》)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子路》)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子路》)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筮。”(《子路》)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雍也》)見:俞志慧《古語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種背景與資源》,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15-216頁。, 均與上下文融合無間。可見,儒家歷來重視先代重言、格言、警句等語言資料的運用與傳播,其言語活動,也不斷創造出新的重言、格言、警句來,從而促進文學語言的發展。
要之,上博簡孔子言論大量使用比喻、夸張、對偶、排比、反詰、重言、警句等修辭手段,并常見綜合使用多種修辭手法的例子,從而大大增強了文章的表現力與說服力,也提升了先秦散文的藝術品格。上博簡孔子言論,已經是較為成熟的散文作品。
[參 考 文 獻]
[1] 陳桐生.七十子后學散文研究[M].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208.
[2] 阮元.十三經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79.
[3] 黃懷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解義[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276.
[4] 劉信芳.楚簡帛通假匯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5] 劉勰.文心雕龍[M].徐正英,羅家湘,注譯.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349.
[6]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 李守奎,曲冰,孫偉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775-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