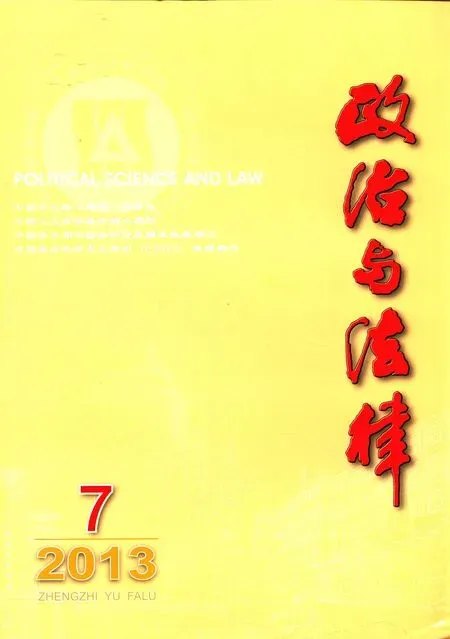論合規藥品致害之國家責任*——基于合規藥品致害的民事和行政救濟的局限之展開
杜儀方
(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浙江杭州3100023)
2013年新年伊始,新華每日電訊以《找病的馬兜鈴科草藥》為題刊發方舟子博文《一大類可怕的草藥》,直揭以馬兜鈴科草藥為原料所制藥品的嚴重危害,將本已沉寂的龍膽瀉肝丸事件再次推入公眾視野。1龍膽瀉肝丸事件源于2003年2月新華社記者朱玉的報道《龍膽瀉肝丸——清火良藥還是“致病”根源》。該報道證實,傳統中藥龍膽瀉肝丸即使正常服用也會造成腎損害。后經驗證,《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以下簡稱《藥典》)記載的龍膽瀉肝丸配料中的“關木通”含有馬兜鈴酸,而馬兜鈴酸可導致腎病。2003年4月4日,國家藥品監管局正式取消關木通藥用標準。2003年3月起,有超過170多名受害患者將作為龍膽瀉肝丸生產商之一的同仁堂告上法庭,要求給予損害賠償。而同仁堂認為,藥廠是按照藥典合理合法生產的,其已對消費者盡到法定的責任和義務,國家藥典委員會應該承擔責任。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相關訴訟最終都敗訴、被法院駁回或不予受理。2
透過龍膽瀉肝丸事件不難發現,上述藥害的產生并非由于傳統意義上的合格藥物的副作用所導致。一方面,藥品完全符合藥品標準的相關規定,但另一方面,藥品本身的缺陷卻又確實存在。該情形明顯有別于藥品因未被發現的內在缺陷或者因患者的特異體質而產生的藥品副作用,因此無法適用一般情形下藥品不良反應的損害賠償模式。3為表述方便,本文暫且用“合規藥害”指代這一類藥品損害。值得重視的是,龍膽瀉肝丸事件也并非是極小概率事件。在《藥典》的修訂過程中,有相當一部分藥品標準得到了修改。若換個角度,我們可以認為,新標準的制定至少可以說明原藥典中所記載的標準存在一定的問題或者改良空間。從這一層面而言,龍膽瀉肝丸的悲劇絕不會成為偶然事件。從公共政策或社會正義的角度觀之,受損害者獲得補償,應是社會追求的正面價值。在此種情況下,如何能兼顧損害填補與經濟效率的需求,一直是整個損害賠償法制所追求的機能。那么,問題就轉換為,對于上述合規藥害的損害應如何彌補,誰又能為此負責?
一、合規藥害民事救濟之可能性
當出現藥物損害后,尋求藥物制造者的責任無疑是相對最為便利的救濟途徑。藥物制造者是藥物產銷流程之源頭,從理論上而言其與藥害的法律關系最為密切;同時,藥品制造者往往財力相對雄厚,從保障相對人的角度出發也應將其作為求償對象。4因此,民事侵權責任似乎就成為最為直接和便利的救濟方式。但是,事實果真如此簡單嗎?
(一)規范法學的進路
首先需要尋求民事救濟在規范層面的依據。《藥品管理法》第93條規定:“藥品的生產企業、經營企業、醫療機構違反本法規定,給藥品使用者造成損害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據此,藥品致害賠償責任必須以違反規定為條件。而就藥品質量本身而言,可適用《侵權責任法》第41條和第59條,即如果藥品由于存在缺陷而致害,那么藥品生產者將責無旁貸。問題是,在何種情況下,可以認定為藥品存在缺陷,換言之,究竟何為藥品缺陷呢?《產品質量法》第46條規定:“本法所稱缺陷,是指產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財產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險;產品有保障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是指不符合該標準。”而在藥品領域,《藥品管理法》第32條規定:“藥品必須符合國家藥品標準,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和藥品標準為國家藥品標準。”該法第48條規定:“當藥品所含成份與國家藥品標準規定的成份不符的為假藥。”地方立法層面,以《藥品管理法》及該法的實施條例為基礎,各省、市都出臺了相應的地方性法規,但是基本沒有對藥品缺陷作出更為詳細的規定。由此,從立法角度而言,所謂缺陷,就是違反各級藥品監督部門所制定的藥品標準,而合規藥害顯然不在此列。
通過上述法規梳理,我們只能夠得出以下階段性結論:當藥品不符合國家藥品標準時,可以被認定為缺陷產品,生產經營者的侵權責任成立。但當藥品生產者遵守藥品標準時,是否可以以不存在缺陷作為抗辯事由從而不承擔侵權責任,現行法律卻沒有給出答案。當立法失語,留給學界的任務就是理論先行。此時的研究話題可被界定為:對于合規藥品造成的損害,是否應追究民事侵權責任?
(二)合規侵權致害的理論維度
1.概述
對于合規侵權致害問題,不少學者已經展開了一系列相對成熟的研究。5為尋求理論與實踐的最佳契合點,現有對于合規致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環境侵權領域,將研究重點置于獲取排污許可或者符合污染排放標準的行為而導致的污染損害。在以環境領域為例證的合規侵權研究中,相關的觀點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觀點認為合規即可以免除民事侵權責任,這一觀點的依據是199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該法第61條第1款規定:“受到環境噪聲污染危害的單位和個人,有權要求加害人排除危害;造成損失的,依法賠償損失。”該法第2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環境噪聲污染,是指所產生的環境噪聲超過國家規定的環境噪聲排放標準,并干擾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學習的現象。”如果對上述條文進行文義解釋,則意味著環境噪聲如果符合法定的噪聲排放限度,就不構成立法意義上的環境污染,即使造成損失也無法尋求該法所規定的賠償責任。
第二類觀點是完全不考慮是否存在合規情節,認為行為人只要給他人帶來損害并由此獲得了利益,就應對該不利結果負責。其基于傳統侵權歸責原則中的“結果歸責”,出于填補損失的需要而不問原因對加害者課以責任。“事故是在追逐利益的過程中產生的,而獲得利潤就應對由此而形成的風險負責……事故的責任應當加到從事這種危險活動的人的身上”。6《侵權責任法》第65條規定的環境污染侵權責任印證了這一觀點。
第三類觀點認為當行為遵守行政機關所確立的基準,其所造成的損害雖不能免除行為者承擔賠償責任,但是應將合規情節作為是否能夠免除責任或者影響責任承擔的因素之一。此類觀點將關注重心落于規則本身,規則本身的性質將影響到責任的存否和程度。合規行為仍需承擔責任的原因主要有:規范本身不具有妥當性;規范所設定的義務不是以保護人為目的的義務;侵權行為違法性中的違法并不限于具體的法律法規,還包括權利濫用和公序良俗的違反等。當然,也有學者從公法私法分立的角度論述合規不免責的法理基礎:立法者在制定公法規范或者標準時只是從公法的角度衡量,既無暇也無力仔細考量其民事效果,對于公法規定在私法領域的具體適用,如何與私法自治的價值適度調和等問題都還未作決定。7
通過對上述觀點的比較,筆者認為,相較于前兩類觀點而言,第三類觀點顯然更為合理。將合規情節作為免除責任的必然藉口顯得過于絕對,這不僅與公法私法二元體系相矛盾,也不利于受害者權益的保護。與之相對,如果不考慮合規情節而單純從受害者角度出發,結果責任原則更能使其所受損失得到救濟,但是畢竟純粹基于受害者立場有失公允。在整體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合理分擔損失已成為當今侵權賠償制度的主流,在一定情況下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某些個體的受損對于社會整體而言可能是一種必需。正如有學者所說的“很多公共風險,無論他們有多么危險,事實上比所要消除這種風險更為安全或者有益,那么就要竭力對其成本最小化”。8這一觀點在環境污染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當環境污染如同影子一般常伴工業文明左右時,合規排污正是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點。因此,此時如一味追究合規企業的侵權責任就顯得過于苛刻。“試圖讓合規行為對其行為所造成的損害承擔侵權責任,顯然是混淆了私人風險和公共風險的界限,這樣做并不會減少風險,相反,卻可能會增加事故,導致社會福利的損失。”9但是即便如此,在出現合規侵權時也無法完全免除侵權者的民事賠償責任,合規只能作為抗辯的情節之一。按照通說,侵權行為主要構成要件為加害行為、損害結果、因果關系以及違法性和過錯,而合規情節正是當事人過錯程度的其中一種體現。
上文以環境領域為例對合規致害的論述可以概括為:拋棄完全不考慮違法與過錯要件的“結果責任”,肯定“合規”情節與侵權責任之間存在一定關系,合規并非意味著免責,合規可以作為考量注意義務的因素之一對責任的承擔產生影響。
2.藥品領域中的合規致害
在藥品侵權領域,基于與環境領域侵權類似的推演,有學者認為,制藥方無法因合規而免于承擔賠償責任。這是因為遵守藥品標準只是產品符合行政規范的根據,并不是說產品就不構成“缺陷”,因此這不能構成免除侵權責任的抗辯事由。具體原因在于,藥品標準的選取有諸多考量因素,其不能包含一切安全性能指標,并且標準往往只是給予一般性的制約,其也無法去把握和斟酌每個侵權個案所涉及的個別因素,與此同時,藥品標準制定的目的和初衷并非著眼于侵權案件的解決。對于符合標準的行為是否會引發侵權責任,需要對相關的諸多因素和利益進行綜合的衡量。10該推演似乎順理成章,但是卻忽視了基本前提,即參照領域的同一或相似性。事實上,合規行為在侵權法上并不具有一個統一的效力,而是隨著領域的不同呈現不同的效力,甚至在相同的領域中也有不同的效力。雖同屬合規致害,但與環境合規污染相比,合規藥物致害卻存在自身特性。
首先,環境領域與藥品領域的規范本身性質不同,即“規”不同。在環境領域,污染一旦被排放勢必會引發損害,而這種損害的發生卻又是工業化進程所不可避免的產物。盡管確立排污標準是試圖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尋求平衡點,但是符合排污標準只是在侵權的前提下降低損害。換言之,環境領域的排污雖以經濟發展這一公共利益為目的,但污染排放為個體帶來的損害畢竟是負面效應,而且這種損害是排污行為人可預見甚至可期待的,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污染排放的“規定”只是對于負面效應的一定程度的減輕,合規并不能改變“規”本身的負面效應。而在藥品領域,雖然時有副作用的發生,但無論是對于公眾還是個體而言,藥品的整體存在和個體適用都只是為了能夠治病救人這一正面目的,損害的發生并非藥品本身所希望達成的效果。而藥品標準更是基于規范藥品質量而產生,是對藥品正面目的的進一步加強,“規”本身當然是正面的。
其次,環境領域與藥品領域合規的方式不同,即“合”亦不同。在環境侵權領域,行政規則所制定的標準往往只是行政機關基于整體控制而確定的最低標準,違反標準將可能招致行政處罰,遵守標準則只是履行了底線的注意義務。對于排污者而言,合規排污只是第一步,在此基礎上依然要設法減少污染物所可能造成的損害后果。也就是說,此類技術標準規定的只是一個具有“可接受性”的而非“安全”的閾值,它所給予的是一個一般性的控制,它不可能也無法去把握和斟酌每個侵權個案所涉及的個別因素,因此它對于個案正義是無能為力的。11對于個案中加害行為的責任判斷不僅要考慮到合規情節,更要綜合考慮其他影響到過錯程度的注意義務。與之相對,藥品標準彰顯的則是另外一種價值。藥典所規定的藥品標準對藥品制造商而言必須遵循且不具有任何判斷余地。為確保標準的實效性,行政機關可以采取施以行政處罰、拒絕許可方式對制藥企業予以控制。例如《產品質量法》第7條對于生產不符合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產品規定了行政處罰;在藥品領域,對于生產經營不符合藥品標準的企業,可以根據《藥品管理法》吊銷其許可證。更為嚴厲的是,我國《刑法》第141條、第142條分別規定了生產銷售假藥罪、生產銷售劣藥罪。而其中“假藥”、“劣藥”的概念就是指《藥品管理法》第48條第1款規定的成份、含量或者其他不符合國家藥品標準的藥品。因此,對于藥品制造商而言,在藥品管理行政機關所確定的標準之下不存在任何判斷余地,對標準的遵守就可以認為盡到了注意義務。
基于規范法學進路,規范即技術標準分類所遵循的依據是《標準化法》第7條,根據是否需要強制執行可將技術標準分為強制性標準和推薦性標準,強制性標準必須執行,推薦性標準國家只是鼓勵企業自愿采用。《標準化法實施條例》第18條將藥品標準、環境保護的污染物排放標準和環境質量標準等明確作為強制性標準,對于標準規定的內容當事人都“必須”遵守或者“禁止”違反,而對于違反標準的行為可被施以處罰。盡管同屬必須遵守的強制性標準,但不同的強制性標準的強制程度有所不同。對于以藥品標準為代表的強制性規范,當事人必須嚴格遵守標準的規定,沒有選擇余地,即在一個加害行為中,加害者即使存在侵權行為、損害結果、因果關系三項要件,但可基于遵守精確性強行標準而排除其過錯,從而允許加害人作遵守標準的抗辯;而對于以排污標準為代表的強制性規范,當事人遵守限制性強行標準只是遵循了必要的底線條件,因標準本身具有開放性,要實現免責還需要在合規前提下,實現最佳合規,即盡到更嚴格的注意義務。在這種情況下,符合標準仍然造成對他人的損害的,“合規”就不能作為排除侵權責任的正當理由,最多只構成從輕或者減輕責任的酌情考慮因素。更進一步說,前一種強制性標準規定的是精確適用標準,后一種則僅給出了標準的強制適用范圍。正基于此,將合規藥品致害與環境污染致害置于同一合規致害的邏輯維度中就會存在局限性。在合規藥物致害中,符合規定而制造藥物致害應有別于獲得一般藥物許可而導致的藥品不良反應致害,后者可以認為行政法規規定的僅是最低標準,制藥商不可以以獲得政府許可而為抗辯。12
(三)小結
再回到龍膽瀉肝丸事件。當《藥典》或者藥品標準在成分的記載上出現了差錯時,即使制藥商已經發現木通類中藥材在其他國家早已因其對腎臟的危害而被禁止進口,或者也意識到因服用龍膽瀉肝丸而患尿毒癥的病例已經存在,但是基于對生產“假藥”的恐懼,制藥商也不可能違反相關藥品規定而擅自更改配方以實現其“注意義務”。13對藥品標準這一精確性的強制性標準而言,合規而生產藥品的制藥企業只有完全符合規定才可以免除行政甚至刑事責任,而完全符合規定也可被認為已經盡到了完全注意義務。由于在一個侵權過程中缺乏違法性要件,制藥企業的民事賠償責任無從履行。
有損害必有救濟這句古老的法諺至今流傳。然而,在合規藥品致害領域,民事賠償對損害的救濟顯然已無能為力。此時,就要將視角轉向行政救濟。既然制藥企業基于符合藥典的規定而被免除民事侵權責任,那接下來的追問就是:制定藥品標準的行政機關是否存有過錯?或者說,是否存在尋求行政賠償或補償之可能性?
二、合規藥害行政救濟之可能性
(一)行政法視野中的藥品標準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關于頒布和執行〈中國藥典〉2005年版有關事宜的通知》指出:“《中國藥典》是執行《藥品管理法》、監督檢驗藥品質量的技術法規;是我國藥品生產、經營、使用和監督管理所必須遵循的法定依據”,是“國家為保證藥品質量、保護人民用藥安全有效而制定的法典”。顯然,將《藥典》稱為“法典”是言之過甚。與其他領域的標準一樣,《藥典》是由行政機關即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組織藥典委員會制定和修訂,并由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頒布的《標準化法》所規定的強制性技術標準。我國行政法學界習慣將制定行政規范的行政活動(抽象行政行為)分為兩大類:行政機關制定法規和規章的行政立法行為和行政機關制定其他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行為。14而從藥品標準文本公布、刊登和編纂形式等來看,其確實都與《立法法》以及相關規定的要求不盡相同,從而可將其排除于法律規范之外。15因此,藥品標準應屬于其他規范性法律文件,或借鑒大陸法系的一般概念而稱之為行政規則。16
雖然其不具備法律規范的外形,但是在實踐中行政機關卻往往將藥品標準作為事實認定構成要件判斷的根據,并根據事實認定的結果作出是否給予許可甚至處罰的決定。換言之,盡管藥品標準從形式上不屬于法律規范,也不是通過法律條文來規定人們的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但是它通過設定量化的數值、指標等直接藥品配方和工藝流程,通過行政機關對技術標準的反復適用,對法律概念作出了解釋,對行政裁量權運作形成了自我拘束;同時,通過行政機關采取的一系列后續確保標準實效性的手段,從而間接地為私人規定了權利義務,對私人產生了外部法律效果。17因此,可以認為以藥典為代表的技術標準是一種具備了外部效力的行政規則,并更接近于解釋性行政規則。18
(二)合規致害的行政賠償責任
1.規范法學的進路
如上所述,可以認為藥品標準屬于行政規則。《國家賠償法》雖然并未將行政規則列為排除范圍,但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行政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6條明確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發布行政法規、規章或者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侵犯其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賠償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該規定以法院不受理的方式事實上將公民對于行政規則賠償訴訟請求排除在外。法院對于針對行政規則的行政賠償案件是慎之又慎,實踐中也尚無一例判決。19
2.理論層面的梳理
在學理上,行政規則本身一直不被認為是行政賠償的免責事項。20因此,只要能夠證明規則存在錯誤或者不當,并且行為和損害結果之間確有因果關系,那么基于行政責任基礎理論,具備了外部性的行政規則就難逃賠償責任。但是,藥典存在錯誤或不當是否就必然等同于行政機關存有違法或者過錯呢?
不可否認,藥品本身就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不安全產品,為求藥物使用之效益,常須容忍相當之危險存在。因此寄希望于國家嚴格管理以完全防止事故發生實屬不能,而國家藥物標準也只是在藥品有害性和有用性之間所尋求的一種平衡,以實現藥品整體的可控性。同時,即使已經進行了充分試驗,藥物的有害性仍可能在長期潛伏后才發作。因此,如果確實是鑒于科技水平滯后或者市場資訊不靈而產生錯誤標準,且行政機關已經就藥物有效性、安全性及公益性作了全面判斷,此時行政機關在其職權內可適用行政裁量,從而無法認定其行為存在違法或者過錯。《藥典》五年一次的修正,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因應五年里美國藥典(USP)、英國藥典(BP)以及日本藥局方(JP)等國外先進藥品標準的進展,以及我國藥品分析和檢驗技術的發展。基于這樣的原因,在一定時間段中即使藥典出現問題,也應由于缺乏違法要件而排除行政賠償。21
當然,裁量權的存在并不當然意味著行政絕對免責。基于憲法上國家對于公民的安全保障義務,當有證據表明行政機關制定標準的當時或在標準制定后已發現藥品可能產生不良反應,就可基于行政機關具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而認定其行為違法,并由此要求其承擔行政責任。從日本轟動一時的一系列亞急性脊椎視覺神經癥案中,可以探尋行政機關在藥品行政中所應擔當的角色。法官在京都的有關判決中認為,當藥品安全性可能影響到國民的生命、健康,并可能產生不可逆轉的重大后果時,如果在當時最高的學問水準和知識水平下,經過慎重縝密的審查仍然對該藥品的安全性存在疑惑時,那么該藥品的價值就存在質疑,行政機關的裁量余地就應限縮。22法官在東京的有關判決中也認為,當對于國民生命、身體、健康有損害發生的危險可能時,如果行政機關在權限內的行為可能使損害容易防止時,對于行政機關而言裁量權就應縮減,必須行使權力防止損害行為。23也就是說,只要藥品安全性存疑,即使還未出現具體的損害事例或者有確實證據證明會發生損害,也應當認定行政機關具有對該醫藥品可能產生的損害的預見能力,從而判定行政行為違法,并可依照國家賠償的相關規定要求其賠償。
3.小結
在龍膽瀉肝丸事件中,藥害事件曝光后不到2個月的時間內,國家藥監局即正式取消關木通藥用標準,并要求相關生產企業修改成藥標準。應該說,在事件爆發后國家藥監局的反應相當迅速且符合程序,不存在任何層面的拖延履行或者不履行,對此難以認定其行政不作為。同時,也沒有證據可以表明在龍膽瀉肝丸事件發生之前國家藥監局及相關行政機關能夠知曉該藥品可能產生損害或者不安全,因此缺乏行政裁量縮減中的預見可能性要件。24故在此事件中,行政機關的行政賠償責任依然無從談起。
(三)行政補償
1.規范法學的進路
我國目前的行政補償是以行政征收征用補償為基礎,以因合法行政行為而導致特別犧牲的財產或其他權利遭受損害而給予的補償制度。25我國現存法律體系中與藥品相關的行政補償制度僅存在于預防接種領域。《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第46條規定,對于合格的疫苗在實施規范接種過程中或者實施規范接種后造成受種者機體組織器官、功能損害,造成受種者死亡、嚴重殘疾或者器官組織損傷的,應當給予一次性補償,其中第一類疫苗補償費用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財政部門在預防接種工作經費中安排。也就是說,即使行政機關在疫苗接種的各個環節中都完全盡到了注意義務,而接種疫苗仍然造成公民生命或者健康受損時,就應當給予公民一定額度的行政補償。然而,非常遺憾的是我國其他藥品領域的行政補償制度尚未確立。
2.理論層面的梳理
大陸法系的補償概念是源于征收,即指對個人被迫于公益而超過可忍受的犧牲利益的填補。然而,藥害損害與一般意義上的征收損害有所不同。在通常意義下的征收補償中,法律賦予侵權行為以合法性(例如征收行為),給相對人造成的損害后果必然是法律所承認的(例如土地和房屋被征收),此情形下的補償是對該合法行為所造成的損失的填補。但是在藥害中,藥物所產生的損害后果——副作用或其他損害后果——并非法律所預設的效果,因此對藥物致害而作出的補償也并不等于從正面承認了國家對于生命的剝奪以及身體的侵害的合法性。26故傳統意義上的征收補償制度在涉及人身損害時不可適用。
在征收補償的基礎之上,大陸法系又發展了征收性質侵害補償,其是指行政機關的合法行為雖然不是公用征收,但其結果造成民眾“不正常的、非本意且非可預見的附帶效果”的特別犧牲,對此給予的補償。27例如市政府依據法定程序挖掘馬路導致沿路民房龜裂受損;合法建造與管理的市立垃圾場吸引烏鴉覓食,使得臨近稻田果園果實被啄食;合法建設并依規定管理的市立污水處理廠發出惡臭,影響臨近房屋價格等。28這類損害并非該合法行為所意欲和預見,而是附隨產生造成公民之特別犧牲,從這一角度出發,征收性質侵害補償制度確實彌補了征收補償所形成的理論漏洞。29基于上述理念,我國對強制接種疫苗致害的補償也可被歸于這一體系。
3.小結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征收補償還是征收性質補償,行政補償的產生前提無疑都是公民由于行政行為所導致的特別犧牲。也就是說,在現有行政補償的概念體系下,無論是公權力刻意為之的征收損害抑或是附隨造成的征收性質損害,至少一方面損害和公權力的行使具有直接因果關系,另一方面該損害是基于公共利益而做出的特別犧牲,給予行政補償屬應有之義。然而,在合規藥害中,藥品損害畢竟是由服用藥品這一非強制性行為所導致,公權力在這一過程中并沒有直接參與,因果關系很難證成;退一步而言,即使可以證明公權力與致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合規藥害也難以解釋為是個人為公益而作出的“犧牲”。因此,以征收為基礎的行政補償制度在此領域又難以適用。
三、救濟體系之新發展:國家衡平補償責任
通過前述分析,似乎可以看到,現有體制對合規藥害的救濟問題已然集體失語。合規藥害之所以會在規范和理論層面均救濟無門,雖是由于規則制定者對藥品的階段性認知水平不足,但主要還是因為既有責任理論對藥害領域的回應性不強。
現有責任體系產生于工業社會。在工業社會以前,社會生活中主要的損害來自自然災害,由于它來自于人類社會以外的力量,人們往往視之為命中注定,將其歸結為神明的力量或者理所當然地存在著的世界,責任追究也就無從談起。30進入工業社會后,個人命運論的責任觀遭到淘汰,考慮到民眾所遭遇的風險主要來源于私人主體之間的侵權,建立在個人自治的基礎之上的私法責任體系得以確立,強調侵權行為的過錯以及它和救濟之間的因果聯系,而這也奠定了民事侵權責任和國家賠償責任制度的基礎。
進入現代社會后,隨著社會風險的多樣化日漸擴散,傳統侵權責任中過錯和因果關系等元素在現代社會的損害中或者難以證成或者干脆泯滅不見,無法通過民事賠償獲得填補損害的情況日漸增多。合規藥品致害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在現代社會中,民眾常常會深陷轉基因食品、氣候變化、核輻射、生態災難等既具有不確定性又有高度危害的致害之中,卻無法在傳統私法責任體系中獲得救濟。現實與既有理論的不適應就形成了一項制度上的困境:由人為風險造成的顯性與潛在的破壞日趨嚴重,卻沒有人或組織需要對此負責,即有組織的不負責任。31現代社會中風險的產生原因和表現形態已超出以往任何時代中人們對于損害的想象力,其不可避免地對已有救濟體制產生沖擊。
針對現代社會所遭遇的種種現象,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于1986年提出“風險社會”理念:現代社會是一個風險四伏的社會,人類面臨著威脅其生存的由社會所制造的各種風險;對于這些風險,知識是有限的,不僅難以保證認知所有風險,且會掩蓋風險,甚至會締造風險。32由于風險的整體必然性和其產生的蝴蝶效應,傳統侵權行為法和國家責任法完全基于個人自治原理所作的設計在風險救濟中已經不能再適用。例如在藥品合規致害等一系列風險事件中,僅通過個體干預企圖符合正義通常無法滿足現實的需求,民事侵權責任在風險領域往往無法適用。而客觀現實和社會心理卻開始要求國家擴大干預的范圍,將國家的安全保障職責從關心現狀、保護或重建一個不受干擾的狀態為己任,發展到以未來為目標全面型塑社會。33在此背景下,憲法上的社會國概念開始在風險社會中延伸。基于社會國原則,國家對于人民所受若干損失,得主動給予一定之補償,藉以實現社會正義。34“為了保證社會公平,保持或者促進經濟結構的繁榮,國家還必須對社會和經濟進行全面的干預……‘排除危險’是國家的法定的和不可變更的任務,該任務通過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的供應、給付和補貼等任務得到補充。”35因此,以干預行政為中心而發展起來的現代行政法之前一直是國家干預社會和個人活動的重要工具。然而,以保障和提供個人福利為中心,確保個人體面地生活的給付行政應是現代行政這枚硬幣的另外一面,正是給付行政為個人提供了一個福利保證系統,從而可以消解個人在當今社會遇到的各種風險。36
現代意義上的衡平補償責任正是以上述社會國概念為基礎發展出來的。在傳統意義上,衡平補償多適用于犯罪被害人之補償、政治受難者之補償等,其所彌補的損失或和損害與國家機關或公務員之作為或不作為之間欠缺直接關聯性,所以一度未被列入行政補償的范疇。37然而,如果從更廣義社會連帶學說出發,事實上國家中每個人彼此之間均有一定程度的連帶關系,此連帶關系透過國家制度予以“鏈結”。在此“鏈結關系”下,偶有遭到無可避免的損害,由于關系錯綜盤結,難以追究損害之肇事責任,亦難以用“特別犧牲”予以涵攝,故應透過損失補償制度彌補這一類型損失。38因此,衡平補償的概念在風險社會逐漸擴張,具體是指因特殊事故或特別狀態,某些特定人無可避免地成為受害者,國家基于社會正義的理性,對遭受到特別人為或制度性災難的人,予以補償。39與征收征用補償、征收性質補償相比,衡平補償針對的是人民所受的損失并未達到特別犧牲的程度(往往是受損失的人數眾多,不屬于個別情況),或者與公權力之間欠缺直接而緊密的關聯,毋寧是經過較長時間的累積或較為間接的關聯而形成的。當然也有學者認為,此時國家所承擔的責任似乎已經偏離了原有行政補償的內涵,其不僅不再注目于個別公權力的行使,更以廣義的危險狀態為基礎,因此同時具備了行政補償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性質。40但是無論如何,衡平補償作為國家責任的重要補充形式已經毋容置疑。
在此制度體系下,不存在行政違法或者過錯的合規藥害救濟就可被納入到衡平補償體系之中。我國臺灣地區2000年頒布的“藥害救濟法”第4條規定:“因正當使用合法藥物所生藥害,得依本法規定請求救濟。”我國臺灣地區也有學者明確將藥害補償列為戰爭補償和刑事被害人補償以外的第三種衡平補償的類型。41在我國,雖然在立法中不存在衡平補償概念,也并未建立起刑事被害人補償體制,但是在具體領域,衡平補償的規定也不乏實例,其集中體現在生態資源等領域的補償。42在未來立法上建立藥害尤其是合規藥害之行政補償制度也可期待。
四、結語:尋找風險社會下的救濟法理
為實現合規藥品致害的損害救濟,應在立法體系的建構方面完善對私法和公法相關規定的協調,并與此同時推動藥品損害救濟理論研究的發展,具體而言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效仿我國臺灣地區“藥害管理法”的相關規定,并參照我國《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的立法模式,在《藥品管理法》中增加由藥典制定機關承擔責任的規定,即“對藥品由于藥典規定標準存在缺陷而造成死亡、嚴重殘疾或者器官組織損傷的,應由藥典制定機關(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給予一次性補償,補償金額納入財政預算”,從而推動我國藥品損害救濟綜合體制的發展。第二,在《藥典》中增加責任條款,明確當藥品標準存在缺陷時應由制定者承擔相應責任,并就缺陷認定程序、補償方式、范圍和計算標準進行說明。由于我國尚未有統一的國家補償法可作借鑒,模糊的規定可能會使補償最終難以落到實處。第三,以合規藥品致害事件為契機,參照《侵權責任法》第37條以及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公安機關不履行法定行政職責是否承擔行政賠償責任問題的批復》的規定方式,在《侵權責任法》中增加引致條款,規定:“因行政機關的行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該行政機關承擔責任。在確定具體數額時,應當考慮該行政行為在損害發生過程和結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第四,在理論研究上逐步推動藥害行政補償制度的體系發展,為藥害受害者提供應有保障,并在此基礎上完善我國國家責任尤其是衡平責任理論研究,構建以特別犧牲的征收補償為基礎、福利行政的衡平補償為補充的完整國家責任體系。
由合規藥品致害所可能引發的思考其實不限于藥品領域。毋容置疑,在已經到來的風險社會大潮中,合規藥品致害只是其中泛起的一葉微瀾。相較于人類有限的認知而言,風險是不可預測的,人類有限的防范能力在萬千變幻的風險面前顯得捉襟見肘。43在這樣的背景下,風險社會下與救濟相關的法學理論新發展就更能凸顯其意義所在。傳統法律救濟制度根基于法律責任的概念,法律責任又與違法行為或先行行為密切相關,是基于違反了第一性義務而應承擔的不利后果。而在風險社會下,國家所承擔的救濟責任已遠非如此。例如2003年“SARS事件”后給予死者的喪葬費、塵肺等職業病患者的免費醫療、“7·21北京特大暴雨”受害者的補助等,在上述與國家并無明顯關聯的事件中,國家均發揮了救濟損害的功能。顯然,此時國家對于公民所擔負的責任已經脫離了“先行行為”、“特別犧牲”等條件,更超出國家賠償責任和國家補償責任等法律責任,而具備了國家救助和社會保險的內涵。當然,在傳統概念譜系下,國家所擔負的上述責任并不屬于法律責任的范疇,而屬政治學意義上的國家責任。44然而,在上述事件中,承擔了巨大損害并獲得一定救濟的民眾卻開始要求政府應承擔更多的責任(甚至是賠償或補償等法律責任)。45與之相應,近年來法學界也出現了相對激進的聲音,有學者認為隨著風險社會的臨近,在現代國家理念框架下,國家應負有保障公民各項基本權利的義務,與之對應,公民也應具有法律上的請求權:這種請求權既可以表現為一種事先的預防請求權,使公民超越法律的層次,直接運用憲法上的基本人權來攻擊某些行為,法院也可以不必以法律存在為前提直接裁決;46其也可以表現為一種事后的救濟請求權,運用憲法上的人權保障條款而請求法院判決政府承擔賠償或補償的法律責任。52如照此思路推演,公法上的法律責任將與行為漸行漸遠而只關注損害結果本身,換言之,法律上和政治上國家責任的分界將由此變得模糊,而這無疑會導致法律責任理論和制度的重大變革。為此,在損害頻發的風險社會,如何重構國家責任以及救濟制度的法理,將會是今后亟需回答的問題。
注:
1參見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3-01/04/c_132078381.htm,2013年1月5日訪問;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2e4i4.html,2013年1月5日訪問。
2相關報道可參見《龍膽瀉肝丸——清火良藥還是“致病”根源》,ht 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2/23/content_740961.htm,2012年1月5日訪問。
3在藥品不良反應致害的問題上,世界各國和地區提供了風格各異的救濟途徑,主要可以分為以德國、瑞典為代表的保險模式以及以日本、我國臺灣地區為代表的基金模式等。上述救濟方式已經脫離了傳統法律責任的范疇,本文不作探討。參見宋瑞霖:《完善中國藥品不良事件救濟機制研究》,中國法制出版2011年版,第150頁。
4 Hearing on Drug Safety Before the Sub comm.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of the House Comm.on Government Operations,88th Cong.,2d Sess.,pt.1,at 147(1964)。轉引自朱懷祖:《藥物責任與消費者保護》,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09頁。
5相關研究可參見金自寧:《風險社會背景下的合規抗辯——從一起環境污染損害案例切入》,載《北大法律評論》2012年第13卷第2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傅蔚岡:《合規行為的效力——一個超越實證法的分析》,《浙江學刊》2010年第4期;解亙:《論管制規范在侵權行政法上的意義》,《中國法學》2009年第2期;宋華琳:《論行政規則對司法的規范效應》,《中國法學》2006年第6期。
6學者約瑟朗德提出形成風險說,參見H.&L.Mayeaud/Tunc,Traitéde la responsabil ité civile,I,1965,N.336-361。轉引自朱巖:《危險責任的一般條款立法模式研究》,《中國法學》2009年第3期。
7蘇永欽:《再論一般侵權行為的類型》,載蘇永欽:《走入新世紀的私法自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29頁。
8參見Clayton P.Gil let te& James E.Krier,Risk,Cour ts,andA gencies,138 U.Pen.L.Rev.1O27,1028(1990).轉引自傅蔚岡:《合規行為的效力——一個超越實證法的分析》,《浙江學刊》2010年第4期。
9傅蔚岡:《合規行為的效力——一個超越實證法的分析》,《浙江學刊》2010年第4期。
10宋華琳:《論政府規制與侵權法的交錯——以藥品規制為例證》,《比較法研究》2008年第2期。
11參見Teresa Moran Schwartz,The Role of Federal Safety Regulations in Products Liabi lity Action,41 Vand.L.Rev.1131(1988);許宗力:《行政法對民、刑法的規范效應》,載葛克昌、林明鏘主編:《行政法實務與理論》,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03年版,轉引自宋華琳:《論行政規則對司法的規范效應——以技術標準為中心的初步研究》,《中國法學》2006年第6期。
12 Hearing on Drug Safety Before the Sub comm.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of the House Comm.on Government Operations,88th Cong.,2d Sess.,pt.1,at 147(1964)。轉引自朱懷祖:《藥物責任與消費者保護》,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37頁。
13當然,藥品制造商也可以在可能出現的兩難境地中選擇停產停業從而盡到“注意義務”,但是這對于以贏利為目的的企業而言顯然承擔的義務過重。
14參見羅豪才主編:《行政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139頁、第142-169頁。
15宋華琳:《行政法視野中的技術標準》,浙江大學2006年博士學位論文,第38頁。
16大陸法系的主流學說根據行政所制定的抽象規范有無形式上的法律規范性將這類規范分為“法規命令”和“行政規則”。參見[日]鹽野宏:《行政法》,楊建順譯,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頁;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253頁。
17參見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頁。轉引自宋華琳:《行政法視野中的技術標準》,浙江大學2006年博士學位論文,第54頁。
18參見[美]理查德·皮爾斯:《立法性規則和解釋性規則的區別》,宋華琳譯,《公法研究》(第2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430頁。
19沈巋:《國家賠償法原理與案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頁。
20通說認為,對于抽象規范的性質,雖然其與法律或者規章相當,但是從其產生之機關及過程而言,則與法律或規章不同,并非由有免責權的民意代表集體制定,如其符合國家賠償的其他要件則尚無予以排除之理。參見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頁;薛剛凌主編:《國家賠償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頁;皮純協、馮軍主編:《國家賠償法釋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頁;周友軍、馬錦亮:《國家賠償法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191頁。
21 Hearing on Drug Safety Before the Sub comm.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of the House Comm.on Government Operations,88th Cong.,2d Sess.,pt.1,at 147(1964)。轉引自朱懷祖:《藥物責任與消費者保護》,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49頁。
22日本京都亞急性脊椎視覺神經癥事件判決書:京都地判1979.7.2,判例時報950號。
23日本東京亞急性脊椎視覺神經癥事件判決書:東京地判1978.8.3,判例時報899號。
24依職權行政不作為可以依照是否具備預見可能性、回避可能性、期待可能性以及受損法益的重要性等要件進行判斷。參見胡建淼、杜儀方:《依職權行政不作為賠償的違法判斷標準——基于日本判決的鉤沉》,《中國法學》2010年第1期。
25參見胡建淼:《行政法學(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58頁;羅豪才、湛中樂主編:《行政法學(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77頁。
26杜儀方:《惡魔抽簽的賠償與補償——日本預防接種事件中的國家責任》,《法學家》2011年第1期。
27李震山:《行政法導論》,臺北三民書局出版社2009年版,第640頁。
28董保城、湛中樂:《國家責任法》,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0頁。
29當然,也有觀點認為,征收性質侵害僅指對財產造成的損害,而如對非財產法益造成侵害則應構成“公益犧牲補償”,后者特指對個人因政府公法上的行為直接造成人的生命、身體、健康以及人格等法益之損害進行補償。參見廖義男:《國家賠償法》,臺北三民書局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頁。
30[英]安東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爾森:《現代性:吉登斯訪談錄》,尹宏毅譯,新華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頁。
31勞東燕:《公共政策與風險社會的刑法》,《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
32[德]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何博聞譯,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33[德]埃貝哈特·施密特-阿斯曼,烏爾海希·巴迪斯編選:《德國行政法讀本》,于安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頁。轉引自趙鵬:《風險社會的自由與安全》,載季衛東主編:《交大法學》(第2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34李建良:《損失補償》,載翁岳生編:《行政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450頁。
35[德]哈特穆特·毛雷爾:《行政法學總論》,高家偉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頁。
36章劍生:《現代行政法基本理論》,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頁。
37[日]宇賀克也:《國家補償法》,有斐閣1997年版,第512頁。
38、39、41李惠宗:《行政法要義》,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651頁,第627頁,第629頁。
40鹽野宏:《行政法》,楊建順譯,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頁;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頁。
42參見《民族區域自治法》第65條、《水土保持法》第31條、《水污染防治法》第7條。
43金自寧:《風險規制與行政法治》,《法制與社會發展》2012年第4期。
44政治學中的國家責任是指一個國家不僅要為其國民的生存、發展、安全、健康、幸福生活和可持續發展承擔和履行責任,同時,國家作為國際社會中的一員,出于道義和社會責任,應為全人類的安全、健康、幸福和可持續發展承擔和履行責任。參見楊光斌主編:《政治學導論(第四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頁。
45參見《非典后遺癥患者生存調查》,http://heal th.sohu.com/20100225/n270418683.shtml,2013年1月5日訪問;《5公民要求監察部等追究北京721暴雨瀆職公務員責任》,http://wq.zfwlxt.com/newLawyerSite/BlogShow.aspx?itemid=03e1dcfb-aa50-418a-bd79-a0b101181304&user=186561,2013年1月5日訪問。
43例如,德國學者Rossnagel在關于核能利用的討論中,提出了“免于恐懼”的自由,該自由和其他個人自由一樣是對抗國家的給付請求權。他認為,人類在面對未知或未經實驗的科技時,經常是極為無助的,人性尊嚴受到威脅的可能也是非常大的。因此,對于科技發展可能產生的風險,若已達到社會國家原則下的最低生活保障的標準,人民具有主觀的請求權。參見郭淑珍:《科技領域的風險決策之研究——以德國法為中心》,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2006年碩士學位論文,第68-69頁。轉引自趙鵬:《風險社會的自由與安全》,載季衛東主編:《交大法學》(第2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47例如,日本學者原田尚彥指出,在現代民主福利國家背景下,國家行政機能日益擴大且公眾對行政機關的依賴日益加深,應將反射利益“公權化”,將行政活動所產生之利益推定為國民應享之權利,只要公眾的利益被行政機關侵害,就應當允許公眾提起行政賠償之訴。參見[日]原田尚彥:《薬害と國の責任—可部判決の理論をめぐって》,《判例時報》899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