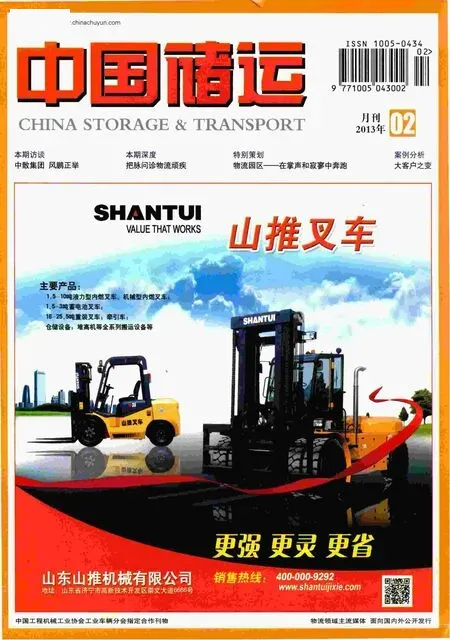柯羅連科的火光
文/李煒光
大約100年前的一天,俄羅斯的作家們正在舉行晚會。一位年輕女作家手里拿著一本紀(jì)念冊,在人群中焦急地尋找著心中偶像——作家弗拉基米爾·柯羅連科,希望他在自己的本子上簽名。
她終于在人縫中看到了他,急忙忙地打招呼。柯羅連科看著可愛的女作家,靜靜地微笑著。她把本子遞到他面前,傾慕而充滿期待地望著他。他卻并不急著在上面簽字,而是皺起眉頭,用筆在手掌心里輕敲了幾下。女作家以為他要拒絕,睜大眼睛問道:“怎么,您不愿意為我寫點什么嗎?”柯羅連科搖搖頭,凝視著女作家美麗的眼睛,他的眼睛也亮了一下,似乎想起遙遠(yuǎn)的往事。他接過紀(jì)念冊,走到大廳一角,伏在桌子上,奮筆疾書起來。
女作家在一邊等候著,又驚又喜,沒想到作家會在她的本子上寫這么多,也不知道他寫了什么。終于,作家寫完了,把本子交回到姑娘的手里。她感覺眼前一亮,上面是柯羅連科即興寫下的一篇散文詩。她興奮地讀著,情不自禁地念出聲來:
很久以前,在一個漆黑的夜晚,我泛舟在西伯利亞的一條陰森森的河上。
船到了一個轉(zhuǎn)彎處,只見前面黑茫茫的山峰下面,有一支火光驀地一閃。那火光又明又亮,好像就在眼前……
我高興地大聲叫道:“好啦,謝天謝地!我們終于可以到過夜的地方啦!”
船夫扭頭朝身后的火光望了一眼,又不以為然地劃起槳來。
“遠(yuǎn)著哪!”
我不相信船夫的話,因為那火光明明就在那里閃爍。可事實上,船夫是對的,那火光離我們的確還遠(yuǎn)著哪。
這些黑夜的火光的特點是:它能沖破黑暗,閃閃發(fā)亮,近在眼前,令人神往。乍一看,你只需再劃幾下就到了……其實,它還遠(yuǎn)著哪!
我們在漆黑如墨的河上又劃了許久。一個個懸崖,迎面駛來又向后移去,消失在茫茫的遠(yuǎn)方,而那火光,卻依然停在前面,閃閃發(fā)亮,令人神往——依然是這么近,又依然是那么遠(yuǎn)……
在現(xiàn)實生活中,又有多少這樣的希望之光,不僅僅地在召喚著我一個人,我們的生命之河,也依然在陰森森的兩岸之間流著,而那火光,也依然是那么遙遠(yuǎn)。
我們,只有用力劃槳!
因為,火光啊,畢竟就在前頭!
這首散文詩,就是后來流傳于世的名作《火光》。400字短文,凝結(jié)著作者對人生的認(rèn)知和對青年的熱切期望。
如果把《火光》只是當(dāng)作一篇勵志文,收入課本,鼓勵“好好學(xué)習(xí)”,那只是理解了《火光》的部分含義。它的另一層寓意,卻是以往人們讀《火光》所忽略了的。
柯羅連科青年時代因涉嫌同革命活動來往而被捕流放,1881年,又因拒絕向亞歷山大三世書面效忠被流放遙遠(yuǎn)的西伯利亞。他反對君主專制,同情勞苦大眾,抨擊腐敗政府和社會制度。他的作品《索羅慶采悲劇》、《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洋溢著民主思想和人文精神,表現(xiàn)人民覺醒和向往自由的意志。這樣一個有著強烈社會責(zé)任感的作家,怎么可能只寫出一篇訓(xùn)導(dǎo)別人的庸俗文章呢?
柯羅連科眼中的火光,是一盞是人類文明的航標(biāo)燈,鼓勵青年一代勤奮寫作,同時也指出了他們的方向——向著人類文明之光前進。這方向是不能錯的。而我們的教科書,又有哪一種明確指出了《火光》的這個關(guān)鍵之點呢?
今天我們站在時空交點上,古希臘遠(yuǎn)去了,古希伯來遠(yuǎn)去了,“光榮革命”遠(yuǎn)去了,法國大革命遠(yuǎn)去了,美國憲法的開創(chuàng)者也遠(yuǎn)去了,而人類社會的主流文明,民主、法治、自由、民主、憲政,似乎還離我們還很遠(yuǎn),像是遠(yuǎn)方閃爍的火光。有許多次,我也產(chǎn)生過與柯羅連科同樣的感覺。不是在西伯利亞河上,也不是泛舟于懸崖峭壁之間,而是在內(nèi)心深處。理想變?yōu)楝F(xiàn)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也許50年,也許100年。追索光明的旅程,不也有如在陰森森的河流上航行么?
但文明火光畢竟已經(jīng)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了,以它看似的“近”吸引著我們。即使是逆水行舟,我們也必須抱定希望,不言放棄。因為我們無路可退。我們身后,是無窮無盡的黑暗。
我們懷揣著希望,艱難前行,正一點點地接近那遠(yuǎn)在天邊的希望之火。
誰又會放棄這似遠(yuǎn)又近的“火光”的導(dǎo)引,和它所帶來的希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