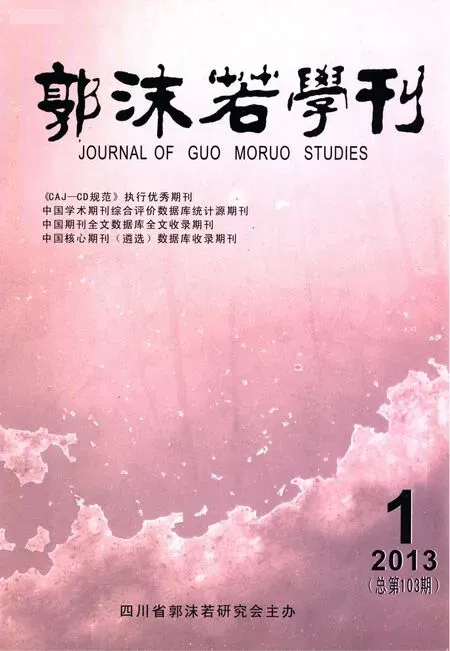郭沫若三首寺字韻佚詩談
魏奕雄
(樂山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四川 樂山 614000)
近翻樂山市圖書館所藏四川辭書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郭沫若書法集》,見到郭老1940年1月在重慶書贈于立群卷軸上的《寺字韻詩七首》手跡。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后,許多全國著名的文化人聚集渝城。那時候他們流行以寺字韻作詩,互相唱和。1965年2月15日郭老在這個卷軸末尾題跋:“三十五年前在重慶曾為寺字韻十三首,此卷存其七首,余六首如石沉大海矣。”
《郭沫若學刊》2011年第3期刊發中國郭沫若研究會會長蔡震先生《郭沫若用寺字韻詩作考》一文,除了考證上述七首的寫作時間外,又將“石沉大海”的另一首《十二用寺字韻》披露出來。我最感興趣的是其中的第二、第五和第十二首,因為其內容都與樂山密切相關。今將我讀這三首佚詩的粗淺領會記錄于下,以就教于方家。
思源只記故鄉名
郭沫若的《再用寺字韻》,描述了故鄉沙灣的地名變遷及對故鄉的深切眷念之情。詩句如下:
綏山之麓福安寺,中有明碑安磐字。
碑言古鎮號南林,舊隸峨眉縣亦異。
叔平夫子來涪岷,相與辯之言訚訚。
南疑楠省邑境革,合乎故訓殊雅馴。
抗戰以來逾二載,剩有蜀山猶健在。
四方豪俊會風云,一時文藻壯山海。
刻章戲署南林卿,見者為之心目驚。
實則卿鄉原不二,思源只記故鄉名。
這首詩的開頭,說峨眉山第二峰綏山之麓福安寺中有明代安磐書刻的碑記,碑上稱沙灣古鎮為“南林”(郭老墨跡中“南林”之后多寫了一個“縣”字)。郭沫若在自傳《少年時代》曾記載:沙灣場南端“過橋不遠在山麓的傾斜中,有一座明時開山的古寺叫茶土寺。中有一座碑是明末的鄉賢嘉定人安磐寫的。”
福安寺又名茶土寺,位于沙灣古鎮南部一公里左右,今已不存,遺址在今中川紙廠內。安磐是明代著名的“嘉定四諫”之一,嘉定城里三峨坊人,正德年間歷任吏兵二科給事中,嘉靖初升兵科都給事中。他寫的《福安寺記》,我仔細看了,安磐寫的是“南陵”,不是“南林”。查民國版的《樂山縣志》,第26頁在“觀峨鄉”中介紹“沙灣場,唐時名南林鎮”。
200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沙灣區志》第44頁“區名由來”中,講到沙灣鎮“始設于唐玄宗天寶元年(公元742),號‘柘林’,位置在今中川紙廠外的樂山水泥廠處。唐德宗貞元九年(公元793),城柵被吐蕃軍焚毀。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高駢為劍南西川節度使修復城柵,將鎮移至姚河壩,因當地廣生楠樹且成林,故將鎮名改稱南林鎮,亦稱南陵鎮。又一說因地處峨眉山南麓而名南陵。南宋詩人、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在淳熙四年(公元1177)離任回京前,曾作峨眉三山游,寫下贊譽峨眉三山的詩篇,評南陵地處‘靈山秀水沙岸灣環處’。清高宗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南陵鎮沒于大水,鎮始移于今址。由于在‘靈山秀水沙岸灣環處’建場,故名沙灣,沿襲至今。”
199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峨眉縣志》第35頁:“明崇禎十七年,明將楊展住嘉州時,將峨眉之銅山、沫東、茶土溪、羊鎮以下地區,劃入嘉州(今樂山)。”茶土溪今屬樂山市沙灣區沙灣鎮,沫東今屬沙灣區嘉農鎮,在沙灣鎮北端。這說明古沙灣場原屬的觀峨鄉的部分地區,明代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之前,曾經歸峨眉縣管轄。
以上資料表明:沙灣古稱確實是南林或南陵。郭沫若認為“南疑楠省邑境革,合乎故訓殊雅馴”,說得頗為確切:“南”字是由“楠”省去“木”旁,“邑境革”自然指沙灣先屬峨眉縣(邑)后歸樂山縣了。
郭沫若1939年2月底至3月上旬,由重慶回沙灣14天,探視重病臥床的父親。很可能他抽空重游了小時候多次游覽過的茶土寺,或許還拓下安磐的碑記,帶到重慶,其中有模糊不清之處,與因文物南遷而抵重慶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字叔平)一同辨析,發生了分歧,故有“相與辯之言訚訚”句。“訚訚”者,朱熹注“和悅而諍也”。這兩位考古學家友好地爭辯著,至于所辯是南林與南陵,還是別的什么,現在誰也說不清了。
我讀郭老這首詩的最大收獲,在于從中得知他老人家曾經自號“南林卿”,并且刻成圖章,為的是“思源只記故鄉名”。這是先前任何印刷品不曾透露過的新鮮信息,頗為難得。那時候重慶有人見到“南林卿”圖章,驚訝郭老的家鄉怎么變了呢(見者為之心目驚)?郭老說,我的家鄉沒有變(實則卿鄉原不二),南林只是沙灣的古稱而已。
郭老的這首詩,讓我感受到了他深切的愛鄉愛國憂國憂民的情懷。
怒斥敵機濫轟炸
郭沫若《五用寺字韻》手跡,赫然印著郭沫若怒斥日軍狂轟濫炸樂山等城市的詩句:
無邊浩劫及祠寺,機陣橫空作雁字。
由來倭寇恣暴殘,非我族類其心異。
國都播遷入蜀岷,至今和戰交爭訚。
憨者逋逃黠詭隨,欲驅豪杰化柔馴。
岳墳淪陷近三載,會之鐵像應仍在。
素審敵仇似海深,近知奸惡深于海。
南都北闕偽公卿,婢膝奴顏寵若驚。
何時聚斂九州鐵,鑄像一一書其名。
其中“憨都逋逃黠詭隨”“南都北闕偽公卿”,概括了以下一段史事:1938年12月汪精衛由重慶經昆明逃往越南河內,投降日本,開始策劃籌建偽中央政權。1939年5月6日乘日本專機回上海;9月19日到南京,與駐北平的華北偽臨時政府主席王克敏、駐南京的華中偽維新政府主席梁鴻志等,協商在南京成立偽中央政府,并對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偽政府頭目參加偽中央政府的名額進行分配。郭沫若對這些漢奸恨之入骨,期盼收集全國各地的廢鐵,像杭州西湖岳飛墓前跪置秦檜鐵像那樣,一一鑄出諸位大漢奸的丑像(郭老墨跡中第十句首字“會”是“檜”的假借字)。由此可以推斷,此詩當是1939年9月下旬或10月份寫于重慶。
“無邊浩劫及祠寺,機陣橫空作雁字”兩句,沒有明確點出樂山,作為詩詞,可以理解得寬泛一點,說是郭沫若表達對日軍飛機轟炸全國許多城市的憤慨也行。從四川來說,1939年5月3日,日機45架轟炸重慶;4日,27架日機再次轟炸重慶;其后又多次轟炸重慶。6月11日,日機27架轟炸成都……但詩中既有“祠寺”二字,范圍就可以縮小了。郭老是1939年7月11日從重慶趕回樂山沙灣治理父喪,9月上旬返重慶。其間的8月19日,36架日軍中型攻擊機,猛烈轟炸樂山城區。據民國時期檔案記載,炸死838人,炸傷380人,炸毀街道12條半,半個城區成廢墟,一萬多人無家可歸。西遷樂山的武漢大學經濟系學生住宿的龍神祠,那天也挨了炸,當場死亡學生4人,傷多人。當年親歷轟炸的老人都說,當時敵機是3架一組成品字形,3組連成一隊;臨近城區上空時變成一字隊形。這也與“機陣橫空作雁字”相符。
既然“8·19”大轟炸當天郭老在沙灣,估計一兩天后就聽說了樂山城區慘不忍睹的情況,也知道了龍神祠的慘狀,故有“無邊浩劫及祠寺”句,斥責日軍進行無差別轟炸,連祠寺都不放過,痛罵“倭寇恣暴殘”。
重慶“5·3、5·4”大轟炸中也有一些寺廟遭殃。郭沫若曾經寫下《慘目吟》一詩來渲泄心中的仇恨:“五三與五四,寇機連日來。渝城遭慘炸,死者如山堆……”。而《五用寺字韻》的前四句,必是受樂山“8·19”大轟炸的刺激而流瀉于筆端的憤恨,或者說,它至少包含了對樂山這次慘烈轟炸的無比憤恨,當然也包含了對重慶、成都等城市挨炸的強烈憤恨。實際上,這首詩的主題就是一個恨字:恨日本鬼子!恨漢奸!
頌揚故宮護寶人
《十二用寺字韻》如下:
從寸之聲是為寺,于文當即古持字。
秦刻用之以為持,鼄鐘有例亦不異(鼄公牼鐘有“分器是寺”語)。
石鼓于今已入岷,無咎先生言訚訚。
花崗之石趺坐銳,質堅量重難調馴。
一鼓費一卡車載,纊裹網維箱底在。
初移寶雞后峨眉,暴寇無由攘過海。
星之景兮云之卿,視此奇跡不足驚。
扶持神物走天下,宇宙恢恢乘大名。
我向蔡震先生電話請教此詩出處,答曰抄錄自一位朋友收藏的一幅郭老墨跡,那是1940年1月7日郭老“聞石鼓已入蜀,書奉無咎先生教正”的。但《郭沫若書法集》中書贈于立群的《寺字韻詩七首》手跡沒有這一首。
“無咎”是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的號。這首詩表達了郭老對故宮文物特別是石鼓遷藏峨眉的關注。
1933年2月,北京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等的19000多箱珍貴文物,為避免落入日寇手中,秘密遷徙上海。因為都由故宮博物院統一裝運,統稱“故宮文物南遷”。1936年12月移存南京朝天宮。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南京岌岌可危,又分三路西遷。南路80箱向貴州安順;中路9000多箱走水路,經漢口、宜昌轉運,1938年1至5月陸續載至重慶,1939年7月至9月移置樂山安谷;北路6000多箱(包括石鼓10箱),由陸路先遷陜西寶雞,二遷漢中,三遷成都,四遷峨眉,于1939年5月17日至6月17日先后入藏峨眉大佛寺和武廟。我們姑且不說南路和中路,就說這石鼓所在的北路,從漢中遷出后12天,原先存放文物的漢中南鄭文廟,即被日軍飛機扔下7顆炸彈夷平。漢中至成都途中,發生了三次汽車翻車事故。從成都大慈寺遷往峨眉后7天,成都也挨了日軍的狂轟濫炸。郭老詩中的“初移寶雞后峨眉”,濃縮了這一漫長曲折艱險繁雜的歷程。據原故宮博物院峨眉辦事處主任那志良在《典藏故宮國寶七十年》一書回憶,當時十個石鼓就存在峨眉武廟西配殿里。
南遷文物千千萬萬,為何郭老獨獨提到石鼓呢?這是因為他曾經專門研究過石鼓文的緣故。大革命失敗后,郭老流亡日本,于1932年開始對東京文求堂所存石鼓文拓片進行梳理,1933年寫成《石鼓文研究》初稿。
石鼓是唐代出土的刻有記敘東周秦國國公陪同周天子游獵盛況的石碣,故又稱“獵碣”,共有介于籀與篆之間的文字500個左右,無論是史料價值,還是書法雕刻藝術價值,都珍貴無比。有宋代以后的多種拓本存世,最佳的是宋代先鋒本、中權本、后勁本和天一閣本四種。郭老《初用寺字韻書懷》一詩中,曾有“嘗從獵碣考奇字。先鋒后勁復中權,宋拓良與今石異。”
十個石鼓是從陜西鳳翔府陳倉荒郊岐山之陽發掘的,亦稱“陳倉十碣”或“岐陽石鼓”。其實它并不像鼓,上小下大,頂圓而底平,四周略作方形,也有正圓的,四面環刻陰文。石質堅硬,每個重約一噸。由于年代久遠,有些刻了字的石皮已與鼓身分離,稍有不慎,就會剝落下來。當年文物南遷時,最難包裝的就是這十個原存于國子監的石鼓了。馬衡在《跋北宋石鼓文》中記載:“余鑒于此種情狀,及既往之事實,知保護石皮為當務之急。乃先就存字之處,糊之以紙,縱使石皮脫落,猶可粘合;次乃裹以絮被,纏以枲綆(麻繩),其外復以木箱函之”。木箱是特制的,箱的內壁塞滿了稻草,釘牢后,外面又用鋼條綁扎封死。一輛卡車只載一箱,連同一塊銓釋石鼓文音義的碑刻,單獨用了11輛卡車運送。這就是郭老詩中描述的“花崗之石趺坐銳,質堅量重難調馴。一鼓費一卡車載,纊裹網維箱底在。”
對于石鼓的雕刻年代和國別,長期以來眾說紛紜。馬衡先生是著名金石學家、考古學家,對石鼓頗有研究,寫過一本《石鼓為秦刻石考》,認為不應稱“鼓”,主張叫“秦刻石”。他考證所刻文字是春秋繆公(一寫作穆公)時期的,而郭老則認為是春秋秦襄公時所作,也有學者說是戰國秦獻公時的。盡管年代有爭議,但都認定為東周時期秦國的遺物。

石鼓文拓本(明安國十鼓齋存)
郭老這首詩中第三句“秦刻用之以為持”,即言石鼓系“秦刻”。詩的開頭,也是從石鼓文切入,說寺字韻的“寺”字,在周代就是“持”的通假字。不但秦國刻的石鼓上這樣用,東周鼄(一寫作邾,音朱)宣公的牼鐘上銘文“分器是寺”也不例外,這個“寺”字也是“持”。
1938年春,馬衡先生到達重慶,建立了故宮博物院重慶辦事處;郭沫若也在同年12月底隨同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抵重慶。他們時有往來,不時切磋文史問題。郭老1963年為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一書所作序言中寫道:“一九三九年同寓重慶,曾以青田石為我治印一枚,邊款刻‘無咎’二字。”并且特地提到抗日戰爭時期“馬先生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之職,故宮所藏古物,既蒙多方維護,運往西南地區保存。即以秦刻石鼓十具而論,其裝運之艱巨是可以想見的。但馬先生從不曾以此自矜功伐。”1939年7月,長沙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郭老的《石鼓文研究》。恰巧此時,十個石鼓剛剛存于峨眉不久。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可以想象,當這兩位都是潛心研究過石鼓文的考古學家聚在一起,談到石鼓,那是怎樣的眉飛色舞,自然就有了郭老“石鼓于今已入岷,無咎先生言訚訚”的詩句。那纊裹網維、一鼓一車的細節,也必定是郭老聽了馬衡先生的詳述而吟成。全詩通篇圍繞石鼓著筆,我們似乎也可以理解為郭老以石鼓代指南遷的文物。
故宮文物南遷是反法西斯戰爭中保存中華文脈的可歌可泣偉大壯舉,是戰勝無數艱難險阻驚天地泣鬼神的文物長征,也是保護全人類共有的文明結晶的重大貢獻。郭老用“暴寇無由攘過海”來概括南遷的目的。他熱情洋溢地贊頌故宮人“扶持神物走天下,宇宙恢恢乘大名”。這里用的是“扶持”,而不用“護送”或其他同義詞。讀到這里,才明白開頭用了四句大講“寺為持字”的原由了。他說,天邊出現了卿云璨燦的祥瑞氣象,有人感到驚奇;但當你知道了南遷文物歷經千難萬險的奇跡,那就不會驚訝了。作為歷史學家,他視文物為“神物”,稱眾多價值連城的國之瑰寶安全轉移為“奇跡”。文化不亡,民族不滅。他對中華文物的精華部分得到有效保護,深感欣慰,充滿了敬意,也惦量到了這一行動的沉甸甸分量。所以這首詩,實在是郭老對馬衡及其同仁在戰火紛飛中跋山涉水“扶持神物”的勛勞的旌彰。

馬衡院長曾于1944年集石鼓文字為聯“蒦寺古宮庶物,來乍我麋寓公”,兩旁題跋:“(民國)二十八年夏,自成都移故宮文物于峨眉,石鼓與焉,因集其字為聯以紀念之.鼓文以寺為持,以乍為作,蒦護古故勿物麋眉古通.卅三年秋鄞馬衡書,時為寓公五年矣。”(馬衡籍貫浙江鄞縣),依馬衡題跋中對古代通假字的解釋,這聯應讀作“護持故宮庶物,來作峨眉寓公”,其中“我”與“峨”亦相通.此聯的內容與郭老的這首詩相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