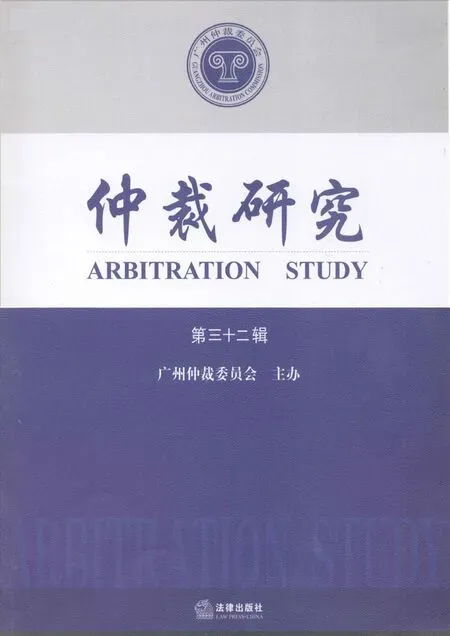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仲裁
——未來的挑戰*
Bernard Hanotiau著 傅攀峰譯 宋連斌校
?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仲裁——未來的挑戰*
Bernard Hanotiau**著 傅攀峰****譯 宋連斌****校
全球化使國際合同的數量與日俱增,由此,復雜的商事糾紛相應地也急劇增多。全球化的力量促使商人們選擇國際仲裁作為解決他們之間糾紛的首選方式。基于人們對更自由的仲裁程序的共識,全球化進一步導致了仲裁在程序及實體方面的“非國家化”,以及國內仲裁立法和仲裁機構規則的趨同。全球化為仲裁庭適用國際商法中被各國普遍接受的一般原則打開了一扇窗,并促進了國際仲裁文化的發展。同時,當今國際仲裁面臨諸多挑戰。人們對仲裁的司法化、仲裁在時間及經濟方面的效率以及職業道德方面的問題越來越感到擔憂。如何克服這些挑戰以及如何保證仲裁今后繼續保持以往使其取得成功的質量與優勢,亦為本文所探討的重點。
國際仲裁 經濟全球化 挑戰
一、引言
毋庸置疑,過去的幾十年見證了現代國際秩序的重大調整。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社會、政治以及經濟方面的活動跨越了國與國的疆界,致使在地球某一角落的發生的事件、作出的決策以及進行的活動會迅速地影響地球另一角落的個人以及社區。
全球化主要體現在世界各國經濟的日益相互依賴,而這源于不斷增長的商品與服務的跨境交易、國際資金流動和技術創新。
由于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法律活動不再受到地域疆界的限制,因此,經濟全球化促進了地域空間的“非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經濟全球化還促進了民族國家傳統角色的轉變,這是因為民族國家一方面日益依賴國際市場,另一方面卻又面臨著控制國民經濟以及經濟、金融領域活動者的行為的重大挑戰。①
經濟全球化也同樣促進了國際商貿的發展和國際合同數目的遞增,并致使有待解決的商事糾紛亦不斷遞增。
二、全球化與國際仲裁的發展
伴隨經濟全球化而日益增多的商事糾紛正是國際商事仲裁的用武之地。在當今全球化的世界里,傳統的糾紛解決方式日益顯現得不合時宜,或者至少可以說是難以勝任解決從大量的國際商事合同中產生的復雜糾紛。這出于以下幾點原因:在性質上,傳統的法院管轄依然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于民族國家范圍之內;法官在地方性的文化背景下工作,適用在此環境中被接受的程序性規則;國際商人擁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懷有對法律以及程序的不同期望。
而且,法官的工作語言并非必然是糾紛所涉合同的語言。再者,在許多情形下,這些合同都相當復雜,它們時常會要求適用跨國原則或“非國內”規則,而法官對其卻不一定諳熟,而且它們可能還會涉及到技術性很強的標的物。對于內容極為復雜且涉及層面極廣的國際合同糾紛,裁決前,案件的分析、研究以及裁決書的起草將需要數周乃至數月的時間。
以上即是國際仲裁在二十世紀逐漸發展成為商人們優先選擇的國際商事糾紛解決機制的原因。除了上述原因外,以下被公認的國際仲裁的內在屬性也是其在二十世紀得以發展的原因:一、仲裁的過程迅速,效率較高;二、仲裁具有保密性;三、仲裁庭中立;四、當事人可以選擇具有相關語言背景的仲裁專家;五、仲裁程序相當靈活,具有變通性,可根據具體情形滿足當事人的各種期望;六、裁決具有終局效力;七、裁決的執行比較容易。
全球化推動了國際仲裁的發展,然而,其影響不僅僅止于此處,更為重要的是,全球化已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仲裁以及仲裁程序的態度。這種趨勢可以用三個詞來概括:非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趨同化(convergence)和自由化(liberalization)。
三、全球化與國際仲裁的“非國家化”
首先,經濟全球化對國際商事仲裁的影響之一即是所謂的“非國家化”現象的產生。“非國家化”是指,無論是程序方面還是實體方面,仲裁的整個過程都獨立于仲裁地法,換而言之,即將國家法院對仲裁過程的干涉最小化。②
過去的幾十年里,針對國際仲裁的法律性質,人們爭論不休:國際仲裁究竟是一種自治的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抑或是一種由國家的特別法律予以規制的授權性糾紛解決機制?③
根據契約說(contractual theory),仲裁庭的管轄權以及裁決權限完全源自于當事人的共同協議。當事人有資格決定仲裁程序的進行方式以及規制仲裁程序的法律,不受任何國家法律的干涉。
然而,正是在國家法律的允許下,相關爭議才可以被提交仲裁;也正是在國家法院的支持下,仲裁裁決才能夠得以被承認和執行。契約說卻忽視了這一事實,它還忽視了仲裁裁決需要國家法院進行某種最低限度控制的要求。
另一方面,司法權說(jurisdictional theory)強調的是,國家擁有控制其領域內任何國際商事仲裁的權威和監督權力。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該學說相當盛行。許多國家曾經(至今在某些國家,比如荷蘭或者德國)堅持著一條相當普遍的原則(該原則有時或被相關國家寫入憲法),即將爭議提交給 “自然法官”(natural judge)進行審判是當事人的一項基本權利。這里的“自然法官”當然指的是國家法庭。④如此一來,仲裁被國家立法者視為對該原則的例外予以接受(或說“忍受”),結果導致仲裁的方方面面都在國家立法的嚴格管制之下。根據該學說,仲裁協議也被認為應嚴格地加以解釋。
但是,司法權說沒有充分考慮到當事人協議以及意思自治的重要性。很難說這種學說與國際仲裁在過去幾十年里的發展形勢相一致。
實際上,以上兩種學說都有一定道理。一方面,仲裁依賴于私人協議;另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仲裁程序又受到國家的控制(或說“協助”),且沒有國家的允許,仲裁裁決不可能得到承認和執行。換而言之,國際仲裁的成功仰賴于以下兩種因素的互動:國際公約和國家立法。根據國際公約,在爭議雙方簽有仲裁協議之時,國家有義務促成以仲裁的方式解決爭議;另一方面,在國家法律框架下,法院有義務協助仲裁程序的開展,以及為確保基本程序原則得到遵循,對裁決進行最低程度的控制。⑤
契約說和司法權說的優點在于,它們都深刻意識到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與國家對仲裁程序的監督和控制兩者之間的張力。因此,本文需要闡釋的問題是:全球化是否具有平衡這兩方面力量的作用?正如全球化對經濟其他方面的作用一樣,全球化是否也有助于消融國家對仲裁程序的控制與管理?
答案是肯定的。隨著國際貿易的不斷發展和相應而來的國際糾紛的不斷增多,法律也在朝著使國際仲裁逐漸擺脫國內法和法院的控制的方向不斷發展。這種束縛的擺脫體現在國際仲裁脫離于仲裁地法的控制的過程。我們將會看到,這一過程的本身和與此同時發生的各國仲裁法律、法規的趨同化的趨勢不可分離。
四、全球化與仲裁3規則的逐漸趨同化和自由化
實際上,全球化不僅促進了國際仲裁“非國家化”的逐漸發展,而且還促進了各國仲裁法律、仲裁機構規則以及其他規制國際商事仲裁的調整性規范的日益趨同。當然,與此同時仲裁在一定程度上的多樣性仍會延續,以反映各國不同的文化傳統和歷史發展。
(一)趨勢的發展進程
仲裁規則趨同化與自由化的發展趨勢肇始于1958年《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即《紐約公約》)。該公約以促進裁決在全球的順利執行為宗旨,對拒絕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理由進行限制,自其被采納以來逐漸得到了廣泛的批準,⑥且其中的不同條款也逐漸獲得了一致的解釋。
國內立法方面,在上世紀最后四分之一的時間里,不少國家的仲裁法律依然陳舊過時,或至少是秉持嚴格限制仲裁的態度,有些國家甚至缺失仲裁方面的立法。在經濟全球化的壓力下,各國開始決定修改其仲裁法或者頒布新的仲裁法,使其適應時代的發展。毫無疑問,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于1985年主持制定的《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以下簡稱《示范法》)是導致仲裁國內立法新發展的重要因素。《示范法》的立場是要強調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價值,即主張當事人可以根據案件的具體情形選擇程序的進行方式而不受國內法律的制約;與此同時,另一方面,要限制法院對仲裁程序和仲裁裁決的審查權限。
上世紀80年代法國仲裁法改革掀起了世界范圍內仲裁法改革與現代化的浪潮。其后,幾乎每一年都有國家效仿法國的改革,及至今日,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或地區都已更新其仲裁立法。某些國家選擇全部采納《示范法》,另一些國家則對《示范法》的某些條款稍作修改再加以采納,還有些國家選擇借鑒《示范法》的內容,這因國而異。在亞洲許多國家,情形亦是如此。⑦然而,有些國家對《示范法》的態度異于前述情形,最典型之例莫過于英國,鑒于其仲裁機制的特殊性,該國未效仿《示范法》。
在更新或修改仲裁法的過程中,各國仲裁立法的主要差異得到了消除。例如,法律問題可以得到上訴、反對仲裁員以友好仲裁者的身份進行仲裁、不要求作出包含理由的裁決書,這都是普通法系向來對仲裁所持的態度,然而,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已逐漸消失了;另一方面,在大陸法系,獲取證人證言的障礙也已經逐漸得到了消除。
(二)邁向更自治、更靈活的仲裁程序
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各國已使其仲裁立法偏向于支持更為獨立、靈活的仲裁程序。這種態度不難被理解,因為各國對靈活、迅速的國際糾紛解決機制具有長足的需求,且各國已意識到國際仲裁已形成欣欣向榮的市場發展態勢,皆希望在其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由此,各國對國際仲裁市場的競爭促進了仲裁的自由化和“非國家化”。
所有這些立法努力致使各國仲裁法日趨高度統一,即各國仲裁立法朝著同一方向并行發展,這源于各國在推動國際仲裁不斷獨立、自治這一問題上已達成了基本共識。所有最新的仲裁立法都接受以下這條原則,即當事人可依其意愿設計仲裁程序,選擇適用或者不適用國家程序法或仲裁規則,僅需滿足尊重正當程序原則、當事人的抗辯權利和平等原則的基本要求。大多情形下,當事人不再受國內法庭關于證據可采性及其效力等級的約束,通過選擇某一不特定國家的法律或者一般法律原則,他們可以自由決定案件實體問題所應適用的規則。所有這些最新立法都承認仲裁條款獨立原則、管轄權自裁原則(即仲裁員有權決定自身對案件是否具有管轄權),以及確認法院在仲裁程序中應當扮演更為謹慎的監督角色,確切來講,在大多情形下,法院的角色已被限定為,在仲裁庭組成以前(如采取臨時措施)或在仲裁進行中(如在一方缺席情形下,指定一名仲裁員)應當事人之請求,支持或輔助仲裁的開展。
(三)仲裁與仲裁地逐漸脫鉤
此外,仲裁程序與仲裁地的關聯明顯遭到不斷的侵蝕。法國法院(著名的Hilmarton案⑧和Putrabali案⑨)以及最近荷蘭法院(Yukos案⑩),通過相關判決表明,即使裁決已被仲裁地法院撤銷,其也有可能在它們國家得到執行。這些判決背后的理論依據是,外國仲裁裁決是一個國際性的裁決,它不會自動并入到被請求執行國的法律秩序中;只要裁決不違反國際公共秩序,執行國法院有權根據自身的規則決定是否將裁決并入其法律體系中,這是為《紐約公約》第7條所允許的。
雖然尚沒有國家已放棄對在其領域內進行的仲裁的完全控制,但在許多情形下,仲裁地對仲裁程序的控制已降至最小的程度了,換而言之,當事人基本上只有提起撤裁之訴的可能了。更有甚者,在瑞士、?比利時、?突尼斯?和瑞典?,當事人若與這些國家無任何形式的聯系,他們便可協議排除任何一方對在這些國家作出的仲裁裁決提起撤裁之訴。在必要的情形下,對仲裁的控制將會在裁決執行的背景下進行。
最后,如同執行地法院拒絕執行國際仲裁裁決的依據一樣,仲裁地法院對在其領域內作出的國際仲裁裁決的審查依據,如今大體上已被限制在嚴重超裁、違反正當程序原則、不尊重當事人的抗辯權利以及違背公共秩序等這些情形。即便如此,法院對上述審查依據的解釋也是愈趨嚴格。例如,在違背公共政策方面,大多數國家傾向于效仿美國最高法院在Parson & WitthemoreRaktai案?中對公共政策進行嚴格解釋的態度,即當事人欲使其公共政策的抗辯成立,必須證明確實存在違背法院地最根本的道德觀念和司法正義的情形。有些法院,特別是在歐洲,在這點上行得更遠,法國即為一例。自最近Thalès案?判決作出后,巴黎上訴法院即秉持以下態度:如果從閱讀裁決文本的過程中,無法察覺出違背公共秩序的明顯跡象,且潛在違背公共政策的情形僅可能通過反復考量仲裁庭的決議程序方能得知,那么此時公共政策不得作為撤裁之依據。這種傾向似乎被西歐國家的法院愈加頻繁地效仿。
(四)對歷史文化傳統的尊重
人們可能會毫不遲疑地斷定,在當代,相對統一的國際仲裁法律體系業已產生,仲裁開始朝向更自治的方向發展。然而,有關仲裁的國內立法差異依然存在,而這些差異大體源于各國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例如,某些國家仍然區分國內仲裁與國際仲裁,而其他國家則不作此種區分;某些國家在可仲裁性(arbitrability)問題上相當開放,比如在德國和瑞士,所有涉及經濟利益的事項,即所有具有財產價值的請求,都可以仲裁的方式解決,?而其他國家則明確某類爭議不得仲裁;?某些國家的立法限制國家機構作為當事方進入仲裁程序的可能,?而其他國家則無此種限制;?某些國家,如法國,將法院對仲裁程序的控制降至最低限度,而其他國家,如英國,雖已朝該方向作出了努力,但相對而言,它們仍賦予其法院更為廣泛的權力以干預仲裁程序。上述差異源于以下這一事實,即當立法者決定修改其仲裁法之時,它受到兩種力量的牽制,一種力量促使其建立最為開放的仲裁機制以更好地與其他仲裁地競爭,另一種力量則迫使其尊重本國的文化傳統和特殊的國內政策因素。因而,立法者不得不在這兩種顧慮之間作出平衡選擇。
(五)仲裁機構、國際組織和大學的角色
然而,在國際仲裁的規范框架下,仲裁趨同化以及與其相隨的仲裁自由化,不僅僅是國際或國內層面立法努力的產物,它們也是仲裁共同體中的其他參與者的工作成果,這些參與者包括仲裁員、學者、律師、法院、仲裁機構以及其他專業組織。
在仲裁機構層面,國際商會(ICC)在國際仲裁領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于1975年和1998年兩度修改其仲裁規則(目前又開始進行一次新的修改)以在仲裁的程序和實體事項的決定上賦予當事人更大的自治權利。[21]國際商會每次完成對其仲裁規則的修改,其它仲裁機構都會紛紛效仿,它們彼此間亦會相互借鑒、相互吸收,因而致使當今不同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大同小異,且在很大程度上,各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都融入了相同的“非國家化”之態度。
新UNCITRAL仲裁規則自2010年7月1日起生效,它體現了由來自世界各地的仲裁專家們經過多年的討論而達成的共識,可以期待的是,它將進一步促進全球仲裁規則的統一和仲裁程序的“非國家化”。
仲裁的趨同化存在于仲裁的規范框架之中,其亦受益于一系列軟法(soft law)的出現。軟法的形式包括建議(recommendation)、指南(guideline)、指令(directive),它們由仲裁機構、國際組織(如UNCITRAL)、仲裁組織(如CIA)或法律人協會(如ILA、IBA)所闡述。以IBA(國際律師協會)為例,IBA在利益沖突[22]和證據規則[23]領域(特別是在書證制作方面)已彌合了大西洋兩岸存在的實踐差異。IBA《沖突指南》作為解決利益沖突問題的全球參考,很大程度上為所有的仲裁機構所遵從。IBA《證據規則》(新版本最近已生效),在幾乎所有的國際仲裁中,被當事人和仲裁庭所遵從,以使仲裁程序得以順利展開。在書證制作方面,雖然大西洋兩岸依然存在由彼此文化傳統與期望不同所導致的差異,但是當仲裁牽涉到來自歐洲和美國的兩方當事人時,他們通常會接受由IBA所闡述的帶有普遍性質的暫定協議(modus vivendi)。
以上尚非仲裁趨同化之全部,仲裁的趨同是一個多維度的進程。仲裁世界的所有參與者相互影響著,通過大型會議、小型研討會、普通見面以及學者們的出版物等機制,各種觀念得以交互融合(作者將這一觀念交互融合的過程形象地稱作cross-fertilization)。趨同化不僅僅源于法律和規則方面的統一,它還受益于仲裁機構、大學、仲裁組織的教育培訓功能,和仲裁界及學術界中的對話、討論和觀點交流。
(六)爭議實體問題處理的統一
各國仲裁立法、各仲裁機構規則的趨同化,以及仲裁程序的自由化和“非國家化”,都源自于全球化的發展。然而,全球化是否還導致國際仲裁庭在處理爭議實體問題上達到了統一呢?
新近的國家仲裁立法和仲裁機構規則的修訂,皆將寬泛的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奉為圭臬。根據該原則,當事人一般可自由選擇其認為最為合適的法律或法律規則以解決爭議。在爭議實體問題的法律適用上,國際仲裁的自由化實際上產生了兩大重要影響。一方面,與早期的國際仲裁實踐相反,當今,在大多國家或地區的國際仲裁實踐中,若當事人未就仲裁應適用的法律作出選擇,仲裁庭并無義務適用仲裁地的沖突法規則,其可自由選擇適用于爭議的法律或法律規則;另一方面,諸多現代仲裁立法和仲裁機構規則采納了這樣一條原則,即解決爭議問題的準據法并非必須是國內法律,這點與前一方面影響直接相關。例如,新《法國民事訴訟法典》第1496條第1款規定,仲裁庭須根據當事人選定的法律規則仲裁,若當事人未作此種選擇,仲裁庭可根據其認為合適的規則仲裁。類似的規定同樣存在于歐洲大陸及其以外的諸多其他國家,并且愈趨于更為頻繁地被新的立法所采納。我們亦可在許多仲裁機構規則中覓其蹤影,如ICC(國際商會)仲裁規則第17條規定:“當事人得自由約定仲裁庭處理案件實體問題所應適用的法律規則。當事人沒有約定的,仲裁庭適用其認為適當的法律規則”
另外,其他一些國家的立法以及新UNCITRAL(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的措辭,似乎顯得更為嚴格。如新UNCITRAL仲裁規則第35條,僅允許仲裁庭在當事人有明示選法協議之時方可使用法律規則;否則,仲裁庭得使用其認為合適的法律。新頒布的SIAC(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仲裁規則第27條亦作出如此之規定。筆者不確定這些不同版本的規定其間的差異是否重要,因為同大多數現代仲裁立法、其他仲裁機構規則以及聯合國《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一樣,新UNCITRAL仲裁規則第35條第3款,以及新SIAC仲裁規則第27條第3款都規定,仲裁庭須考慮到可適用于相關交易的貿易慣例,因此,所有這些立法和仲裁規則,都不同程度地為仲裁庭適用國際商法的一般原則和所有商業國家普遍接受的原則打開了一扇窗。
那么,上述原則在當代國際商事仲裁中的地位如何呢?[24]廣為所指的商人法(lex mercatoria)并非自治的國際法律體系。商人法規則過于模糊,因而無法構成一個客觀的法律體系。而且,縱使商人法在大陸法系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其亦難以在原則上被普通法系所接受,雖說英國1996年《仲裁法》第46條規定了仲裁庭可根據當事人合意選擇,允許仲裁庭在獲得當事人授權的前提下適用商人法。[25]
在仲裁庭適用國際商事仲裁一般原則的問題上,如果可以尋找到業已為仲裁界所達成的一定程度的共識的話,那么,這種共識很可能是將商人法視為一個逐步進化的過程,這個過程代表著國際商業中的貿易慣例與當事人的期望的整合,而這些貿易慣例和當事人的期望又可作為仲裁準據法的補充。
應當承認,在當今全球化的經濟中,存在著相當多的習慣、貿易慣例、標準條款、行業期望等,仲裁庭在作出裁決之時,須將其納入考慮范圍之中。這些習慣、慣例的地位相當重要,因為爭議的處理須符合商界的期許。姑且不論所謂的商人法是否已被視為一種法律淵源,至少上述習慣、貿易慣例以及國際商事仲裁的一般原則在國際商事仲裁的決議程序中已產生了實實在在的作用。這是因為諸如《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或者UNIDROIT原則等國際公約已得到適用,或因為上述習慣、貿易慣例等已經成為國內法的一部分,或因為它們的存在已逐漸被法院的判決和仲裁庭的裁決所認可。相信無人會輕易否認以下原則的存在及其適用:根據合同條款之規定,善意地履行合同的義務;一方對合同的根本性違約將賦予另一方解除合同的權利;當事人賠償的內容包括業已造成的損失及其利潤(damnum emergens and lucrum cessans);受損方須采取措施減輕損失,且不可無故拖延主張其相應的權利;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可作為合同履行的抗辯;禁反言規則(estoppel)及大陸法系與其相對應的概念或規則(venire contra factum proprium or l’ impossibilité de se contredire au détriment d’autrui)的存在;任何一方在其履行義務在先之時,都不可拒絕履行該種義務。
經驗已證實,在仲裁中通過合同解釋和適用前述所列原則(不論其源自何處)就足以解決大多數商事爭議。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不論仲裁庭適用何種法律或規則,相當多的爭議都可僅通過適用為所有國家及法律體系所接受的商事仲裁的一般原則來解決,而實踐中的實際情形亦是如此。
五、全球化與全球仲裁文化的發展
最后,仲裁參與者之間的互動,一方面通過相互的交流和融合,促使了各國仲裁立法、各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逐漸趨于一致,并促使了國際商法的一般原則的產生;另一方面它也催生了超越兩大法系之傳統界限的全球仲裁文化。此種全球仲裁文化尤其體現為國際仲裁員在仲裁程序問題上皆采納相對統一的方法,而這種方法同時借鑒了兩大法系的實踐:來自大陸法系方面,當事人須連續交換兩項附上書證的備忘錄;來自普通法系方面,當事人須提交 證人證言、專家報告,并請求對方當事人出示書證,以及請求圍繞證人、專家進行盤問而非圍繞口頭抗辯進行審理。
六、未來的挑戰
雖然仲裁已取得以上諸多積極成就,而且正持續蓬勃發展,但其同時亦面臨著諸多重大挑戰,有人甚至質疑仲裁的成功能否在將來得以持續。仲裁越來越成為批評的對象,這種批評不僅僅來自于其終端使用者,即仲裁當事人,而且還來自于仲裁機構和仲裁者本身。
(一)諸多問題
人們越來越對國際仲裁愈趨“司法化”(judicialization)之現象感到擔憂。換而言之,仲裁程序本具有非正式化的特點,但如今卻日趨朝向正式化、復雜化方向演化,由此導致仲裁期限的延長和仲裁費用的累增。普遍認為,該現象應當歸咎于國際仲裁的“美國化”(americanization)現象,雖然這一說法并非必然成立。對于歐洲的法律從業者來說,法庭或仲裁庭的傳統角色乃解決由當事人向其提交的爭議,它們不可拒裁,亦不可超裁。例如,在歐洲大陸,律師并沒有向法庭或仲裁庭出示對其當事人不利的證據文件的義務。然而,隨著全球法律業務的重心轉向大型國際律師事務所(主要在普通法系國家),另一種訴訟方式隨之亦成為焦點,這種訴訟方式的內涵在于,仲裁庭需要扮演發現案件事實的角色。這意味著,仲裁庭采納一套日益類似于美國法院的程序,由此,在庭審過程中便會出現大量的證人陳述、專家報告以及各種可能與解決爭議相關的文件。
因此,在現代國際商事仲裁中,存在著兩種宗旨稍異的程序性取向,它們分別是歐洲大陸法的傳統程序模式和英美普通法程序模式(更偏向于美國普通法),它們之間的張力日漸擴大。相應地,對于何為仲裁的宗旨,以上兩種程序模式的態度亦存在不同之處:一方面,國際商事仲裁應如商界人士所期盼的那樣,保持著省時、經濟、非正式的特點;另一方面,國際商事仲裁在程序上應更具可預測性,這要求仲裁庭應當在查清所有與爭議相關的事實(包括與爭議潛在相關的事實)后再行裁決,如此一來,仲裁將會變得更加正式化、更加程式化,最終與法院訴訟相差無幾。
從某種程度上講,仲裁已經“過于”成功、“過于”精細。其結果便是,仲裁程序中的時效要求已不再被遵守,因為許多律師事務所中仲裁部門律師團隊的工作量過大,或者因為律師們確實難以很好地控制證據文件的制作流程,導致程序上的期限要求不可避免地被忽略。
仲裁機構為此應承擔一部分責任。仲裁機構適用于仲裁案件管理的內部規則日益復雜,這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在過去,仲裁庭的組成僅需數天即可完成,如今,卻可能需要數月。某些仲裁機構的內部程序可能會導致這樣的狀況,即在某些情形下,仲裁庭作出裁決數月后,仲裁機構才向當事人發出通知。
國家對此亦難辭其咎,近年國際仲裁實踐表明,國家法院(特別是在某些新興國家)可能會發布不正當的禁訴令(anti-suit injunction),或者在仲裁程序開始后,作出輕率的裁定,宣告仲裁庭對仲裁中的某些問題不具備管轄權,以此阻擾仲裁的順利開展。實踐中,還會出現以下這種情形,即雖然作為《紐約公約》的成員國具有遵守該公約的義務,但某些成員國的法院卻會尋找一些不合理的借口,以拒絕執行在國外作出的不利于其本國國民的仲裁裁決。
對于當今國際仲裁所受之批評,仲裁員亦負有相當一部分責任。有的仲裁員承接仲裁案件過多,而其本身卻又無法在合理期限內作出裁決;有的仲裁員易受當事人意見左右,對當事人言聽計從;還有的仲裁員,或許出于對其無法再度被當事人委任的擔憂,在仲裁程序的進行過程中,對一些不恰當的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缺乏站出來指正的勇氣。
國際仲裁在全球范圍內的巨大發展也使得國際仲裁所面臨的問題變得愈加突出。近些年,國際仲裁的新參與者數量眾多,而這些新參與者當中相當一部分從未有過仲裁的經驗,或者對仲裁文化或仲裁職業道德尚比較陌生。在世界某些地區,律師時常在仲裁程序中玩弄違反職業道德的“戰略性游戲”,其行為甚至可能會超越法律的界限,這無不使當今的仲裁機構倍感擔憂。友好性(conviviality),正如瑞士著名仲裁員克勞德·雷蒙德(Claude Reymond)教授所指出的,是國際仲裁的主要優點之一,如今卻很難在仲裁程序的行為方式中被發現。如訴訟一樣,仲裁已經時常變得像一場“戰爭”:“戰爭”最初體現于當事人違反事先已被其自愿接受的仲裁機構規則,拒絕支付墊金;隨著仲裁程序的逐步開展,這場“戰爭”還體現在當事人不斷極盡駁斥對方意見之能事。
這就是當今國際仲裁的現狀。國際仲裁面臨著重大的挑戰,仲裁界人士已經意識到,若不正視種種挑戰,那么仲裁以往的成功將難以為繼,其也難以持續滿足當今國際仲裁市場的需求。尋找到克服當今國際仲裁所面臨的種種挑戰的方案并非易事,在今后一系列的國際研討會中,包括2012年7月在新加坡舉行的以“仲裁的新時代”為主題的ICCA會議,各種建議及方案將會陸續被提出來。
(二)對仲裁程序的反思
筆者個人相信,克服國際仲裁當前所面臨的挑戰,首先需要我們對所有仲裁參與者的角色、功能、責任以及互動進行反思和重新定義,以下幾點尤為重要:
1.與當前愈漸盛行的做法不同,仲裁程序的開展不應當從一開始便由律師搶先主導,而是應當由律師與仲裁庭協同決定,這一點需要貫穿仲裁程序的所有階段,包括草擬仲裁員委任條款,決定仲裁日程安排及規制仲裁的程序性規則,以及任何涉及調整仲裁日程以及推延仲裁開庭審理的決定。律師負責保護當事人的利益,而仲裁員負責做出公正的裁決,兩者之間在地位上并無從屬關系。仲裁進行的每一階段,仲裁員與律師應當全力配合,以決定所有相關問題。然而,遺憾的是,這往往并非當今國際仲裁的實踐情形。
2.當事人的代表應與仲裁程序保持更為緊密的聯系。當事人的內部法律顧問或高級代表應出席每一次仲裁庭審或電話會議,以使當事人充分知曉由他們的律師或仲裁庭所提出的建議將會產生的后果——特別是在時間與金錢方面。
3.仲裁員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比如在涉及需不需要一定的證人和專家出面質證的問題上,應扮演一個更為積極的角色,這一點得到不少人的建議。換言之,仲裁員應充分利用《IBA證據規則》(IBA Rules of Evidence)第9條所賦予的權利,排除因缺乏與案件具有充足關聯或者對案件結果無實質影響的書證、書面證言或者口頭證供(第9條a項),對上述證據的排除亦可因程序經濟上的原因而為之(第9條g項)。在任何適當的情形下,應建議律師召開由事實證人(factual witness)或專家證人(expert witness)出席的證人會議。當一切準備就緒,證人會議在各方面將極具效率,它不僅可以節省時間和金錢,而且能活躍證據的呈現這一過程,并可能在某些情形下使人們更為精確地把握案件的事實。在任何方便的情形下,仲裁庭可考慮采用其他方法,如讓專家共同協作,以促進人們更好地理解專家證據(expert evidence)。在實踐中,由當事人委任各自的技術專家,特別是會計專家,這可能由于當事人各自的戰略考慮,最終導致雙方專家各自為政,并采取完全不同的路徑對待案件中出現的相關證據問題。因此,專家共同協作模式(teaming of experts)頗值推崇:在當事人雙方提議的基礎上,仲裁庭委任兩名專家組成專家組,他們從一開始便攜手合作,共同致力于解決同一份清單上所列出的相關證據問題。
4.和解對于當事人來說總是最好的結果,從這一點出發,仲裁員應當考慮,在任何適當的情形下,建議當事人見面協商,并盡可能以和解方式結案(當然仲裁員也應意識到,在某些法域,這可能是一個敏感的問題)。仲裁員甚至可以為當事人之間協商和解提供協助,當然,這需要以當事人同意以下幾點條件為前提:首先,和解過程保密;其次,若和解不成,當事人在后續的仲裁程序中不能再援引和解過程中對方當事人的陳述;最后,當事人不會因仲裁員在前續和解過程中提供了協助而挑戰仲裁庭。所有這樣或那樣的措施都本著同一宗旨,即不僅使仲裁程序節省時間與金錢,而且使其更具透明度,并抑制影響仲裁效率的程序策略。
5.近年來國際社會所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表明,國際仲裁界已經清醒地認識到,基于國際仲裁在文化層面上具有非地域化的性質,國際社會有必要效仿業已建立的有關仲裁員的利益沖突規則及其職業道德規則,發展一套約束國際仲裁律師的行為準則。[26]在此方面,資深律師Doak Bishop最近在里約熱內盧舉辦的ICCA會議上提出了一些建議,另一方面,IBA也已成立了一個特別任務小組,專門處理這方面的問題,其目前正在針對仲裁界人士實施一項問卷調查。事實上,發布國際仲裁律師行為準則,并使其通過律師協會或仲裁機構等渠道產生約束力,以保證律師在仲裁程序中做到獨立、正直、公平和忠實的時機已經成熟,對于這一點,人們似乎已形成了廣泛的共識。
6.同樣重要的是,仲裁機構以及大學也應該采取一些其他措施:
(1)仲裁機構應反思其控制受案量的內部程序,并盡量對這些內部程序進行簡化,以保障仲裁程序在時間上的效率。
(2)大學應不僅僅向學生傳授國際仲裁理論方面的知識,還應當激發學生去思考與探索國際仲裁文化及其職業道德。這可以通過設置以“國際仲裁”為主題的研究生課程來實現,如英國、法國、瑞士、瑞典以及美國等國家的大學機構已經采取了這樣的措施。
7.最后,值得期待的是,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國家將承認其在國際仲裁中盡量做到誠實、公正的必要性,并將淡化法院在仲裁中的角色意義,避免法院阻礙仲裁程序的正當開展以及不利于本國國民的仲裁裁決的順利執行。
以上僅為有限的幾點建議。國際社會正在反思國際仲裁中存在的問題,通過筆者前面提到過的“觀念的相互融通”(cross-fertilization)這一過程,以后將有更多的方案與意見陸續呈現。
七、結語
全球化促進了國際仲裁的發展,并使其取得了成功。仲裁已不再停留在50年前僅為法院正義的一種獨特替代,它已走向了成熟,并獲得了自治。倘若我們能夠成功克服當今仲裁所面臨的挑戰,那么,在未來,仲裁一樣能夠延續昨日的成功。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即所有一切都必須建立在仲裁參與者對他們的角色與責任進行反思,并接受其在功能模式上的某些轉變的基礎上。惟其如此,仲裁才能在未來幾十年里繼續擔當國際商務的“自然法官”這一角色。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 a Global Economy: The Challenges of the Future
By Bernard Hanotiau
The forces of globalization have generated an increased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contracts, which in turn have resulted in an enormous increase in complex commercial disputes. These forces have fuele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s the preferred choice of businessmen for the resolution of their disputes. They have further led to a denationalization of arbitration, both procedurally and substantively, as well as to a convergence of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institutional rules, based on a consensus on a greater liberalization of the process. The forces of globalization have also opened the door to the application by arbitral tribunals of gener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 common to all nations, and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ulture. Beyond its succes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s facing today many challenges. There is an increased concern over its judicialization, its time and cost efficiency, and various ethical issues. What can be done to overcome these challenges, and make sure that arbitration will continue to offer the qualities and advantages that have been the keys to its succes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allenges
*本文原標題為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 a Global Economy: The Challenges of the Future,原載于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Vol. 28, No. 2. (2011)。本文的翻譯與發表已得到原作者的授權,在此,謹致謝忱。宋連斌教授對譯文進行了仔細的校對,并提出了相當中肯的修改意見,在此,亦深表感謝。
**Bernard Hanotiau,世界著名仲裁專家,比利時魯汶大學教授,國際商事仲裁委員會(ICCA)成員,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顧問。
***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博士生。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內外多家仲裁機構仲裁員。
①關于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及其對仲裁的影響,請特別參見Katherine Lynch,(2003); Reza Banakar,and Anthony G. McGrew,, in325, 347(Volkmar Gessner &Ali Cern Budak eds., 1998); and Karim Youssef,
②Lynch, supra note 1, at 64.
③On this issue, see, e.g., J. Lew, Application Law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ch. 2 (1972) .
④See on this principle Youssef, supra note 1, at 342 et seq.
⑤Lynch, supra note 1, at 167.
⑥譯者注:迄今,已有147個國家批準了該公約。
⑦On this issue, see P. Binde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 UNCITRAL Model Law Jurisdiction (2000), and in particular the comparative charts at ch.10.
⑧Omnium de Traitement et de Valorisation v. Hilmarton, Judgment, June 10, 1997, 1997 Rev. Arb. 376 and note Fouchard, and 22 Y.B. Com. Arb. 696 (1997).
⑨P.T. Putrabali Adyamulia v. Rena Holding, Judgment, June 29, 2007, 2007 Rev. Arb. 507.
⑩Rosnefe/Yukos, Netherlands Supreme Court, June 25, 2010 (LJN:BM1697).
?參見《瑞士聯邦國際私法》第192條。
?參見《比利時司法典》地1717條第4款。
?參見《突尼斯仲裁法》第78條第6款。
?參見《瑞典仲裁法》(1999年)第51節。
?1 Y.B. Com. Arb. 205 (1976).
?S.A. Thalès Air Defense/GIE Euromissile, November 18, 2004, 2005 Rev. Arb. 751. See, e.g., on this decision D. Besaude, Thalès Air Defense B.V. v. GIE Euromissile: Defining the Limits of Scrutiny of Awards Based on Alleged Violations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22 J. Int’l Arb. 239 (2005).
?《瑞士聯邦國際私法》第192條第177款規定:“任何涉及財產之糾紛皆可提交仲裁解決。”;《德國民事訴訟法典》第1030節(譯者注:《德國民事訴訟法典》第1025節至第1066節對“仲裁程序”作出了規定)。
?例如,1988年8月5日頒布的《保加利亞仲裁法》第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3條。
?例如,《比利時司法典》第1676條第2款,《法國民法典》第2060條。
?例見,《瑞士聯邦國際私法》第177條第2款。
[21]關于 ICC仲裁規則,see Y. Derains & E. Schwartz, A Guide to the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2d ed. 2005).
[22]IBA Guidelines 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pproved on May 22, 2004 by the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23]IBA Guidelines on the Taking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dopted by a resolution of the IBA Council, May 29, 2010.
[24]On this issue, see F. De L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and Lex Mercatora (1992); K.P. Berger, The Creeping Codification of Lex Mercatoria (1999); K.P. Berger, The Practice of Transnational Law (2001); Lynch, supra note 1 , ch. 7.
[25]M. Hunter & T. Landau, The English Arbitration Act 1996 129 n. 79 (1998).
[26]Doak Bishop & Margrete Stevens, The Compelling Need for a Code of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Transparency, Integrity and Legitimacy,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ICCA meeting in Rio de Janeiro, May 2010.
(責任編輯:余蕊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