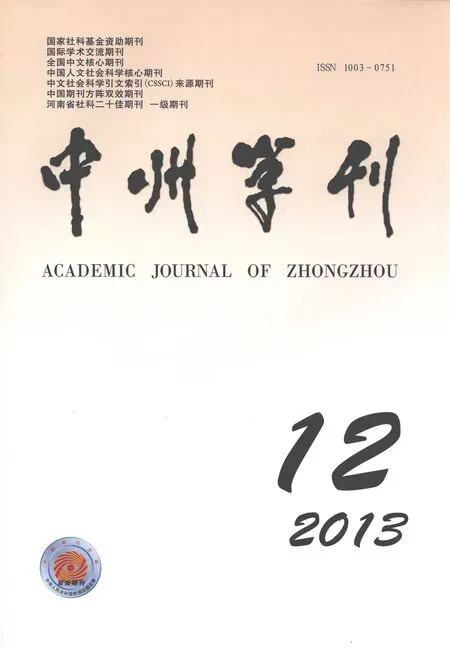被放逐的資本主義及其文化悖論*
陳緒新 吳豫徽 丁婷婷
瑞士學者漢斯·昆認為,“現(xiàn)代”這個術語,“最初用于17世紀法國啟蒙主義,它用以表明西方由懷舊的文藝復興階段進展到一個充滿樂觀向上精神的歷史時期”①。也就是說,“現(xiàn)代”作為西方世界的一個歷史分期,是從16世紀末17世紀初開始的。“現(xiàn)代性”意指現(xiàn)代社會的基本屬性,它包含了一整套相互關聯(lián)的基本觀念和價值原則。“現(xiàn)代”是與西方中世紀的“傳統(tǒng)”相對立而言的。在中世紀,上帝是那個時代的基本觀念和價值本源,《圣經(jīng)》是一切知識的源泉和行動的指南。真理、道德和價值統(tǒng)統(tǒng)源出于上帝和他的圣訓。事實上,隨著社會世俗化的發(fā)展,上帝早在15世紀左右就開始遭到歐洲人的冷漠甚至批判,以至于最后尼采宣稱“上帝死了”②。
一、上帝從神龕步入塵世后人性的被放逐
上帝真的死了嗎?文藝復興之后席卷整個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并非意味著宗教對日常生活控制的廢除,而是以一種全新的控制方式代替舊的控制方式,那就是上帝逐漸從超驗的“神龕”上走下來,步入尋常百姓家。在這場轟轟烈烈的宗教或道德的世俗化運動中,上帝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供基督徒們頂禮膜拜的神,它開始駐進人們的心靈,實現(xiàn)了人與神的統(tǒng)一。上帝沒有真的“死去”,上帝變成了“我自己”。上帝從超驗的世界走向世俗的生活,“敬神如神在”,就如同“人人皆可為堯舜”、“涂之人皆可為禹”、“人人皆可為佛”一般。塵世生活的普通人也似乎找到了使自己的行為能夠遵循某種前后一致的道德規(guī)范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行善”,即帶著“為上帝增添榮耀”的意圖行事,使人們從“自然狀態(tài)”變成“蒙恩狀態(tài)”,從而賦予世俗活動(主要是職業(yè)勞動)以宗教和文化的意義,適度緩解了新基督徒們創(chuàng)造財富的沖動與基督教禁欲主義之間存在的心理張力。從此,經(jīng)濟合理主義成為資本主義的精神內(nèi)核。
隨著天國的帷幕徐徐拉上,原來毫無遮蔽的人的心靈也不得不封閉起來。人們對幸福和自由的追求也作了相應的調(diào)整:由主要從上帝那里領取“配享”的愛和關懷轉(zhuǎn)變?yōu)橄蜃匀弧⑾蛩恕⑾蛏鐣魅∠硎芎涂鞓罚瑥娜偵系坜D(zhuǎn)向取悅人、利用人。然而,自然能提供給人們的物質(zhì)財富是有限的,并且取悅人又是彼此相互的,有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這種新的生活方式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惡性競爭、人與自然的根本對立和身與心的分割背離。人們由此失去了上帝庇護下的平靜和恬淡,內(nèi)心充滿著難以擺脫的存在性孤獨與安全性焦慮。
一是新的世界秩序使人從服從上帝和君主的意志轉(zhuǎn)向服從數(shù)學化的客觀規(guī)律和社會的總體需要,人的感性和個性的需求被遮蔽和壓抑著。與此同時,反抗也相伴而來。當樂觀向上的激情一旦在夢中被減弱,那么來自“無意識”(弗洛伊德語)底層的巖漿就必將開始燒灼著忙碌一天的現(xiàn)代人的神經(jīng)。
二是“隨著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增長,制度支配人的權力也在同步地增長”③。在世俗化的現(xiàn)代人把天國的享樂看作是虛幻的自欺之后,他們就把現(xiàn)實生活的享樂視為人生的首要追求。這種享樂生活引起的生存競爭,在“凱恩斯消費主義”的推波助瀾下,把現(xiàn)代人帶入了一個生產(chǎn)—消費—再生產(chǎn)的“單向度的社會”。當人們正試圖帶著愉快的心情開始新的生活時,卻又發(fā)現(xiàn)自己不知不覺中被現(xiàn)代化的大生產(chǎn)線束縛著。剛剛擺脫了對原罪和地獄的恐懼的人們,又重新被效率所左右,被突飛猛進的科學技術所裹挾,被所謂的民主政治(溫和的專制主義)所操控。
三是現(xiàn)代人不得不選擇呆在“牢籠”里——如果不情愿的話,我們將寸步難行。“科學”這種有著“真理桂冠”的話語又被整合到政治、經(jīng)濟等話語中,成了政治活動和經(jīng)濟生活合法化的辯護詞,人們逐漸失去了對現(xiàn)實的批判意識,變得麻木不仁,隨波逐流,在責任和擔當面前選擇了“理性的無知”。人們滿足于社會提供的需求,同時又被社會不斷制造的虛假需求所牽引,現(xiàn)代人就是在需求的滿足和對新需求的癡迷中消耗著高昂的主體和主體意識。
直到20世紀下半葉,現(xiàn)代人和現(xiàn)代社會才開始對理性、科學、現(xiàn)代性進行批評性反思,反思的結果就是催生了西方的“后現(xiàn)代思潮”。后現(xiàn)代思想家在反思中發(fā)現(xiàn)了西方現(xiàn)代性及其道德謀劃存在如下的道德悖論:一方面,既然自然被認為是其自行規(guī)律長期進化的結果,現(xiàn)代人對它的秩序應當持守一種虔敬和尊重的態(tài)度,那么對它的大規(guī)模控制和改造就意味著對自然和諧的破壞;另一方面,如果奉行一種樸素無為的價值觀的話,那么同樣由自然進化而來的人和他的理性能力為何又要壓抑自己呢?在反思現(xiàn)代性的過程中,康德的思想重新又被重視起來:限制理性,為宗教和道德法則留下一些地盤。
科學爭奪了宗教的“真理的桂冠”,并發(fā)展成為西方現(xiàn)代性過程中的一個根本現(xiàn)象。科學因?qū)ψ匀坏那擅羁刂贫玫搅巳祟惿鐣臒o比青睞。笛卡爾以來的哲學使命就是為科學作真理性辯護的。然而事與愿違,不僅哲學的這種努力沒有成功,而且在科學劃定的秩序——自然秩序、社會秩序、道德秩序——下生活的現(xiàn)代人又遇到了新的焦慮和困惑。“上帝死了”之后,人類就從未停止過對現(xiàn)代性及其道德謀劃的反思。可以這么說,“后現(xiàn)代思潮”不是什么新鮮事物或理念,它只不過給人類對近現(xiàn)代以來自身發(fā)展過程進行反思賦予了一個新的名詞,而且是一個有別于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性的“現(xiàn)代性稱謂”罷了,不存在對現(xiàn)代性的否定、懷疑和消解。
在后現(xiàn)代思潮那里,“上帝之后”的西方現(xiàn)代性及其道德謀劃又是一幅怎樣的圖景呢?簡單地說,就是人們利用現(xiàn)代科學技術,全面地改造自己生存的物質(zhì)條件和精神條件的過程,如經(jīng)濟領域的工業(yè)化、政治領域的民主化、生活方式現(xiàn)代化以及人的現(xiàn)代化等。在價值層面上,現(xiàn)代性突出表現(xiàn)為自我實現(xiàn)的個人主義突顯與張揚、工具主義理性的勃興與延展、自由民主的歷史進步觀的發(fā)起與實踐。現(xiàn)代性理論及其實踐,一方面使西方世界以前所未有的動力和勇氣擺脫了中世紀的黑暗統(tǒng)治,從自然的束縛和封建專制統(tǒng)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在科技革命推引下,創(chuàng)造了人類豐富的物質(zhì)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另一方面也導致現(xiàn)代西方社會的個人利益至上主義、技術統(tǒng)治和相對溫和的專制主義。
不止如此,作為西方現(xiàn)代性及其道德謀劃的產(chǎn)物,文化傳統(tǒng)及其內(nèi)蘊的價值體系被“顛覆”,社會人倫關系和人格同一性被“解構”,傳統(tǒng)的價值觀認同、社會關系認同、人格同一性認同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或“危機”。正如馬克思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所描述的那樣:“一切固定的古老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于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待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系。”④
二、道德理想被放逐后貼上了個人主義標簽
伴隨著西方現(xiàn)代性的降臨,與人們生產(chǎn)和生活息息相關且真實的道德與理想正在被低級、放縱的個人主義的庸俗形式所遮蔽。被冠之以“自我實現(xiàn)”美名的個人主義,采取文化中立和價值寬容的態(tài)度立場,信奉“一個自由社會必須在關于善的生活由什么構成的問題上保持中立”⑤。個人主義選擇“自我實現(xiàn)”而不再考慮真實的道德和理想,它主張:一方面每個人都有一個屬于自己的獨一無二的原創(chuàng)的做人方式,都有關于自己之所是、之所在和之所為的價值判斷;另一方面,每個人都與他人密切關聯(lián),“自我實現(xiàn)”可以相互成就。⑥故而,傳統(tǒng)意義上的道德和理想就失卻了它的價值魅力,甚至沒有了存在的必要,只剩下人與人之間的“互利共贏”。
通過“解構”早已固定成型的文化與約定俗成的制度模式和慣例,并使其從道德要求的中心里轉(zhuǎn)移出來,現(xiàn)實生活完成了與道德理想的脫離和對立。其結果就是形式、方式獲得了獨立性和尊嚴,生活的本真、意義和價值被虛擲。脫離了意義和價值,個人主義蛻變?yōu)橐宰晕覟橹行牡摹白詰僦髁x”,科學主義蛻變?yōu)楣ぞ呃硇灾髁x,民主政體蛻變?yōu)榭膳碌摹熬薮蟮谋O(jiān)護權力”,溫和的專制主義以輕柔、舒緩的方式剝奪了人們的自由。對真實的道德和理想的解構、對“人類中心論”的癡狂,產(chǎn)生了這樣一種可怕的后果:“通過摧毀一切重要意義視野,用意義的喪失以及由此而使我們處境瑣碎來威脅我們。在某個時候,我們把自己的處境理解為高度悲劇性的,孤獨地處在一個死寂的宇宙中,沒有內(nèi)在意義,被判定要去創(chuàng)造價值。但隨后,這個相同的學說,憑其固有的偏好,產(chǎn)生了一個平庸的世界,其中不存在什么很有意義的選擇,因為不存在任何重要的問題。”⑦
現(xiàn)代人從傳統(tǒng)的具有濃厚情感和人格色彩的具體場景或情境中抽身出來,逐漸從人格的真實統(tǒng)一性、共同體的完整性以及文化的價值共享中抽身出來,不僅具體的人和他的生活被抽象化了,人們所寄身其中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組織也被抽象化了。雖然現(xiàn)代性所開辟的使人獲益的可能性、創(chuàng)造財富的經(jīng)濟沖動力超越了它的負面效應,但是,現(xiàn)代社會和現(xiàn)代人從未停止過對現(xiàn)代性的反思,特別是道德哲學家和社會學家。馬克思認為,階級斗爭是資本主義秩序中產(chǎn)生根本性分裂的根源,同時他還設想了一種更為人道的社會體系即共產(chǎn)主義社會體系。法國著名社會學家涂爾干則相信,工業(yè)主義的進一步擴張能夠建立一種和諧而完美的社會生活,并且這種生活將通過勞動分工與道德個人主義的結合而被整合。只有馬克斯·韋伯最為悲觀,他把現(xiàn)代世界看成是一個自相矛盾的世界,人們要在其中取得任何物質(zhì)的進步,都必須以摧殘個體創(chuàng)造性與自主性的官僚制的擴張為代價。即便如此,韋伯終其一生都在為自由資本主義做文化或道德合理性辯護。
在自我實現(xiàn)的個人主義價值觀的驅(qū)策下,西方現(xiàn)代性始終秉持“非此即彼”的“主客二分”價值原則,“以自我為中心”,漠視“他者”的存在及意義,使得“自我”與“他者”出現(xiàn)分離,標榜著“自我”對“他者”的征服、侵略和掠奪。依循“一往直前”的生存邏輯,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真實的自相矛盾的世界,并勾勒出這樣一幅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主導下的現(xiàn)代人的生活圖景:每個人都仿佛真實地生活在心靈的孤島上,被孤寂、恐懼和莫名的無奈籠罩著,周圍只有茫茫無際的大海。大海給予人們以希望,卻又性情暴戾,總有一天會將人們徹底地拋棄或淹沒。遭受這種孤寂之苦的人們卻又因此而愈加孤寂、恐懼和無助,并最終將自己封閉在自己的世界里。現(xiàn)代人在自然、他人和自我的挑戰(zhàn)面前,忙于應付,疲于奔命。“前工業(yè)社會——這仍然是今日世界大部分地區(qū)的狀況——其主要內(nèi)容是對付自然界”,“工業(yè)社會,由于生產(chǎn)商品,它的主要任務是對付制作的世界”,“后工業(yè)社會的中心是服務——人的服務、職業(yè)和技術的服務,因而它的首要任務是處理人際關系”。⑧人類無休止地與身外之物展開競爭,只知一味地向前,卻遠離了實存。個體迷失了自我,社會迷失了方向,心靈得不到皈依,現(xiàn)代人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存在性孤獨和焦慮。
三、個人被放逐后的存在性孤獨與焦慮
資本主義文化主導下的現(xiàn)代社會,宗教和道德世俗化,不僅使道德理想因被貼上個人主義標簽而變得低級庸俗,而且會使現(xiàn)代人因為對人與自然關系及其意義、人與人關系及其意義、人與自身關系及其意義的認識論危機,出現(xiàn)前所未有的存在性孤獨以及安全性焦慮。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焦慮和渴望,可以說,現(xiàn)代人的焦慮是對前途未卜的存在性焦慮,現(xiàn)代人的渴望是對自我認知的渴望。自我實現(xiàn)的個人主義,使得自由的現(xiàn)代人為了各自的權利或利益之需,借助于一種我們名之為“契約”這一工具形式,組建了一個利益攸關的共同體——市民社會。然而生活在市民社會里的人們往往是因為權宜之計而形式地結合在一起,當雙方或者一方的利益獲得滿足之后,緊隨其后的便是醉酒的癡狂。醉狂后的空虛、放逐后的孤獨、莫名的憂傷相繼襲來。醒來之后,空虛、孤獨和憂傷隨即又被新的欲望和需要沖淡。可以這么說,陌生的現(xiàn)代人比以往任何時代的人們都更為迫切地渴望知道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將到哪里去?正因為如此,后現(xiàn)代思想家呼吁,現(xiàn)代人和現(xiàn)代社會“應該在思想上重建在社會上被消滅了的、打碎了的、被分散在部分性體系中的人”,這樣做的目的或理由是,“人作為自身完美的總體,他內(nèi)在地克服了或正在克服理論與實踐、理性與感性、形式與內(nèi)容的分裂;對他來說,他要賦予自己以形式,這種取向并不意味著是一種抽象的、把具體內(nèi)容扔到一邊的理性;對他來說,自由和必然是同一的”⑨。
現(xiàn)代人和現(xiàn)代社會之所以會出現(xiàn)有關“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向何處去”等一系列自我認知的困惑,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存在性孤獨感和焦慮,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資本主義結構范式主導下的現(xiàn)代社會抽象體系(比如商品市場和貨幣資本)的極度擴張改變了傳統(tǒng)社會關系的友誼般性質(zhì)。西方現(xiàn)代性及其道德謀劃造就了這樣一個我們實際生活的鏡像:“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搖擺不定,內(nèi)心存有某種麻木不仁,精神深處出現(xiàn)了理想和取向的空白,以致我似乎忘記了該怎樣去過一種人的生活。”⑩現(xiàn)代人——即使是在最先進的社會里——的人際關系與農(nóng)業(yè)社會相比,不僅出現(xiàn)了布萊克在《比較現(xiàn)代化》中所描述的明顯淡漠、親切感和聚合力不強以及個人具有一種難以衡量和估計的孤獨感,更為危險的是,現(xiàn)代人心理的基本邏輯就是“移情”(西方心理科學一個最為重要的主題),即轉(zhuǎn)移自己的良好的或不良的情緒狀態(tài)或能量,這種邏輯必然導致人性的向外擴張,從而達至人與人之間的持續(xù)永恒的斗爭。征服、掠奪、索取成了他們?nèi)诵院蜕鐣l(fā)展的主旋律。
現(xiàn)代人、現(xiàn)代社會之所以會出現(xiàn)前所未有的存在性孤獨感和焦慮,也是因為現(xiàn)代性及其道德謀劃使得現(xiàn)代人從傳統(tǒng)文化、從以真實的美德和人倫關系為基礎的生活情境中走出來,失卻了傳統(tǒng),離開了家門,打著自我實現(xiàn)的個人主義借口,一味地追求著時尚和潮流,爭先恐后,誰也不會自甘落后。不僅如此,時間效率、瞬間滿足、生產(chǎn)與消費最大化、社會關系的工具化以及通過商業(yè)電視和網(wǎng)絡新媒體等傳遞給我們的“文化碎片”,不能為現(xiàn)代人和現(xiàn)代社會提供完整的關于人與自然、人與人或人與社會、人與自身關系問題一致的、有深度的答案。“信仰不再成為可能。藝術、自然或沖動在酒神行為的醉狂中只能暫時地抹殺自我。醉狂終究要過去,接著便是凄冷的清晨,它隨著黎明無情地降臨大地。這種在劫難逃的焦慮必然導致人人處于末世的感覺。”(11)
四、經(jīng)濟被放逐后不見了斯密的“同情心”
現(xiàn)代主流經(jīng)濟學家只見亞當·斯密的“自私”和“精明”,而不見他的“友善”和“同情心”。印度裔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經(jīng)濟學與倫理學》開篇伊始就對現(xiàn)代主流經(jīng)濟學的“道德貧困化”或“倫理不涉”給予良多關懷。(20)他認為,秉持標準行為假設和“帕累托最優(yōu)”的現(xiàn)代主流經(jīng)濟學家,即便作為個體的他們一定會表現(xiàn)出實足的友善,但是在其積極建構的經(jīng)濟模型中,卻假設人類行為的動機是純粹的、自私的,以保證其模型不會受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一書中所崇尚、宣揚的內(nèi)心的友善、同情心和行為的合宜性等道德情操的干擾。經(jīng)濟學家和其他領域的專家一樣,幾乎棄絕任何的“感情用事”。因此,為了純粹理性的研究,為了能在實驗室里推算和建構自己的“效用函數(shù)”或經(jīng)濟模型,他們不得不把復雜的事情搞簡單了。人類社會因標準行為假設而變成了一個典型的泰勒主義式的工作流程,變成了一個不停運轉(zhuǎn)的“機器”,每個人實際上成了這個機器系統(tǒng)的“零部件”甚或是一個“螺絲釘”。
事實上,被后人視為古典主義經(jīng)濟學或者自由主義經(jīng)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在當時的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卻是以邏輯學教授和道德哲學教授為名義執(zhí)掌教鞭和開展研究的。他一生的主要著作有兩部:一部是《道德情操論》(1759年),另一部就是奠定了近代經(jīng)濟學學科基礎的《國民財富的性質(zhì)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以下簡稱《國富論》)。也許正是出于害怕后人或者他的尾隨者們對他本人、對他的研究成果以及他的信仰產(chǎn)生誤解的考慮,亞當·斯密“處心積慮”的先出版了《道德情操論》,18年后才正式出版《國富論》,雖然后者影響力遠遠大于前者。事實上,比起重視《國富論》來,斯密似乎也更重視自己的《道德情操論》。《道德情操論》不僅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也是他在逝世前的最后幾年里竭盡全力進行修訂的一本書,他在身患重病、知道自己已經(jīng)時日無多的情況下,對這本書進行了最重要的一次修訂,這說明了倫理學在斯密心目中的地位。對于道德真理的探討在斯密那里是貫穿始終的,正如《亞當·斯密的生平與著作》的作者斯圖爾特所說:“這些崇高的真理在他年輕時離開學院之際,第一次激起了他的天才的熱情,他最后的精神努力也是寄托在這方面的。”(13)然而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斯密本人卻被他的崇拜者們尊稱為“自利的宗師”。或許是因為斯密的尾隨者們引用最多的一段話就是:“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我們自己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好處。”(14)
客觀地講,也不乏一些經(jīng)濟學家引斯密為典范,認為經(jīng)濟學家也應關心道德問題,諸如諾斯、奧康納、阿瑪?shù)賮啞ど热恕5豢煞裾J的是,斯密以后絕大多數(shù)的經(jīng)濟學家——相當一部分是斯密的尾隨者——卻只見斯密《國富論》中的“自私”和“精明”,而不見了他《道德情操論》中的“良心”、“同情心”和“行為的合宜性”。那么,現(xiàn)代主流經(jīng)濟學家包括亞當·斯密的尾隨者們?yōu)槭裁磿灰姟熬鳌倍灰姟巴樾摹蹦?我想緣起不過有三點:一是近現(xiàn)代以來基于牛頓力學的機械論占據(jù)主導地位,其他學科領域的話語權完全或者部分地服從和服務于機械論者;二是經(jīng)濟學家的主觀故意,因為經(jīng)濟學家們迫于生存和學科發(fā)展的需要,往往不得不依附在資本家和政治家身上,為資本家和政治家搖旗吶喊,獲得政治的袒護和經(jīng)濟的資助,經(jīng)濟學家失卻了人格的完整和研究的自由;三是經(jīng)濟學家們“鐘情于”模型經(jīng)濟學,他們喜歡或者習慣于運用二元函數(shù)建構屬于自己的經(jīng)濟模型,通過這樣的研究方式和路徑研究出來的成果往往更容易為人們所接受,更容易說服人,更具有科學理性的一面。當然也就更加遠離生活,遠離普通勞動者和普通人,經(jīng)濟學變成了經(jīng)濟學家的專利,或者說是少數(shù)專家壟斷了經(jīng)濟學。此外,近現(xiàn)代以來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幾近為科學理性主義所主宰,政治生活和經(jīng)濟生活也不能例外。
一言以蔽之,在現(xiàn)代主流經(jīng)濟學的辯護下,在資本家們經(jīng)濟沖動力的驅(qū)策下,在現(xiàn)代民主政府的政治偏袒和保護下,昔日的自由市場經(jīng)濟像一匹“脫韁的野馬”,任意馳騁。現(xiàn)如今,這匹“脫韁的野馬”變成了一頭“跛足的驢”,而且可能是一頭拉也拉不回的犟勁十足的驢。
五、“牢籠”中的現(xiàn)代人變得麻木不仁
文藝復興運動以降,西方世界沿著人類中心主義的文化方向和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路向,揮舞著人類認識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旗幟,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和操控下,在科技革命的大力推引下,再加上現(xiàn)代民主政府強有力的干預,本著“為義務而盡義務”的“天職”倫理觀念、“時間就是金錢”的職場倫理精神、“誠實就是上策”的合理經(jīng)濟行為,以及韋伯自以為新覺的資本主義精神內(nèi)蘊甚至是固有的新教禁欲主義的價值關懷(15),形成了技術或知識、財富或經(jīng)濟以及政府或官僚三位一體、互為支撐的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結構范式。
在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結構范式的主導下,“經(jīng)濟人”的生存邏輯就是所謂的“帕累托最優(yōu)”,其實質(zhì)就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以他人的利益最小化為前提。資本家和企業(yè)家為了追求豐厚的利潤,常常打著“為上帝造物”的旗號;政治家和官僚為了募集政治資金,常常借著“為公共福利”的美名;科學家和知識分子為了祈求可憐的研究經(jīng)費甚至是養(yǎng)家糊口,常常以“人類自由和解放”先行者自居。殊不知,對金錢、財富、地位和話語霸權的盲目崇拜和追求,使得原本應該為了“增加上帝的榮耀”的資本家、為了“增進全人類公共福利”的政治家、為了“助推人類自由和解放事業(yè)”的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不但未能走出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一手炮制”的“牢籠”,也未能走出古典經(jīng)濟學家所提出的、現(xiàn)代主流經(jīng)濟學故意曲解或誤讀的“經(jīng)濟人假設”的園囿。
資產(chǎn)階級民主政府既是為了贏得選舉的善款、政治傭金、微薄的公共福利金,也是為了狹隘的GDP的數(shù)字增長,而不得不任由出資人的擺布,甚至在政策上故意偏袒為其選票提供政治傭金的財團。因此,像美國出現(xiàn)的次貸危機、法國銀行的內(nèi)部丑聞、韓國出現(xiàn)的政治黑金就不足為奇了。教育、科技和傳媒為了獲取和鞏固有限發(fā)展權,為了獲得必要的資助,同時,從業(yè)人員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忘卻和違背自己的信念、信仰,從價值中立的立場出走,一味地迎合市場,迎合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教育產(chǎn)業(yè)化,科技市場化,傳媒商業(yè)化,最終的結果是教育成為有錢人的專利,專家知識分子成為商家的鼓吹手或幫兇,傳媒成了生產(chǎn)性企業(yè)和商業(yè)企業(yè)推銷自己產(chǎn)品和服務的平臺。
生活在現(xiàn)代社會——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主導下的和資本主義社會結構范式宰制下的——現(xiàn)代人,情愿或不情愿地選擇呆在“技術—經(jīng)濟—政治”三位一體、共同打造的“牢籠”之中。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結構范式中,人們由于認知的有限和個體力量的弱小與無助,而將自己的權利和權益拱手交給了那些他們自認為值得信賴而且也是不得不信賴的“守夜人”和“牧羊人”,希冀著“守夜人”和“牧羊人”能夠盡心盡力地看護好他們的家園,經(jīng)營好他們的土地,用好管好他們的錢財,真心實意地維護好、實現(xiàn)好、發(fā)展好他們這些“羔羊”的最根本利益。然而事與愿違的是,“守夜人”打著為人們“守夜”的旗號,偷雞摸狗,侵犯人們的利益;“牧羊人”打著“牧羊”的旗號,出賣羔羊,從他們身上榨油,從他們身上賺錢。當華爾街神話轟然倒塌,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的時候,人們才頓然發(fā)現(xiàn),自由市場經(jīng)濟這匹任意馳騁的“脫韁的野馬”現(xiàn)如今卻變成了一頭“跛足的驢”,一頭犟勁十足、拉也拉不回來的驢;人們才捫心自問自己到底應該相信誰;人們也才意識到因為“情愿”選擇——“不情愿”的話,人們將寸步難行——呆在“牢籠”之中而變得麻木不仁,只好任人擺布和宰割;人們也因此才豁然開朗地覺察到,原來經(jīng)濟學離他們很遠,它只不過是少數(shù)經(jīng)濟學專家的案頭擺設,而又被“從牛身上榨油,從人身上賺錢”的資本家們奉為“圣經(jīng)”。
六、結語
自然資源的消耗殆盡、自然環(huán)境的惡化消退,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因財富、技術和官僚政治的操控性而變得更加沒有人情味,沒有了人的真實性。人類在享有著前所未有的物質(zhì)生活的豐腴的同時,卻不得不忍受著因純粹的經(jīng)濟沖動、商品拜物和社會關系的工具化所帶來的心靈無比脆弱、相互猜忌和不信任。反思西方現(xiàn)代性及其道德謀劃的基本路向,規(guī)勸現(xiàn)代社會和現(xiàn)代人,使人類社會的現(xiàn)代性和它的道德謀劃重新回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與人和諧共存、身與心和諧共進的科學理性的軌道上來。故此,當下中國應該吁求一種全新的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模式,實現(xiàn)包容性增長。這種新的發(fā)展模式,追求適度而不是更多;這種新的發(fā)展模式是“以人為本”的,其發(fā)展的成果應該照顧到“最少受惠者(社會弱勢群體——筆者注)的最大利益”;這種新的發(fā)展模式充分考慮到滿足基本需求和確保長期安全的同等重要性,充分考慮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繁衍與人類自身發(fā)展進步的同等重要性,充分考慮到滿足當代人需求與照顧子孫后代生存權利的同等重要性。
注釋
①[瑞士]漢斯·昆:《神學:走向后現(xiàn)代之路》,王岳川主編《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與美學》,包利民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59頁。②[德]弗里德里希·尼采:《上帝死了》,戚仁譯,三聯(lián)書店,2007年,序言。③[德]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曹衛(wèi)東譯,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第76頁。④[德]馬克思、恩格斯:《共產(chǎn)黨宣言》,中央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31頁。⑤⑦[加拿大]查爾斯·泰勒:《現(xiàn)代性之隱憂》,程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9、78頁。⑥魏治勛:《真實性、解構及其法治——析查爾斯·泰勒的社群主義法治觀》,《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07年第9期。⑧ (11)[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嚴蓓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9年,第101、97頁。⑨[德]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曹衛(wèi)東譯,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頁。⑩[美]史蒂芬·羅:《再看西方》,林澤銓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序言。 (20)[印度]阿馬蒂亞·森:《倫理學與經(jīng)濟學》,王宇等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8 頁。 (13)[英]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樊冰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譯者序言。 (14)[英]亞當·斯密:《國富論》上卷,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26—27頁。 (15)[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彭強等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