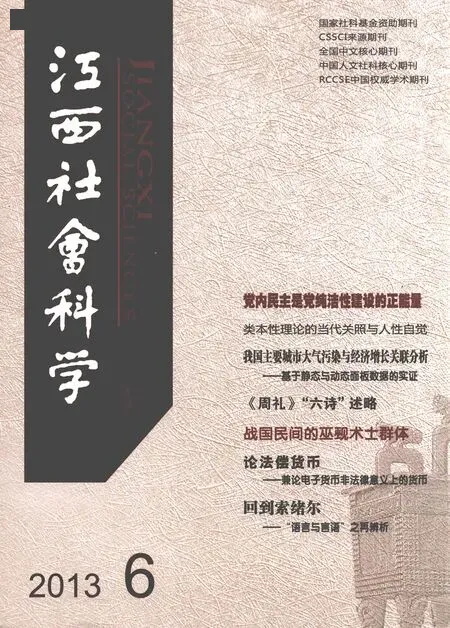《周禮》“六詩”述略
■徐麗鵑 陶水平
“六詩”蘊含了三代禮樂文化很多學術信息。“六詩”一詞見于《周禮·春官·大司樂》:大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另一處見于《周禮·春官·瞽矇》:“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系,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六詩體系與《毛詩序》提出的“六義”說有一定差別,“六義”說是在詩、樂、舞分離后才出現(xiàn)的理論,它從思想方面解釋風、雅、頌,而沒有道及音樂性質(zhì),這種意義的闡釋是《詩大序》“詩教”的產(chǎn)物,顯然要晚于《周禮》。“六詩”到底是什么?《周禮》并未講明,后人的理解也有很多爭議。
一、六詩研究概論
現(xiàn)存最早研究“六詩”的是鄭司農(nóng),他明確將比、興釋為詩法,認為孔子之前就有《風》、《小雅》、《大雅》、《頌》,沒有比、興。《論語》曰:“吾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孔子正樂時正出比、興,鄭司農(nóng)將“六詩”與“六義”同等齊觀,混淆了兩者差別。除此,關于《六詩》有很多解釋,大致分述如下:
(一)六詩皆體說
雖都持六詩皆體之說,但又有所不同。而且賦比興三詩是否存在,又各執(zhí)一詞。鄭玄揉合《詩大序》的“六義”說,著眼于“六詩”的內(nèi)容與寫作方法進行解釋,認為賦、比、興作為詩篇是存在的,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鄭玄注《周禮》“六詩”帶有明顯政教色彩。宋代王質(zhì)同樣認為詩本是有六體的,不過今賦、比、興三詩皆亡。章太炎在《檢論》中倡導賦、比、興與風雅頌同為詩之六體,認為賦的形式是“不歌而誦”,即不能被之管紋,只能吟誦;“比者,辯也”,“其文亦肆,不被管弦與賦同”,故被排除在周代的樂歌與孔子的《詩三百》之外;“興”相當于述贊一類,因為“篇第填委,不可遍理,又亦不益教化”,所以孔子依自己的編詩體例,未曾選入。章太炎打破經(jīng)學傳統(tǒng),將其轉(zhuǎn)變?yōu)槭穼W問題,但其說法違反了舊時分類遵循用統(tǒng)一標準進行的原則,又因無據(jù)而被視為臆斷。
朱自清提出鄭玄注六詩是重“義”時代的解釋,他推斷六詩皆樂歌,以聲為用,大概“賦”是合唱,“比”也是樂歌名,變舊調(diào)唱新辭。“興”也本是樂歌名,疑是合樂開始的新歌。[1](P71-77)朱自清的解說屬于大膽臆測,沒有論據(jù)和論證。當代郭紹虞對章太炎的說法進一步修正,把賦、比、興三體由章太炎所說的大史所記官方文獻改為民間詩歌,指出:“其入樂者則稱為風,還有許多不入樂者則稱為賦比興。”[2]因不合樂,賦比興被孔子刪去。郭氏之說關注民間俗樂,為六詩研究拓寬了思路,但因民間詩歌通體用賦、用比、用興的很少見,對其原因也沒有進一步論述,所以也被視為臆測。
除此,魏炯若、蕭華榮都認為六者一樣皆為詩體。當代歷史學家周策縱否定孔子刪賦比興三體詩,葉桂桐曾指出:“六詩”之“詩”是《詩經(jīng)》成書之前,或《詩經(jīng)》編定時代的全部詩歌,即不限于《詩經(jīng)》中的詩歌。總之,六詩皆體說雖多但又不同,且賦比興三詩是否存在,又各執(zhí)一詞。實際上,早期詩、樂、舞不分,在體用兼并的基礎上,人們更多注重詩樂的使用功能。上古時期還沒有很清晰的文體區(qū)分意識。
(二)三體三用說
體用相分的說法在鄭玄那已經(jīng)有所呈現(xiàn),后世很多說法都持這種觀點。如西晉摯虞、南朝劉勰、梁鐘嶸,最明顯的是孔穎達和朱熹的三“體”和“三經(jīng)”、三“用”和“三緯”之說,這與鄭玄的政治教化說大異其趣。元人楊載也提出賦比興詩之法混合于風雅頌詩之體中,總謂之六詩。這些說法都分割了詩與樂舞在上古的同源關系,使得“六詩”向“六義”學說轉(zhuǎn)變。
當代魯洪生根據(jù)春秋戰(zhàn)國教詩、用詩、論詩的具體情況分析,提出風、雅、頌最初是由于用于不同的典禮而進行的分類,賦、比、興則是對賦詩言志的用詩方法以及用詩全過程的總結(jié)概括。[3]這種說法實際也只是將賦比興作為“三用”看待。劉麗文在《〈周禮〉“六詩”本義探》中對六詩的功用和順序進行了細致和較合理的分析,認為大師作為王官,其所教不僅僅只是技術,更主要的是詩在祭祀或其他典禮上的使用語義和內(nèi)涵。只是劉文解釋實質(zhì)仍體現(xiàn)“三體三用”特征。“三體三用”說是對現(xiàn)存《三百篇》的最圓融的解釋,但仔細分析含義,又分明是晚出的文學觀念,它是受到后世如兩漢經(jīng)學、魏晉南北朝詩歌甚至唐代詩歌創(chuàng)作實踐洗禮的詩學觀念,同時,也違反了古時分類遵循統(tǒng)一的原則。
(三)六詩皆用說
此說繁雜各異,宋代程頤最早提出。20世紀80年代章必功進一步指出“六詩”是周代國子教學的綱領,產(chǎn)生于大師以《詩經(jīng)》為教本教國子過程,反映了周代國學“聲、義”并重的詩歌教授內(nèi)容和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的詩歌教學過程。“風”、“賦”要求熟練地歌唱詩、朗誦詩,前者以“聲”為用,后者以“義”為用;“比”“興”要求掌握詩歌義理訓練,學會以“義”為用;“雅”“頌”是正聲詩樂訓練,以“聲”為用。[4]他對六詩排序給予了一定論證,展現(xiàn)了從聲到義的流變過程,但也有牽強之處,賦比興以“義”為用,為何后世獨言“詩可以興”?
王昆吾注意到六詩的樂舞性質(zhì),指出六詩是運用于儀式上的唱誦樂舞,但它不是周代國學的教學內(nèi)容,而是西周對瞽矇樂教的六個項目。他將六詩視為儀式樂歌形態(tài)為六詩早期形態(tài)的解讀提供了重要的參照意義。不過只將“六詩”看作詩的傳述方式之分,是為樂工設立的職業(yè)技術學校的技能教學內(nèi)容,這種觀點與早期詩樂舞不分的情形相違背,其說一時也無法讓人信服。持六詩皆體皆用觀點的還有陳桐生。一般而言,中國古人思維方式是即體即用、體用不二,無論體制、內(nèi)容等都可屬于教化,況且六詩除“歌”以外,還存在很多其他運用形式,所以,六詩遠比“六詩之歌”具有更加豐富的內(nèi)涵。
(四)六詩皆體皆用
章太炎觀點蘊含了此說法,但他沒有具體展開。20世紀80年代張震澤指出六詩包含了詩、樂、舞、禮全部的體統(tǒng)之體,但也是不同場合的用。由于用于宗廟祭祀、朝會燕饗、日常生活之禮而形成了《詩》之風雅頌三體,賦比興不限于周代教學的一般應用,而是賦詩言志之用,有時需要直陳,就用賦的方法,需要以善物喻善事,就用興的方法,不敢直斥其非,就用“取比類以言之”的比的方法。[5]值得注意的是,張震澤“六詩”觀仍有“三體三用”之特征。
郭英德進一步指出“六詩”實際是樂詩行為方式的分類,由于上古詩歌基本功能是用于儀式上的記誦、祝禱或頌贊,詩歌采集為了各種儀式誦讀、歌唱或演唱的需要,因此六詩成為《詩》文本篇章分類的胚胎。他依據(jù)堂下之歌為“詩”,堂上之歌為“雅”,廟堂之歌為“頌”,把風、賦、比、興四種歌唱方法囊括于堂下之歌 (所謂“詩”)的合唱形式,周道衰敗時,《詩》作為賦誦諷諫的文本方式及其功能漸趨突顯,而作為儀式的行為方式及其功能則愈益淡化。[6]郭英德的觀點實際繼承發(fā)展了王昆吾之說,不過將“風、賦、比、興”視為所謂堂下之歌“詩”的說法,還欠文獻證據(jù)支撐。
明確持六詩即體即用的還有劉懷榮,他從文化人類學角度展開研究,指出:賦比興與風雅頌在原初各兼體用、以用為主,只是賦比興的時代,樂與詩均為獨立,故在用失之后,雖以之名體,卻仍不免體亡,最后賦比興只能包含觀念化的用的內(nèi)涵。六詩排列完全是以教學程序為準,從易到難。[7](P146)劉先生將賦比興與風雅頌視為古會盟制和新會盟制所對應的樂舞形態(tài),其說尚值得商榷。關于古會盟制缺乏進一步材料考證,且會盟制在春秋時代才凸顯。
通過以上對六詩研究的梳理,越來越多學者將六詩與樂、禮相結(jié)合,尤其是將六詩與上古儀式樂歌相連,為其學術研究奠定了扎實基礎。但我們也發(fā)現(xiàn)六詩研究遠沒有受到充分重視,目前學者們過多從一詩或三詩角度出發(fā)研究,或把六詩視為一個靜態(tài)的文化現(xiàn)象,缺乏歷史動態(tài)視野。在此,本文只結(jié)合“詩”字與儀式關系來考察六詩整體藝術形態(tài)。
二、“詩”字源考與六詩形態(tài)演變
六詩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現(xiàn)象,其形成、發(fā)展和嬗變是在特定環(huán)境中生成的,具有特定文化結(jié)構(gòu)意義。要了解“六詩”的性質(zhì),首先必須對“詩”字的語源學進行研究。“詩”字在《尚書》中出現(xiàn)兩次。一在《堯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另一處在《金縢》:“于后,公乃為詩以詒王,名之曰《鴟鸮》。”《尚書》中這兩篇文章的寫作時間難以確定,一般認為是“詩”字大概是周代才有的。關于“詩”的含義,大致有三種不同看法:
(一)詩言志
許慎《說文解字》:“詩,志也。志發(fā)于言,從言,寺聲。”聞一多在《歌與詩》中列舉數(shù)證說明漢朝人每訓詩為志。從而得出結(jié)論說:“志與詩原來是一個字。志有三個意義,一記憶,二記錄,三懷抱。”[8](P201)楊樹達《釋詩》說:“‘志’,字從‘心’,‘止’聲,‘寺’字亦從‘止’聲。‘止’、‘志、’‘寺’,古音蓋無二……其以‘止’為‘志’,或以‘寺’為‘志’,音近假借耳。”[9](P25-26)
(二)詩即詞
王鳳陽認為“詩”其實就是“詞”,《尚書·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國語·魯語》“詩所以合意也,歌所以詠詩也。”大致“詩”是“歌”的內(nèi)容部分即“詞”。[10](P304)
(三)詩有“持”義
“持”,主司事也,即主持某事。饒宗頤先生引銅器銘文考證認為先秦典籍中“詩”從“手”從“音”從“口”,“寺”聲字形作“持”,本義為“治事”、“司主”。王安石《字說》云:“詩為寺人之言。”今人葉舒憲力主此說,認為“寺”本意是經(jīng)過嚴格的逐次祭儀的祭司或巫師。“漢語中‘詩’概念與‘謠’、‘歌’等有不同來源。它最初并非泛指有韻之文體,而是專指祭政合一時代主祭者所歌所頌之‘言’,即用于禮儀的頌禱之詞也!”[11](P158)葉舒憲指出了上古先民祭祀活動與詩歌產(chǎn)生之間的密切關聯(lián),但他認為上古祭祀主持人就是“寺人”,即經(jīng)過閹割的男性,這種假設無充分證明,屬大膽臆測。
上述三種觀點具有某種共通性。“詩言志”追求的是“神人以和”,作為“詞”,其本身最早也被認為具有某種巫術力量。“對原始人來說,去占有詞也就是去占有詞所代表的事物。詞就像一個人的靈氣那樣,無論是誰只要他能流利地操縱詞,那么他也就能像通過某物的圖像去操縱某物那樣去控制住由詞所代表的事物,這種把詞看作不可思議的神秘力量的行為曾為世界上許多原始部族中所盛行的各種形式的祭禮所證實。”[12](P204)遠古的原始藝術最普遍特征即是詩、樂、舞與宗教祭祀儀式的密不可分,作為祭司、巫師所職掌的也正是“法度之言”。劉師培在《舞法起于祀神考》中說:
古代以樂舞為最先,古代樂官大抵以巫官兼攝。
三代以前之樂舞,無一不源于祭神。鐘師、大司樂諸職,蓋均處于古代之巫官。[13]
從“六詩”所掌主體瞽矇之職也可側(cè)面證明“詩”與祭祀有著密切關聯(lián),胡厚宣、陳夢家、黃錫全等幾位先生考證,詩的古文字中“?“為祭名。
中外人類學考察也發(fā)現(xiàn),原始宗教儀式必以樂舞為手段,大概以為樂舞具有通神的功能。《尚書》早就記載樂正夔“百獸率舞”,“簫韶九成”引得“鳳皇來儀”。早期詩即主要采用儀式樂歌形式,樂正掌樂歌辭大部分是用于宗教儀式。王昆吾指出用于儀式上的記誦、祝禱或頌贊,是早期詩歌最基本的功能。如果沒有儀式活動,那么,既不會有詩三百的結(jié)集,甚至也不會有“詩”這種文學樣式的產(chǎn)生。韓高年在《禮俗儀式與先秦詩歌演變》中也鮮明指出先秦詩歌起源與儀式密切相關,并詳細探討了頌詩類型演進是三代儀式文化演變的產(chǎn)物。[14]
基于此,我們認為,大師所教“六詩”正源自上古原始祭儀歌謠,宋代黃度曾云:“大師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是也。神人以和,通幽明之故也。夔擊之,而百獸率舞,發(fā)于其心,應于其手,至和之所感召者,與人不同也。夔自獻其能如此者,以見作樂,必能如舜之命也。”[15](P10)當然,儀式樂舞不僅僅局限于宗廟儀式和宮廷儀式樂舞,還包括民間禮俗形式。在上古階段民間禮俗與宮廷雅樂之間的關聯(lián),并不是截然分離的,二者有很密切的關聯(lián)。“六詩”中“風詩”寓于首端,足見當時地方風謠之作經(jīng)統(tǒng)治者加工改造后,具有重要的禮俗教化功能。六詩經(jīng)過瞽矇樂師之手被之管弦,以神靈觀念和巫術祭祀為思想基礎,它與政治、禮教、道德、風俗等社會體制和民間禮俗之間都有著密切關聯(lián)。古代學術是政教合一,官師合一。“古學”形成于一個以宗教為背景、以“王官”為主體的禮制文化傳統(tǒng),六詩作為儀式樂歌在一定場合的典禮使用,“六詩”是基本材料,六律將其轉(zhuǎn)化為音樂,以“六德”為之根本,這既是對早期藝術實踐主體的要求,更表征了三代禮樂儀式制度建設的特質(zhì),六詩的展演最終要在特定群體或文化中起到溝通、強化秩序及整合教化的效果。
“六詩”形態(tài)在漫長歷史進程中逐步變化。最初“六詩”乃詩樂不分、體用兼一,上述六詩皆體皆用的觀點某種程度上比較符合歷史的實際狀況。早期詩、禮、樂三者結(jié)合為一個統(tǒng)一體。《墨子·公孟》說:“儒者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又“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六詩作為口傳祭儀樂歌存在,其形態(tài)應包括歌、誦、弦、舞等多種表演形態(tài)。周代統(tǒng)治者“尊崇”詩樂,應用場合是取其聲、義二者并用。趙奎夫指出,早期歌、樂與詩歌密切結(jié)合,人們不可能為了取其內(nèi)容而排斥形式,或為了追求形式而否定內(nèi)容,而必然是在二者的結(jié)合中,聲、義并用。隨著詩、歌、舞、樂不斷的發(fā)展和豐富,才獲得了彼此獨立的可能。[16]這個觀點比較符合歷史發(fā)展實際。詩言志,歌詠言,周代詩教、樂教是并重的,詩樂聲律有益于教,體用兼?zhèn)洹;诖耍艽按髱煛辈艜浴傲姟睘榻獭kS著時代發(fā)展,詩樂的聲用功能減弱,辭義功能加強。朱淵清《六詩考》和楊朝明《〈周禮〉“六詩”與周代的樂教傳統(tǒng)》文中都從傳播角度對“六詩”進行破解,他們認為六詩經(jīng)歷了從口傳樂歌到書面?zhèn)鞑ッ浇椋Q雖得以保存,但其原始功能卻喪失了。西周以后王官瞽矇地位下降,六詩“聲用”功能減弱,最終由儀式樂歌轉(zhuǎn)變?yōu)榱酥S諫之用。由此,依據(jù)傳統(tǒng)禮義解讀“六詩”才基本奠定后世解讀《詩經(jīng)》的基礎。換言之,后世被納入儒家經(jīng)典體系的《詩三百》有可能就是“六詩”流傳下來的鮮活歌辭文本。
由此,六詩的形成、發(fā)展、成熟、衰落是經(jīng)過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據(jù)顧頡剛先生研究,上古文化是不斷地層壘而積成的。《周禮》的主體和細節(jié)部分也是戰(zhàn)國人的追憶補記。“六詩”大體是由樂官們按照一定原則,對三代禮俗的各種儀式樂歌進行采編、傳教、運用,最后總結(jié)而成為一個體系的,它是三代儀式文化演進與政學合一的文化體制產(chǎn)物。根據(jù)三代思想總體上由巫術、祭祀到禮樂文化的發(fā)展進程,本文認為,“六詩”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形態(tài)及功能是有所變化的:在巫術儀式文化中六詩的內(nèi)容主要是占卜祝辭;在祭祀儀式文化中其內(nèi)容主要是祭祖頌歌,而在禮樂文化中,其內(nèi)容主要是不同典禮場合演奏的禮樂歌辭。
[1]朱自清.詩言志辨[M].長沙:岳麓書社,2011.
[2]郭紹虞.文論札記三則[J].武漢大學學報,1980,(5).
[3]魯洪生.從賦、比、興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看其本義[J].中國社會科學,1993,(3).
[4]章必功.“六詩”探故[A].先秦兩漢文學論集[C].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5]張震澤.詩經(jīng)賦比興本義新探[J].文學遺產(chǎn),1983,(3).
[6]郭英德.由行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變遷——論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的生成方式[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05,(1).
[7]劉懷榮.賦比興與中國詩學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8]聞一多.歌與詩[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9]楊樹達.積微居小學經(jīng)石論叢[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0]王鳳陽.古辭辨[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11]葉舒憲.詩經(jīng)的文化闡釋[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12]朱狄.藝術的起源[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13]劉師培.劉師培全集[M].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
[14]韓高年.禮俗儀式與先秦詩歌演變[M].北京:中華書局,2006.
[15](宋)黃度.尚書說(卷1虞書)[M].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6]趙沛霖.《詩經(jīng)》與音樂關系研究的歷史和現(xiàn)狀[J].音樂研究,19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