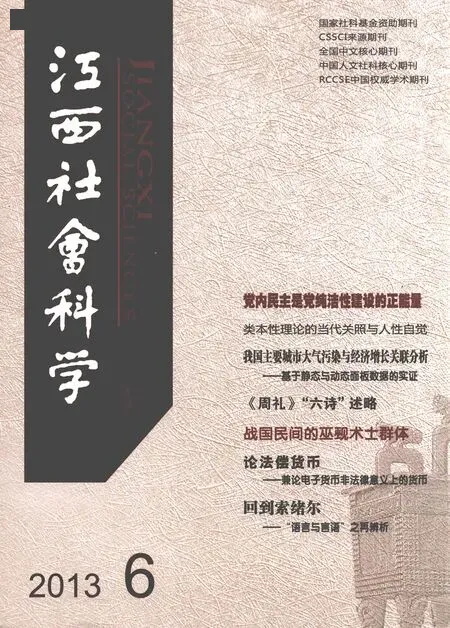宋元之際的理學詩風及其反撥
■史 偉
作為宋代主流的學術思想,理學及理學家的詩歌創作、詩學理論近年來受到較多的關注。但理學詩風概念的界定、理學詩風本身的流衍及其影響,均頗為豐富復雜;而在理學詩風盛行的時代,實已起反撥的聲音,元滅宋之后,這種傾向尤為突出,這為我們觀照理學和理學詩風提供了很好的視角,但同時也增加了此種復雜性。本文即欲對宋元之際理學詩風的形成,尤其是其所引發的相應的反撥的論說,作一梳理,就教于方家。
一
理學詩之所謂“擊壤派”的名目,起于四庫館臣,胡云翼《宋詩研究》則把“理學家的詩”與“詞人的詩”作為南宋“反江西詩派”而能自開生面的一個詩派特別提出[1](P136)。有學者更就“擊壤派”之淵源流變進行了史的評述,以為“擊壤派”源于邵雍《伊川擊壤集》,其形成則在宋元之際數十年內,而與真德秀《文章正宗》、金履祥《濂洛風雅》的編定和刊行及理學自身的發展進程密切相關;至元代許衡、金履祥、王柏及明代陳獻章、王慎中、唐順之諸人,則其流衍而已。所論亦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說而別有發揮。
一時風氣,是否遽以“派”目之,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對于理學詩風,我們可從以下兩方面進行認識:一方面,雖是理學家所作,但不完全是理學詩風之詩,邵雍《伊川擊壤集》相當一部分并不是“詩源心造化,筆發性園林”的語錄之壓韻者;魏了翁實是南宋中后期為數不多的詩學老杜而可得其格調神理者;金履祥七古則全承李賀作滌蕩跳脫之調,更不用說詩文造詣絕高的朱熹,更非“擊壤”所能拘限。但另一方面,理學詩也確實是宋元之際一種普遍的風氣,如劉克莊《跋恕齋詩存稿》所言:“近世貴理學而賤詩,間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壓韻者耳。”[2]這不僅表現在以理學自命的人在做理學詩,也表現在一大批以詩名稱世的人,亦不免染此習氣。《濂洛風雅》所收曾幾、呂本中、楊萬里、趙蕃亦皆詩家巨擘,一時風氣,于此可見端倪。錢鐘書《談藝錄》論道學詩頗多,稱其謂“此乃南宋之天行時氣病也”[3](P405),妙語誠可以解頤,而就事論事,其時道學之詩與詩人之詩,至少就作者本身而言,似乎也并不像《四庫提要》所說的“千秋楚越”,涇渭分明。
二
關于理學詩風的形成,在祝尚書的文章中,論列已多。這里強調兩點,其一,理學詩風可以溯源至邵雍《擊壤集》,但對于理學詩風真正起極大推動作用的恐怕還是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其二,以朱熹《感興詩》為代表的理學詩之所以能夠引起很大的反響,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感興》一類的詩對于理學后學之傳習修道起到了指示門徑的作用,至于后來理學詩流于虛聲影響,是緣于理學定于一尊后,后學以此作勢利名聲之求,卻是朱熹所不能任其責的。
朱熹少好詩,詩名頗盛,以至于胡銓等以“詩人”的名義加以薦舉,引起朱熹的戒懼,但是仍然未能廢詩[4](P112)。一方面詩是朱熹衷心所好,另一方面作為理學家,朱熹也希望以義理之學來規范詩,他以后所做的詩也確實逐漸開始向理學詩轉變。事實上,被薦舉前,朱熹與張栻等即有《南岳酬唱集》,張栻贈詩云:“遺經得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朱熹答云:“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明論。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圣同茲源。曠然摸遠御,惕若初不凡。”這些已經是理學詩的格調。所以,理學詩風的流衍,與理學中人彼此的唱和酬答也有著密切的關系。
此后,乾道八年(1172)朱熹在《齋居感興二十首》(自序)中提到的“雖近乏世用”,“然亦恨其不精于理,而自托于仙佛之間以為高也”等,仍然是理學家的聲音,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朱熹欲借此匡正義理,與同道切磋砥礪的意味。此外,如他在一首詩題中所說的“頃以多言害道不作詩兩日讀大學誠意章有感至日之朝起書此以自箴蓋不得已而言云”[5](P85)的體道有得、不得不發的詩;觸物有感、動合義理的詩,如《云谷二十六詠》、《云谷雜詩二十首》、《觀書有感二首》等以及同志友朋酬唱砥礪證道的詩,如前面提到的《南岳酬唱集》等,都屬于理學詩的范疇,其中多為五言古體,遠承陶淵明、陳子昂、韋應物,義理則一出于正。而這正是其《答鞏仲至第四書》中于虞廷擊壤、《詩經》之后,所提倡的第二等詩[6](P3336—3339)。
翁方綱這樣評價朱熹《感興詩》:“朱子《齋居感興二十首》,于陳伯玉采其菁華,剪其枝葉,更無論阮嗣宗矣。作詩必從正道,立定根基,方可印證千條萬派耳。”他在稱引了朱熹《次陸子靜韻》“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的詩句后說:“朱子詩自以此種為正脈,曾從道中流露也。”[7]這也可以作為朱熹藝術水平較好的理學詩的總體評價。實際上,也就是這樣體道有得,深于理致而不墮于理窟的詩作奠定了理學詩成為一時風氣的基礎。
朱熹《齋居感興二十首》在南宋中后期影響極大,岳珂《桯史》“晦庵感興詩”條言:
朱晦翁既以道學倡天下,涵造義理,言無虛文。少喜作詩,晚年居建安,乃作《齋居感興二十篇》,以反其習,自序其意,斷斷乎皆有益于學,而非風云月露之詞也。[8]
這段文字是岳珂與同鄉蔡元思(念成)誦《齋居感興二十首》后的札記,他認為朱熹的這些詩與“少喜作詩”時的詩不同,是“斷斷乎皆有益于學,而非風云月露之詞”的詩。他在引述了朱熹自序和這20首詩之后說:“(《感興詩》)習馳騁今古,剟華反實,斯可謂志之所存者。其中二篇,論二氏之學,猶若有輕重有無之辨,晚學恨不得撰杖履以質疑焉。”他是把《感興詩》當作修習義理的程課,與《近思錄》等量齊觀了。宋末元初的王柏《朱子詩選跋》言:
首卷雖先生手自刪,取名《牧齋凈稿》,然實少年之作也。今觀《遠游》一篇,已見其規橅之大,立志之堅,既有以開拓其學問之基矣。其次卷則自同安既歸,受業于延平之后,時年二十有八。自是往返七年,豁然融會貫通,然寄興于吟詠之際,亦往往推原本跟,闡究微渺,一歸于義理之正,凈洗詩人嘲弄輕浮之習,其《挽延平》時年三十有四誦其本本存存之句,亦可驗其傳河洛之心矣。《南岳酬唱》實乾道丁亥時,年三十有七。《齋居感興二十首》,其壬辰癸巳之間乎,凡篇中所述,皆道之大源,事之大義,前人累千萬言而不能仿佛者,今以五言約之此,又詩之最精者。真所謂自然之奇寶。[9]
王柏篤奉朱熹之學,其《詩疑》刪“淫詩”以合“思無邪”的詩旨,實則是對朱熹《詩》學觀念的極度推衍。朱熹的這部詩選《宋史·藝文志》沒有著錄,可能入元已經亡佚。王柏以知人論世的方法,為朱熹詩大致做了系年,又以此推求其義理。這也正是他們解經的觀念和方法,只是與朱熹相去尚近,推求不至于離開事實太遠。其詩歌標準則是“寄興于吟詠之際”,“推原本跟,闡究微渺,一歸于義理之正,凈洗詩人嘲弄輕浮之習”。但理學后學詩學素養及于理學體會之親切,均與朱熹相去太遠,所以理學詩就只能成為“語錄、講義之壓韻者”了。
理宗朝,理學定于一尊,至宋末,理學詩風乃衍成風氣。虞集《玉井樵唱集序》云:“當先宋之季年,談義理者以講說為詩,事科舉者以程文為詩。”[10]“事科舉者以程文為詩”,入元后形成元初詩壇上的所謂“時文故習”;“談義理者以講說為詩”則衍成理學詩風。這種“天行時氣病”入元依然流行,尤以南宋遺民為甚。紀昀《瀛奎律髓刊誤序》斥方回論詩“三弊”,其二即為“攀附洛、閩之道學”,其詩亦多道學語,此外見于熊禾《勿軒集》、陳著《本堂集》等別集之道學詩亦層見疊出。
如果說方回、陳著、熊禾諸人或以理學自命,或以講學聞名而學有淵源,那么,王義山以詩事為“吾學”[11],其文集中理學詩卻并不少見。
衛宗武《理學》詩述理學源流,及無極太極、性命理道,幾乎是一部具體而微的《伊洛淵源錄》:
寥寥二千歲,道統幾欲墜。濂洛暨關中,浚源接洙泗。乾淳諸大儒,流派何以異。無極而太極,性命發其秘。先天而后天,理道稽其致。[12]
衛宗武亦詩承江湖余習而留意詞翰者,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蓋理學洐至宋末暨元初,幾成禪家之所謂“口頭禪”,機鋒解悟,觸處而發,已不以為意了。
三
值得注意的是,在理學極為盛行的時候,已經起了反撥的聲音。這種反撥主要來自于浙東學派,確切地說是與浙東史學關系密切的葉適及其后學。葉適被認為呂祖謙、薛季宣、陳傅良浙東事功之學向朱熹之學靠攏、轉向的一個關鍵人物。全祖望在《宋元學案·水心學案序錄》中說:
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學,至水心始一洗之……咸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間,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文,流于辭章。[13](P1736)
這也是全祖望于永嘉學案之外別立水心學案的原因,所以,他在葉適生平之后特別加了一段按語:“祖望謹案:許及之、雷孝友之劾先生也,當時無以為然者。自方回始據之以抵先生,其意特以先生論學有所異同于朱子,遂拾小人之說以毀之。《宋史》亦不復白其誣。予續修《學案》,始別為立傳,而特詳其事跡以明之。”[13](P1743)
不過,葉適之學格局極大,其于文學的見解與朱熹不同,同時也無意對文學嚴加規范。錢基博于葉適詩文淵源有很好的梳理,稱其:“藻思英發,其為詩文原本唐人,文則偶必錯奇,得韓、柳之意,不如歐、蘇之條達疏暢,一往不返。詩亦疏不害妍,則李杜之遺;不如黃陳之生獷拗蹇,披猖失諧,似欲力復古調,不逐時賢后塵。”[14](P523)則葉適的文學也如他的學術,取徑頗廣,而有所樹立。葉適之后,于晚宋詩壇影響最大的是劉克莊。《宋元學案》將劉克莊歸入林光朝“艾軒學案”和真德秀“西山學案”,而未入葉適“水心學案”,這可能是因為《宋元學案》重在學術淵源,文學并不在考量范圍之內(葉適極力提攜的“永嘉四靈”也未入水心學案)。但事實上,劉克莊精于史學,與葉適消息暗通,學術傾向上也頗近于葉適,而有較為宏大融通的學術旨趣,只是劉克莊于理學流弊體會得更清楚,所以其于理學末學的詆訶也更嚴厲;至于文學,葉適于劉克莊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劉克莊《黃孝邁長短句》引葉適語云,郭紹虞認為劉克莊之于詩,受到林光朝的影響,又受葉適的賞識,故能“以道學家而兼詩人”[15](P77),所見極明。故劉克莊亦有“理學興而詩律壞”的感慨[16]。
宋亡之后,元代士人于理學詩的批駁見于言論者,更多、更嚴厲,也更能切中肯綮。這與元初科舉廢止,理學不再成為仕進之途有關;也與入元士人對理學所作的普遍的反思有關。
舒岳祥、戴表元皆浙東天臺人,是宋末少有的科舉之士而能詩者。袁桷《李景山鳩巢編后序》敘述“近世”詩歌風貌云:
先生諱表元,字帥初……失仕歸剡,遂俾桷事先生,始盡棄聲律文字,力言宋百五十年理學興而文藝絕。[17]
戴表元所謂“理學興而文藝絕”的言論,另見于《方使君詩序》、《張仲實詩序》、《陳晦父詩序》等,他入于《宋元學案》中王應麟的“深寧學案”,全祖望在序錄中說:
祖望謹案:四明之學多陸氏,深寧之父亦師史獨善以接陸學。而深寧紹其家訓,又從王子文以接朱氏,從樓迂齋以接呂氏。又嘗與湯東澗游,東澗亦兼治朱、呂、陸之學也。和齊斟酌,不名一師。《宋史》但夸其辭業之盛,予其微嫌于深寧者,正以其辭科習氣未盡耳。[18](P2856)
王應麟折中于朱熹、陸九淵、呂祖謙之學,“和齊斟酌,不名一師”,其史學尤為精深,“王門首座”胡三省即以史學著稱[18](P2870),而其“辭科習氣未盡”也頗有浙東學術的流風余韻。引文中王子文即王(?——1260年),子文其字,浙東金華人,《宋史》有傳,與劉克莊、戴表元均有交誼,亦為本學術,隆師友,且詩“粹美無疵”識見通達之士[19]。
舒岳祥列入《宋元學案》的“水心學案”,水心學案“吳氏門人”部分稱舒岳祥:“受文法于吳荊溪 (吳子良——著者按),荊溪序其集,以‘異稟靈識’稱之。宋亡,避地四明之奉化,與戴表元友善。所著有《史述》、《漢砭》、《補史家錄》、《蓀野稿》、《避地稿》、《篆畦稿》、《蝶軒稿》、《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談叢》,又有《叢續》、《叢殘》、《叢肆》、《昔游錄》、《深衣圖說》,共二百二十卷,通曰《閬風集》,今多不傳。然自水心傳于筼窗,以至荊溪,文勝于學,閬風則但以文著矣。”[13](P1825)葉適以下,從陳耆卿(筼窗)至舒岳祥漸“流于文辭”,但即以舒岳祥而言,其著述見于著錄者,史學尤為大宗,可見其淵源所自。戴表元亦師事舒岳祥,《宋元學案》稱:“時同郡王厚齋、天臺舒閬風并以文章師表一世,先生皆受業焉。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者,唯先生而已。”[18](P2875)均與浙東學術有著密切的關聯。
袁桷師事舒岳祥、戴表元,以史學稱世,亦可謂承浙東史學之緒余,有以接中原故國文獻。其于理學之壞詩,詆訶頗多:
近世言詩家頗輩出,凌厲極致,止于精麗,視建安、黃初諸子作,已憒憒不復省,鉤英掇妍,刻畫眉目,而形干離脫,不可支輔。其間凡偶拙近者,率悻悻直致,棄萬物之比興,謂道由是顯,六藝之旨闕如也。[17]
所謂“凌厲極致”蓋指“江西”末流粗豪一路,“精麗”云云指“四靈”、“江湖”晚唐習氣。而“凡偶拙近”、“謂道由是顯”云云,則是指理學一脈而言。理學家的詩,或理與情融,道與境會,確可寫出極富“理趣”的詩。但大多數的理學家,直以理入詩,率口肆心,直白無文,如“禪家偈子”,適成理障,這就是袁桷所說的“直致”,“棄萬物之比興”,“六藝之旨闕如也”。袁桷在《樂侍郎詩集序》中又嘗專論理學,其中,“大率以模寫宛曲為非道”即是“棄萬物之比興”,即是“直致”。“錯冗猥俚”即是“凡偶拙近”,袁桷詩學承舒岳祥、戴表元而來,于理學詩之弊端看得是很清楚的。
舒岳祥、戴表元師表東南學術文章,袁桷在大德初年北上大都入翰林國史院后,于元代詩文嬗變也有重要影響,顧嗣立《寒廳詩話》論及元詩流變言:“元詩承宋金之季,西北倡自元遺山,而赫陵川、劉靜修之徒繼之,至中統、至元而大盛,然粗豪之習時所不免。東南倡自趙松雪,而袁清容、鄧善之、貢云林輩從而和之,而詩學為之一變。”[20]此外,對于元代文學包括詩學有著重要影響的方鳳、謝翱、吳思齊、吳景昌以及柳貫、吳萊、黃溍等皆入《宋元學案》“龍川學案”,亦與浙東學術有著深切淵源。可以說,對于理學詩風的批駁宋末直迄元初,以浙東事功一脈所發最為激烈,也最為持久。其于宋元之際詩風影響最大,也在事實上奠定了元代詩學的基礎。
四
元代對于理學詩風的反思和調整,不只來自于有著浙東學術背景的文人,也來自于朱熹理學的內部。學宗朱熹者,固然也有嚴承朱熹詩學者如程端禮等[21]。以吳澄為代表,也有對理學詩風作折中撥正之論的。在《張達善文集序》中,吳澄對儒者之文進行了辯解:
朱子祖述周、程、張、邵,而辭莫有同者焉,誰謂儒者之文不文人若哉。彼文人善于詆訶,以為洛學興而文壞。夫朱子之學不在于文,而未嘗不力于文也……韓、柳、歐、曾之規矩也,陶、謝、陳、李之律呂也。律之、呂之、規之、矩之,而非陶、非謝、非陳、非李、非韓、非柳、非歐、非曾,是豈區區剽掠掇拾者,而猶有詆訶者乎?[22]
這固然是對儒者之文的辯駁,但其辯駁的理由卻是立足于文本身,所謂“朱子之學不在于文,而未嘗不力于文也”;同樣吳澄對于文人的批駁,也只是指摘其剽竊模擬,而沒有重拾道學家“作文害道”的老話頭,因此就其趨向而言,其實是重文而調和文道,卻不是以道來貶低或者規范文[23]。
這其實是元初理學家的普遍傾向。金履祥所編訂的《濂洛風雅》,被后來學者當作是“擊壤派”詩歌之淵藪,這個看法或失之于偏頗。金履祥見于《宋元學案》“北山四先生學案”,但其治學有獨自樹立之處,全祖望言:
勉齋之傳,得金華而益昌,說者謂北山絕似和靖,魯齋絕似上蔡,而金文安公尤為明達體用之儒,浙學之中興也。[18](P2725)
蓋金履祥于學無所不究,宋季國勢阽危之時,獨進奇策,請以舟師由海道直趨燕、薊,以解襄、樊之圍。其敘洋島險易,歷歷有據,時不能用。金履祥的計議是否能夠施行,且做別議,要之其迥出于一般腐儒之上,這就是全祖望所說的“尤為明達體用之儒”,這是時代給他的刺激而在學術上的反映。他在義理上與朱熹也不無抵牾,這與乃師黃震之謹守朱學也頗異其趣了[18](P2737-2738)。所以,其于詩學其實也無特別的偏見和執著,從《濂洛風雅》選詩的情況看,選詩體例仍然可以看到真德秀《文章正宗》的影響,重古體、重樂府,但就入選的詩人和詩作而言,如前所述,金履祥選入很多理學氣味不重的詩人,甚至一些頗受理學家排斥,包括被詆為朱熹作詩害道的詩人如趙蕃等的詩作;曾幾為宋室南渡后出入理學、詩派的詩家巨擘,但《濂洛風雅》選入的曾幾的詩中,如《長淮有感》、《夏夜聞雨》、《寄許子禮》、《食筍》等,都不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而《長淮有感》等所寄予的黍離麥秀之悲,正曲折反映了金氏故國之情。假如與方回《瀛奎律髓》做一比較,這一點會體現得更加清楚。《瀛奎律髓》被紀昀譏為“攀附道學”,方回把一些工詩的理學家如朱熹納入江西詩派的法統。兩者比較,可以認為,金履祥站在理學家的角度對詩做了包容,而方回則以“攀附道學”的方式從詩的角度,融通了理學家。他們從不同的角度,體現了元初詩學融通調和的理論旨趣。論者論及元詩,多言其“宗唐得古”的風氣,此種風氣固然是在對江湖詩風、江西詩派全面反思的基礎上的選擇,也是對理學詩風全面反思基礎上的選擇。
[1]胡云翼.宋詩研究 [M].長沙:岳麓書社,2011.
[2]劉克莊.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14)[M].四部叢刊本.
[3]錢鐘書.談藝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4.
[4]羅大經.鶴林玉露(甲編卷6)[M].北京:中華書局,1983.
[5](宋)朱熹.朱熹集(卷4)[M].郭齊,尹波,點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6](宋)朱熹.朱熹集(卷64)[M].郭齊,尹波,點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7]翁方綱.石洲詩話(卷4)[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8]岳珂.桯史(卷13)[M].北京:中華書局,1981.
[9]王柏.魯齋集(卷13)[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李修生.全元文(第26冊)[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11]稼村類稿(卷6)[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2]秋聲集(卷1)[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3]黃宗羲.宋元學案(3)[M].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6.
[14]錢基博.中國文學史(下)[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
[15]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
[16]劉克莊.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8)[M].四部叢刊本.
[17]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1)[M].四部叢刊本.
[18]黃宗羲.宋元學案(4)[M].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6.
[19]劉克莊.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4)[M].四部叢刊本.
[20]丁福保.清詩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1]程端禮.畏齋集(卷3)[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2]吳澄.吳文正集(卷15)[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3]查洪德.理學背景下的元代文論與詩文[M].北京:中華書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