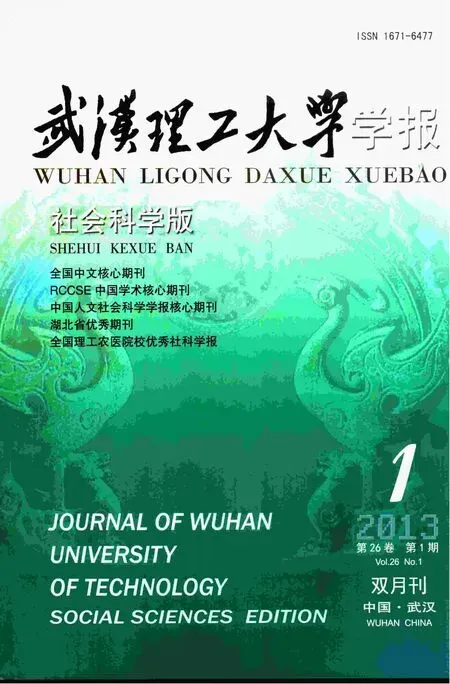顧炎武對“道統論”的再詮釋
王 寅
(南開大學 歷史學院,天津 300071)
梁啟超曾說:“大抵清代經學之祖推炎武”,又評價其有“‘篳路藍縷’之功,不能不推顧亭林為第一”,“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個人”[1]。顧炎武學術成就被學界廣泛肯定更多在考據、經世方面,而對于他學術中蘊含的義理闡述較少。顧炎武在講考據的同時也在講義理,尤其對先秦儒家經常闡述的“道”多有發揮,在宋儒“道統論”的基礎上,更是建立了自己的“道統”學術思想。
一、中國古代“道統論”的形成
“道”是中國古代思想體系中一個重要的概念,從先秦諸子到清朝晚期,很多學派和學人都給出了自己的理解。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2]又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
儒家學派對道也有自己的解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3],“一陰一陽之謂道”[3]161。“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3]196。“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4]。鄭玄注:“道,多才藝者。”[4]
在繼承先秦儒家學派對道的論述的基礎上,后世的儒家學者逐漸構建了“道統”體系。孟子曰:“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余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余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余歲。”[5]
繼承孟子的思想,韓愈說:“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6]后來朱熹說:“蓋自上古圣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于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圣圣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繼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其功反有賢于堯舜者……顏氏、曾氏而得其宗。及曾氏之在傳,而復得孔子之孫子思……自是而又在傳以得孟氏。”[7]至此“道統論”體系最終完成,并成為宋明理學的重要思想[8]。
二、顧炎武對“道統論”的詮釋
顧炎武總的學術思想根源是來自先秦儒家典籍,他著重從先秦儒家經典的角度對“道”和“道統論”進行了重新解釋。
(一)提倡先王之道
“先王之道”是古代儒家典籍中經常出現的詞語,如“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9]《孟子》中也有“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5]284-286
可見“先王之道”是上古先王綜合運用禮、樂、仁義、孝悌等原則來治理國家方法,以求達到政通人和的目的。董仲舒說:“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10]雖然這種美好制度多少有些幻想色彩,但此后的帝王多把實現“先王之道”作為目標,即“守文之君,當涂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10]2496。
顧炎武提出只有恢復“先王之道”,才能扭轉明末政治昏暗,群臣的互相傾軋以及社會混亂的景象。而由誰來推行“先王之道”則是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顧炎武認為儒者和生員應該負起責任。他說:“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為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11]
但是現在儒者們卻沉浸于科舉之中沒有起到推行“先王之道”之責,所以顧炎武首先認為應該改革科舉制度。顧炎武對科舉有較深的認識。他曾經多次參加科舉,先后在科舉考試上白白浪費了十四年的光陰[12]。他看到了當時學人不求學問,只求功名的現象。他說:“凡今之所以為學者,為利而已,科舉是也。”[11]151面對這種“孔孟之道”不行的世風,顧炎武發出了“廢天下之生員而政府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13]這樣振聾發聵的呼喊。雖然這種思想在當時無法實現,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顧炎武希望恢復“先王之道”,使得政治清明百姓安居的愿望。
其次,顧炎武提倡“先王之道”反對“小人之道”。他說:“唐書載尚書左丞賈至議曰:‘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取士之失也。”[13]“小人之道”盛行的根本原因是“儒道之不舉”。
最后,顧炎武認為只有“先王之道”得以實行,“儒道”才能發展和昌盛。顧炎武認為“先王之道”只有依靠儒者才能傳承。因此他說:“周、程、張、朱五子之從祀,定于理宗淳佑元年。顏、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于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后國無異論,士無異習。歷元至明,先王之統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13]276。這里顧炎武肯定了“周程張朱”,“顏曾思孟”等人對“先王之道”傳承的貢獻。
(二)圣人之道
儒家把堯、舜、禹、周公、孔孟等人尊稱為圣人,而后世學人們只有尊崇“圣人之道”才算真正體會儒家的內涵。歷代大儒把“圣人之道”看得極為重要,如《禮記·中庸》載:“太哉,圣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14]這里贊美“圣人之道”的偉大,是世界萬物的發源,并把它和天等同起來。
顧炎武也看到了“圣人之道”在儒家學說中的重要地位。他認為經過宋代以來理學的改造,“圣人之道”已經湮沒無聞。他說:“試問百年以來,其能通十三經注疏者幾人哉?以一家之學,有限之書,人間之所共有者,而猶苦其難讀也,況進而求之儒者之林,群書之府乎,然圣人之道,不以是而中絕也。”[11]94顧炎武認為由于儒家經典的逐漸增多,最初的西漢六經發展為唐宋的九經,最后清朝又擴展為十三經,使得學者要想讀通這些經書是不可能的。因為經學的日益繁多,人們無法盡讀,這就間接導致學者都空談成風,干脆放棄了研讀經典,從而使得“圣人之道”“中絕”。
為了恢復圣人之道,顧炎武從“體”、“用”、“文”三個層面入手。
第一,關于“體”的方面,顧炎武認為,要達到“圣人之道”,對一個人的內在修養也有要求。他說:“所謂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于文,曰行已有恥。”[11]93提出了在學術方面要做到博覽群書,在個人行為上要有羞恥之心。要想達到圣人,就是對待自己要以“忠”為標準,對待他人要以“恕”為準則。即“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13]129當“行有不得者”時要“反身修德”做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15]就“可以入圣人之道矣。”[11]101
第二,關于用的方面,顧炎武提出要想達到“圣人之道”的標準,還要從自身做起,從日常生活中開始和體會。他說:“圣人之道,未有不始于灑掃應對進退者也。”[13]135“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13]129顧炎武去除了圣人之道的神秘性和神圣性,讓人感到圣人之道不是遙不可及,高不可攀的,只要每個人從灑掃應對進退等小事做起就能達到圣人的標準。由此他認為:“圣人之道,所謂備物以致用。”[13]395
最后關于“文”的方面,顧炎武認為,要想恢復“圣人之道”,就要拋棄后人添加的經書而只求諸于六經。所以他補充說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尚其占”。《易經》中蘊含著“圣人之道”,而要想明晰其中的道理,就要“以《詩》《書》執禮,而《易》之為用,存乎其中,然后觀其象,而玩其辭,則道不虛行,而圣人之意可識矣”[11]94。顧炎武最后把全部“六經”都囊括進“圣人之道”中來。
以上顧炎武的思想正和儒家的“內圣外王”思想觀相符合。《莊子·天下》說:“是故內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16]后來這一思想為儒家繼承,特指個人修養與政治主張。“內圣”,就是將道藏于內心,自然無為;“外王”就是將道顯示于外,推行王道。“內圣外王”指的是內有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是人格理想及政治理想兩者的結合[17]。顧炎武提倡的對內要“忠恕”,“博學于文,行已有恥”;對外要“灑掃應對進退”,“備物以致用”。正是繼承了儒家“內圣外王”思想的體現。梁啟超說:“‘內圣外王之道’一語包舉中國學術之全體……其旨歸在于內足以資修養而外足以經世,所謂古人之全者即此也。”[18]
(三)六經之道
顧炎武很尊崇“六經”,他認為孔子之所以被稱為“素王”可以與上古圣王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相媲美,最主要的功績就是刪述了“六經”。他說:“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11]110又認為“六經”集中了上古圣人的所有智慧,后人不需要進一步加以創造發明,只要明了“六經”的含義就可以了。他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孔子之圣,但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是故六經之業,集群圣之大成,而無所創矣。”[13]25
雖然“六經”是儒家的重要經典,但在流傳過程中也并非一帆風順。到了董仲舒和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六經”才重顯于世。顧炎武在詩歌中描述了“六經”由“絕”到“盛”的過程。他說道:“微言既以絕,一變為從橫,下以游俠權,上以刑名衡,六國固蚩蚩,漢興亦攘攘,不有董夫子,大道何由明,孝武尊六經,其功冠百王。”[19]
明代學風空疏,人們多不習“六經”。江藩在《漢學師承記》中不由感慨道:“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講章為經學,以類書為博聞,長夜悠悠,視天夢夢,可悲也夫!”[20]顧炎武身處于那個時代,他尖銳地批評明代的學者不讀經典,讀書只是為名而已,“為文辭著書一切可傳之事者,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11]151顧炎武指出明人亂改經書,他說:“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經之病。”[11]103最后顧炎武感嘆人人不識“六經”,使得孔子之道無法施行,“尼父道不行,喟然念泰山,空垂六經文,不覩西周年”[19]311。
顧炎武提倡回到經典中去發掘古人之意。他認識到,通過對“六經”的研讀,在上可以與先秦儒家的“圣人”、“先王”思想相溝通,在下可以作為自己建立學術體系的立足點。顧炎武正試圖借助于“道”的內涵和外延著手建立了自己的學術體系,而“六經”正是匯通“道”與“學”的關鍵。從此顧炎武便開創了后世乾嘉學派以“六經”為本源的學術路徑。
三、結 論
“道統論”最初從孟子開始就構建的儒家正統學說,最終由宋儒發揚光大,占據了從宋至明的中國古代思想界的主流。到了清代,學術風氣為之一變,清代學者有感于明代政治的腐朽,紛紛認為是學術上的空疏之氣導致了這一結果。因此清代學者紛紛對宋明理學加以批判,由此清代考據學風成為了學術界的主流,同時也涌現出一批學人,形成了乾嘉考據學派。由于清代學人對宋明理學的否定,使得“道統論”也失去原來的地位,逐漸不被人們所提及,但它的影響猶在,還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雖然顧炎武也反感宋明理學的學風,但對于宋明理學的優點也加以吸收與改進。正是受到宋明理學的啟發,顧炎武從先秦典籍中挖掘并重新闡述了“道統論”學說,借助儒家傳統的“先王之道”、“圣人之道”和“六經之道”,賦予了“道統論”以新的內涵。顧炎武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學術思想體系,并且對后世學術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1]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北京:中國書店,1985:52-53.
[2]王 弼.老子注[M]∥諸子集成: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54:14.
[3]阮 元.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2009:171.
[4]阮 元.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2009:1700.
[5]焦 偱.孟子正義[M]∥諸子集成: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54:608-610.
[6]馬茂元.韓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18.
[7]朱 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14-15.
[8]郭 瑩.中國文化講習錄[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350-354.
[9]阮 元.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2009:5338.
[10]班 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2499.
[11]顧炎武.亭林文集[M]∥四部叢刊:第8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80.
[12]清史編委會.清代人物傳稿[M].北京:中華書局,1986:353.
[13]顧炎武.日知錄集釋[M]∥四部叢刊:第6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312.
[14]阮 元.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2009.
[15]劉寶楠.論語正義[M]∥諸子集成: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54:263.
[16]王先謙.莊子集釋[M]∥諸子集成: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54:216.
[17]湯一介.反本開新:湯一介自選集[M].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149.
[18]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2.
[19]顧炎武.亭林詩集[M]∥四部叢刊:第8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50.
[20]江 藩,漆永祥.漢學師承記箋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