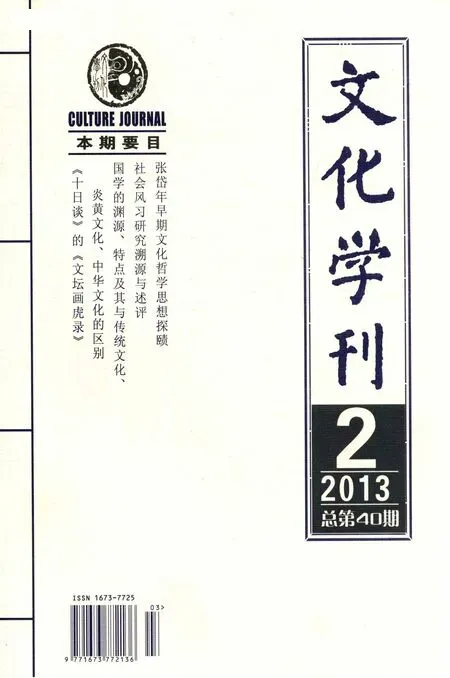告 別
王充閭
(作者系著名作家)
我們來到法蘭克福的第二天,參觀過國際書展之后,晚間,應東道主邀請,在萊茵河畔的“老歌劇院”,聆聽了一場格調高雅且令人心旌搖蕩的交響樂。
我原是音樂的“不良導體”,混了幾十年,也沒有鍛煉出來一對“有樂感的耳朵”。特別是對于具有復調性、交響化特點,被人稱作“莊嚴宏偉的音樂殿堂”的西洋交響樂,更是接觸不多,知之甚少。什么多樂章的交響曲啦,什么交響詩、協奏曲啦,什么音樂會的序曲、組曲啦,充其量也只能粗加分辨,至于品鑒其所謂“稀世之美”、“味中之味”,則是一片茫然。
記得大文豪肖伯納曾經說過,一切音樂作品都是標題樂。而且認為,音樂越是向文學靠攏,越是不純,越好。但他終究不是出色當行的音樂家、作曲家,他的觀點并沒有得到音樂界的普遍認同。相反地,許多高層次的聽樂者,則趨向于追求那種絕無背景、一空依傍的“純音樂”,他們主張擯棄文學與視覺的干預,寧心靜慮地直接傾聽本文,以求溶入音樂藝術的化境,窺探其“無形之相”。聽說,有人要貝多芬闡釋他的一支曲子的意蘊,貝多芬默然無語,只是重新把這個曲子演奏了一遍。這個人沒有理會,再問貝多芬意蘊何在,貝多芬淚流滿面。一曲奏罷,竟然不能被人理解,這是音樂本身的悲哀,也是作曲者、演奏者的悲哀,進一步說,也是聽眾的悲哀。在這種多重悲哀的情勢下,這位“樂圣”只好用悲愴的眼淚告訴世人:曲外無文,一切都在樂曲里邊,并沒有什么外在的、需要用語言文字補充和闡釋的意蘊。
而像我這類初涉樂趣的“半吊子”,在樂海漫漫、茫無津渡的情況下,倒是喜歡找個入門的向導,覺得如果樂曲能和文學聯結起來,比如,借助歌詞的導引、標題的提示,理解起來總比直面本文要更容易一些。因此,當聽說晚上這場音樂會將有海頓的《告別交響曲》時,情致格外濃烈一些。但是,它的結果,會不自覺地陷入望文生義、以偏概全的泥淖。
即以這個“告別”二字來說,當時我所縈懷的,是“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進而引發我無窮的聯想——中國歷代的文人騷客,由于長期受農耕條件下生活方式的影響,安土重遷,不慣流徙;加之,古代關山迢遞,道路阻隔,正如《別賦》作者江淹所說:“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是以行子腸斷,百感凄惻”。人們往往把背井離鄉同生離死別聯系到一起,結果是“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因而,從《楚辭》中率先唱出“悲莫悲兮生別離”的哀歌開始,一部古代文學史載滿了《別賦》、《感別賦》、《嘆別賦》、《離別賦》、《別思賦》、 《惜別賦》……就這樣, “告別”的文章足足作了兩千余年。
就這樣,直到演奏開始之前,我一直在想著慘然長別的場景。
二
這座“老歌劇院”在法蘭克福久負盛名,始建于19世紀80年代,于今已有一百三十年歷史了。這是一座典型的歐式建筑,兩層起脊,中間又凸起一層,上下兩層燈柱襯著八扇窗戶,放射出雪亮的輝光。劇院通體由石頭砌造,顯得莊嚴、肅穆、古樸、大方。
作為巴黎歌劇院的復制品,它是這里最著名的建筑之一,也是一流的文化場所,每年有大批來自國內外的藝術團體和個人到此演出。特別是我們所在的這座可容納七八百名觀眾的莫扎特大廳,尤為豪華、典雅。據介紹,在這里演出的古典音樂和現代音樂,涵蓋了巴洛克早期到先鋒派時期的各類作品,有交響樂、音樂劇、爵士音樂、搖滾音樂、流行音樂等多種形式,為觀眾提供了豐富多樣的選擇余地。
開場演奏的是貝多芬的交響曲,那種新穎的風格、宏偉的形象,一下子就攫住了聽眾的心魄。過去聽過他的《熱情》、《悲愴》奏鳴曲,這天晚上也還想聽聽他的英雄史詩般的《第三交響曲》、《第五交響曲》、《第九交響曲》,可是,演奏的卻是以“田園”為標題的《第六交響曲》——一幅表達鄉間情趣的“音畫”。聽來倒也輕松、流囀,只是后面帶上了一點感傷的意味。關于這部交響曲,背后還有一個動人的故事。大概給它加上一個“告別”的標題,也還大致能夠說得過去。
1807年仲春,“樂圣”貝多芬來到維也納近郊一位伯爵家里,教伯爵的妹妹丹蘭士演奏鋼琴,沒有想到,很快他就墜入了情網。每天早晨,他都要和丹蘭士手挽著手,到充滿綠色鄉風的田園里去散步,還一起參加當地農民舉行的舞會,沉浸在濃郁的歡情里。這天,他感到有一種強烈的創作欲望,奔騰鼓蕩在靈府之中,無論如何,也抑制不住,于是,大步流星地奔回伯爵的府邸,立即用鋼琴記下了交響曲前三個樂章的雛形。后來,情況發生了驟變,丹蘭士由于抵抗不住母親的粗暴干預,不得不忍痛離開他的身邊,這給貝多芬帶來了莫大的苦楚。在一個暴風驟雨、雷轟電閃的秋天,他久久地佇立在窗前,凝神專注地望著滂沱的急雨和利劍般的閃電,心頭透露出一種陰郁透骨的寒涼。在這種情況下,樂曲第四章的初稿誕生了。
到了第二年的初夏,貝多芬憶起這一段永生難忘的經歷,把春花般艷麗的柔情和激蕩胸臆的雷雨連綴在一起,譜寫出一支清音悅耳的華章,這就是《田園交響曲》。海頓不愧是一位杰出的音樂家,盡管是一些細微的表征,也逃不脫他那敏銳的聽覺。他告訴貝多芬:人們在您的作品中無疑會發現美麗動人的心音,但是,同時也會覺察到一種特殊的東西,陰暗的東西,因為你自己就有一點特別和陰暗。貝多芬聽了,感動異常,把海頓奉為并世的“知音”與“解人”。
海頓之所以有此敏銳的感覺,端賴于他的高妙、超拔的修養。在音樂的欣賞中,與其說是憑借理解,毋寧說是靠的是體驗與領悟。作為心靈的感應,欣賞者依賴的是自己豐富的感受;不具備這種感受,是絕對無法達到這種境界的。海頓這樣的音樂大師,正是通過心靈感應,領悟到樂曲中細膩而微妙的情感表達。
這天晚上,我們還欣賞了勃拉姆斯的《第三交響曲》。由于樂曲中不同情緒的輪番交替,手法更接近于浪漫樂派,因此,所得印象比較模糊。當然,這和我一心關注著《告別交響曲》的演出,也有一定關系。
三
海頓是奧地利一位多產的作曲家,僅交響曲就寫了一百零四部之多。一般地說,他的樂曲充滿鮮明的形象,具有樂觀、幽默的特征。早期作品中三個樂章的占一定比例,后來,逐步定型為四個樂章,唯有這部《第四十五交響曲 (告別)》是五個樂章。這部樂曲不僅意境動人,而且,演出方式也十分奇特,樂隊一登臺,就以每人手擎一只點燃著的蠟燭而引人注目。
演奏開始了,首先出現的是精神抖擻的快板,爾后,越來越緊張、激烈,給人一種急管繁弦、慌亂不安的感覺。第二樂章是溫和、寧靜的柔板,類似抒情的小夜曲,長笛和小提琴溫柔、凄惋地奏鳴著。第三樂章是輕盈的小步舞曲,洋溢著海頓的舞曲所慣有的輕松與幽默。第四樂章重又回到急速而慌亂的格調上來,音樂像旋風般地奏鳴著,速度越來越快。當時猜想,整部交響曲大概就要在這種遒勁、激越的和弦中結束了。但我立刻又劃了一個問號:若是這樣,“告別”的意蘊又從何說起?果不其然,急促的音樂到此猝然中斷,接著,轉換為溫存的、愛撫的旋律,類似第二樂章的柔板。就這樣,第五樂章出人意外地開始了。看來,這部交響曲的前四個樂章,原是一部完整的套曲,而其最后的第五樂章,是為著特定的目的與要求補充進去的。
第五樂章是整部交響曲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演奏繼續進行著,但樂曲的情緒和氣氛逐漸地低沉、黯淡下來,節奏也趨于平緩了。這時突然發現,表情有些哀惋的第一雙簧管手和第二號手,各自吹熄了樂譜旁的蠟燭,擎著樂器默默地退場了。不一會兒,低音大管的樂師也滅燭而去。緊接著,第二雙簧管、第一法國號、低音維奧爾琴的樂師也都相繼下場。樂音漸漸寥落,唯有弦樂聲部還在持續地演奏著。但是,沒過多長時間,先是大提琴手,接著是小提琴手,最后是中提琴手,一個接著一個,也都陸續退場了。樂曲臨近尾聲,曲調格外哀惋、凄切。臺上只剩下兩個小提琴手,他們神情寂寞地,用微弱而凄戚的音調,靜靜地演奏完最末一個音符,隨后便吹熄蠟燭,黯然離去。舞臺上一片漆黑。過了一會兒,樂師們重新登臺、謝幕,演出宣告終止。
想來,所謂“告別”,是和這樣一個令人黯然神傷的結尾有直接聯系的。可是,問題接著就出來了:這位享譽世界的作曲家,為了什么,或者說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要設置這樣一個結尾呢?當日,我們帶著一個很大的疑團,離開了這個同樣有些迷離惝恍的“老歌劇院”。
四
直到讀過海頓的傳記,才算揭開了這個謎底。
原來,海頓從29歲的丁壯之年來到艾斯哈特齊親王府邸,一直到58歲離開,在這個貴族之家足足當了30年的樂長。親王是一個頭號的“樂迷”,他對音樂的酷愛和在這方面的特殊要求,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決定了音樂成為宮廷中的至高無上的需要。
本來,他的府邸是在維也納東南八十公里外的艾森斯塔特,但他作為匈牙利最富有的而且權傾朝野的一個貴族,對于當時尚屬奧地利統轄的匈牙利境內的薩托更感興趣。他把這個林木蔥蘢的勝地更名為艾斯泰爾哈澤,大肆擴建宮室,置備各種豪華設施,每年絕大部分時間都在此地勾留,自然,他所親自經營的音樂活動,也在這里夜以繼日、無時或息地進行著。
這可就苦了海頓指揮下的管弦樂隊。因為大多數樂師都是奧地利人,長年在外從事緊張的音樂演奏,思家戀親之情與日俱增。但他們受雇于王府,每天都以仆人的身份奉命登場,誰也不敢向親王貿然提出回家探親的要求。長期以來,海頓忍受了太多的“俳優畜之”的恥辱,每天穿著繡花的號衣,飯前飯后在客廳里隨時聽候主人的吩咐;作為樂長,他當然更能理解樂師們的苦衷。于是,他那幽默中又帶有幾分淘氣的性格起了作用,索性以暗示的方式,通過樂曲的演奏,提醒親王:如果不放大家回去,就將面對“告別”的場面了。
據說,這天聽說樂長將有新作面世,親王率領家族和親朋好友,意興盎然地前來欣賞。結果就是前面敘述的那樣,樂師們一一退下,最后,海頓樂長也收起了指揮棒,向親王及貴賓深深鞠躬,示意演出到此結束。親王不愧是超級樂迷,的確有著一雙妙悟的耳朵,第二天就下令:全體人員返回奧地利境內的艾森斯塔特。爾后,人們就給這部《第四十五交響曲》加了一個《告別》的標題。
在歐洲音樂界還有另一種傳說:艾斯哈特齊親王為了減縮府內支出,考慮要解散或者精簡樂隊人員。30多位賴以謀生的樂師聞訊后,憂慮重重,惶惶不可終日。樂長海頓出于同情,遂譜寫了這部交響樂曲,作為解散前的告別演出。親王聽了,深深為之感動,便打消了解散或者精簡樂隊的主意。
不管是哪一種背景,這場演出和這最后樂章用以結束整部交響曲的特別方式,都給當時以至后世的聽眾造成了強烈的反響。萊比錫的《普及音樂報》有過這樣的記述:“當樂隊演奏員開始熄滅燭光并相繼悄然退席時,聽眾的心都收緊了”,“而當最后的小提琴奏出的那微弱的聲音終于也消失時,聽眾深受感動地開始默然散開,好像同他們所欣賞的東西也永遠告別了似的”。德國著名作曲家舒曼聽過這部交響曲的演奏后也寫道:“對此,誰也笑不出來,因為這絕對不是為了消愁解悶而寫的。”
五
“對此,誰也笑不出來”,確切地反映了聆聽這部交響曲時聽眾的心態。但是,也僅止于“笑不出來”的苦澀與沉重,卻并非如我開初時所臆想的那種生離死別的深悲劇痛,或者臨歧哽咽的黯然神傷。我想了一下,之所以產生這樣的差距,還是和我對于《告別》這個標題的內涵的理解有直接關系。
原來,標題音樂是借助于主導動機來表達特定的思想的。但是,主導動機這種手法,實際上起作用的是語言、文字,而并非樂曲本身具有這樣的功能。這里不完全是形象思維,還有很大的抽象思維成份。如果去掉了這個文字的提示,聽眾有時就很難曉得這種所謂“主導動機”的含義究竟是什么。
藝術講究“通感”,音樂作品所表達的感情,須能喚起聽眾所經歷過的感情體驗。而這種感情體驗也好,或者音樂作品表現的感情也好,都是間接地反映思想意識的,不可能像語言、文字那樣明晰、確鑿。這就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作為形象化的樂曲,能否準確無誤地表達出這種主導動機呢?也可以把話翻過來說,如果標題是后加的,像海頓的《第四十五交響曲》那樣,它又是否能夠恰切地把握形象化的樂曲的意蘊呢?即便是它能恰切地表達樂曲的固有意蘊,還有個聽眾如何理解的問題。這些環節有哪一個解決得不好,都會產生誤導的現象。恐怕這也是音樂界許多人對于標題樂不以為然的一個原因。
回國以后,我曾專門找來海頓的《第四十五交響曲 (告別)》的光盤,反復聽過幾次。由于脫離開了舞臺演奏的場面,感覺總不像在“老歌劇院”那樣明晰,那樣強烈。由此,我又悟出一個道理:雖然我們都承認,音樂是時間藝術、聽覺藝術,但是,如果要賦予它表現思想的功能,那就不僅要與語言、文字結合,而且,配合舞臺演奏也是必需的。就這個意義來說,它又何嘗不是空間藝術、視覺藝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