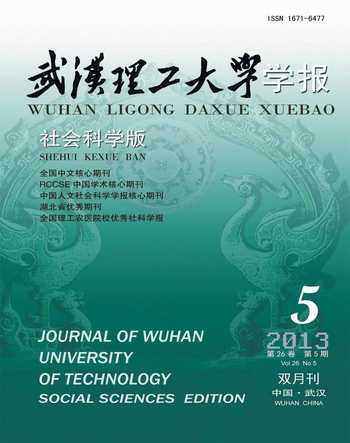自然化認識論的進展
摘要:蒯因在其1969年的文章《自然化認識論》中提出將認識論研究納入到心理學的一章中,并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的認識過程,從而以描述性的認識論取代以規范性辯護為中心的傳統認識論。對于認識論的自然化綱領,金在權、邦久等人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指出這一做法將會取消認識論作為傳統哲學重要分支的獨立性。而戈德曼等自然化認識論的支持者,則提出了具體的自然化方案,并且認為在個體主義的方法論之外,人們還應該從社會維度研究“真理”概念的形成、辯護標準的確定以及真理的社會傳播等問題。
關鍵詞:自然化認識論; 描述性; 規范性;社會認識論
中圖分類號:B017文獻標識碼:A
自從笛卡爾的《第一哲學沉思錄》問世以來,認識論就一直是現代西方哲學的核心領域之一。關于外部世界和人類自身,我們究竟能夠知道些什么?在形成知識的過程中,我們該如何正確利用感官和理性?真正的知識和一般性信念或意見之間有什么根本的區別?這些都是認識論的核心問題。而在20世紀中后期,伴隨著“葛梯爾問題”的提出,對于傳統認識論將知識理解成為“得到辯護的真信念”(JTB)這一做法的批判引發了大家的廣泛討論,許多人開始質疑笛卡爾以來的基礎主義者所孜孜以求的知識的絕對確定性,他們認為這實際上超出了某個具體的認知者所能滿足的要求。很多哲學家試圖修改并強化JTB框架來回應懷疑主義對于知識確定性的挑戰。而在這場爭論中,以蒯因為代表的一些哲學家提出了所謂自然化的認識論綱領。他們認為傳統認識論對于知識絕對確定性的要求是不切實際的,人們需要在對概念進行邏輯和語言分析之外,以行為主義心理學的方式從客觀角度來研究人的認知過程。通過自然科學而非思辨的或形而上學的方式來研究人類的認知活動,從而將規范性的認識論轉變為描述性的認識論,使之成為心理學,特別是認知心理學的一個章節。贊成的一方認為,蒯因的自然化綱領對于現代認識論在研究主題和方法論上尋求突破提供了重要的啟示;而反對者認為,描述性的認知心理學無法為認識論中十分重要的規范性問題提供滿意的答案,自然主義方法論的普遍有效性也還值得推敲。但是毋庸置疑的是,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西方認識論研究中圍繞自然化認識論所展開的討論是十分重要的,本文試圖考察自然化認識論的基本綱領,某些代表人物的具體理論,以及這一綱領本身面臨的問題和出路。
一、認識論的自然主義綱領
自從蒯因在1969年發表的文章《自然化認識論》中提出認識論的自然化口號以來,哲學家們圍繞自然化認識論綱領的內涵是什么,具體應該采取什么方式將自然化認識論予以推進,以及自然化綱領是否意味著對規范性的削弱乃至取消等問題,展開了一系列的爭論。以金在權、邦久為代表的一派哲學家對于自然化的綱領提出質疑,認為以自然科學的描述來闡明人的認識機制將會取消傳統認識論所關注的辯護,知識的(絕對)確定性等主題,從而使認識論蛻變為認知心理學的一個分支。作為從哲學母體中分離出來才100多年的現代心理學,其方法論的合理性并非足夠牢固。另一方面,蒯因、戈德曼等自然化認識論的支持者則從現代認知心理學、神經科學的視角對正常狀態下的認知心理活動,命題態度的形成,命題內容與外在世界的關系作出一種自然主義的說明。另外還有以Hilary Kornblith為代表的一些哲學家,他們既肯定自然化的綱領對于開拓認識論的研究領域與方法論創新的積極意義,又主張保留傳統認識論對概念的邏輯和語言學分析,那么作為這些爭論之核心的自然主義綱領究竟是什么呢?
對于了解傳統認識論的人而言,如果我們要談論什么叫做認識論的自然化,那么首先面臨的三個基本問題是:第一,認識論是否應該被看作是隸屬于自然科學的一門學科?其次,自然科學的方法是否是從事認識論研究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再次,傳統的認識論問題是否應該被認知科學的基本問題所取代?
正如Hilary Kornblith所提到的那樣,“自然主義既不是源自于蒯因,認識論中的自然主義方法論也不是從他開始的”[1]39。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在1969年發表的《自然化認識論》一文卻對當代認識論研究的方向產生了深遠影響。在蒯因看來,20世紀60年代以來以“葛梯爾問題”為代表的懷疑論對于傳統知識定義的有效性的挑戰成為任何研究者必須重視的問題。盡管哲學家們設計出諸如“non-defeater”理論、可靠論、因果論等多種方式來對“JTB”定義予以修補,但是從真信念到具有完全確定性的知識之間所存在的鴻溝卻一直難以徹底消除。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笛卡爾以來的傳統認識論一直將追尋知識的絕對確定性作為首要目標,并且希望將數學、邏輯知識作為樣本,按照一種基礎主義的模式來建構整個知識大廈,也就是從所謂“自明的”真信念開始,通過可靠的邏輯推理,最終獲得具有同樣確定性的新信念,并且這些信念的內容與外部世界之間具有一種相符合的關系。這種意圖在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者那里表現得尤為明顯,像卡爾納普等人希望借助科學觀察,從我們的感覺經驗出發,經過恰當的邏輯構造得出科學知識。但是蒯因認為,這種對于邏輯在建構經驗知識過程中作用的夸大以及對于認識活動中認知主體所處狀況的理想化的處理,完全不符合我們實際的認知過程。首先,科學知識的形成絕不僅僅等同于經驗觀察加上相應的邏輯推理,從觀察到理論的建構是一個創造性的過程。同時與某一組觀察相一致的理論可能有多個備選項,這一點在他論證“翻譯的不確定性”時就已經得到闡明。此外,在我們實際的認知過程中,由于認知主體會受到其背景知識、某個時刻的心理狀態和具體外部環境的綜合作用,特別是認知主體的心理與大腦活動在此過程中發揮了重要影響,因而他主張將認識論作為現代心理學,特別是行為主義心理學的一個章節,從研究人的認知行為過程中具體發生的心理與大腦活動開始,以嚴格的自然科學的方法來描述人類知識形成的客觀機制,以及“經驗證據是如何和理論相關聯,我們關于自然的理論是如何超越于手頭的證據”[2]。對于蒯因而言,認識論研究的出發點是我們形成可靠的真信念并能指導行動的實際認知過程,因而它必須被納入到自然科學的研究范圍之中。
蒯因的自然化認識論是否和傳統認識論毫無共性可言呢?在《指稱之根》一書的開篇,當蒯因談及(自然化)認識論問題的時候,他說:“這是一個經驗心理學的問題,人們既可以在某個時候在實驗室中研究它,也可以在某種思辨的層次上探討它,它的哲學意義是顯然的……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真理的一切就是要探明證據關系,即支持理論的觀察相對于理論的關系。”[3]3-4因而,根據蒯因的理解,自然化認識論一方面需要說明我們的感覺證據是如何支持科學理論的;另外還要從發生學的角度探討科學理論從感覺證據產生的實際過程。基于以上看法,蒯因的自然化綱領并不是完全排除哲學方法對于認識論研究所起到的作用,特別是對于感覺證據與科學理論關系的說明問題上,我們需要考慮證據與理論的邏輯關聯。而對于自然化認識論所涉及的第二方面的問題,蒯因認為人類掌握科學理論的過程即對于相關的科學術語、假說等諸多內容進行語言學習過程,因而發生學的方法就是最為重要的方法。其中既包含“對于從感覺輸入到觀察語句的學習機制的詳盡的神經生理學和心理學的解釋”[3]6,也包含“對于從觀察語句到理論語言習得的許多不同的類比步驟的詳細的說明”[3]6。由此我們可以認為,蒯因的自然化認識論在很大程度上仍舊帶有濃重的基礎主義色彩,只不過他所理解的作為基礎的部分是感覺經驗,是由科學的語言提供的觀察報告。
費爾德曼將蒯因之后的哲學家們所提出的認識論的自然化綱領分為三種類型:“替代論題”、“合作論題”、“實質性的自然主義論題”。蒯因的“替代論題”在認識論研究者中得到的支持并不多,大家更多討論的是“合作論題”。Philip Kitcher在1992年一篇名為“自然主義的回歸”的文章中提到,如果我們在20世紀對于認識論研究中科學成分的漠視是源自哲學領域一種反心理主義的普遍傾向的話,并且要是我們依舊承認認識論是在研究人在形成信念,獲取知識過程中的心理機制,那么自然科學的方法與相應的成果就必將被考慮進來。“合作論題”并不反對傳統認識論的概念分析方式,只不過它認為需要實際確定的是那些(借助概念分析所得到的)原則是否真的能夠幫助我們獲得真理,而經驗科學能夠幫助我們確定這個問題的答案。
蒯因本人并沒有考察自然化認識論的具體實施方案,他所謂的“將認識論研究納入到心理學的一個章節”實際上就是以行為主義心理學來具體闡釋人的認知活動,也就是利用“sense data”、“visual image”等關于生理(物理)狀態的術語來說明我們對于某個對象形成概念,作出判斷的過程。但是后來的自然化認識論支持者沒有完全按照“替代論題”來進行,以戈德曼為例,他采取的是“合作論題”。在《認識論與認知》一書中,他在可靠論的框架下對重要的認識論概念進行了分析,并引述關于人類認知活動中具體機制的科學說明來支持他的理論。戈德曼既希望保持傳統認識論的概念分析方法,同時試圖借助認知科學關于我們認識機制的經驗說明給認識論提供科學根基。
二、戈德曼的自然化認識論與社會認識論
如果當代認識論主要是對于經驗知識賴以產生的根基與機制進行研究,那么很顯然,自然化認識論就要排除形而上學的方法以及對于先天因素的分析。我們的知識必須植根于經驗基礎之上,而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經驗證據和科學理論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不僅僅是邏輯性的,也涉及到心理學和語言學方面。根據米建國[1]109的理解,蒯因的自然化綱領主要反對的是傳統認識論中的還原論、先天知識和形而上學的方法論,他強調對于經驗知識的發生學描述并不能取代對于知識的辯護。由于近代以來“哲學家們試圖從認識論出發來為自然科學知識進行辯護和證明的夢想早已被休謨式的懷疑論一掃而光”[1]109,因而蒯因所持的自然化認識論旨在排除形而上學為知識奠基的目標,并且主張將這種關系顛倒過來,即將認識論研究建立在自然科學的研究之上,按照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為知識的產生作出說明。而對于先天知識,蒯因表示堅決拒斥,首先,他反對所謂的先天知識的不可修正性,而是認為經驗知識(甚至包括邏輯與數學知識)有可能被修改;其次,在“經驗主義的兩個教條”一文中,蒯因一方面批評傳統經驗論對于分析命題與綜合命題的二分缺乏充足的理由,另一方面,邏輯經驗主義所持還原論的立場也很難成立;再次,在考慮感覺經驗同科學假說或者理論的驗證關系的時候,感覺經驗在可接受性方面更加具有優先性。
與蒯因這種較為激進的“替代論題”不同的是,美國當代的哲學家戈德曼依據可靠論框架提出了認識論自然化的方案。他最為關心的問題是:基于每個認知者較為有限的經驗觀察和感覺證據,我們是如何形成關于外部世界和我們自身的可靠知識乃至科學理論的。
根據弗爾德曼在“Goldman on epistem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一文里的理解,戈德曼所謂“重構認識論”的計劃是通過引入一些被傳統認識論所排除的議題,而正是這些議題需要從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中獲得幫助。對于認識論的自然化,費爾德曼認為蒯因的“替代論題”的核心是:將認識論中的哲學分析完全排除從而將認識論看作是自然科學的一個分支。傳統認識論具有兩個重要特征:其一是對于基本的認識論概念的邏輯和語言學分析,其二是對于懷疑主義關于知識確定性挑戰的回應。而蒯因的“替代論題”則完全取消了傳統認識論所具有的這兩個特征。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戈德曼1986年的《認識論與認知》一書中,我們卻仍舊可以看到關于這兩個方面的內容。弗里德曼認為,存在另外一種更加溫和的認識論自然化的態度,即“合作論題”。“除非我們能夠首先確定人們是如何形成信念的,我們才能決定應該以何種方式獲取信念才是恰當的”[4]。“合作論題”的支持者們認為自然科學的經驗研究成果能夠為諸多哲學問題的解決提供重要幫助,但與此不同的是,戈德曼并不認為所有的認識論問題都必須尋求科學的幫助,至少在《認識論與認知》一書的前半部分,他主要是圍繞可靠論的基本框架對于辯護規則進行哲學分析,戈德曼給出了所謂的J規則:
S(認知者)在時刻t相信命題P是有根據的當且僅當a,S在時刻t相信命題P符合某種正確的J規則系統;b,這種符合關系并不和S在時刻t的認知狀態相沖突[5]63。
而所謂的J規則是指:
一個J規則系統R是正確的,當且僅當R允許存在一些基本的心理學過程,這些過程的例示能夠產生滿足特定閥值(高于0.5)的真信念的比例[5]106。
對于戈德曼而言,一個信念得到辯護就意味著它能夠獲得某一可靠的規則系統的支持。而費爾德曼認為,戈德曼在《認識論與認知》前半部分的工作表明他對于相關認識論概念的分析既沒有獲得經驗科學的支持也沒有被反對,因而戈德曼的自然化綱領不能歸到“合作論題”之中。
對于“先天”(A priori)這一概念,戈德曼也采取了與蒯因極為不同的態度。按照他在A priori warrant and naturalistic epistemology這篇文章里的解釋,他將先驗方法看作是辯護類型而不是真理類型,其所謂的先驗辯護是在某種具體的心理機制中實現的,只不過它在內容上是純粹的概念分析而不會涉及到任何經驗證據。此外,在本文中,戈德曼認為認識論的自然化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種是科學的自然主義,即認識論作為自然科學的分支,認識論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自然科學的經驗方法,這一種觀點是蒯因所支持的。但是戈德曼認為“不存在包括心理學在內的任何經驗科學的分支可以勝任確定知識或者辯護的證據、條件或標準的任務”[5]25。第二種自然化的方案是經驗主義的自然主義,即將所有的辯護都看作是經驗性的,認識論就是要弄清這些辯護方法的細節所在。但戈德曼認為并不是所有的知識都需要經驗性的辯護,他舉了數學知識為例以表明存在先驗方法的辯護。因而在他看來,第三種所謂的“溫和的自然主義”是較為合適的做法,即所有的認識論辯護都是產生信念的心理過程的某種功能,但是在內容上并非所有的辯護都是涉及經驗的。戈德曼所理解的“重構之后的”認識論研究需要借助自然科學、特別是認知科學對于這些心理過程進行說明。
戈德曼在《認識論與認知》的導言部分就明確指出,他所理解的新的認識論與舊的認識論的關聯體現在“第一是在認知科學方面,第二是對于與知識和信念形成相關的人際和文化過程的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研究方面”[5]7。在《認識論與認知》的前半部分,戈德曼對于認識論的核心概念諸如知識的趨真性、辯護、認知過程的可靠性以及得到辯護的信念內容與實在的關系進行了哲學分析,并且在可靠論的框架下給出了相應的說明。在他看來,傳統的認識論研究主要采取的是一種個體主義的方法論,他用“primary epistemics”來指稱這一方面的內容,即將認知者看作是單個處在理想認知狀態下的個體,而認識論就是要對于這種狀態下的認知者從形成真信念到對其進行知識辯護所涉及的主客觀因素進行研究。但是在戈德曼看來,人們實際的認識過程除了受到認知者自身內部因素(感知能力、推理能力等)的影響之外,還受到相關的背景知識、文化環境等社會因素的影響,即使對于信念的真假和認知過程的可靠性評價而言,也不完全是由單個認知主體所決定的。因此除了借助自然科學的方法對于個體的認知行為進行研究,并且弄清由感覺經驗到理論知識的可靠形成機制之外,我們還有必要對于不同的認知主體之間關于“真”的標準的形成,對于信念的評價等內容所涉及的社會維度進行研究。這一看法在《認識論與認知》的后半部分中得到具體體現,在引述了大量認知科學對于感知、記憶、推理、判斷等等與信念形成機制相關的解釋之后,戈德曼將它們看作是可靠論的辯護策略的經驗證據。
而他在1999年出版的《社會領域中的知識》一書則可以看作是《認識論與認知》的姊妹篇,他在此書中具體發展了他的社會認識論理論,與20世紀早期多數的認識論研究路徑不同,他將認識論看作一項“多學科交叉的事業”。在他看來,認識論研究可以劃分為個體認識論和社會認識論兩個領域。以往的認識論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個體作為單個的認知者如何對自己所形成的信念通過找尋證據,并按照一定的標準(如自明性、與其他真信念的一致性、與事實相符合等)來進行評價,以決定是否應該將其納入到知識的范圍之內。戈德曼認為,除此之外,知識的形成與評價過程更是一種“文化的產物,它借助語言和社會交往來傳播”[6]1。社會制度架構對于“真”之標準與合理性標準的形成具有深刻影響。但是必須要強調的是,他將社會認識論理解成為一門關于最利于形成知識的實踐與制度研究的規范性學科。他在《社會領域中的知識》一書的前言中提到[6]1,社會認識論是對于傳統以單個認知者為中心的辯護認識論的擴展,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能夠將形形色色的以科學、文化的社會維度為相對主義進行鼓吹的做法與之混為一談。正如個體認識論需要借助認知科學為其提供堅實的經驗基礎,社會認識論也必須借助社會科學對于交往方式、信息傳遞等制度方面的研究來解釋真理的傳播與“真”之標準形成的客觀過程。因此他首先考察了“真理”概念在社會維度的意義及其建構的過程,并且具體考察了舉證、論辯、信息傳遞、言論控制等社會機制對于人們真理觀念的形成和辯護過程的影響,最后他以科學、法律與民主政治為樣本具體分析了真理概念在這些相關領域的建構過程與方式。
戈德曼認為20世紀70年代之前的認識論主要關注信念的辯護問題,特別是從一個信念到另一個信念之間邏輯推理的合法性占據了認識論的核心地位。其實心理學方面的考慮很早就滲入到認識論之中,它對于具體認知者從感覺經驗到信息的處理、分析、評估到最后形成信念的動態過程的關注,使得描述性的心理學對于認知機制的把握成為可能。只是戈德曼認為傳統認識論中對于知識作為真信念的辯護仍舊具有規范性的意義,他反對將傳統認識論中的概念分析與心理學、認知科學的實驗方法完全對立起來。
三、結語
以上對于蒯因到戈德曼的自然化認識論之進展的考察使我們看到,一方面,認識論的自然化擴展了傳統認識論研究的主題,并且通過引入新的心理學、認知科學的實證方法,使得認識論研究更具科學性與客觀性;另一方面,透過對于自然化綱領的一些批評,傳統認識論所追求的規范性要求仍舊顯示出其重要的理論價值,并且在個體主義的方法論之外,我們對于“真理”概念的理解與建構還必須考慮到社會因素的影響,因而正如戈德曼后期社會認識論研究所展現的那樣,在自然化的綱領之外,我們還應從社會維度進一步深化對于認識論問題的研究。
[參考文獻]
[1]Chienkuo Michael Mi,Ruey-lin Chen.Naturalized 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M].Amsterdam:Rodopi B.V.,2007.
[2]M.Cahn,Steven.Philosophy for the 21th century,a comprehensive reade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226.
[3]W.V.O Quine.The roots of reference[M].La Salle:Open Court,1973.
[4]Richard Feldman.Goldman on Epistem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J].Philosophia,1989,19(2-3):197-207.
[5]Alvin I.Goldman.Epistemology and Cognition[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6]Alvin I.Goldman.Knowledge in a social world[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責任編輯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