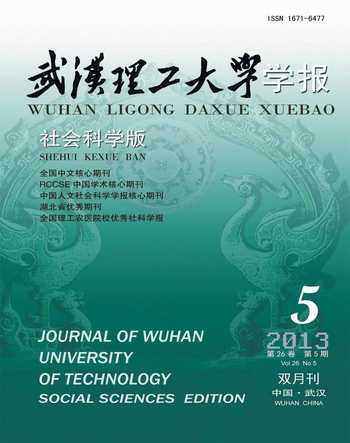最低工資標準的經濟增長和社會效應實證分析
摘要:為了考察我國最低工資標準對失業率、各地區人均GDP以及收入分配的影響,并盡量克服指標間較強的內生性問題,利用VAR向量自回歸模型分省份對失業率和各地區人均GDP進行了測度分析,并使用動態面板模型考察了最低工資標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研究發現,單純地認為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不利于就業和經濟發展的觀點是片面的,最低工資標準的就業效應和經濟效應在不同省份以及不同的政策滯后期內影響各異。
關鍵詞:最低工資標準;失業率 ;GDP;基尼系數
中圖分類號:F244.2;F042.2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國內對是否實施最低工資標準一直存在較大的爭議,而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在最低工資標準的失業率影響效應和經濟發展效應上。最低工資的提高會使得企業的利潤空間進一步壓縮,在生產技術沒有出現革新之前,一味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無視勞動力市場的實際供求情況,最低工資極有可能導致企業縮減勞動力需求以保持利潤,導致失業人數增加的幾率變大[1]。在最低工資標準明顯低于地區經濟發展可承受的最低工資水平時,適度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并不會對失業率產生太大的影響。
對于最低工資標準的經濟社會效應,許多學者利用面板數據模型進行了實證研究。Bell[2]使用墨西哥和哥倫比亞工業企業制造數據,發現實施最低工資標準對兩國的失業率影響不同。Lemos[3]利用巴西居民調查數據分析發現,最低工資對巴西的正規和非正規部門都存在負向效應。羅小蘭[4]使用面板數據,對最低工資對農民工就業的影響進行研究,發現最低工資標準存在閾值。
無論是用面板數據還是時序數據研究,都無法避免指標之間即最低工資與失業率(或者經濟發展)之間的內生性問題。比如,最低工資的上調可能會影響經濟發展速度,但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時,可能會對提高最低工資產生壓力,從而減緩最低工資的上調。同樣的問題也會出現在最低工資與失業率指標之間。而VAR向量自回歸模型可以很好地解決上述問題,它不需要設定特定的回歸結構,重點考察兩兩變量之間的路徑依賴方式和相互影響方向。本文將采用VAR向量自回歸模型,對27個省的最低工資與失業率及經濟發展進行回歸研究,探討最低工資標準的經濟社會效應。
二、最低工資標準的失業率效應
VAR模型估計假設失業率與最低工資標準互為內生變量,實證首先需要對失業率和最低工資指標進行單位根檢驗,根據單位根檢驗結果確定變量是否需要差分處理,然后根據AIC、HQIC、SBIC以及FPE等準則確定滯后階數,最后進行VAR模型估計。27個省份的VAR結果見表1。
從表1中我們可以看到,最低工資標準對失業率的影響在不同省區間是存在差異的。在北京、上海、遼寧和廣東4個省份,最低工資標準的變動在任意一期中對失業率都沒有顯著的影響。這一現象說明,在控制失業率為目標的前提下,該4個省份的最低工資可能控制在最優范圍之內。
其余省份的最低工資在不同的滯后期中對失業率影響不同。天津、河北、山東、重慶、甘肅和青海6個省份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大部分滯后期內對失業率的影響顯著為正;說明樣本年份內,上述省份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后,在相當穩定的一段時期內會增加省區的失業率。如果以控制失業率為目標,上述6個省份都應適當下調最低工資標準。
吉林、黑龍江、河南、湖北、廣西、貴州、陜西、寧夏和新疆9個省份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后,對失業率的影響在大部分滯后期內都顯著為負。說明上述省份在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后,在相當長的政策效應期中都能有效降低城鎮失業率。仔細分析發現,上述省份都處于中、西部地區,屬于勞務輸出大省,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上述省份可能過于壓低了勞動者的工資報酬,因此適當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可以有效促進勞動力的生產積極性,提高經濟競爭力,降低失業率。
其余省份最低工資標準與失業率的影響在不同滯后期顯現出不同的影響。在這些省份中,最低工資標準對失業率的影響并不穩定持續,政策效應轉化較快。
三、最低工資標準的經濟增長效應
本文為了進行最低工資標準對各地區經濟增長的VAR模型測算,使用各地區人均GDP增長率衡量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經濟發展速度,檢驗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對各地區經濟發展速度的即期和滯后效應。見表2。
最低工資標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大致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包括北京、天津、山西、遼寧、黑龍江、上海、江蘇、浙江、江西、山東、廣東、重慶、四川、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1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上述省份每提高一個單位的最低工資時,在滯后一期的情況下都會降低經濟增長速率。部分省份(如天津、黑龍江和重慶等)在滯后兩期甚至更長的時間段內會顯現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部分省份提高工資標準后,基本在所有滯后期內對經濟增長都是顯著的負向效應,如上海。這一類型省份超過所有省份的60%,也就是說,對大多省份而言,提高最低工資在短期內會不利于經濟增長,但是如果最低工資的提高能夠有效促進勞動者的積極性,進而增強產業競爭力,最終有可能促進經濟的持續發展。
第二類包括河北、內蒙、吉林、安徽、河南、廣西和貴州7個省份,上述7個省區在滯后一期內,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能夠有效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從滯后兩期甚至更長的時間來看,提高最低工資都不利于經濟增長。我們注意到,上述7省絕大部分位于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為落后,如果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以至于超過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可承受的范圍,那么在較長時期內是不利于當地經濟發展的。
第三類是湖北省,湖北省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后,在模型允許的滯后期內,對地區經濟增長并無顯著影響。
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到,總體來講,不同省區經濟增長對最低工資標準的沖擊響應效應是不同的。東部絕大部分省份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以低價勞動力換取經濟發展的模式使得最低工資長期位于正常水平之下,因此上述省份在提高最低工資后,雖然短期內會使經濟發展產生下滑的風險,但是從長遠來看,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反而有利于經濟發展。對于中西部的部分省份,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滯后,財政負擔相對較重,對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必須更加謹慎,否則將會給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四、最低工資標準的收入分配效應
(一)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考慮到我國的現實情況,并借鑒研究最低工資標準與收入分配問題的一般研究模型,可建立以下實證模型:
lngc=a+blnmws+cln gur+d ln ssspc+εit
1.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的高低受諸多因素的影響,本文所重點考慮的最低工資標準在一定程度上將會對基尼系數產生影響[5]。
由于受統計數據的約束,計量方法在時間序列的處理上無法滿足大樣本的要求,所以此處使用面板數據這一刻畫與事實更貼近的方法。對于基尼系數(gc)這一系數,數據選取的是1997年到2010年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和直轄市的數據。而刻畫基尼系數所使用的是:(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用此方法計算基尼系數,一方面可以刻畫城鄉間的收入分配,另一方面可以更科學地得出比例關系。
2.最低工資標準。
由于中國各個省份、直轄市都根據本省(市)自身情況制定了多個檔次的最低工資標準,而且各個省份調整時間也不盡相同,存在相互影響,但并不一致。我們在這里采用羅小蘭[6]和石娟[7]的做法,使用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最低工資標準的最高檔次,且使用加權平均法來處理不同省份公布的調整日期不一致的情況。例如北京市2009年最低工資標準為800元,2010年7月調整至960元,使用加權平均法來計算北京市2010年的最低工資標準為(800×6+900×6)/12=880元。
重慶市直到1997年才被列為直轄市,為保持一致,此處計算為1997-2010年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最低工資標準的面板數據。湖南、福建、海南和西藏由于沒有搜集到完整的數據而被剔除掉。數據來源于中國勞動人事網和勞動咨詢網。
3.城鄉差距水平。
城鄉收入水平是基尼系數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本文主要描述的是最低工資標準,所以,在研究重點上比較的是工資這一收入標準,對于城鄉差距水平這一系數(gur),主要依據收入差距水平進行測算。同樣使用1997—2010年27個省、市、自治區以及直轄市的面板數據,此系數用歷年各地區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與歷年各地區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之差來表示。
4.人均社會保障支出。
中國的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存在著東中西各個地區間的差距,以及城市和農村社會保障支出總量不足和不均的情況。總量的不足和地區差異對于居民收入分配和基尼系數有著直接的影響。對于人均社會保障支出這一系數,我們采用的衡量數據為全國1997-2010年度各地區(27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省級財政社會保障總支出與年度人口總量的比值。
數據說明:為了更合理地考察最低工資標準、城鄉差距水平和人均社會保障支出對于基尼系數的影響,也為避免使用時間序列無法滿足大樣本數據的要求,此處均使用1997-2010年度中國27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年度面板數據來解決小樣本問題,以提高估計精度。重慶自1997年劃分為直轄市,海南和西藏由于數據的缺失而不列入面板數據中。最低工資數據來源于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國勞動人事網和勞動咨詢網,其余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和各地區統計年鑒。
(二)實證結果
最低工資收入分配效應的估計結果,見表3。
如表所示,模型1使用的是pooled ols 并把最低工資標準的一階滯后納入進來,最后只得到最低工資標準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而城鄉差距水平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我們考慮到各省的個體差異,例如最低工資標準的不一以及城鄉差距水平的原因不一,進而使用固定效應模型,把個體效應控制住。如表中模型2使用了固定效應模型,最低工資標準和人均社會保障支出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城鄉差距水平在1%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使用描述性統計可以發現各解釋變量均有隨時間推移而增長的趨勢,所以可以考慮使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即控制個體效應同時控制住時間效應。表中模型3顯示,最低工資標準在10%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最低工資標準的一階滯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城鄉差距水平依然在1%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考慮到前幾期的收入分配情況可能影響到當期的情況,所以我們使用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如模型4所示。在模型4中,把基尼系數和最低工資標準的滯后一期作為解釋變量,基尼系數的1階滯后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最低工資標準在5%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城鄉差距水平在1%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
(三)結論
從上面的實證結果來看,城鄉差距水平對基尼系數影響最為顯著,系數為0.7~0.9之間,即城鄉差距水平每增加1個單位,而基尼系數將會增加0.7~0.9個單位,城鄉的差距擴大將非常不利于收入分配調整,城鄉之間的差距增大可以代表整體經濟大部分的收入分配不均的擴大,而城市和農村內部差距只能解釋少部分的經濟整體收入分配的擴大。
從動態面板模型來看,上一期的基尼系數的程度對當期的基尼系數的影響也是顯著的。上一期的基尼系數的系數為0.4左右,過去收入分配不均程度確實影響著后期的收入分配調節,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低收入(或高收入)有著慣性作用,現實情況中存在著對低收入人群進一步提高收入的障礙。盡管可能是該收入者的主觀性作用,如懶惰;也有可能是制度性障礙,如要素的獲得。
從幾個模型來顯示的情況看,最低工資標準的系數為-0.05至-0.15左右,即最低工資標準每增加1個單位,基尼系數降低0.05~0.15左右,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能夠輕微地降低收入分配不均的情況,但是影響是輕微的。造成此情況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最低工資標準的設定受益者為城市低收入者和部分農民工。而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城市內部的收入差距縮小所能帶來的收入分配調整效果甚微,且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大多數為弱勢群體,不能很好地得到應有的法律保障。而從幾個模型可以看出,最低工資標準的滯后1期對當期的收入分配影響不明,且并未完全通過檢驗。同樣,人均社會保障支出對基尼系數的影響不明,目前不能作為調節收入分配的工具。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主要考察了最低工資標準對失業率、經濟發展以及收入分配的影響,為克服指標間較強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利用了VAR向量自回歸模型,分省份對上述前兩種效應進行了測度,同時使用動態面板考察了最低工資標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研究發現,單純認為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不利于就業和經濟發展的觀點是片面的,最低工資標準的就業效應和經濟效應在不同省份以及不同的政策滯后期內影響各異。
我們的研究結論是:中部和西部的部分省份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后,會釋放低工資對勞動積極性的壓力,增進就業;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不適當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又可能使由此產生的成本負擔對經濟發展產生下滑的風險;中西部省份的地方政府對制定最低工資標準必須更加謹慎。相比而言,東部省份的最低工資大致處于合理范圍內,并且鑒于最低工資在較長政策期內會顯現對經濟發展的促進效應,東部地區省份可以在財力可承受的范圍內,適當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最低工資標準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具有正面作用,但影響輕微。最低工資標準的設定對農民增收收效甚微,受益者多為城市低收入者和少部分農民工,尤其是在城市工作中常處于弱勢群體的農民工受益更少。城鄉差距代表了大部分收入分配不均的大部分原因,目前尚不能把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作為調節收入分配不均的重要工具。
[參考文獻]
[1]蔡昉,王美艷.中國城鎮勞動參與率的變化及其政策含義[J]. 中國社會科學,2004(4) 68-79.
[2]Bell.The impact of Minimum wages in Mexico and Colmbia[J].Journal of Labor markets,1997,15(3):102-135
[3]Lemos S.Minimum Wage Effect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Z].working Paper,2006:89-111
[4]羅小蘭.我國勞動力市場買方壟斷條件下最低工資就業效應分析[J]. 財貿研究, 2007(4):1-5.
[5]王祖祥,中部六省基尼系數的估算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06(4):73-88.
[6]羅小蘭. 壟斷勞動市場下的最低工資減貧效應:以中國農村為例[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1(8):60-65.
[7]石娟.我國最低工資標準的就業效應:基于全國和地區的實證研究[J].當代經濟管理,2009(12):8-11.
(責任編輯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