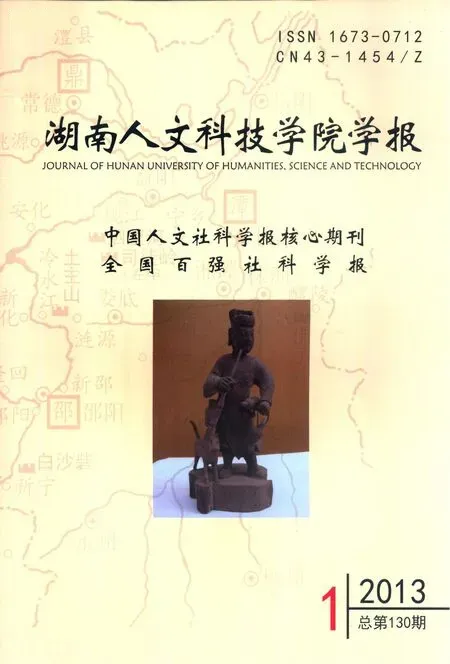行進中的霸權——以接合理論談《新娘來到黃天鎮》
張小龍
(湘潭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南湘潭411105)
小說《新娘來到黃天鎮》記敘了警長杰克·波特在東部城市圣安東尼奧結婚后,與新娘乘火車回到他的家鄉西部小鎮黃天鎮的過程;與此同時,斯克拉奇·威爾遜在黃天鎮上鬧事及鎮上某酒吧里東部行商和其他人對鬧事所作的反應。威爾遜鬧事,拿槍胡亂掃射,恰好在波特家門口與正趕回家的杰克夫婦相遇,最后威爾遜放過這對手無寸鐵的新婚夫婦,黯然離開。
接合乃是能夠在一定條件下將兩個不同的原素形成一個統一體的一種連結形式。“社會學上使用‘接合’這一術語,出自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原指不同生產方式的接合,而在這些生產方式中,往往某一種占據著支配地位,或凌駕于其他生產方式之上,并強迫它們進行調整以適應其要求”[1],與霸權(建立起領導權的合法性,發展共同的理念、價值觀、信仰和意義——即共享的文化,在此基礎上組織贊同)涵義有著相互交融的地方。本文借以接合理論更深層次剖析《新娘來到黃天鎮》中蘊含的東部文化霸權,提供了研究的新視角。
一 “新娘”來了
從文章標題來看,主語是來自圣安東尼奧的新娘,即東部文明的代表。因此東部文明的來到黃天鎮意味著什么,又會造成什么影響?新娘來到黃天鎮的這個過程,是一個不斷接合,解接合,再接合無窮盡過程中的一個片段。“接合”(articulation)一詞從詞源學來說,一種意義指兩種不同的事物相互鉸合或咬合在一起,如“鉸接式”卡車,其車頭(駕駛室)和后半部(拖車)相互連接起來而組成一個卡車整體。“(‘鉸接式’卡車的)兩部分彼此相互連接,但是要通過一個特別的環扣(linkage)連接起來。”[2]99故事從 19 世紀末圣安東尼奧開往黃天鎮的火車開始說起。這火車就好像接合的環扣,把美國得克薩斯州東部的圣安東尼奧與西部的黃天鎮連接在一起,形成接合。圣安東尼奧是德克薩斯州的三大城市之一,通墨西哥鐵路線的要站。起文處提到,如果向窗外看一看,就能看到德克薩斯的平原向東邊飛逝。可以看出,黃天鎮是位于圣安東尼奧的西部,是德州眾多小鎮之一。雖兩地均屬德州,但又在相對地理位置就分出了東西差別,經濟發展水平不平均。但是位于美國西南部的德州整體上像黃天鎮一般欠發達。鐵軌向西部的挺進,不僅加劇工業化的進程,還帶來了各種文化之間的交互,強勢文化的入侵。德州工商業進程確如普爾曼火車一樣,飛速前行。
來自黃天鎮的警長杰克·波特與東部圣安東尼奧姑娘的婚姻是關鍵的接合。他倆象征著西部文化與東部文化的聯姻,但作為個體,二人又有不同的地方,不能把該接合給本質化。“不過接合最終要形成一定程度的統一,盡管這統一是暫時的、不穩定的。因為很顯然,不能形成一個哪怕是暫時的統一體,人是無法認識這個世界的。”[2]101他倆的接合是一種偏向東部文明的接合體,新娘,新郎在圣安東尼奧有朋友,穿著西裝,購買當地精致貨物——新娘的小銀表,表明他正遠離西部文明,朝一個新人發展。他們選擇的是高檔普爾門式列車。該列車為19世紀美國發明家George M Pullman設計的豪華型列車車廂,常用為特等客車。車內裝飾有“織有圖案的海藍色天鵝絨,耀眼的黃銅、白銀和玻璃的裝飾與器具,以及像油池表面一樣烏亮的木制品。車廂的一頭,立著一具作為單人臥室支柱的青銅像。在車廂天花板的合適的地方,繪著橄欖色和銀白色的壁畫。”[3]598在這樣豪華裝飾的火車上的乘客一定不會是生活都無法保障的底層人士。新婚夫妻將自己裝飾得與東部人士毫無二致,他們的真正的歸屬卻從神情和動作等方面顯示出來。“新郎多日來日曬風吹,皮膚紅紅的,一身嶄新的黑衣服,使得那雙磚紅色的雙手總是顯得非常困窘的樣兒,”[3]598對于身處的環境,他并不如魚得水,想必不是真正屬于這個地方。紅紅的皮膚磚紅的手,說明作為警長的他經常在戶外工作。小心打量一身的新黑衣服的他,像等待理發一樣的他,偷偷瞟其他乘客的他,動作神情均局促不安。是什么讓他產生了深深的不自信?作為警長的他應該英姿颯爽,而不是畏畏縮縮十分困窘。就連最后將近下車時,侍者毫無傲氣為他刷衣服的時候,他學著給小費動作都是困難又僵硬。與此同時,“新娘并不漂亮,也不很年輕。”[3]598可以看出的是,她是一名家庭主婦,以后的工作大概就是家務活。她穿的也是一件新衣服,開司米質地綴上天鵝絨,但是硬又直的胖袖使她非常不自然。他們的種種不自信和尷尬的原因在于,在他們的常識上看來,這些動作和表情都是不地道的。常識等同于“一致輿論”或“普遍贊同”,因而也可以說是一種“共識”。葛蘭西將霸權理解為建構常識的斗爭,也就是說將各種不同的利益、信念和實踐接合和重新接合為常識。“一個階級行使霸權,并不在于它能夠將一種統一的世界觀念強加于社會中的其他階級,而在于它能夠將各種不同的世界觀念如此地接合起來,以至于它們之間的潛在對抗被中立化。”[4]這對新人未能熟練習得東部文化的社交技能,內心深處承認自己低于車廂內的其他人,而沒有對于此種隱性的霸權有著半點的反抗,可見強權已經中立化在了所有人的心中。不但這對新人看不起自己,其他乘客和黑人服務員,對于他倆的態度均是不屑與嘲笑,是強勢臨下于弱勢。
火車上東部文明不論在車廂裝飾或是人們的活動方面都彰顯無遺,而就算來到黃天鎮,由于工商業的發達和交通的便利化,強勢文明的侵襲并沒有受到地域的限制。其一是更多的東部人士來到了黃天鎮。酒吧里的主角之一,東部貨郎,不同于新娘,他是個善于交談言辭的人。貨郎依靠著酒柜,為酒吧里所有的人自信滿滿地講著故事。他滔滔不絕的話語主宰了整個酒吧,酒吧里的所有西部人都成為了他的聆聽者,一聲不吭。除了斯克拉奇·威爾遜,因為他的出現使得整個小鎮一動不動,當然酒吧也包含在內。即使他再強悍,也抵擋不過東部服飾文化的侵襲。從威爾遜的衣著來看,統統都是東部特色的輕工業產品,如“身穿紐約東區猶太婦女縫制的作為裝飾品的栗色法蘭絨襯衫”,“腳上穿的是新英格蘭山坡上滑雪少年在冬季愛穿的那種燙金的紅頭靴子。”[3]604他的穿著并不是普普通通粗糙之物,而是精致的襯衫,少年們所愛的靴子。不論這是威爾遜的真心所愛的潮流,還是無意為之隨便挑選衣物穿著,都是東部物質和文化無孔不入對威爾遜,對黃天鎮的入侵。無論是影響人們的審美觀念,抑或商品市場上的強權,不得不說,黃天鎮的特色都在逐漸隕落。可以看出,不論在物質方面抑或意識方面,接合的內部的東部元素正一步步占據上風,并持續下去。
二 “新娘”受阻
不容置疑,福柯說過“哪里有權力,哪里就有反抗”[5]。面對霸權欺凌,西部人有著自己的反擊。波特是鎮上的警長,是個令人害怕也叫人尊敬的人。在越發接近黃天鎮的時候,他漸漸感到壓抑。其實結婚對于黃天鎮是件歡天喜地的事情,并且依照鎮上的習俗人們憑自己的喜歡跟人結婚。“他很清楚,這樁婚姻對他那個小鎮來說是件重要的事情。這一消息只有像新旅館起火那樣的事才能相比。他的朋友是不會原諒他的。”[3]600如果東部文明主要表現在物質生活方面,那么文中的西部精神便是與東部抗衡的有力武器。黃天鎮是個民風淳樸的小鎮,大家對于結婚一事也是有商有量。當波特想到對于朋友的義務,這事情完全沒有考慮到的時候,他好像犯了大罪一般。同根同脈的情結,使他為難。波特內心的西部情懷也似乎隨著列車的西行漸漸將自己的東部傾向給邊緣化,使得自己朝著西部轉化回來。從接合所構成的原素上看,這些原素本身也是被接合成的,其本身同樣也可以看作是一個接合。波特這個人物的變化正體現了其內部意識因素斗爭的結果。波特的焦慮使得新娘也變得焦慮。下車后,見到情勢并未如他料想的那么糟糕,于是他笑了。趁著絕佳的時機,拉上新娘趕快在無人的街道跑回家。笑中帶嘆氣,到底只是竊喜,嘆氣的他也未能徹底釋懷,只能趁著大家都不在,飛快趕回家。
然而在黃天鎮上,霸權的反抗表現得更加顯性。威爾遜的鬧事肅靜了整個小鎮,沒人能與他正面對抗,除了警長波特。酒吧內所有人,內心與身姿全部處于一種屈服的狀態。行商也不得不嚴肅起來。好奇的他開始詢問發生了何事。待氣氛更加緊張,他看看這個又望望那個。“‘那么他會殺人嘛?你們準備怎么辦?這種事常常發生嗎?他每個禮拜都要這樣橫沖直撞嘛?他會打破那扇門嗎?’”[3]603一連五個問句,一口氣問出,行商明顯十分緊張。他不時詢問門窗是否牢固,威爾遜的來路,一邊漸漸加強防護。行商說著,汗也出來了。從善于言辭、自信的他,轉眼間就成了言辭慌張又流汗的膽小鬼。“接合由此不僅僅是一件事物(不僅僅是一種連結),而是一個創造聯結的過程,這與領導權是相同的,就是領導權不僅僅是統治,而是創造和維持同意的過程或共同確定利益的過程。”[6]這個時候再也不是話語主導者的他,變得言聽計從起來,最后他只好坐在箱子上低頭,才獲得安全感。東部貨郎的不穩定,象征著東部先進文化的弱點,即外表光鮮下其實隱藏了許多的不確定,許多不自信,在面對原始強勢的時候,在秩序失控的時候,東部文明何以駐足?相比之下,西部硬漢威爾遜算是黃天鎮上最后一個老流氓了。不喝醉酒,他是一個品性純良的人。但如果醉酒,那可怕程度是無法用語言來描述的。醉前醉后兩種人,兩種極端,一個是最好的人,一個是無法形容的兇猛。一個是平時純真善良無害的模樣,一個是喝酒后內心隱藏的惡魔。“接合雖然不是必然的,但接合又并不是任意的,而是需要“條件”的,這條件一方面是接合者的意圖,一方面就是歷史條件;”[2]100文中所提到的酒左右了他的雙重人格,酒就是使另外一種人格接合顯現的歷史條件。喝醉酒的威爾遜到底會是多么不好,已經沒人能說準。因此小鎮像被拋棄了一般,街道空無一人,根本無人應戰。威爾遜朝天狂呼,但毫無反應。他一邊揮舞著手槍,一邊四處咆哮著。這是屬于威爾遜一人的獨角戲,周圍一切毫無動靜,沒有任何人出現,沒有另一人物出現在這出表演中,唯獨一條狗。當然人獸之戰也只是小小一段,不久連狗都嚇得四處打轉。當然沒有人敢反抗,因為小鎮人們全部歸順于安靜平穩的東部文化。這是他向東部文明的反抗,是西部精神向東部文明的大肆侵略的報復。
三 “新娘”贏了
當波特帶著新娘回家遭遇威爾遜的時候,他忘了帶槍,甚至把威爾遜的存在忘記了。讀者由此便能順勢猜想到暴怒的威爾遜一定會輕而易舉地贏得這場戰斗。新娘見此,嚇得面色蒼白,無力招架。波特在面對關鍵時刻,心中是此起彼伏的,因為“接合就不是一個靜止的完成的物件,而是一個不斷的接合——解接合——再接合的動態的過程,一個接合完成后接著就進行下一個或下一次接合,所謂的統一也就只是暫時的。”[4]100他經歷了從立馬強硬,到解釋服軟,再堅毅起來,接著回憶早上發生的一切,內心平衡偏重不平,但最終他還是期望能為剛剛所開始的新的生活尋找一絲繼續下去的希望。同時當下情勢也只能讓他以靜制動,又不能求情失了從前勇士的精氣。他沒有為自己求情,更沒有為妻子求情。然而最終當波特解釋是因為他從圣安東尼奧娶了個妻子回來,所以沒有帶槍之后,這西東博弈的局勢開始了轉盤,威爾遜從開始面色鐵青慢慢變得鎮靜。“結婚了”這句話,威爾遜先是疑惑,繼而不愿相信,他一再詢問,而每一次的詢問都較上一次的氣勢減弱。他看到的新娘是一個“萎靡頹喪的女人。“‘不!’他說,好像一個人看到了另一個世界。他后退了一步,持槍的手垂了下來。”[3]607面對一個來自圣安東尼奧的陌生女人,未知的面孔,雖然她一到黃天鎮后就沒有了話語,以弱勢的形象展現于作品中,但表面弱勢的她卻帶著東部文明強勢的符碼,以不自覺的形式壓制異質文明,更能彰顯東部文明的隱性霸權。威爾遜看到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巨大威力,垂下了手中的槍。酒始終要醒,能讓野性的接合體顯效的歷史條件漸漸地消退。這槍若是開,威爾遜要失去唯一的對手。這槍若是不開,波特也要將重心放在安寧的婚后生活,而不可能像往常一樣與他進行殊死搏斗,同樣是失去對手。看著對手的無力應戰,及今后可想而知的孤掌難鳴,僅存的斗士精神也就只是茍延殘喘。心中最后的英勇無畏,失去了發揮的環境。一切歸于和順與秩序,西部精神只剩下背影。
威爾遜酒后向東部文明發出的挑戰,由于從圣安東尼奧來的新娘,這場戰斗在無聲中流了產,他輸得無聲無息,輸得那么落寞。面對著東部文明的入侵,他無力應對,是寂寥的。他的不戰而敗,不僅是個人的,而且是在東部文明的大潮下,工業化的鐵輪對于整個西部不斷的碾壓。工商業生產方式對于西部農牧業生產方式的凌駕和規約調整,發展共同理念和文化,以東西接合的方式逐漸吞噬西部原始特色,形成以東部為主導的文化。像杰克的婚姻一樣,水到渠成,這就是西部的宿命。整部作品冷峻客觀,讓人不覺一絲悲戚,卻滿心哀涼。
[1]約翰·費斯克,等.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M].2 版.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16-17.
[2]和磊.沒有必然的對應:霍爾的接合理論分析[J].理論界,2011,4(10).
[3]BROOKS C,WARREN R P.小說鑒賞[M].主萬,等,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6:598-607.
[4]LACLAU E.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M].London:New Left Books.1977:161.
[5]汪民安,陳永國,馬海良.福柯的面孔[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458.
[6]MORLEY D,KUAN-HSING C,ed.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M].London:Routledge,1996: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