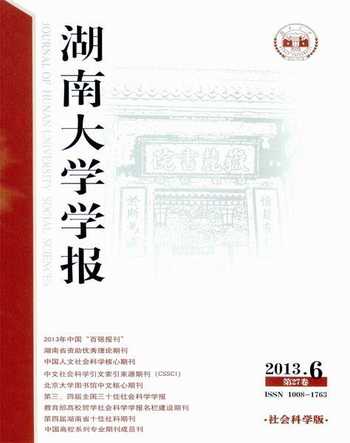弗蘭納里?奧康納《智血》中的“眼睛”
[作者簡介] 曾竹青(1968—),女,湖南邵陽人,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國文學.
[摘要] 在美國小說家弗蘭納里·奧康納的第一部作品《智血》中,“眼睛”這一意象貫穿小說始終。奧康納賦予“眼睛”高度的象征意義。它代表著求知求真的激情,引導主人公認知自我。它也象征著通向超越世界的心靈之眼,照亮現代人尋找精神家園之路。但并不是所有的“眼睛”都能獲得心靈之眼的視覺。要想獲得心靈之眼就必須犧牲肉體之“眼”。
[關鍵詞] 弗蘭納里·奧康納;《智血》;“眼睛”;心靈之眼
[中圖分類號] I106.4[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8—1763(2013)06—0095—04
《智血》是美國小說家弗蘭納里·奧康納的第一部小說。它講述了剛從二戰戰場歸來的黑茲爾從質疑基督到最后皈依基督的心路歷程。在敘述這一歷程的過程中,對眼睛以及與眼睛有關的活動的描寫貫穿小說的始終。它推動情節的發展,塑造人物的性格,尤其是黑茲爾用石灰弄瞎眼睛的舉動,更是讓眼睛這一意象具有了高度的象征意義。因此,在小說中眼睛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視覺器官,它代表著求知求真的激情,引導人們認知自我,也象征了觀照超越世界的心靈之眼,照亮了現代人回歸精神家園之路。一認知自我之眼
眼睛在西方傳統中具有一種形而上的意義。這一傳統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對古希臘人而言,眼睛是人賴以接受日神阿波羅光明的器官,是知識之源,因而被視為人類身體最高貴的器官,[1]24并且在日常和哲學話語中常常運用眼睛以及與之相關聯的視覺隱喻來意指對真理的認識。海德格爾就引用荷爾德林的“俄狄浦斯王也許是多一只眼睛”的說法來形容俄狄浦斯求知求真的激情。在他看來,《俄狄浦斯王》這出戲的展開是“外表(遮蔽和歪曲)與去蔽(unconcealment)(真實和存在)(being)之間的一場斗爭”。[2]106在這場斗爭中俄狄浦斯有著質疑表象,求“此在”和“去蔽”的激情,為了求得真相而不計任何后果,不惜一切代價。而這都源于他比別人多一只眼睛,“這多出的眼睛是所有大問與大知的基本條件”。[2]107在《智血》中,奧康納沿用了西方傳統中有關眼睛的比喻意義,賦予小說主人公黑茲爾的眼睛形而上的求真功能,甚至還沿用了海德格爾對荷爾德林的“俄狄浦斯也許是多一只眼睛”的解釋,塑造了一個為求真而不顧一切的現代版本的俄狄浦斯。
黑茲爾有一雙在外觀形態上令人矚目的眼睛。在火車上,黑茲爾的鄰座希區科克太太最先注意到的是他那雙“陷進去那么深,在她看來就像是引向遠方的兩條通道”[3]對小說的引用均出自于周欣譯的《智血》,只在文中標注頁碼。的眼睛。薩巴思對她父親說她喜歡黑茲爾的原因是他的雙眼“看起來一直在盯著看,卻讓人覺得什么都沒看”。(99-100)黑茲爾的房東太太第一次與他見面時,就覺得他的雙眼有著隨時都想向前沖,想要得到什么東西的架勢。即便是后來黑茲爾自殘了眼睛后,那深深的眼窩也能激起除了錢以外,對任何事物都無動于衷的她的好奇心,努力想看到那眼窩深處到底有什么東西,最后她仿佛看到他空洞洞的眼底深處有一個光點。在這些描述眼睛的語匯中,“引向遠方的通道”讓人想起對真理的漫漫求索之路,“盯著看,卻什么都沒看”意味著他的視覺想要超越以表象呈現的事物,直達真實的存在,“光點”更是指真理之光。總之,它們都喻示了黑茲爾眼睛的求知求真功能。而在行動上,黑茲爾的眼睛總是充當求真的先鋒,一點也沒有辜負那些描述他的眼睛的語匯。可以說,黑茲爾的每次揭示真相之旅都始于他對要揭露的對象的“一直盯著看”。小說一開始,在開往托金漢姆城的火車上,黑茲爾的眼睛就一直望向他車廂里的列車員,就連他的鄰座找話題與他聊天時都沒能讓他的眼睛離開那位列車員,因為他斷定這位列車員來自于他的家鄉,他要識別他真實的身份。在托金漢姆城遇見了霍克斯之后,他千方百計設法要站在霍克斯面前,每次都“定定地瞅著”霍克斯偽裝成盲人用的墨鏡,“好像想透過那副墨鏡把他仔細瞧個夠似的”。
可見,黑茲爾的眼睛不論在外觀上還是在行動上都表明他是一個有著求真意識的人。而實際上黑茲爾的求真意識如此強烈,以至于可以用激情兩字來形容他對真相的渴望。在小說中,他是一個質疑一切的人,大到不相信世上有原罪和有基督拯救人類之說,小到懷疑一個列車員的身份。為了追尋真相,他可以動用一切手段。比如說,當他認定霍克斯是圣保羅的化身,以為通過與他對質就能證明耶穌是否真的存在時,他千方百計尾隨至霍克斯的住處,不斷騷擾他,甚至不惜動用引誘霍克斯女兒的手段來接近他。他仇恨世上任何不真實的事和人。當他發現肖茨不是真心信仰“沒有耶穌的教派”以及索勒斯假冒他宣揚他創立的教派時,他不惜用車門夾傷肖茨的手指甚至用車碾死索勒斯這樣暴力的方式來消滅這世上的不真。正是在這種激情的驅使下,他每一次的“盯著看”都能收獲真相。在他的審視下,列車員每次都躲著他已證明他們實際上是同鄉;而霍克斯最后也在他的對視下現出了假裝盲人的原形。不過,他的求真激情最大的收獲是他對自我的認知。
黑茲爾的質疑一切的精神和對揭示真相的執著體現了自啟蒙時代以來人對于自身認知能力的自信:人可以依靠自身的認知能力,而不是外在的權威與力量,比如說上帝,去認識真理,探求未知世界的真諦。這種自信使得人們擺脫了對上帝的心理依附,是人的精神的大解放,極大的激發了人的創造力。在小說中,黑茲爾既秉承了現代人對自身認知能力的自信,同時也讓這自信過度膨脹為一種想要超越上帝意志的自負。最能表現這種自負的是他所說的“有一輛好車的人是不需要什么人(上帝)來赦免的”,言外之意就是說有一輛好車的人就是全能全知的上帝。車是人類自身認知能力的成就之一,是人類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產物。乘著這一人類科技成就的翅膀,他似乎實現了與上帝比肩的雄心壯志:在宣揚沒有原罪就沒有墮落的教義時,他就站在車的引擎蓋上;他像上帝懲罰違背他意志的人一樣懲罰索勒斯時,所用的工具就是車;他想去別的地方宣揚他的“沒有耶穌的教派”,只要一踩油門,那輛車會帶他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可見,車真是一件實現他的自由意志的好工具。
但對種種真相的揭示,甚至與上帝比肩都沒有給黑茲爾帶來多少滿足感和成就感。他在書中大部分時間都處在一種焦慮不安的狀態中。這種不安主要從他的夢境中反映出來。比如說,在宣講了他那否定原罪、否定救贖的教義并懲罰了肖茨的不真實之后,他夢見自己在車里被活埋,“期待霍克斯手拿扳手出現在橢圓形窗口”來搭救他,而在當時的他的眼中,霍克斯仍然還是圣保羅的化身。這樣的夢境表明在他潛意識當中希望上帝化身霍克斯來拯救他。在雷根看來,黑茲爾的這種既否定上帝又想要上帝來拯救的矛盾心理體現了存在主義的焦慮,[4]162-165即人類在擺脫上帝的懲戒和監視之后,為不得不要由自己為沒有標準的選擇擔當責任而感到不安和恐慌。然而,對于黑茲爾而言,他的焦慮不安也同時是由于他那不斷追尋真相的激情使他總是隱約感到最終的真相還沒有獲得所造成的。因此,在發現霍克斯假盲的事實從而認定他已不宜作為質疑上帝的途徑時,黑茲爾決定離開托金漢姆城,繼續他的追尋真相之旅,也正是在這一旅途中他發現了最終的真相。
離開托金漢姆城沒多遠,黑茲爾的車就被警察推下高高的堤坎。沒有了車的黑茲爾從與上帝比肩的云端跌落在公路上的堤坎上。他失神地呆站在堤坎上,腳下是被摔得七零八落的車,臉像鏡子一樣照出了“那穿越林中空地直到天涯海角的整個遠方,從眼睛伸向灰蒙蒙的遼闊天空,一直深入到那無垠的太空”。此時此刻,黑茲爾的眼睛映照了一幅對比鮮明的圖畫:“遼闊天空”與無垠的太空襯托出黑茲爾孤零零站在堤坎上的身影是多么地渺小,以及被毀的車有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擊。盡管此時的黑茲爾默默無語,但他的眼睛所折射的景象已昭示了他對自我的認知:人的自由意志無論多么強烈和強大,無論其實現的手段有多么發達和先進,都如同他那輛車一樣脆弱,更遑論超越上帝的意志了。認知了人的局限性的黑茲爾用石灰自殘了雙眼,懲罰了自己對神的狂妄,清算了以不知為知的過錯。比起霍克斯不敢弄瞎自己眼睛的怯懦,黑茲爾自毀眼睛時的決然和從容充分顯示了他為真相而不顧一切的勇氣和激情。從這一點看,他就是一個海德格爾所說的比別人多一只眼睛的俄狄浦斯。
二觀照超越世界之眼:肉體之眼與心靈之眼
雖然眼睛是五官中最適宜理性認知的器官,但古希臘人又認為,眼睛的肉體性質決定了它在認知中永遠不能像理性那樣完善。也就是說不是所有的眼睛都能認知真理。基于這一觀點,柏拉圖將眼睛分為肉體之眼和心靈之眼。它們分屬不同領域、具有不同功能。肉體之眼對應現實世界,負責觀看外在事物的形式,易受欲望控制而陷入錯誤的認知。心靈之眼對應理念世界,負責洞察內在精神的真理,能斬斷欲望的牽絆,直達真理,[5]115甚至能看到理智在天上運作的過程。[1]25用柏拉圖這兩個概念來考察《智血》中所有人物的與眼睛有關的活動,我們可以看出,奧康納也將眼睛分為肉體之眼和心靈之眼。在她筆下,肉體之眼對應塵世的欲望,而心靈之眼也像柏拉圖帶有神學色彩的概念一樣,對應上帝的超越世界,而要想獲得心靈之眼就必須犧牲肉體之眼。
在小說中,伊諾克是一個典型的只有肉體之眼視覺的人。他與黑茲爾一樣,也有著盯著看的愛好。這位托金漢姆城市中心公園的看門人每天必做以下幾件事:首先是去游泳池偷看女人游泳,女人露出來的胳膊和腿總是讓他臉紅心跳;享受完小吃攤上的巧克力麥乳精后,他去看關在籠子里的動物,那些養尊處優的動物每次都惹得他惱怒萬分,因為他自己的居住條件沒法與它們相比;最后是去博物館景仰干尸,因為在他眼中那干尸有著令他敬畏的神秘力量。與黑茲爾不同的是,他的觀看對象都代表著塵世的欲望。他觀看它們不是像黑茲爾一樣詰問虛像,揭示真相,而是為了滿足他本能的欲望,或發泄因欲望不能滿足而產生的不滿。這都源于他對物質的崇拜—那具博物館的干尸本來只是一件物品,但伊諾克卻把它當作神來跪拜。這也是為什么他對“超市有種特殊的喜愛”,因為五顏六色的商品能驅逐他心靈的空虛和無聊。
小說中的托金漢姆城是一個“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6]143的祛魅之城。在這里,人們把對上帝的信仰只看成是一種心理迷戀,不再在乎誰信不信上帝。街道上燈紅酒綠,路上行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但心與心之間的距離卻相隔十萬八千里。所有人都忙忙碌碌于對物欲的追求,無暇思索靈魂得救與否。然而伊諾克的雙眼受控于塵世的種種欲望,無法讓他認清他周圍世界的真相。因此,他身陷于物欲的泥潭而不能自拔,靈魂空虛而沒有歸宿。到最后,為了獲得人群的接納以充實空虛的心靈,他竟然將自己物化成一只做廣告的猩猩。不過他裹在獸皮中的模樣嚇跑了人們。最后他留給我們的是一個站在山頂上望著山下喧鬧的托金漢姆城的孤寂的背影。這個被物質消費世界完全腐蝕的年輕人盡管受盡了物質世界的白眼,但到最后他向往的仍然是那個物欲橫流但人與人之間疏離的物質世界。
面對伊諾克這樣的肉體之眼,黑茲爾有著天然的反感。他每次都用呵斥打消伊諾克想要親近他的企圖,甚至用石頭砸伊諾克以懲罰伊諾克引誘他觀看代表著塵世欲望的那些景點。到最后他撕碎伊諾克想要他充當新耶穌的干尸,徹底摧毀了伊諾克信仰的拜物主義。他對伊諾克的抗拒顯示了他的眼睛能斬斷塵世種種欲望的誘惑,看清了他所處的世界已精神沉淪這一事實。盡管抗拒像伊諾克這樣的人的誘惑使他成為小說中最孤獨的人,但他的這種孤獨是克爾凱郭爾所描述的現代社會中為了保存自我的完整,通過自我放逐的方式將自己與墮落的世界保持距離以體現存在的真實性的“孤獨個體”的孤獨,也是尼采所描述的現代社會中忍耐分離、拒絕現代文化與社會習俗規范的悲劇英雄的孤獨。[9]112從這一點看,他仿佛已具有了直達真理的心靈之眼。但是,在奧康納看來,這還不夠。因為此時的黑茲爾的眼睛雖然能看清像伊諾克這樣的人的真相,卻由于受制于人的自由意志能超越一切的自負而兩次錯過了上帝的召喚。一次是他剛到托金漢姆城時,上帝幻化成“建造浩大、神秘而威嚴的宇宙工程的腳手架”出現在喧囂的城市上空, 還有一次是他駕車與薩巴斯兜風來勾引她時,上帝先是幻化成一朵白胡子老頭般的白云,后又幻化成一支靈魂之鳥出現在他的頭頂上。而當時的他不是趕著去褻瀆神靈以證明不管有罪與否都不會受到上帝的懲罰,就是糾結于私生女是否能在他的教派中得到赦免而無暇顧及。他當時的這種狀態正印證了霍克斯第一次與他見面時說他有眼睛卻看不到的話。
最終,黑茲爾看到了上帝,但那是在他沒有眼睛之后。自殘雙眼后的黑茲爾不再宣稱他是“潔凈的”,認為自己有罪,欠了上帝很多“債”。他每天腳穿里面放了碎玻璃和石頭的鞋子外出步行一上午,到了夜晚身纏帶刺的鐵絲睡覺。用折磨肉體的方式來償還上帝的債,向上帝贖罪。這一切都表明他又回到了他童年時的狀態:對上帝充滿了敬畏,所作的一切只為讓上帝滿意。這樣做的結果是他的心靈因回歸上帝、重回精神家園而變得寧靜。他不再像目盲之前那樣,為世上是否真有耶穌而糾結不已,也不再有存在主義的焦慮感。每天默默地起居,對外界的一切無動于衷。當他死后,奧康納更是用“冷峻”、“寧靜”以及“安寧”這樣的詞來形容他沒有知覺的臉。可見,黑茲爾毀掉肉眼的視覺是為了開啟了觀照超越世界的心靈之眼,讓自己沐浴在上帝之光中,以求得心靈的寧靜。
黑茲爾的心靈之眼還照亮了房東太太回歸上帝之路。在小說中,房東太太是一個眼里除了錢什么都看不到的人。但是面對黑茲爾空洞洞的眼窩,她平生第一次思考永恒、生和死以及光明這些有關人的價值的問題。她還數次想象自己如果瞎了之后會是什么樣的情形。漸漸地,她竟覺得黑茲爾的眼底深處有一個亮點。在基督教中,光亮代表著上帝。可見,房東太太的心靈開始向超越世界敞開。但這還不夠,因為她總覺得自己被擋在通向那個亮點的入口處,讓她無法將那亮點牢牢裝在心中。只有當她坐在黑茲爾的尸體旁,閉上雙眼,才終于覺得進入了那條通向光亮的長長的通道,“看見他正在越來越遠地離去,深入到黑暗中,直到變成了那個光點”。她終于看到了上帝之光,只不過是在閉上受物欲控制的雙眼之后。奧康納正是用房東太太閉上雙眼這一象征性地失去肉眼視覺的舉動再一次強調,要想獲得感知超越世界的心靈之眼,讓靈魂回歸精神家園,就要犧牲肉體之眼,即斬斷塵世的種種欲望。
三結語
奧康納曾在一封給讀者的信中說:“我的讀者是那些認為上帝已經死了的人。我很清楚自己正是為這些人而寫作的。”[8]943而且,她也很清楚,現代人在經歷了宗教改革、近代理性主義、實驗科學精神、工業化、存在主義思潮等等祛魅浪潮后,要他們相信真有上帝存在可以說是一個無法完成的任務。因此,她常常在作品中通過描寫暴力、死亡或者畸形來震醒因敬畏感缺席而道德滑坡的社會和因信仰缺失而心靈麻木的人。在她看來“對于耳背的人,你要大聲呼喊;對于幾近目盲的人,你不得不畫出大而驚人的人物”。[9]806在《智血》中,奧康納正是用主人公自殘雙眼這一暴力行為意圖震醒她的讀者。黑茲爾這一驚世駭俗的舉動如同茫茫黑夜中的一道閃電,照亮了現代人尋求精神歸趨之路。
[參考文獻]
[1]Jay, Martin. 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2]Heidegger, Martin.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M]. Trans. Ralph Manhei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3]弗蘭納里·奧康納.智血[M].周欣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
[4]Ragen, Brian Abel. A Wreck on the Road to Damascus: Innocence, Guilt, Conversion in Flannery O’Connor [M].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9.
[5]高燕. 論海德格爾對視覺中心主義的消解[J]. 上海大學學報,2010,(7):114-124.
[6]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 于曉,陳維綱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7.
[7]凌津奇.離散三議:歷史與前瞻[J].外國文學評論,2007,(1):110-120.
[8]O’Connor, Flannery. “Letters”, in Collected Works [M].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88.
[9]O’Connor, Flannery. “The Fiction Writer and His Country”, in Collected Works [M].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