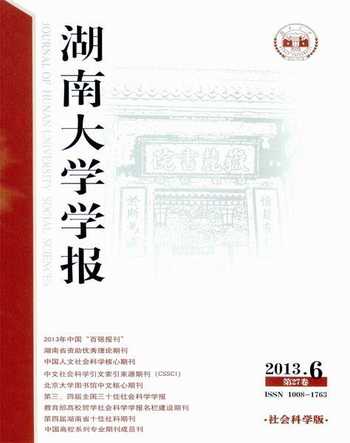盜竊罪與詐騙罪的關系
[作者簡介] 陳洪兵(1970—),男,湖北荊門人,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研究方向:刑法解釋學
[摘要] 雖然處分行為是區分盜竊與詐騙的關鍵性要素,但只需認識到財物外形上的占有轉移即可,因而“處分意思不要說”相對合理;三角詐騙與盜竊罪間接正犯的根本區別在于,受騙者是否具有處分他人財產的權限和地位,此應以陣營說為基礎,結合社會的一般觀念進行判斷;盜竊罪與詐騙罪不僅可能形成想象競合,還可能存在法條競合,同時符合兩罪構成要件時,應以盜竊罪定罪處罰;承認二罪之間存在競合關系,有助于認識錯誤和共犯問題的處理。
[關鍵詞] 詐騙罪;盜竊罪;處分意思;處分權限;競合
[中圖分類號] D92411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8—1763(2013)06—0134—08
刑法第264條規定:“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第266條規定:“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從法定刑看,盜竊罪與詐騙罪似乎沒有差別,其實兩罪的處罰嚴厲程度有所不同。一是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是單獨入罪的條件,沒有數額較大的要求,而成立詐騙罪必須達到數額較大;二是司法解釋規定,盜竊罪數額較大的標準是1000元至3000元以上,而詐騙罪是3000元至1萬元以上,相應地,盜竊罪中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也比詐騙罪要低得多。不難看出,盜竊罪的處罰實際上比詐騙罪要嚴厲。所以,準確區分二罪,在量刑上具有重要意義。此外,在罪質評價上,二者也存在差異。相對于盜竊罪這種他損犯罪,詐騙罪是一種自我損害的犯罪,被害人具有一定的過錯,要么出于貪婪心理,要么過于輕信對方,盜竊罪則不然,即便是疏于保管等原因導致被盜,被害人也往往沒有明顯過錯。被騙是否比被盜更難于啟齒,雖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不可否認,具體行為是被評價為盜竊罪,還是詐騙罪,即便被害人不關注,被告人也不可能不在乎。再者,準確闡釋各罪的構成要件,清晰界分此罪與彼罪,也是罪刑法定主義的要求。故而,明確盜竊罪與詐騙罪的關系,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處分意思的要否
詐騙罪的基本構造是:欺騙行為→錯誤→交付(處分)→財物·利益轉移。詐騙罪是基于他人有瑕疵的意思交付(處分)財產而轉移占有的犯罪。而盜竊罪,是違反被害人的意思,將他人占有下的財物轉移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雖然二者同為奪取罪(即占有轉移罪),但詐騙罪屬于表面上得到被害人同意的交付罪,而盜竊罪是未經被害人同意的盜取罪。
雖然理論上均認為,處分行為的有無是區分盜竊罪與詐騙罪的關鍵,
但對于處分行為人是否需要處分意思(即處分意識),以及處分意思的內容如何,則存在分歧。處分意思必要說認為,評價處分行為,不僅要求受騙者在客觀上具有處分財產的行為,而且要求主觀上具有處分財產的意思。如果肯定無意識的處分行為,會導致難以區分盜竊罪與詐騙罪。
而處分意思不要說認為,只要被騙者客觀上存在處分行為即可,不以主觀上存在處分意思為必要。
處分意思緩和說(即折中說)認為,即便是處分意思不要說,為了肯定存在“基于對方有瑕疵意思的占有轉移”,也以存在某種轉移意思為必要;而且,也將虛構所交付之物的價值的情形包括在內,因此可以認為,如果對處分意思的內容作相對寬泛的理解,兩種學說之間只是限于表面的對立。
應該說,“日本刑法理論中的處分意識不要說與處分意識必要說在具體結論上,并不存在特別差異。”因為,“處分意識不要說一般將‘處分意識’理解為財產處分者對所處分的財產的價值(價格)、數量、種類、性質有完全的認識,進而認為不要求這種完全的認識;而且,持處分意識不要說的學者,為了肯定受騙者‘基于意思而轉移占有’,也要求受騙者有某種轉移的意思;而持處分意思必要說的學者通常對處分意識做緩和的解釋。于是,二者的對立呈現表面化的局面。”
關于處分意思是否必要的各種學說,實質分歧在于,對處分意思的內容,即處分行為人的認識內容、認識程度的理解的不同。主張處分意思緩和說的日本學者山口厚認為,只要出于占有轉移的意思,即便并未具體認識到所轉移的物或者財產性利益的存在亦可;對所轉移的物或者財產性利益的價值、內容、數量存在錯誤,也可認定存在“基于意思的占有轉移”;謊稱要去處理掉,而拿走了夾有1萬元紙幣的舊雜志,或者謊稱已經履行了債務,而事實上逃避債務履行的情形,也包括在內。
可見,山口厚教授認為財物種類即質的認識錯誤,仍屬于詐騙罪中的認識錯誤,而肯定具有處分意思。主張處分意思必要說的張明楷教授認為,“在受騙者沒有意識到財產的種類而將財產轉移給行為人時,不宜認定具有處分意識。”
可見,張教授認為只有量的認識錯誤,才屬于詐騙罪中的認識錯誤,才能肯定行為人具有處分意思,而種類即質的認識錯誤,不宜肯定行為人具有處分意思和處分行為。
筆者認為,處分意思不要說具有相對合理性。只要被騙人認識到財物外形上的占有轉移,即使沒有認識到所轉移的具體財物的種類、數量、價值,即無論是量的錯誤還是質的錯誤,均屬于詐騙罪中的認識錯誤,應肯定存在處分行為而成立詐騙罪。
Symboly@@ ]因為,盜竊罪與詐騙罪具有占有轉移的共同本質,只是占有轉移的原因不同;盜竊罪是他損犯罪,是行為人單干完成的犯罪,而詐騙罪是自損犯罪,是被害人由于受到行為人的欺騙,主動奉上財物的犯罪;二罪侵害法益一樣,非難上的差異僅在于促使財物占有轉移的手段上;既然行為人使用了欺騙手段,對方因受欺騙而直接將財產轉移給(必須符合詐騙罪的直接性要件)行為人占有,即便沒有具體認識到轉移占有的財物的種類,也無法否認具備了欺騙的行為本質;而且將種類的錯誤歸入“詐騙”,也符合一般人的觀念;相反,若認為只有量的錯誤才成立詐騙,質的錯誤應成立盜竊罪,則明顯使得盜竊罪與詐騙罪的區分人為地復雜化。
張明楷教授設想了四個案例:(1)甲將商場中的便宜照相機與貴重照相機的價格條形碼互換,店員將貴重照相機按照便宜照相機的價格“出售”給行為人(以下簡稱“價格條形碼案”);(2)乙取出照相機包裝盒中的泡沫,將兩個照相機塞入一個照相機包裝盒中,店員僅收取一個照相機的貨款(以下簡稱“照相機案”);(3)丙取出方便面包裝盒中的方便面,將照相機塞入方便面包裝盒中,店員按照方便面的價格收取貨款(以下簡稱“方便面案”);(4)丁明知被害人的書中夾有一張貴重郵票(被害人沒有意識到),假裝向被害人借書而非法占有其中的郵票(以下簡稱“郵票案”)。張教授指出,首先,在受騙者沒有認識到財產的真實價值(價格)但認識到處分了該財產時,應認為具有處分意識。因而,上述“價格條形碼案”成立詐騙罪。其次,在受騙者沒有認識到財產的數量(或財物的數量),但認識到處分了一定的財產時,也宜認定為具有處分意識。上述“照相機案”宜認定店員具有處分意識,乙的行為成立詐騙罪。再次,在受騙者沒有意識到財產的種類而將財產轉移給行為人時,不宜認定具有處分意識。上述“方便面案”中,不宜認定店員對照相機具有處分意識。因為在根本沒有意識到方便面包裝盒中有照相機的情況下,不可能對照相機具有處分意識。其實,行為人將照相機放入方便面包裝盒中只交付方便面的貨款,與行為人在購買方便面時將照相機藏入自己大衣口袋里只交付方便面的貨款一樣,對于店員而言沒有實質區別。如果將后者認定為盜竊罪,那么對前者(方便面案)也應認定為盜竊罪。最后,在受騙者沒有意識到財產的性質而將財產轉移給行為人時,也不宜認定具有處分意識。上述“郵票案”中,不宜認定被害人具有處分意識,因為被害人根本沒有意識到郵票的存在,只是轉移書的占有,并沒有轉移郵票占有的意思,丁的行為成立盜竊罪,因為丁實際上是以借書為名掩蓋盜竊行為。
筆者同意張明楷教授關于“價格條形碼案”與“照相機案”的分析及結論,但不贊同關于“方便面案”和“郵票案”的處理結論和理由。就“方便面案”而言,認為“行為人將照相機放入方便面箱子中只交付方便面的貨款,與行為人在購買方便面時將照相機藏入自己大衣口袋里只交付方便面的貨款一樣,對于店員而言沒有實質區別。如果將后者認定為盜竊罪,那么對前者(方便面案)也應認定為盜竊罪”的觀點,筆者以為值得商榷。將照相機藏入自己大衣口袋,根據刑法理論通說,盜竊行為已經既遂,
而將照相機塞入方便面紙箱中,只要行為人沒有走出收銀口,照相機都還在商場的占有之下。致使照相機的占有發生轉移的原因,正是丙將裝有照相機的紙箱冒充普通方便面紙箱交給收銀員結賬,收銀員因受到欺騙而做出了將裝有照相機的方便面紙箱,作為普通的方便面紙箱處分給行為人的決定。而且,如果張教授的類比成立,則在行為人將照相機裝入方便面紙箱時就已經成立盜竊罪的既遂,但想必張教授也不會認同這個結論。可以肯定,致使照相機占有轉移的行為,是行為人在收銀口將照相機冒充方便面結賬的欺騙行為,因而應以詐騙罪予以非難。
至于“郵票案”,認為“被害人根本沒有意識到郵票的存在,只是轉移書的占有,并沒有轉移郵票的占有的意思。丁的行為成立盜竊罪,因為丁實際上是以借書為名掩蓋盜竊行為”,這種看法也值得討論。郵票的占有之所以發生轉移,是由于丁欺騙了被害人,使被害人誤認為是將一本普通的書借給了丁;也就是說,轉移占有的手段是“騙”,而不是“竊”。被害人雖然沒有認識到郵票的存在,但認識到了連同郵票在內的財物外形上的占有轉移,而且,占有之所以轉移,正是因為受到丙的欺騙;而詐騙罪,本來就可謂盜竊罪的間接正犯,
是借助被害人的手轉移占有。此外,所謂掩蓋犯罪事實,一般都是發生在本來的犯罪之后,同時發生的,也難言“掩蓋”;而且,本案也不是行為人將郵票藏入書中,而后以借書為名轉移郵票的占有。
筆者認為,因受欺騙而做出財物占有轉移的決定的,只要行為人認識到了財物外形上的占有轉移,就應肯認處分行為的存在。而且,在現代經濟社會,雖然使用者關注的是商品的種類,但商家關注的只是價值,商家既可以單賣,也可以將不同種類的商品捆綁銷售,就說明了這一點;對于商家而言,無論是方便面,還是照相機,最終都只關注價值上的損失,如果方便面的紙盒足夠大,行為人放入一個照相機的價格并不高于一箱方便面的價格,那么即使行為人將一個照相機冒充一箱方便面結賬,店員因受“欺騙”也陷入了種類上的認識錯誤,但想必商家也不會認為自己遭受了財產損失。所以,對于只追逐價值和利潤的商家來說,區分種類與數量的認識錯誤,認為前者構成盜竊罪,后者構成詐騙罪,并沒有多少實質意義。我們應關注的,是發生財物占有轉移的原因,究竟是“騙”,還是“竊”。
國內學者劉明祥還討論了賣魚案:假定行為人趁店員不注意將店員的錢包丟進魚袋中,稱重付款后一并帶走。劉明祥教授認為,由于“店員并不知道袋子里面有自己的錢包,沒有把錢包這種特定的財物轉移給行為人占有的意思,因而不能認為有交付錢包的行為,以錢包為對象的詐騙罪當然不能成立。”而且,“實際上,行為人把店員的錢包放入裝魚的袋中時,就已經構成盜竊罪,至于后來店員交付魚的行為,只是為其實現對錢包的占有起了幫助作用,不能以此作為定詐騙罪的理由。”
筆者對此抱有兩點疑問:一是即便店員沒有認識到魚袋中裝有自己的錢包,但也認識到了包括錢包在內的財物外形上的占有轉移,而且轉移占有的原因是因為受到欺騙。二是認為行為人將店員的錢包放入魚袋中,即便尚未稱重付款,就已經構成了盜竊罪,這恐怕不符合客觀事實,因為付款前裝有錢包的魚袋仍屬于店員占有。也就是說,將錢包放入魚袋中,頂多屬于詐騙罪的預備行為,若認為放入魚袋中就已經構成盜竊罪,無疑使財產犯罪的處罰過于提前。
還有學者討論了所謂新型的機票款詐騙案:2010年7月22日,孫某通過某訂票網提供的電話“4006-488823”預定機票,客服人員要求孫某通過網銀匯款,孫某遂按照其要求將958元機票款匯至工行某賬戶。雖經查詢已扣款成功,但對方說錢未到賬,聲稱需要通過ATM機“聯網操作”以使付款生效。于是孫某又按其引導,在ATM機上輸入所謂的使購票款生效的激活碼“18356”(實際上該數字輸入到了ATM機的轉賬數額一欄),相應數額即被轉入騙子賬戶。此時,孫某丈夫來電,說接到短信通知,賬戶被扣18356元。孫某急忙找客服交涉,此時客服稱,之前通過網銀支付的958元機票款已收到,機票也已生效,賬戶被扣18356元系失誤操作所致,可通過網銀轉賬退還,并教孫某如何操作。之后,騙子以輸入驗證碼的名義“指導”孫女士輸入數字“280838”。得手后,騙子又以退款操作為由,用同樣手段轉走2萬余元。該案中,行為人前后轉賬四次,總共被騙32萬余元。
有人指出,只要實際管控財產且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主體因為被騙而實施了財產處分行為,即使其主觀上沒有處分財產的意思,也應當認定為詐騙罪中的處分行為。被害人的處分意識只是學者們通過不完全歸納推理出的被害人特征,不是認定詐騙犯罪的必要條件。在上述新型機票詐騙案中,被害人雖然客觀上實施了四次轉賬行為,但在后三次轉賬行為中,其主觀上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會產生轉賬的后果,根據處分意識不要說,該案應當定性為詐騙罪。
筆者認為,雖然成立詐騙罪不要求行為人具有處分意思,但必須認識到財物外形上的占有轉移,也就是說,必須認識到自己在轉移財產;如果認為沒有意識到轉移財產的事實也能成立詐騙罪,無異于否定成立詐騙罪必須存在處分行為,可能導致欺騙醉漢“簽名紀念”,而實際上是簽署收條的行為,也能成立詐騙罪。上述案件中,被害人“受騙”不假,但被害人只是以為自己在進行退款操作,根本沒有認識到自己在進行轉賬操作。也就是說,被害人根本沒有認識到財產占有轉移的事實;這種情形下不僅沒有處分意思,更沒有處分行為,跟欺騙醉漢簽名沒有區別,故不應認為成立詐騙罪。該案實際上是利用沒有故意的被害人這種“工具”,盜劃被害人的存款,屬于違反被害人的意思、轉移財物占有的行為,故應成立盜竊罪。利用被害人本人的盜竊罪間接正犯與詐騙罪的區別在于,被害人有沒有認識到財物外形上的占有轉移的事實,根本沒有認識到自己正在實施轉移財物占有的行為的,應評價為盜竊罪的間接正犯。
是否認識到“財物”外形上占有轉移的事實的判斷并不難,困難的是“財產性利益”的占有轉移認識的判斷,如無錢食宿、無票乘車。行為人一開始就不具有付錢的意思而點菜吃飯或住宿的(所謂犯意先行型),成立詐騙罪(系舉動詐騙)沒有問題。行為人食宿之后才產生不付錢的意思(所謂食宿先行型),趁人不注意悄悄溜走的,成立利益盜竊也沒有問題。問題在于,謊稱送朋友馬上回來而趁機溜走的,這時店員是否存在處分行為,存在爭議。筆者認為,即便店員沒有明確的免除債務的意思,而只要認識到因為顧客的外出而一時無法結賬的事實,就應認為存在處分行為,就能肯定詐騙罪的成立;即使結賬時間未到(如規定十二點前退房結賬),只要認識到因為顧客外出而可能無法結賬即可。事實上,店員同意顧客外出時,通常不難想到顧客可能逃債,但礙于情面只能將疑慮存在心中而已。也正因為此,現在各賓館一般要求顧客事先交存足夠的押金,以避免逃債。在無票乘車的場合,一開始就打算逃票的,屬于利益盜竊;上車后售票員詢問是否有人沒買票時保持沉默的,成立不作為詐騙;行為人下車時才產生不付錢的意思,大搖大擺走出車站檢票口的,屬于利益盜竊(逃避債務);謊稱馬上補票而趁機溜走的,成立詐騙罪。
二三角詐騙與盜竊罪間接正犯的區分
刑法理論一般認為,被騙人具有處分被害人財產的權限或者處于可以處分被害人財產的地位時,成立三角詐騙,否則,成立利用第三人的盜竊罪間接正犯(不同于前述利用被害人本人的盜竊罪間接正犯)。
為此,受騙者是否具有處分被害人財產的權限或地位,成為區分(三角)詐騙罪與盜竊罪間接正犯的關鍵。
根據何種標準認定受騙者是否具有處分被害人財產的權限或地位,國外刑法理論存在各種學說。事實的接近說認為,只要作為受騙者的第三人與財產之間具有客觀的接近關系,對財產具有事實上的介入可能性,那么他就可以成為財產處分者。主觀說認為,應以受騙者是否為了被害人而處分財產為基準,如果受騙者是為了被害人而處分財產,則行為人的行為構成詐騙罪,反之則成立盜竊罪。陣營說認為,應以受騙者是與行為人的關系密切,還是與被害人的關系密切為區分標準,即以受騙者是屬于行為人陣營,還是被害人陣營為標準進行區分,屬于被害人陣營的成立詐騙罪,屬于行為人陣營的成立盜竊罪。授權說或權限說認為,受騙者在被害人概括性授權范圍內處分財產時,其行為屬于處分行為,行為人的行為成立詐騙罪,反之,受騙者處分財產的范圍超出了被害人的概括性授權時,行為人的行為成立盜竊罪。審核義務說認為,第三人僅僅是單純地主觀上確信自己對財物有支配權限是不夠的,除非他對代理權限的事實條件已經盡了審查和檢驗的義務,在此基礎上的主觀確信就可以支持一個有效的同意。
國內學者的立場也存在嚴重分歧。有學者同意授權說。
有學者主張綜合說,認為“所謂具有處分被害人財產的權限或地位,不僅包括法律上的權限或地位,也包括事實上的權限或地位。”至于受騙者事實上是否具有處分被害人財產的權限或地位,則“應根據社會的一般觀念,以其事實上是否得到了被害人的概括性授權為基準;至于是否得到了被害人的概括性授權,則應根據受騙者是否屬于被害人陣營、是否財產的占有者或輔助占有者、其轉移財產的行為外表上(排除被騙的因素)是否得到社會一般觀念的認可、受騙者是否經常為被害人轉移財產等因素進行判斷。”
車浩博士則提出了一種“客觀權限+審核義務”理論,認為:首先只有第三人在客觀上處于正當許可的范圍內活動,才算是代表了被害人(財產權利人)同意轉移占有的意思。也就是說,要么第三人得到了被害人關于財物處理的全權委托,要么法律或制度上給他的意思活動提供了支持,只有在這些情況下,第三人才算是代表了被害人轉移占有的意愿,才能夠排除盜竊罪中的“打破占有”,轉而成立三角詐騙。其次,在客觀權限理論之外,可以補充進審核義務理論。就保姆案所謂保姆案,是指主人外出保姆獨自在家時,行為人對保姆謊稱,受主人委托前來取要干洗的西服,保姆信以為真,將主人的貴重西服交給行為人拿去“干洗”。而言,如果行為人是雇主家的常客,保姆經常看到行為人到雇主家里,且保姆與行為人也比較熟悉,在這種情況下,對于上門謊稱受雇主委托取走衣物去清洗的行為人,保姆同意其將衣物取走或交付,應認定其已經履行了核實義務,因而行為確定為詐騙罪;相反,如果保姆面對的是一個素不相識、也不知道其與雇主是否有過交往的行為人,那么,保姆未經電話核實等手段進行審核或檢驗,而直接將衣物交給對方或任其取走,此時的處分或同意是無效的,在她做決定的過程中,根本沒有考慮被害人(雇主)的意愿,因此她就成了行為人違反被害人意愿的工具,對此只能構成盜竊罪而非詐騙罪。21]
筆者基本贊同綜合理論,認為車浩博士的“客觀權限+審核義務”理論過于復雜而不足取。只要根據法律、交易慣例或者社會一般觀念,受騙者處于被害人陣營,就應肯認其具有處分或轉移被害人財產的一般性權限,其行為屬于處分行為,欺騙者行為成立詐騙罪。保姆案中,保姆顯然處于被害人陣營,按照社會的一般觀念,負責打理家務的保姆有權處理西服干洗之類的事務,如果認為保姆必須小心翼翼、時時刻刻地向主人請示,一是這種做法未必是主人所樂意見到的,二是也不符合誠實信用的公共生活交往準則。因而,保姆案應屬于典型的三角詐騙。
德國超市小票案]甲經常出入超市,發現購物者付款后,總是丟棄發票或收據。某日,甲在超市撿起婦女乙的購物收據,要求乙把所購之物交還。乙怒斥,與甲爭吵。超市報警,警察無法分辨真相,要求乙交出所購物品給甲,因為甲有購物憑證。事后有人指出,甲曾在其他超市,使用同一手段,多次獲得不法財物。這是臺灣學者林東茂介紹的1991年德國電視臺播放的一個真實案例。林東茂教授認為,此案不構成詐騙罪,而是構成盜竊罪。否定詐騙罪的理由是:如果案例所述是一個私權的紛爭,臺灣的警察在極大多數的情況下沒有處分權,不能要求乙交出財物。私權的爭執,最終要交由司法解決。如果案例所述是一個疑似犯罪的案件,警察更不能私了,必須詳查真相后再作處置。無論如何,警察不能對于那樣的紛爭,當場要求乙退讓。沒有處分權的警察,不能處分他人的財產。所以,甲沒有利用警察的強制處分而獲得乙的財產,詐欺罪不成立。肯定成立盜竊罪間接正犯的理由是:甲利用不知情的警察,在處理爭端時,對于乙形成心理壓力而交出財物。乙在此種情景下交出財物,沒有同意的效力。乙的持有被破壞,甲就此建立了自己的持有。甲不成立詐欺罪,是因為乙的“內在的自由意思決定”被破壞,交出財物不是處分財產。22]
筆者認為,上述案件應當成立(三角)詐騙罪。林東茂教授認為本案屬于私權糾紛,警察沒有處分權限,這不過是通過理性判斷得出的結論。事實上,當時警察介入了私權糾紛,而且憑借警察身份做出了讓被害人乙將財物交付給欺騙者甲的處分決定。財產占有轉移的原因,是警察受到甲的欺騙,利用自己的身份強制處分了被害人乙的財產,被害人乙因為迫于警察的身份,而被迫同意將財物轉移給甲。所以,本案以詐騙罪而不是盜竊罪進行非難,可能更為合適。
德國車庫案]甲男乙女關系親密。乙有一車,停放于住處公共車庫。依照慣例,車主將第二把鑰匙交給車庫管理員,以便車主遺忘鑰匙時,也可以將車開出。甲曾獲得乙的同意,向管理員拿鑰匙開車。其后,管理員知道甲乙二人交深,認為乙同意甲取車,又多次將鑰匙交給甲。某日,甲未得乙同意,向管理員謊稱,乙同意出借汽車;甲取得鑰匙,開走乙車,據為己有。對于該案,德國多數學者認為構成詐騙罪。
筆者認為,車主乙將車鑰匙交給車庫管理員保管,是對車庫管理員的信任,車庫管理員顯然處于乙的陣營。甲男因與乙女交往較深,多次直接從管理員手中拿鑰匙開車,即便按照車浩博士的“客觀權限+審核義務”理論,也應認為車庫管理員既有客觀權限,也盡了審查義務(因甲男多次直接從其處拿鑰匙開走汽車),因而應認為作為受騙者的車庫管理員,具有處分被害人財產的權限或地位,其交出鑰匙的行為屬于處分行為,甲男的行為成立詐騙罪。
超市寄存柜案]2011年6月22日,黃某來到一家大型超市自助寄存柜旁,見鐘某正在存包,暗中記下其所存包的特征。當鐘某進入超市購物后,黃某利用一張作廢的密碼條,找到超市自助寄存柜值班保安張某,謊稱其自助寄存柜打不開,要求張某將鐘某存包的柜門打開。黃某準確說出柜內存放物品的種類及特征,張某打開自助寄存柜進行物品核對,發現與黃某所述一致,于是離開。黃某遂將鐘某存放在該柜內的一個男式單肩挎包及包內物品、人民幣6700元拿走。經鑒定,黃某取走物品共計價值人民幣17萬余元。關于本案的定性,存在盜竊罪與詐騙罪的意見分歧。23]
筆者認為,超市自助寄存柜系超市無償租借給顧客暫時使用的存物場所,即便超市保安有寄存柜鑰匙,自助寄存柜的使用人也擁有絕對的支配權限,未經使用人同意,包括超市管理人在內的任何人都無權打開自助存物柜。換言之,超市保安不處于任何一方的陣營,不具有處分自助寄存柜中財物的權限,其受欺騙打開自助寄存柜的行為,不是詐騙罪中的處分行為,其只是被利用作為“打破持有”的工具,因而欺騙者屬于盜竊罪的間接正犯,不成立詐騙罪。
三盜竊罪與詐騙罪能否競合
盜竊罪與詐騙罪侵害的法益都是他人的財產權,都屬于取得罪和奪取罪(占有轉移罪),不同之處僅在于財產占有發生轉移的原因。二者之間能否存在競合,若存在競合,是法條競合還是想象競合,抑或既是法條競合又是想象競合?這個問題值得研究。德國刑法理論認為,詐騙罪的成立不要求被害人具有處分意思,承認盜竊罪與詐騙罪的競合。24]臺灣學者林東茂對競合論提出質疑:“德國不少刑法學者認為,車庫案例的甲,同時成立盜竊罪的間接正犯與詐欺罪。不過,這個看法會陷入困境。因為,不在構成要件上清楚地區分竊盜或詐欺,必然要面對競合論處理上的難局。如果認為同時是竊盜與詐欺,那么,究竟是法條競合,還是想象競合?假如認為是法條競合,要用什么標準決定哪一個法條必須優先適用?倘若認為是想象競合,又該如何圓說:被破壞的法益只有一個?”25]大陸學者張明楷也反對競合論,指出“本書不承認詐騙罪與盜竊罪的競合,相反認為二者處于相互排斥的關系,所以,需要通過處分意識區分詐騙罪與盜竊罪。”26]日本學者山口厚也認為,盜竊罪與詐騙罪的區別取決于“交付的有無”;如果承認兩者的競合,就不能決定究竟應適用何者;既然兩罪的法定刑相同,就不能說盜竊罪重于詐騙罪,應優先適用盜竊罪,也不能在承認兩罪競合的基礎上,認為無論適用哪一罪均可。27]
筆者認為,反對競合論的理由不能成立。刑法理論一般認為,盜賣他人財物的,成立盜竊罪的間接正犯。例如,甲閑逛時發現本市高速公路旁有一閑置的舊壓路機,即產生變賣的念頭。次日,甲假冒公司人員來到附近一廢品收購站,找到經營者乙,謊稱該壓路機已報廢準備變賣,并與乙一起到現場查看,二人當場決定以6000元的價格成交。次日,乙便組織人力找來切割工和吊車趕到現場,正在拆卸時被群眾發現報警,甲被公安機關當場抓獲。經價格認證中心鑒定,該壓路機價值5萬元。對于該案,應當認為經營者乙只是甲利用的工具,因而甲成立盜竊罪的間接正犯。28]其實,本案的受害人不只是壓路機的所有人,還包括經營者乙,因為壓路機作為盜竊所得的贓物,最終會被追繳后返還給壓路機的所有權人。也就是說,就壓路機所有權人這一被害人而言,甲的行為成立盜竊罪(間接正犯),但就經營者乙這一被害人而言,甲的行為成立詐騙罪。因而,本案中的行為應成立盜竊罪(間接正犯)與詐騙罪的想象競合犯。
如果想象競合的各罪名法定刑相同,且所侵害的法益只有一個,而無法選擇適用哪一個法條,不能成為否定想象競合的理由。刑法理論一般認為,形成想象競合不是法條本身的原因,而是因為偶然的犯罪事實引起的競合。例如,從條文上,很難認為盜竊罪與殺人罪之間會有什么瓜葛,也很難看出強奸罪與殺人罪之間會有什么聯系,但是,在特殊案件中,如明知是心臟病人的救心丸而盜竊,致使心臟病人因心臟病猝發而死亡,就不可否認成立盜竊罪與故意殺人罪的想象競合犯。同樣,明知強奸幼女可能導致死亡,仍然不管不顧地實施暴力強奸而導致幼女當場死亡,無疑成立強奸罪與故意殺人罪的想象競合犯。所以說,即便從條文上看,兩罪可能毫無關系,但在具體個案中,完全可能形成想象競合關系。
刑法理論一般認為,想象競合與法條競合的區別在于,一個行為是否侵害兩個以上的法益,僅侵害一個法益的,不能成立想象競合。29]其實這是認識上的誤區。誠然,盜竊罪、詐騙罪、敲詐勒索罪所侵害的法益均為財產法益,但如果深究,這三個罪名侵害的法益還是有差別的。例如,詐騙罪除侵害財產法益外,還在某種意義上侵害了誠實信用的公平交易準則,侵害了被害人的意思決定自由,而敲詐勒索罪,在侵害財產法益外,還侵害了被害人的意思決定和行動自由。所以,只能說盜竊罪、詐騙罪與敲詐勒索罪所侵害的類法益相同,在具體法益上還是存在些許差異的。
此外,一般認為,法條競合與想象競合的不同在于,前者是法條本身即構成要件上的因素形成的競合,即便沒有具有犯罪事實的發生,也不可否認競合的存在。30]這種觀點基本正確。問題在于,如何解釋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認為不可能存在法條競合關系的,無非是先有結論后再論證罷了。例如,就詐騙罪與盜竊罪而言,若堅持認為,處分行為和處分意思是二罪的分水嶺,的確可以得出二罪是排斥關系而不可能競合的結論。但問題是,這種前提本身就可能存在疑問。雖然可以將盜竊罪界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違反被害人的意思,將他人占有下的財物非法轉移給自己或者第三人占有。將詐騙罪界定為,實施欺騙手段,使他人基于有瑕疵的意思處分交付財物。但不可否認,這些定義中的要素,基本上都是為了將該罪與相關犯罪區分開,而屬于分界要素,并非本質性要素。我們可以認為,財產罪的本質性要素,是通過侵害占有而侵害他人的財產所有,從這個意義上講,故意毀壞財物罪是所有財產罪的兜底性犯罪。相對于毀棄罪,取得罪最本質性的要素,就是利用意思,因而可以認為,侵占罪是取得罪的兜底性犯罪。相對于非占有轉移罪(侵占罪)而言,奪取罪的本質性要素是違反被害人的真實意思侵害他人對財產的占有,因而奪取罪的兜底性犯罪是盜竊罪。雖然相對于盜取罪(盜竊、搶劫、搶奪罪)而言,詐騙罪與敲詐勒索罪屬于基于被害人有瑕疵的意思,轉移財物占有的犯罪,屬于交付罪,但不可否認,詐騙罪中轉移財物的占有仍然是違反被害人的真實意思的,因而,詐騙罪也符合盜竊罪的本質性要素——違反被害人的意思、未經本人真實有效的同意轉移占有。由此,筆者認為,詐騙罪與盜竊罪在法條上存在競合關系。
承認盜竊罪與詐騙罪之間存在想象競合關系,或是存在法條競合關系,都面臨適用哪一個法條的問題。既然盜竊罪是奪取罪的兜底性犯罪,就可以認為盜竊罪相對于詐騙罪而言,屬于基本類型,31]在同時符合兩罪的構成要件時,如盜賣他人財物的,應當以盜竊罪定罪處罰。而且在我國,盜竊罪的處罰事實上重于詐騙罪,按照從一重處罰的原則,也應以盜竊罪定罪處罰。
需要說明的是,主張盜竊罪與詐騙罪之間,不僅存在想象競合,而且存在法條競合,并非意味著任何時候都同時成立二罪,而導致詐騙罪實際上被廢止。而是說,當不能嚴格區分二罪,或者同時符合二罪的構成要件,以及不承認二罪之間存在競合將難以妥當處理時,應大膽認為二罪之間存在競合關系,直接以盜竊罪定罪處罰。當能夠區分二罪,行為明顯符合詐騙罪構成要件,而與盜竊罪構成要件相距甚遠時,還是應當適用詐騙罪定罪處罰。也就是說,承認二罪之間的競合,進而適用盜竊罪定罪處罰,僅限于例外情形。
承認盜竊罪與詐騙罪之間存在競合關系,不僅有助于想象競合時案件的處理,而且有助于處理認識錯誤和共犯問題。例如,甲教唆乙詐騙丙的財物,但丙因精神病發作而喪失意思決定能力,乙的行為實際上符合盜竊罪構成要件時,甲與乙仍應在詐騙罪的范圍內成立共犯,甲成立詐騙罪的教唆犯,乙單獨承擔盜竊罪的責任。又如,甲與乙共同對丙實施欺騙,騙取丙的財物,甲認識到丙是高度的精神病患者,乙誤以為丙是精神正常的人,二者在詐騙罪的范圍內成立共犯,但甲的行為完全符合盜竊罪(利用被害人的間接正犯)的構成要件,對甲應以盜竊罪定罪處罰。如果不承認盜竊罪與詐騙罪之間存在競合關系,上述案件就難以處理。
參考文獻]
[1] [日]前田雅英刑法各論講義(第5版)[M]日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1
[2][日]伊藤真刑法各論(第4版)[M]日本東京:弘文堂,2012
[3][日]松宮孝明刑法各論講義(第3版)[M]日本東京:成文堂,2012
[4][日]西田典之刑法各論(第六版)[M]日本東京:弘文堂,2012
[5][日]山口厚刑法各論(第2版)[M]日本東京:有斐閣,2010
[6]張明楷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7][日]山口厚刑法各論(第2版)[M]日本東京:有斐閣,2010
[8]張明楷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9][日]西田典之刑法各論(第六版)[M]日本東京:弘文堂,2012
[10][日]曾根威彥刑法各論(第5版)[M]日本東京:弘文堂,2012
[11]秦新承認定詐騙罪無需\"處分意識\"--以利用新型支付方式實施的詐騙案為例[J]法學,2012,(3):155
[12]張明楷刑法學(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3]張明楷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14][日]大谷實刑法講義各論(新版第3版)[M]日本東京:成文堂,2009
[15]李世陽論詐騙罪中的財產處分行為[J]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志,2011,(3):56
[16]劉明祥論詐騙罪中的交付財產行為[J]法學評論,2001,(2):70
[17]秦新承認定詐騙罪無需“處分意識”以利用新型支付方式實施的詐騙案為例[J]法學,2012,(3):155
[18]秦新承認定詐騙罪無需“處分意識”以利用新型支付方式實施的詐騙案為例[J]法學,2012,(3):160
[19][日]松宮孝明刑法各論講義(第3版)[M]日本東京:成文堂,2012周光權刑法各論(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20][日]淺田和茂、井田良編刑法[M]日本東京:日本評論社,2012
[21]林東茂刑法綜覽(修訂五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22]車浩盜竊罪中的被害人同意[J]法學研究,2012,(2):117
[23]張明楷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24]鄭澤善詐騙罪中的處分行為[J]時代法學,2011,(4):55
[25]李翔論詐騙犯罪中的財產處分行為[J]法學,2008,(10):137
[26]張明楷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27]車浩盜竊罪中的被害人同意[J]法學研究,2012,(2):119-120
[28]林東茂一個知識論上的刑法學思考(增訂三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29]金林,羅永鑫欺騙超市保安開啟寄存柜取走他人財物如何定性[N]檢察日報,2011-11-15,3
[30]張明楷也論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機上取款的行為性質--與劉明祥教授商榷[J]清華法學,2008,(1):95
[31]林東茂一個知識論上的刑法學思考(增訂三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32]張明楷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33]日]山口厚問題探究 刑法各論[M]日本東京:有斐閣,1999第148頁。
[34]萬劍以欺騙他人實施犯罪的行為如何定性[N]西部法制報,2011-10-22,4
[35]日]山口厚刑法總論(第2版)[M]日本東京:有斐閣,2007
[36]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37]日]林干人詐欺罪の新動向[J]法曹時報,第57卷3號,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