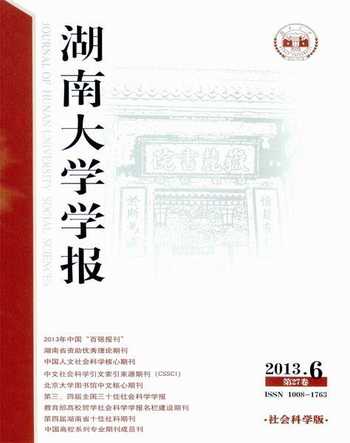論“八二憲法”30年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的變遷



[作者簡介] 林孝文(1976—),男,湖南邵陽人,西南政法大學(xué)行政法學(xué)院副教授,法學(xué)博士.研究方向:憲法學(xué).
[摘要] 近30年我國憲法中所規(guī)定的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重大變遷,主要表現(xiàn)為產(chǎn)權(quán)及其實現(xiàn)方式的多元化、非公有制產(chǎn)權(quán)所占的份量越來越大。我國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變遷的基本方式是:先有產(chǎn)權(quán)及其結(jié)構(gòu)變遷的事實(違憲),然后總結(jié)產(chǎn)權(quán)變遷的經(jīng)驗并制定憲法修正案(修憲),最后在憲法中加以確認(rèn)并加以制度上推廣(合憲)。這樣一條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變遷路線是我國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與憲法變遷的必然結(jié)果,符合當(dāng)時社會變革的需求,促成了我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以及憲法制度的完善,但同時也給我國憲法帶來了極大的挑戰(zhàn)。對我國現(xiàn)行憲法產(chǎn)權(quán)制度進(jìn)行適當(dāng)調(diào)整,協(xié)調(diào)憲法內(nèi)部關(guān)于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各項規(guī)定,盡量減少關(guān)于產(chǎn)權(quán)制度方面的憲法規(guī)定,無疑是回應(yīng)這一挑戰(zhàn)的重要思路。
[關(guān)鍵詞] 八二憲法;30年;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
[中圖分類號] D921[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 A[文章編號] 1008—1763(2013)06—0147—06
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是,近30年來“八二憲法”所確定的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哪些重大變遷,其變遷的原因何在。通過實證研究這些變遷并分析其變遷的原因之后,筆者試圖進(jìn)一步探討這些變遷給“八二憲法”帶來了哪些挑戰(zhàn)以及憲法應(yīng)如何回應(yīng)。這些問題的回答,既是經(jīng)濟(jì)學(xué)理論對我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運(yùn)用,同時也關(guān)涉到“八二憲法”實施的重大理論與現(xiàn)實問題。我們知道,產(chǎn)權(quán)是聯(lián)系經(jīng)濟(jì)學(xué)與法學(xué)之間的紐帶,但是產(chǎn)權(quán)在兩個學(xué)科之間有著重大差別。經(jīng)濟(jì)學(xué)中的產(chǎn)權(quán)注重經(jīng)驗事實分析,法學(xué)則注重價值衡量。對于法學(xué)而言,經(jīng)濟(jì)學(xué)中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及其發(fā)展需要接受憲法與法律制度所確立的基本規(guī)范的確認(rèn)與評價——帶來經(jīng)濟(jì)效益的產(chǎn)權(quán)不一定符合法律的規(guī)定。一直以來,我國憲法對產(chǎn)權(quán)給予了特別的關(guān)注,這為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提供了產(chǎn)權(quán)基本制度框架或制約。從近30年產(chǎn)權(quán)調(diào)整與憲法實踐的過程來看,一方面,“八二憲法”的內(nèi)容變化反映出了我國產(chǎn)權(quán)變遷的整個過程與事實,另一方面它還為產(chǎn)權(quán)的整體變遷提供了基本上的確證與論證。近30年我國所進(jìn)行的政治、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與實踐,都是圍繞著調(diào)整憲法所確立的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而得以展開。
一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變遷的過程與方式
眾所周知,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農(nóng)民冒著生命危險簽署了“分田單干”協(xié)議,這成為啟動我國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的起點,標(biāo)志著我國近30年的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變遷的正式開始。當(dāng)時這些簽了生死狀的農(nóng)民,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們不但沒有被“坐牢殺頭”,反而成了中國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的英雄。我們且先分析農(nóng)村土地產(chǎn)權(quán)的變遷過程,然后再對憲法中所確定的其他產(chǎn)權(quán)變遷做一綜合敘述與分析。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與中央工作負(fù)責(zé)人談話中,充分肯定了小崗村的這一“做法”——使用“做法”一詞,是因為當(dāng)時對此還沒有明確的法律或經(jīng)濟(jì)學(xué)術(shù)語來表達(dá)。1980年底,這一“做法”在解決農(nóng)民溫飽問題上起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不久就引發(fā)了國家正式制度的出臺。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頒布了《全國農(nóng)村會議紀(jì)要》,第一次正式公開認(rèn)可“包產(chǎn)到戶”是“社會主義”的,承認(rèn)了這一“做法”的“合法”性。從1982年到1986年,中央連續(xù)頒布了“五個1號文件”,把這一“做法”推向了全國。在1993年“八二憲法”的修正案中,正式把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規(guī)定到憲法之中。隨著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以及全國經(jīng)濟(jì)形勢的變化,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與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發(fā)展之間開始出現(xiàn)了某些抵觸,經(jīng)營集約化水平低下、大片土地拋荒等現(xiàn)象在某些農(nóng)村變得比較突出。于是,在1999年憲法修正案中對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進(jìn)行了新的修改,建立起了“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為基礎(chǔ)、統(tǒng)分結(jié)合的雙層經(jīng)營體制”。
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的實質(zhì)上是在農(nóng)村推行一種新的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即在原有的土地產(chǎn)權(quán)上,把土地的所有權(quán)與使用權(quán)(經(jīng)營權(quán))進(jìn)行了分離:土地所有權(quán)仍然為集體所有,但是經(jīng)營權(quán)歸于以“戶”為單位的農(nóng)民所有,于是達(dá)成了集體(村和組)與農(nóng)民(戶)之間的產(chǎn)權(quán)契約。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這種產(chǎn)權(quán)制度都大大地節(jié)約了交易成本,是當(dāng)時提高農(nóng)村土地經(jīng)濟(jì)效益的最佳產(chǎn)權(quán)形式。因此,不難理解,它的變革很快獲得了全國上下一致的認(rèn)可,成為我國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的突破口。通過比較“七八憲法”、“八二憲法”及其相繼而來的幾部憲法修正案,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土地產(chǎn)權(quán)變遷線路圖(圖1):
從以上圖表可以明顯看出以下幾點:
第一,農(nóng)民獲得的土地產(chǎn)權(quán)范圍越來越大。在“七八憲法”中,實行土地產(chǎn)權(quán)完全歸屬于集體,農(nóng)民對與土地產(chǎn)權(quán)幾乎一無所有。在“八二憲法”(1982年)中,憲法沒有明確規(guī)定農(nóng)民土地產(chǎn)權(quán)的范圍,但是與1978年比較可以看出,此時已經(jīng)刪除了限制農(nóng)民土地經(jīng)營權(quán)的范圍,在實際中盡量地擴(kuò)大了農(nóng)民承包經(jīng)營土地——在憲法文本中沒有體現(xiàn)。1993年憲法修正案中明確規(guī)定了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第一次明確規(guī)定了土地所有權(quán)與經(jīng)營權(quán)的分離,農(nóng)民在憲法上幾乎獲得了全部土地經(jīng)營權(quán)。1999年憲法修正案則不僅承認(rèn)了農(nóng)民對土地的經(jīng)營權(quán),而且增加了承包權(quán)以及土地流轉(zhuǎn)權(quán)。到此時,農(nóng)民對與土地產(chǎn)權(quán)在憲法和事實上都獲得了除所有權(quán)之外的所有產(chǎn)權(quán)。
第二,農(nóng)村土地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重大變化。1978年憲法是所有權(quán)主宰下的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經(jīng)營權(quán)依附于所有權(quán),農(nóng)民經(jīng)營權(quán)幾乎沒有生存空間。1982年憲法中土地所有權(quán)主宰的地位開始下滑,出現(xiàn)了盡可能地增加農(nóng)民經(jīng)營權(quán)范圍的情形。1993年憲法修正案中則農(nóng)民不僅獲得了完全的經(jīng)營權(quán),而且在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中增加了承包權(quán),出現(xiàn)了所謂的“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1999年憲法修正案中則對以前的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產(chǎn)生了重大突破,出現(xiàn)了“土地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的流轉(zhuǎn)”。也就是說,農(nóng)民不僅可以自己承包、經(jīng)營土地,而且可以把這種權(quán)利依法轉(zhuǎn)讓給他人。
通過以上產(chǎn)權(quán)變遷線路圖(圖1),結(jié)合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中土地產(chǎn)權(quán)變化的實際過程來考察,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我國產(chǎn)權(quán)在變遷的方式有如下結(jié)論:在憲法確認(rèn)之前,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在當(dāng)時憲法中沒有明確規(guī)定、甚至被認(rèn)為是“違憲”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實踐。在每一次有了新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及其實踐的事實之后,在憲法修正案中對這些產(chǎn)權(quán)制度予以確認(rèn)。換句話說,先有“違憲”的制度行為事實,然后再有憲法與法律對這一制度行為事實加以“合憲化”的確認(rèn)。很明顯,在“八二憲法”出臺前,尤其是1993年憲法修正案公布實施之前,就已經(jīng)有了大量的“分田單干”的現(xiàn)象;在1999年憲法修正案還未公布實施之前,在農(nóng)村就已經(jīng)有了土地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轉(zhuǎn)讓的行為事實。這一變革的過程,完全符合鄧小平同志所言的“摸穩(wěn)石頭過河”的改革模式。但不時出現(xiàn)對當(dāng)時憲法規(guī)定有所突破或者說“違憲”,卻是不爭的事實。
以上只是對我國農(nóng)村土地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變遷過程的分析,除此之外,“八二憲法”還對自然資源、城市土地、企業(yè)等幾種重要的產(chǎn)權(quán)進(jìn)行了規(guī)定——它們共同構(gòu)成了“八二憲法”的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通過考察它們在近30年的變遷過程,就可以比較全面地把握“八二憲法”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變遷的大致過程。現(xiàn)在對“八二憲法”及其修正案在近30年內(nèi)的產(chǎn)權(quán)變遷過程作一整體分析,可以總結(jié)如下產(chǎn)權(quán)變遷圖(圖2):
通過對比性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上述各種產(chǎn)權(quán)變遷的過程,與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中土地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變遷極為相似。通過比較與總結(jié)上述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的變遷過程,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條結(jié)論:
一是產(chǎn)權(quán)及其實現(xiàn)方式的多元化,從單一的公有制變成了公有與私有、公有中有私有、私有中有公有等多種形式,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變得越來越復(fù)雜。例如,國家所有并使用城市土地權(quán)到所有權(quán)與使用權(quán)分離;由國家所有并經(jīng)營的“國營企業(yè)”轉(zhuǎn)變到了國家所有但不一定經(jīng)營的“國有企業(yè)”,實現(xiàn)了國有企業(yè)所有權(quán)與經(jīng)營權(quán)的分離。這些產(chǎn)權(quán)的分離,在不同程度上分化了產(chǎn)權(quán)實現(xiàn)形式,增加了產(chǎn)權(quán)的種類與范圍。
二是非公有制產(chǎn)權(quán)所占的份量越來越大,所占的地位越來越高。受傳統(tǒng)產(chǎn)權(quán)所有制理論的影響,公有制與非公有制一直是產(chǎn)權(quán)中比較敏感的問題。但是從圖2中可以明顯看出,非公有制中的產(chǎn)權(quán)范圍越來越大。有人甚至把我國30年來這種產(chǎn)權(quán)變遷過程稱為是“私有化”過程。避開姓“資”姓“社”的問題不談,我國產(chǎn)權(quán)變革確實導(dǎo)向了私有產(chǎn)權(quán)的大量增加。
三是這些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的變遷絕大多數(shù)首先都是在有了產(chǎn)權(quán)制度變遷的事實之后,再通過修正憲法的方式在憲法中予以認(rèn)可。城市土地產(chǎn)權(quán)是如此,個體戶、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出現(xiàn)與發(fā)展也是如此。現(xiàn)以“八二憲法”第11條規(guī)定的非公有制的企業(yè)產(chǎn)權(quán)為例,我們可以進(jìn)一步印證上述結(jié)論。通過比較“八二憲法”第11條關(guān)于非公有制企業(yè)產(chǎn)權(quán)的變遷過程,得出以下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變遷圖(圖3)。
從上表中可以發(fā)現(xiàn):非公制企業(yè)產(chǎn)權(quán)形式不斷增加,最后以“非公有制經(jīng)濟(jì)”囊括了所有的非公有制經(jīng)濟(jì)形式,為新型非公有制經(jīng)濟(jì)的出現(xiàn)與發(fā)展提供了足夠的空間;非公有制企業(yè)產(chǎn)權(quán)的主體地位不斷增強(qiáng),其變化主要表現(xiàn)為:指導(dǎo) 引導(dǎo);保護(hù) 鼓勵與支持。
二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變遷的原因
以上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的變遷以及“八二憲法”對此作出相應(yīng)的調(diào)整和確認(rèn),繼而在制度上不斷加以推廣,這是我國近30年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變遷的事實或現(xiàn)象。現(xiàn)在需要追問的是,發(fā)生上述現(xiàn)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按照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基本原理,制度發(fā)生變遷的根本原因是新的制度可以給人們帶來“潛在利益”。 產(chǎn)權(quán)制度變遷是新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安排對舊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安排進(jìn)行替代的過程,表現(xiàn)為一種效益更高的制度對另一種制度的取代。人們在產(chǎn)權(quán)制度變遷中能夠獲得更高的利益,是推動產(chǎn)權(quán)制度變遷的根本原因。只有當(dāng)人們認(rèn)為在新制度中有利可圖時,制度創(chuàng)新與變遷才有可能。但是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這一原理在很大程度上只適合于分析長時期的制度變遷。對于短期的制度變遷過程,遠(yuǎn)遠(yuǎn)并非如此簡單。原因就是,如果制度能夠按照上述理論變遷,那么人類早就應(yīng)該選擇并取得了最優(yōu)的制度了。但事實上,人們對何為最優(yōu)制度往往缺乏足夠的認(rèn)識與判斷能力。
毫無疑問,人們總是選擇最有利于自己的制度,但是問題的關(guān)鍵是人們?nèi)绾沃朗裁粗贫炔攀亲顑?yōu)的制度。由于理性、意識形態(tài)等條件的限制,人們往往自以為是地選擇了“有利可圖”的制度——實際上這并不是最優(yōu)制度。以產(chǎn)權(quán)制度變遷具有標(biāo)志性意義的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為例,它的出現(xiàn)并不是1978年以后才出現(xiàn)的新“做法”。上世紀(jì)50到60年代,中國許多省份的農(nóng)村就已經(jīng)開始實行了責(zé)任田式的“包產(chǎn)到戶”的實踐,當(dāng)時安徽全省竟然達(dá)到了80%,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經(jīng)濟(jì)效果。
杜潤生:《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改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頁。但這種制度卻遭到了毛澤東等中共領(lǐng)導(dǎo)人的堅決反對。當(dāng)時的《人民日報》發(fā)出了《揭穿“包產(chǎn)到戶”的真面目》為題的評論員文章,指責(zé)“包產(chǎn)到戶是極端落后、倒退、反動的做法。”
《人民日報》,1959年11月2日。于是這一極具生命力的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被扼殺在搖籃之中。
利益確實是制度變遷的重要誘因,但制度的變遷絕不僅僅是經(jīng)濟(jì)利益決定論所說的那么簡單。人的認(rèn)知能力、意識形態(tài)等才是判斷利益的先決條件。沒有足夠的認(rèn)知能力以及與此相適應(yīng)的意識形態(tài),人們往往無法判斷何為最佳利益、何為最佳制度。由此可知,認(rèn)知水平的提高與意識形態(tài)的轉(zhuǎn)型,才是制度變遷的前提。
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社會經(jīng)濟(jì)制度的主流認(rèn)識是,社會主義本質(zhì)是公有制,勞動者共同擁有生產(chǎn)資料,實現(xiàn)平均分配等。在產(chǎn)權(quán)制度取舍的標(biāo)準(zhǔn)上,認(rèn)為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實現(xiàn),對人們越有利益。這種片面追求純之又純的公有制,勢必絕對排斥其它所有制形式,把非公有制看成是公有制的對立物必須加以批判與遏制。受這種認(rèn)識的影響,全國上下大力割除資本主義的“尾巴”、推行“人民公社”、鼓吹“一大二公”的計劃經(jīng)濟(jì),實行純粹的公有制,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了。到1978年,國民生產(chǎn)總值中公有制經(jīng)濟(jì)占了98%;在工業(yè)領(lǐng)域,國有企業(yè)占全部工業(yè)總產(chǎn)值的77.6%,集體經(jīng)濟(jì)占22.4%,個體、私營經(jīng)濟(jì)幾乎為0。
谷書堂主編:《社會主義經(jīng)濟(jì)學(xué)通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頁。在當(dāng)時認(rèn)知水平與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下,以上數(shù)據(jù)也就不足為奇。
由于這一種極端化的“公有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交易成本及其高昂,造成了我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十分緩慢,甚至出現(xiàn)倒退的現(xiàn)象,人民生活極度困苦。變革這種產(chǎn)權(quán)制度,成為舉國上下迫切的需要。事實上,受當(dāng)時認(rèn)知水平以及意識形態(tài)的制約,人們?nèi)匀徊恢绾蜗率帧?978年,無疑是轉(zhuǎn)變上述困境的關(guān)鍵一年。該年經(jīng)過了真理標(biāo)準(zhǔn)的討論,突破了“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為人們打開了視野,為制度變革提供了基本認(rèn)知路徑。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中共十二大的召開,“三個有利于”原則沖破了計劃經(jīng)濟(jì)制度框架,平息了姓“資”姓“社”的爭論。1997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大沖破了“所有制崇拜”,消除了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基本完成了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意識形態(tài)轉(zhuǎn)型。這就為我國產(chǎn)權(quán)制度結(jié)構(gòu)的變遷提供了前提。
在認(rèn)識能力提高以及相應(yīng)的意識形態(tài)轉(zhuǎn)變之后,接下來憲法所對公有制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的重新調(diào)整,基本上都可以利用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基本原理加以解釋。從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理論來看,由于公有制產(chǎn)權(quán)具有很大的制度外部性(externality),
制度外部性的實質(zhì)是社會責(zé)任與權(quán)利的不對稱。當(dāng)外部性存在時,“搭便車”的現(xiàn)象大量存在,而那些為此做出了“犧牲”的人(即承擔(dān)了他人應(yīng)該承擔(dān)的成本)卻沒有相應(yīng)的回報。前一種情況使經(jīng)濟(jì)發(fā)展缺乏動力,后一種情況使經(jīng)濟(jì)發(fā)展增加阻力。導(dǎo)致在改革開放之前 “吃大鍋飯”、“多干少干一個樣”等搭便車的現(xiàn)行盛行。公有制產(chǎn)權(quán)的外部性,嚴(yán)重挫傷了勞動者的積極性,無論“公”還是“私”都很難從中獲得更大的利益。絕對化的公有制產(chǎn)權(quán)無法實現(xiàn)整體利益的提高,因為要實現(xiàn)這種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理想狀態(tài),所需要花費(fèi)的成本極其高昂。例如,在農(nóng)村改革開放前所實行的集體化勞作,由于搭便車的情形隨時存在,如果要提高勞作效率,就需要對幾乎所有的勞作者進(jìn)行不間斷的監(jiān)督——這一點由于監(jiān)督成本太高根本上無法做到。如果不對這些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進(jìn)行調(diào)整,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就會因這些高昂的交易成本而無法實現(xiàn)。從我國產(chǎn)權(quán)制度變遷30年歷程來看,改變極端化的公有制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不斷消除公有制產(chǎn)權(quán)的外部性,降低產(chǎn)權(quán)的交易成本,是我國產(chǎn)權(quán)制度以及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動力源泉。隨著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變遷及其所帶來實際的利益,進(jìn)一步誘發(fā)了人們對新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渴望。于是,又開始進(jìn)入到了新一輪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變遷過程。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變遷的循環(huán)體系。
三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變遷對憲法提出的
挑戰(zhàn)及其回應(yīng)
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的變遷無疑可以得到經(jīng)濟(jì)學(xué)較為完滿的解釋。但僅僅有這樣的解釋,還是不夠的。經(jīng)濟(jì)學(xué)主要在一定的假設(shè)之下對經(jīng)濟(jì)制度事實進(jìn)行經(jīng)驗性的研究,而法學(xué)不僅僅要關(guān)注制度經(jīng)驗,還要對制度的合法性與正當(dāng)性進(jìn)行合理化解釋,并為未來制度變遷提供預(yù)測與規(guī)范指南。也就是說,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的變遷還必須經(jīng)受憲法與法律的約束與檢驗。
在1978年小崗村農(nóng)民冒著生命危險簽署的“分田單干”協(xié)議的時候,小崗村那些按手印的農(nóng)民都深知他們的行為是要“坐牢殺頭”的。這就足夠說明,他們在行為時已經(jīng)完全意識到了,他們這種行為與當(dāng)時的憲法及其意識形態(tài)的嚴(yán)重不符。依據(jù)當(dāng)時的憲法(“七八憲法”),這種單干協(xié)議沒有任何憲法和法律依據(jù),并且在60年代還受到了嚴(yán)厲的批判。但是他們在現(xiàn)實的經(jīng)濟(jì)誘惑面前,寧愿冒“坐牢殺頭”的風(fēng)險,還是決定實行這種“違憲”行為。但這一次讓他們意想不到的是,他們的“違憲”行為竟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且還作為典型在全國加以推廣。小崗村農(nóng)民的這種“違憲”行為所得到的結(jié)果完全是出人意料。當(dāng)我們在稱贊他們?yōu)榻?jīng)濟(jì)體制改革所做的巨大貢獻(xiàn)的時候,卻對我國當(dāng)時的憲法和法律形成了一種莫大的諷刺,因為我們縱容或容忍了這樣一種“違憲”。這充分說明了我國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變遷所具有的極大偶然性與風(fēng)險性。
即使到1982年憲法修改制定時,也并沒有把所謂的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完全納入到憲法之中。當(dāng)時的憲法規(guī)定是:“參加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的勞動者,有權(quán)在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內(nèi)經(jīng)營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業(yè)和飼養(yǎng)自留畜。”當(dāng)時也并沒有對他們這種經(jīng)營行為制定出“法律”——《農(nóng)村土地承包法》到2002年才正式頒布。直到1993年憲法修正案的出臺,才正式確認(rèn)了這一“做法”。同樣地,在1999年憲法修正案還未出臺之前,在農(nóng)村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土地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轉(zhuǎn)讓的行為事實;到1999年憲法修正案出臺時才對這些制度予以了確認(rèn)。對于城市土地產(chǎn)權(quán)、企業(yè)產(chǎn)權(quán)、私有財產(chǎn)權(quán)等都有著如出一轍的變遷方式。
對于城市土地產(chǎn)權(quán)在1988年前一般認(rèn)為,憲法禁止土地轉(zhuǎn)讓,但是在深圳等地方在1988年憲法修正案出來之前已經(jīng)進(jìn)行了土地的有償轉(zhuǎn)讓。1982年憲法修訂時只規(guī)定了個體經(jīng)濟(jì),但是在1988年憲法修正案出臺之前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私營經(jīng)濟(jì)的形式。2004年憲法修正案把私有財產(chǎn)權(quán)范圍從生活資料擴(kuò)大到生產(chǎn)資料,但 2004年之前人們已經(jīng)擁有了大量的生產(chǎn)資料的財產(chǎn)權(quán)。
從上述事實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jié)論:我國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的變遷,并不是當(dāng)時既定的憲法制度實施或演化的產(chǎn)物。從當(dāng)時憲法制度中無法推導(dǎo)出這些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變遷要求。恰恰相反,憲法對這些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的變遷進(jìn)行了約束。也就說,這些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的變遷是對當(dāng)時憲法產(chǎn)權(quán)制度突破的產(chǎn)物。它們的正當(dāng)性來自政治變革的時代要求以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的政治原則,并且以此策略性地避開了當(dāng)時憲法制度以及意識形態(tài)的干擾。可以說,我國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變遷是在實踐中不斷試錯、摸索,并不斷加以總結(jié)的結(jié)果。當(dāng)然,對于這些成功的經(jīng)驗,憲法并不是無動于衷,我們把它們寫進(jìn)了憲法,并在憲法上予以確認(rèn),從而取得了憲法的正當(dāng)性。這是我國非常獨(dú)特的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變遷路徑。它遵循了先有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事實,然后再進(jìn)行修憲與立法加以確認(rèn),這樣一條基本產(chǎn)權(quán)變遷路線。
這樣的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變遷路線,在當(dāng)時的時代背景下是完全有必要的,也是富有成效的。受當(dāng)時制度與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既定的憲法制度無法解決現(xiàn)實的經(jīng)濟(jì)問題,而對于未來的社會主義藍(lán)圖也缺乏具體經(jīng)驗與理論指導(dǎo)。在這種情況下,只能“摸穩(wěn)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推行一種漸進(jìn)式的制度變革。因此,這條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變遷路線的歷史功績,不容抹殺。但是,不可否認(rèn),這條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變遷路線對我國憲法提出了極大挑戰(zhàn),如果現(xiàn)在還不進(jìn)行新的調(diào)整,將會嚴(yán)重威脅到我國憲法和法律的權(quán)威以及它們良好的實施。這些挑戰(zhàn)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良性違憲的嫌疑。上世紀(jì)90年代我國學(xué)者對良性違憲問題曾展開了激烈的討論,贊成與反對者旗鼓相當(dāng)。絕大多數(shù)反對者反對的只是良性違憲的這種提法與理論,并不否認(rèn)我國良性違憲這一現(xiàn)象存在的事實。事實上,良性違憲論者早就注意到我國產(chǎn)權(quán)制度違憲問題。他們指出,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nóng)民沖破當(dāng)時憲法規(guī)定,實行包產(chǎn)到戶,若從狹義違憲的標(biāo)準(zhǔn)來看,他們不算違憲。但此后,安徽、四川兩省的政府在憲法未修改前卻大力推廣了這一做法,就構(gòu)成了“良性違憲”。1988年修憲前,我國政府有關(guān)部門對私營經(jīng)濟(jì)的存在采取默許乃至肯定,也構(gòu)成了一定程度的“良性違憲”。從這些產(chǎn)權(quán)制度變革過程來看,似乎難以走出這樣一條規(guī)律:良性違憲——修憲——合憲。
郝鐵川:《溫柔的抵抗——關(guān)于“良性違憲”的幾點說明》,《法學(xué)》,1997年第5期,第18頁。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的變遷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良性違憲現(xiàn)象,對我國憲法的權(quán)威性提出了極為嚴(yán)重的挑戰(zhàn)。
第二,高昂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變遷風(fēng)險。我國近30年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都是在不斷試錯中探索出來的,實行先試行,然后再總結(jié)經(jīng)驗加以推廣的實踐路線。這種實踐路線優(yōu)勢在于避開了許多沒有必要的理論爭吵與當(dāng)時形勢不合的制度約束,但這一路線極大地提高了制度變遷的風(fēng)險。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既有制度資源的浪費(fèi)。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的建立,需要耗費(fèi)大量的成本,如果在行為時對既有的制度不加考慮,就是對制度資源的極大浪費(fèi)。二是動搖人們對原有制度的信心,事實上就是對現(xiàn)有制度的不信任,造成了人們對整個制度的懷疑,增加了無數(shù)機(jī)會成本與交易成本。人們對制度信任的建立,需要制度能夠保持一定的連續(xù)性。一旦人們失去了對制度的信任,一切行為變得皆有可能,最后是變得所有人們內(nèi)心的浮動以及整個社會的失序。三是由于既有制度無法給人們提供明確的指引,人們無法預(yù)測自己行為,一切行為都在冒險之中。搞得好,就是英雄;搞得不好,就是狗熊,甚至成為社會的犧牲品。這些制度變遷風(fēng)險,在我國近30年經(jīng)濟(jì)改革中時有出現(xiàn),對我國憲法的信任與實施造成了嚴(yán)重危害。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憲法制度,被一些所謂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變革一夜之間就化為了烏有。
以上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變遷對憲法提出的挑戰(zhàn),表明了“八二憲法”在應(yīng)對外在社會變化時的束手無策與軟弱無力。這一方面說明,我國目前社會發(fā)生了急劇變革,憲法由于其穩(wěn)定性很難與社會發(fā)展相適應(yīng);另一方面則說明,我國憲法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很難對外在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提出自身的回應(yīng)。根據(jù)馬克思基本原理,社會總是會不斷變化、不斷往前發(fā)展的,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也總會不斷需要做出調(diào)整——這是我們無法改變的社會事實與客觀規(guī)律。因此,在遵循社會發(fā)展客觀規(guī)律的前提下,思考如何建立一種更能適應(yīng)社會變革的憲法制度,確保制度與社會發(fā)展之間的包容,成為當(dāng)前我國憲法學(xué)者的重要任務(wù)。
筆者以為,為應(yīng)付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的未來變遷,我們需要在立法技術(shù)上對“八二憲法”做出部分調(diào)整。第一,盡量減少關(guān)于產(chǎn)權(quán)制度方面的憲法規(guī)定。產(chǎn)權(quán)制度是憲法和法律的重要內(nèi)容,但是它不一定需要在憲法中加以直接的、無所不包式的規(guī)定。從現(xiàn)在世界各國憲法的規(guī)定來看,在憲法中全面、直接規(guī)定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國家非常少見。在憲法中規(guī)定完備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不但不可能,事實上也沒有必要。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需要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經(jīng)濟(jì)政策的變動中經(jīng)常進(jìn)行某些調(diào)整,而憲法是具有高度穩(wěn)定性、原則性的法律,如果憲法所規(guī)定的產(chǎn)權(quán)太具體就無法適應(yīng)產(chǎn)權(quán)制度變遷以及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需要。因此,筆者認(rèn)為,除開一些原則性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需要在憲法體現(xiàn)之外,其他的有關(guān)產(chǎn)權(quán)的制度完全可以放在具體法律中加以規(guī)定。第二,協(xié)調(diào)好憲法內(nèi)部關(guān)于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各項規(guī)定。例如,我國憲法既規(guī)定了個體經(jīng)濟(jì)、私營經(jīng)濟(jì)、外資企業(yè)等多種非公有制產(chǎn)權(quán)形式,同時規(guī)定了保護(hù)私有財產(chǎn)權(quán)。事實上,無論是什么非公有制形式的產(chǎn)權(quán),最終都會落到私有財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之中。因此,只要規(guī)定與落實了私有財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這一條,其他的私有產(chǎn)權(quán)形式就沒有必要在憲法中加以規(guī)定。
以上憲法制度的調(diào)整,一方面可以杜絕產(chǎn)權(quán)變遷過程中的良性違憲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另一方面則可以降低產(chǎn)權(quán)制度變遷的風(fēng)險,保持了制度的穩(wěn)定性與連續(xù)性。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憲法規(guī)定能為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的未來變遷留下了足夠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