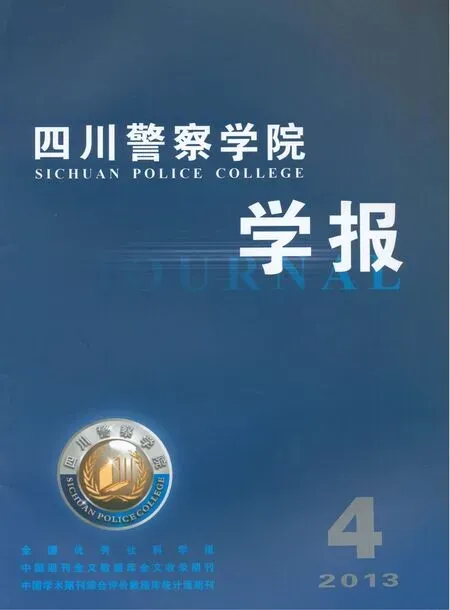沈家本在清末修律中的思想解析
向 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北京 100191)
1902年光緒下諭旨命沈家本、伍廷芳主持修訂法律館,于是清末轟轟烈烈的修律運動拉開了帷幕。修律活動,特別是1907年在他擔任修律大臣兼資政院副總裁之后進展很快,然而圍繞著一些基本的原則,如法律與禮教是分離還是合一?要不要采用現行西方的法律制度?以個人本位還是以家族本位作為修律的指導思想?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后陣營逐漸分化成法理和禮教兩派。這兩派在諸如以上原則性問題上的斗爭是針鋒相對的。同時其中的雙方領袖都是朝廷重臣,幾乎都參加了或法律的修訂、或簽注、或討論、或表決,因而對法律的影響是直接且巨大的,其中法理派的代表是沈家本,禮教派的代表是張之洞、勞乃宣。
一、生平及基本法學思想
沈家本(1840-1913),字子惇,一作子敦,別號寄簃,浙江歸安(今吳興)人。光緒九年(1883)進士,留刑部補官,從此專攻法律之學。光緒十九年(1893)出任天津知府,光 緒二十三年(1897)改保定知府。光緒二十八年(1902)他和伍廷芳受命主持修訂法律,總領修訂法律館事。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改革官制,他任大理院正卿。光緒三十三年(1907),與俞廉三、英瑞一同擔任修訂法律大臣,先后又兼法部右侍郎、左侍郎和資政院副總裁等職。辛亥革命爆發后,清政府命袁世凱組織內閣,沈家本出任袁內閣法部大臣。民國時期,章太炎等舉其為司法總長,辭未就職,于1913年病死北京。
沈家本是典型的學者型的官僚,他“少讀書,好深湛之思”、“髫年畢群經,于周官尤多神悟”。二十九歲開始進入清廷刑部供職,在長期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得以瀏覽歷代法典與刑獄檔案,是當時對中國傳統法律最有研究的人物,曾被譽為“以律鳴于時”、“法學泰斗”及“集中國法系大成的一人”。他不僅深研中國傳統法律,而且對西方法律也“逐字逐句,反復研究,務得其詳”。因而又被譽為“清代最大的法律專家、媒介東西幾大法系成為眷屬的一個冰人”。他這種“融會中西”的法律思想體系為其日后修律“會 通中西”的宗旨打下了扎實的基礎。他不但讀書勤奮,研究刻苦,而且也寫下了大量的著作,主要有《沈寄簃先生遺書》(甲編、乙編)及《讀律校勘記》、《秋讞須知》和《律例偶箋》等。身為清廷重臣,在當時人們對法律多有鄙夷的環境下能深入法律研究,其精神是可貴的;然而能沖破禮教束縛,對西方的近現代法律也頗有研究,其精神尤為可貴,其膽略、見識令人敬服。沈家本正是以其獨特的風格和高超的睿智,為中國法律文化現代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成為傳統法律向近現代轉型的豐碑式的人物。關于沈家本的修律思想可從以下四個方面來闡述。
首先,作為一代法學家,他高度贊揚了法律在治國中的作用。他說:“法者,天下之程式,萬事之儀表也。”如果一個國家無法可循一定不會長治久安。他說:“世無無法之國而能長久者。”同時他又認為,不僅一個國家要有法,而且必須是善法,否則法同虛設,他說:“國不可無法,有法而不善與無法等。”[1]不但如此,即使有了善法還得堅決執行,“法善而不循法,法亦虛器而已”[2]。他認為作為“天下之程式,萬事之儀表”的法必須統一,方可維護其權威性。他主張在法律面前平民貴族平等。他說:“法之及不及,但分善惡而已,烏得士族正庶之分。”因此他指責梁武帝“用法急黎庶而緩權貴”,反對對王室不用法而用家教、而對平民百姓則法外加刑的現象。這種初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后來成了他修律的一個指導思想。
沈家本不僅重視法律對治國的重要作用,還高度評價了法學的價值。認為法學之盛衰與一代之治存在著必然的聯系。他說:“清明之世,其法多平,陵夷之世,其法多頗,則法學之盛衰與政之治忽,實息息相通,然當學之盛也,不能必政之皆盛,而當學之衰也,可決其政之必衰。”[3]沈家本在傳統禮制的中國,又身為朝廷重臣,能有此等思想和卓見是難能可貴的。
二、對中國傳統法律的研究和批判
他對舊律中的刑法作了系統的研究,編成《歷代刑法考》一書,共七十八卷,計二十一冊。研究范圍包括律令、刑罰、赦法、監獄、刑具、行刑之制、死刑之數、鹽礬法、茶酒樓、同居律、丁年制、律目、刑官及誥命等。研究的系統性和深度表現在,他既從總的方面進行綜合研究,又從各個門類進行微觀分析;既重視對內容的研究,也重視形式方面的探討;既 整理散佚律令法制,又針對疑難問題進行考釋。從而深刻認識了中國舊律,為其維護、繼承、批判以及日后的修律打下了扎實的知識基礎。
沈家本對歷代開明君主的寬恕省罰大加贊賞。如沈家本高度贊揚了漢文帝廢肉刑,稱其是“千古之仁政”。并把肉刑與政治統治結合起來,用傳統儒家仁政觀點評價肉刑,說肉刑的廢除乃“千古之勢”,如欲恢復是不知治之本。他還舉例說,殷紂王的剖心法、炮烙刑是“肆其暴虐”,故“終于滅亡”;王莽因實行掘墓鞭尸、焚如刑和汙池法,所以“賊莽之惡,百倍于秦”;而明成祖的三族、九族及十族罪,太監魏忠賢的斷脊、墮指和刺心等刑,是大妄天下之法。
他對我國封建時代的法律典范、中華法系成立之標志——《唐律》也深有研究,他首先肯定了《唐律》刑罰最為適中,不愧為后世歷代王朝制律的榜樣。但他也充分的認識到其不足,即 “十惡”太苛、“八議”太不平等。他說,十惡中的不敬、不孝、不睦和不義等名同實異,而皆以“十惡”歸罪,實有偏頗,未免太酷。他說:“先王之法,恐不若是之苛也,此《唐律》之可議者”[4]。他高度贊揚了清世宗雍正的批評,認為對帝王的親、故、賢、能、功、貴、勤及賓等人實行法律庇護(即八議)是極不公正的。他說:“伏讀世宗圣訓,言之尤為詳明,實在可刪之列。存入律中,徒滋疑惑而已。”[5]十惡、八議是禮教指導法律制定和執行的結果,是禮法結合的集中體現。同時也是封建舊法中的兩大毒瘤。在日后的法理派與禮教派的爭論中,成為焦點性的問題。沈家本主張禮、法分離,維護法律的正義,這也成為其日后修律的指導思想。
沈家本主張禮、法分離,并以此為基礎對教育與刑罰的關系作了說明。但他的這一觀點沒有沖破傳統儒家“德主刑輔”的思想模式。他說:“刑者非威民之具,而以輔教之不足者也”[6]。
與“德主刑輔”的傳統觀念緊密相連的是“人治”。儒家強調統治者的道德教化、人格模范的作用。認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7]、“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8]、“有治人,無治法”、“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9]等等。沈家本對傳統法律的認識批判中,也未能擺脫“人治”的傳統,這就決定了他的法律視角中“人”的重要性。他說,唐初寬刑省罰,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僅二十九人,刑輕且犯者少。而武則天時,唐律未變,但使朝士宗親“咸罹冤酷”,只因為是周興、來俊臣等奸臣執法。又玄宗開元年間,號稱治平,二十五年,刑部所斷天下死罪僅五十八人,而到李林甫為相時,因任用羅希奭、吉溫等酷吏,屢起大獄,誣陷殺害數十百人,如韋堅、李邕等名臣也難以幸免,故“天下冤之”。所以“有其法者,尤貴有其人矣”[10]。雖然沈家本的法律思想未脫離傳統人治的窠臼,但后來他慢慢走出了傳統的牢籠,這是因為他逐漸接受了西方近現代的資產階級法治觀,這一點從他日后的修律中充分的體現了出來。因此使沈家本的“人治”觀包涵了異質于傳統人治的因素。
還值得一提的是,沈家本對中西法律文化作了一定的比較研究,并從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提煉出類似或符合西方近現代法治文明精神的因素。現略舉幾例。
關于法治主義。他認為《管子》立法典民,以法治國,頗似于現代西方,因此,“法治主義古人早有持此說者”。
所謂陪審員制度。他舉例說,《周禮·秋官》的三刺法,斷獄治罪必詢問萬民,萬民以 為可殺則施上服下的刑,與孟子“國人殺之”的意思隱相吻合。他說這是“陪審員之權輿……今東西和各國行之,實與中國古法相近”[11]。
關于罰金之法。據他考證,罰金之名始于《周禮》的“職金”,而詳于 《管子》,用以懲罰較輕的罪。他將之與日本現代刑法比較說:“其事則采自西方,其名實本之于古。”
關于幼者當教。他說,《唐律》七歲以下不加刑,十歲以下雖反逆殺人應死,亦得上請,十五歲以下流罪收贖。這與西方的“幼者可教而不可罰”“實一義”。
這些具有西方現代法律文明萌芽性質的因素和精神,在沈家本日后的修律中都得到了發展,充分反映了一代法學家的人道主義精神及嚴肅的社會責任感和深沉的歷史使命感。
三、對中國舊律的修改意見
沈家本在刻苦研究中國傳統法律的基礎上,充分認識到它的弊端和不足,診斷必須對舊律加以修訂,并總結了以下五個方面的修改意見。
(一)刪除總目,簡易例文。
舊律承《明律》,《明律》承《元圣典》、《元典章》和《經世大典》等書,總目以六部分職。然而官制有的已改,有的已歸并,實情實有所異。故不能仍繩舊式,而應將吏戶禮兵刑工諸目一并刪除,以期劃一。
例文因年而增、因時而變,已多達二千余條,然與律文不合者大有其條,因此形同虛設,所以為求簡易易行,則應量加刪除。
(二)廢除舊法中的重法和附加刑。
為了適應國際輕刑的取向和體現仁政之道,沈家本主張廢除重刑。他以日本為例,說中國跟日本政教、文字及風俗有很多相同之處,故其法可資借鑒。他說日本在新律未頒布之前,就先行將磔罪、梟首、籍沒和墨刑等重法廢除了,從而使民風大變,日本也因此而逐漸強盛。他說:“現行律例款目極繁,而最重之法,亟應先議刪除者,約有三事:一曰凌遲梟首戮尸……一曰緣坐矣……一曰刺字”[12]。又說:“擬請將凌遲、梟首、戮尸三項一概刪除,死罪致斬決為止。……擬請將律例緣坐各條除知情者仍治罪外,其不知情者悉予寬免,余條有科及家屬者準此……擬請將刺字款目概行刪除。”[13]凡律內凌遲、斬梟各條俱改斬決,斬決各條俱改絞決,絞決俱改監候。刺字原主要用于竊盜罪等,刪除后,凡竊盜皆令其入習藝所學藝,按罪名輕重定年限,使之有一技之長,釋后得以糊口。
附加刑就是指“枷杖并用”,即金梁肅所言:“今取遼季之法,徒一年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于斯為甚”[14]。一罪二刑,這與輕刑宗旨相忤,故應刪除“附加之法”。
(三)酌減死罪,改虛擬死罪為徒流,死刑唯一。
對于酌減死罪,他以唐太宗為榜樣,說他精簡絞刑五十,改為役流,為史志稱道。外國死刑也極少,日本雖承用中國刑法很久,也只有二十條。因此,應根據《唐律》及國際通例,將條目繁多的中國死刑量加酌減。有些因中國風俗一時難以驟減的,如盜、搶殺及發冢等,可別輯暫行章程以存其條。
關于虛擬死罪。他說,中國現行律例中的虛擬死罪,主要指戲殺、誤殺和擅殺三項,而外國對此僅處以懲役、禁錮。《唐律》對戲殺、誤殺分別處徒流,就算擅殺,也不一定全處死罪。而清律雖擬此三罪絞,但實與流無別,不過是虛擬的死罪而已,因此為從實計,當改 戲殺為徒,改誤、擅殺為流,皆按新律不用發配,入習藝所,罰其勞役。
關于死刑唯一。沈家本提出此條也是為輕刑計為法律統一計。他說斬使身首兩離故酷于絞,然今除德、法和瑞典等少數國家用斬刑外,其他大多數國家如英、美、俄、西及匈等都用絞,而且僅只其一種。故中國應擬死刑僅用絞刑一種。但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和父母等條俱屬罪大惡極,仍用舊刑,別輯另行。
(四)停止刑訊,刪除比附,更定刑名。
沈家本認為刑訊血肉飛濺,傷和害理,所以除罪應處以死刑,證據確鑿,而硬不供招者,準其刑訊外,其余流徒以下罪名及初次訊供,概不準刑訊,以免冤濫。至于笞杖等罪可懲罰金。
關于刪除比附條。沈家本認為比附之弊端有三:其一、與憲政精神相悖,實行憲政的國家,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如果援引比附,則是司法權對立法權的侵犯;其二、允許援引比附,為司法者出入人罪提供了機會,使司法不能統一,同時百姓遭殃;其三、若于律法之外參予司法者的主觀意志,則使法律權威掃地,民也無所適從。因此,“擬刪除此律,而各刑酌定上下之限,憑審判官臨時審定,并別設酌量減輕,宥恕減輕各例,以補其缺。雖無比附之條,而援引之時,亦不致為定例所縛束”[15]。
關于刑名的更定。沈家本認為現行《大清律例》的“笞、杖、徒、流、死”的規范是歷朝因襲《隋律》的結果,然時致現代,交通日便,使流刑已失去了其歷史意義,而笞、杖則與國際輕刑取向不合。按照西方法律,次死之刑多為自由刑(懲役、禁錮、拘留)及罰金居多,故中國理當更定刑名,將“笞、杖、徒、流、死”改為“罰金、拘留、徒、死”。
(五)統一刑制,提倡滿漢、民賤、男女、僑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滿漢平等是指,改變清初對八旗人犯遣軍徒流罪折枷免于發配,刪除律內折枷各條,與漢人同處。他說:“現既欽奉明詔,化除滿漢畛域,若舊日兩歧之法仍因循不改,何以昭大信而釋群疑。……擬請嗣后旗人犯遣軍流徒各罪,照民人一體同科,實行發配,現行律例折枷各條,概行刪除,以詔統一,而化畛域”[16]。
沈家本也提倡良賤平等,主張廢除人口買賣和奴婢制度。他說奴婢制度和人口買賣一方面是賤視人格,另一方面與憲政宗旨格格不入。因此應廢除二者,以期全民平等。
沈家本同時主張男女平等。他說:“妻者齊也,有敵體之義,論情誼,初不若君父之尊嚴,論分際,亦不等君父之懸絕。……衡于情定罪,似應視君父略殺,庶為平允。”[17]舊律夫妻罪名輕重懸殊,“實非妻齊之本旨”,有悖夫妻“敵體之義”。
沈家本還將法律平等精神擴大到外國僑民。他說西方多采用屬地原則,而中國對僑居于華的罪犯沒有審判權,只因外國以“不仁之名”竊取了中國的治外法權。因此要取得治外法權加緊變法修律,“務期中外通行”。
沈家本作為晚清官僚所進行的修律必然受其階級和時代所局限,因而在修律中有不少牴牾之處。例如他既說良賤之名可除而尊卑之分不可溟,若有相犯,“自難概以平等同論”。但總體而言,沈家本修律,刪繁就簡、廢舊立新、去重從輕及化死為生,廢除了舊律中延續了數百年乃至數千年的重法,使中國法律由落后和野蠻步向先進和文明,為中國法制現代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四、修律中吸收資產階級的法律精神
沈家本在修律過程中,在“融匯中西”原則指導下,注意運用西方的近現代資產階級的 法律文化來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加以改造。
(一)改變舊律民刑不分,實體法與訴訟法不分的法律體例。
他以西方為榜樣,說西方的實體與訴訟法是分離的,這樣有便于司法的運作。他說:“法律一道因時制宜,……查訴訟斷獄附見刑律,沿用唐明舊制,用意重在簡括。揆諸今日情形,亟應擴充,以期詳備。泰西各國訴訟之法,均系另輯專書”[18]。如果訴訟法附著于實體法上面,再完善,也“于法政仍無濟也”。
沈家本以刑事、民事案件性質不同為依據,主張將傳統舊律的民刑一體的法律體例改成民事分立,這樣有便于司法操作。民事主要涉及錢債、房宅、地畝、契約、戶婚、繼承、索欠和賠償等,而刑事則主要是叛逆、偽造貨幣官印、謀殺、故殺、搶劫、盜竊、詐騙及恐嚇索財等。因此主張民刑分立,使刑律“專注于刑事之一部”,這樣就使“斷弊之制秩序井然,平理之功如執符契”。
(二)主張司法獨立,改良監獄。
沈家本為憲政計的立法方針,主張司法獨立,使司法、立法和行政三權“鼎峙”。因為西方憲政的萌芽,“俱本于司法之獨立”,同時這樣可“推明法律,專而能精”。他說:“政刑叢于一人之身,雖兼人之資,常有不及勢,況乎人各有能有不能。長于政教者未必能深通法律,長于治獄者未必為政事之才,一心兼營,轉致兩無成就”[19]。所以他編纂《法院編制法》,嚴格裁明官吏的職責,監督權限,以防止行政權的涉入。
沈家本認為司法獨立的核心是裁判權的獨立,因此為了保持此權獨立,即使總統和君主也沒有裁判權,而只能有有限的赦免權。他認為司法獨立之義,理應包括法部與大理院的職權分立。法部是司法行政部門,只能管司法政策及對大理院實行一定的監督,而大理院為審判機構,具有最高的審判決策權。
沈家本接受了西方現代的監獄理念,認為監獄與司法、立法應三足鼎峙,是“遷善感化”之場所。他說:“監獄者,感化人而非苦人辱人者也”[20]。因為,“犯罪之人歉于教化者為多,嚴刑厲法可懲治肅于既往,難望湔祓于將來,故藉監獄之地,施教誨之方”[21]。這也是適應國際潮流和實行新政的“最要之舉”。為此他提出了改建新式監獄、培養監獄官吏、頒行監獄規制及編輯監獄統計等四項主張以建立現代監獄體系。
(三)主張建立陪審員和律師制度。
沈家本認為陪審員制度與律師制度是國際通行的司法制度,是我國亟應效法的制度。他認為司法官一人,能力和知識有限,難免影響司法的公正性。因此主張在各省會、通商巨埠及會審公堂,應延訪紳士商人民人等,造成陪審員清冊,遇有應行陪審案件即“當依法試辦”。在審判過程中,陪審員應秉公正法,力保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這樣既可防止不肖刑官“賄縱曲庇、任情判斷及舞文誣陷等弊”,更可實現“裁判悉秉公理,輕重胥協輿評,自無枉縱深故之虞”[22]。
沈家本從給訴訟當事人“代伸權利”計,認為通商各埠,華人訟案與中外交涉事件,均有外國律師辦理,不但“桿格不通”,而且后患不堪設想。因此,他主張建立自己的一套律師制度,重案由國家指派律師,一般案件由原被告自請,貧民可由救助會指定而不取報酬。這樣通過律師代理一切質問、對詰及復問等事宜,可以避免訴訟當事人因經驗和知識的缺失而產生驚惶失措從而使自己的合法權利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現象。
(四)對少年犯實行懲治教育。
沈家本將西方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法律觀與中國傳統的“明刑弼教”觀念結合起來,在整個的修律過程中始終貫穿著這一精神。例如他認為丁年(十六歲)以內的少年犯尚不具備獨立的法律行為和責任能力,故他(她)們犯罪不應懲罰而應教育。因此主張各省成立懲治場,收容拘置少年犯。他認為如果將少年犯放在監獄與成人一起管教,因其不成熟故易染各種惡習,如付諸家教,又往往無效。因此應象德國那樣設立類似學校的少年懲治場。
(五)主張另立專案,增設新罪名。
根據“務期中外通行”和“兼采近世最新之學說”的修律宗旨,沈家本充分注意學習西方先進的現代司法制度,同時注意法律的實用性,為此他提出增設一些罪名的主張。
他說各國刑法都設有誣指一科,英國有誹謗外國高位人的罪,德國有毀一國君主榮譽罪,故迫于外交需要當設誣指專條。又外國銀元在華通行,偽造外國銀幣的案件時有發生,然與偽造中國案件略有不同,因此應另立專條,以示區分。他說:“與其就案斟酌,臨事鮮有依據,何如定立專條,隨時可資引用”[23]。另外,他還主張因時制律,增設以下諸罪名:外患罪、妨害國交罪、泄露機務罪、妨害公務罪、妨害往來通信罪和妨害衛生罪等。
(六)主張興法學培養法律人才,加強人們的法制觀念。
沈家本針對中國傳統社會中只重法律而不重法學,沒有專門的法律學堂和法學組織的現狀,主張學習西方,興辦學堂,成立專門的法學組織,翻譯西方法學之書。為此他申請在北京成立京師法律學堂。他說“余恭膺簡命,偕新會伍秩庸侍郎修訂法律,并參用歐美科條,開館編纂。伍侍郎曰:‘法律成而無講求法律之人,施行必多阻閡,非專設學堂培養人才不可。’余與館中同人,僉韙其議。于是奏請撥款,設立法律學堂”[24]。除京師法律學堂外,經沈家本請求,還在各省已辦之課吏館內添設講堂,專設仕學速成科,自候補道府以至佐雜,年40以內者,均令入學肄業,本地紳士亦準附學聽講,經過考試,量才錄用。1906年9月,京師法律學堂開學,沈家本充任管理法律學堂事務大臣。幾年中,“畢業者近千人,一時稱盛”[25]。
1910年11月,在沈家本的指導下,以京師法律學堂及修訂法律館館員為核心,成立了北京法學會,沈家本被推舉為會長。1911年春,北京法學會在財政學堂內設立了法政研究所,并出版發行《法學會雜志》,沈家本慷慨為序道:“弁日法學昌明,巨子輩出,得與東西各先進國媲美者,斯會實為先河矣”[26]。
為修律工作計和為促進中國法學近代化,沈家本還非常重視編譯西方政治法律著作。他說:“欲明西法之宗旨,必研究西人之學,尤必編譯西人之書”[27]。對于西方政治法律制度“非親見之不能得其詳”,于其政治法律著作“非親見而精譯之不能舉其要”[28]。于是以修訂法律館為依托,組織聘請既通外交又懂政治法律專門知識的歸國留學生和學者,“搜討眾作,鑒別去取”,力爭譯出上乘之作。
在他的主持、督促下,從光緒三十年四月修訂法律館開館起,幾年時間,就翻譯了英、法、德、俄、荷蘭、意大利、日本、比利時、瑞士及芬蘭等十幾個國家的幾十種法律和法學著作[29]。
五、博古通今、融會中西的修律指導原則
作為一代法學泰斗,沈家本非常重視作為系統存在的法律和法學,為此在修律中,他非常重視古代法律和外國法律,以資借鑒。他說:“折衷各國大同之良規,兼采近世最新之學說,而仍不戾乎我國歷世相沿之禮教民情”[30]。又說:“我法之不善者當去之,當去不去,是之為悖;彼法之善者當取之,當取而不取,是之為愚”[31]。因為,“當此法治時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討論中法,則法學不全,又安能會而通之,以推行于世”[32]。這是堅持了杜預《晉律法》中所說的“網羅法意”、“非專主一家”之精神。 他強調,學古并不是泥古,也并非疑古;學西方也不是全盤接受,而是兼采其長。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可謂博大精深,在修律中,他也忠誠的貫徹了他的法律精神,為中國的法律現代化作出了偉大的貢獻。雖然當時他所提供的只是形式意義上的法律體例,但這一體例的突破,其價值也是不可估量的,后世的南京臨時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以致新中國的法制無不受其影響。至于實質層面的法律觀念和意識,是受歷史的局限,非一日之功,沈家本對此也回天無力,但他的努力和嘗試卻大大地加強了人們的法制觀念,為中國法律乃至社會現代化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1][3][12][13][14][16][17][20][23][24][26][28][29][31][32]沈家本.寄簃文存[C].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2239;1221;2025;876;799;1227;1362;2681;2267;672;2679;1156;2781;2098;1625.
[2][4][5][6][10][19]沈家本.歷代刑法考[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47;56;68;79;90;125.
[7]禮記[C].濟南:齊魯書社,2006:25.
[8]孔子.論語[C].北京:中華書局,2006:P29.
[9]荀子.荀子[M].北京:中華書局,2007:P52.
[11][18][22][30]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大清新法令[C].上海:商務印書館,2011:28;325;563;489.
[15][21]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C](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36;79.
[25]趙爾巽.清史稿[C].北京:中華書局,2012:87.
[27]編委會.新譯法規大全[C].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