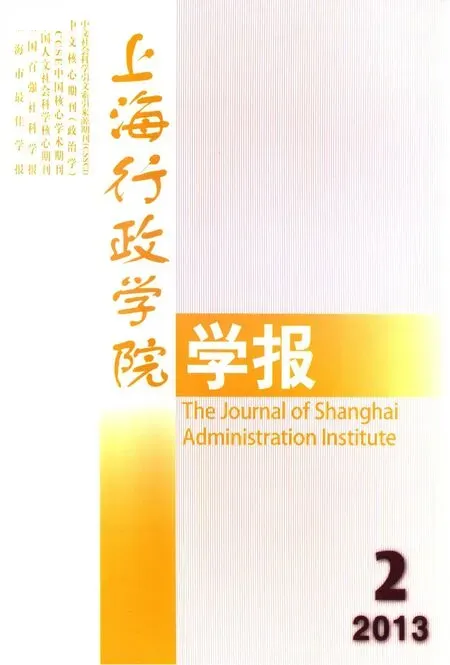邁向勞工政治分析范式的白領工人研究*——理論述評與現實啟示
李中仁 陳周旺
(復旦大學,上海 200433)
“白領”作為一種職業標簽,一般被用來指涉擁有專業知識或技能的非體力勞動者,如高科技產業或生產服務業中的技術人員、工程師及公司經理等。白領職業的出現,直接反映了現代社會勞動分工不斷深化的趨勢。早在19世紀,馬克思便曾對當時工廠里的文職人員與低層管理人員進行過初步考察,并認為他們是產業工人階級之外的另外一群雇傭勞動者。不過,馬克思同樣發現,當時的白領雇員雖然對生產資料沒有所有權,但他們的勞動實際上并不創造剩余價值,他們的階級特征自然不同于傳統無產階級。①由此,在以產業工人階級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白領工人并沒有受到充分重視。
進入20世紀之后,受現代信息技術革命的推動,技術密集型產業最先在西方發達國家中興起,科技白領工作者的人數隨之急劇擴張。20世紀下半葉以來,在全球化進程的驅使下,發達國家中的高科技部門紛紛將業務擴展到了廣大的發展中國家,進而也在當地塑造了一批新興的白領職業群體。面對白領勞工在當今各國經濟生活中的快速崛起之勢,如何在理論資源嚴重匱乏的情況下發展出解釋該人群市場處境及社會地位的學說,遂成為學界的當務之急。
一、研究緣起:勞資二元關系范式中的白領工人階級地位議題
馬克思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散,現代社會內部的階級結構日益呈現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二者對立共存的格局;②至于那些雖擁有生產資料卻又要靠自身勞動創造價值的中間階層(如小資產階級、手工藝者或小雇主等),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會因殘酷的市場競爭而掉落到無產者階級隊伍里。馬克思將這一論點概括為現代社會的“無產階級化”現象。③
然而,20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方社會并沒有出現明顯的無產階級化趨勢,勞工階級內部也經歷了重大分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白領工人群體的產生與壯大。與處在社會底層的體力勞動者相比,白領大多擁有特定的管理技能或知識技能,在企業中主要從事流程管理或產品開發等智識型工作,并享有優越的勞動條件與良好的社會聲望。顯然,這支就業大軍所表現出的各項社會特征完全超出了傳統無產階級化理論的討論范疇,這就要求后世學者盡快發展出新的理論分析工具。
在這些新的研究中,白領群體的社會地位成為各派學者共同聚焦的問題之一。④回顧有關這一主題的相關研究,主要有以下兩大對立的觀點:白領工人無產階級化論與新中產階級論。持第一種立場的主要是馬克思主義學者,而以社會分層學者和后現代理論家為首的研究者則大多采納第二種觀點。
1.白領工人無產階級化論
最早就白領群體階級地位問題展開詳細討論的當屬美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在《勞動與壟斷資本》一書中,布雷弗曼指出:正如馬克思所言,在早期資本主義企業內,非體力工作者的確同雇主有著密切的聯系,其社會身份與意識傾向也更加偏向于資產階級。⑤然而,隨著商品化進程的推進,產業工人身上發生的“去技術化”(De-Skilling)現象逐漸波及到了這些非體力白領雇員:一方面,工作內容的程式化(rationalization)使得他們喪失了以往在生產過程中的優勢地位,繼而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另一方面,隨著科學技術成為剩余價值的源泉,他們的腦力勞動也被納入資本剝削的機制之中。⑥這一變化標志著白領工人經歷了一種特殊的無產階級化歷程,即他們的生產處境和社會地位不斷惡化,在階級特征上越來越向底層無產階級靠攏。⑦
受布雷弗曼啟發,英國學者克朗普頓(Rosemary Crompton)在對英國白領雇員的研究中采取了相同的視角。她發現,很多以往要求高級綜合技能的白領工作實際上已淪為日常性的繁瑣體力工作。據此,她認為現代社會的確存在布雷弗曼意義上的白領工人無產階級化趨勢。⑧加森(Barbara Garson)在對美國金融服務行業職業技能的研究中也持類似觀點。他認為,自動化技術的快速發展,大幅度削弱了白領工人以往對工作的自主控制權,而標準化管理模式的普及,則進一步加劇了腦力勞動的“去技術化”傾向。⑨由此看來,資本對白領雇員的宰制與對產業工人的剝削本質上是相同的。
塞尼特(Richard Sennett)晚近對當代資本主義生產組織流程的探討則指出,以科層制為核心的福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現代市場中已被一種新型的“彈性資本主義”所取代。所謂“彈性”(Flexibility),意指為了適應變幻莫測的市場需求,企業內部的傳統官僚等級制度被有意識地打散或取消,同時大量的臨時性、外包性工作被創造出來,企業內部權力結構變得“集中而不集權”。⑩處于這一新型生產制度下的勞動者雖在工作流程及技能運用上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卻時刻承受著由績效管理體制所帶來的巨大壓力,個人職涯安全與勞動權益均遭到嚴峻挑戰。?
與上述勞動過程視角相比,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賴特(Erik Olin Wright)采取的是通過測量特定時段某一社會中底層無產階級人數的變化趨勢,來推論該社會是否存在無產階級化現象。賴特認為,社會結構是由不同階級位置所共同構筑的社會關系總和,而階級位置則由人們所隸屬的生產關系來確定。如是觀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除了資產階級、工人階級以及老中產階級這三大傳統階級位置之外,還存在另外一類“矛盾的階級地位”?。立于該階級位置的人群主要包括以下兩種白領雇傭勞動者:公司管理人員與技術工程人員。?在賴特看來,這些白領雇員的階級屬性并不穩定,他們極易受到經濟形勢的波動而掉落到無產階級隊伍中或上升至更高的階級地位。賴特發現,1960年至1970年間,半獨立雇傭勞動者群體的人數雖因新興科技產業的發展而有所增長,卻在各產業部門內部急劇下降,因而他們在階級結構中的整體比例呈現出明顯萎縮的態勢;與之相反,傳統工人階級的人數雖因科技產業的興起而有所減少,但在各產業內部卻迅速增加,兩相抵消后無產階級的規模依然大幅擴張。據此,他指出,受經濟形勢的影響,美國社會在20世紀60年代的確存在持續的無產階級化進程。?
2.新中產階級論
社會學家米爾斯率先對馬克思主義流派的觀點做出回應。在其名著《白領》一書中,米爾斯指出:“無財產的雇員(包括雇傭勞動者和薪金雇員)事實上并沒有自動采取社會主義的立場,這就清楚地表明,無財產不是決定內在的意識或政治意愿的唯一因素,甚至也不是關鍵因素。”?借助于韋伯的身份群體理論,米爾斯認為正是市場關系所賦予的象征性社會聲望資源,使得白領雇員們在主觀上將自己同傳統工人階級區分開來,轉而認同中產階級意識形態及價值理念。
對市場地位及主觀社會聲望的重視,構成了米氏駁斥白領工人無產階級化命題的重要論據。異曲同工的是,瓦拉斯(Steven P.Vallas)在對美國通信產業辦公室職員階級意識的研究中也發現,雖然這些白領雇員們在工作中已經強烈感受到了枯燥與不公正的生產制度,但他們并沒有因此主動認同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反而在訪談中依然強調自己的中間階層社會地位與聲望。?
繼米爾斯等之后,英國學者洛克伍德(Lockwood)進一步繼承與發展了這一取向。洛克伍德結合馬克思與韋伯的階級理論,將“階級地位”劃分為“市場地位”(Market Situation)、“工作地位”(Work Situation)、“身份地位”(Status Situation)三大內在面向。他發現:與體力工人相比,白領工人首先在市場中明顯獲得了更為優越的經濟待遇與社會聲望,并擁有更多的晉升機會;其次,白領工人同資本家的關系較為親密,二者的勞資關系一般處于比較緩和的狀態,因而他們也不太會通過組織化的方式來維護自身權益;再次,白領雇員對工作依然保持著一定程度的自由處置權,而不必完全受機器化大生產的制約;最后,上述諸種客觀特質最終使得白領工人在主觀上具備了中產階級的身份認同。?據此,洛克伍德認為,無論是客觀面向還是主觀面向,白領雇員的階級特征皆不同于傳統產業工人階級。這一觀點得到了學者加利(Duncan Gallie)的支持。加利在對20世紀90年代英國國內勞動力市場形態進行細致考察后發現,雖然隨著技術的進步,白領工人與體力工人在生產處境上越來越相似,但二者間由于技能差異與職業晉升前景的差距而產生的階級鴻溝并沒有消失。因此,他同樣傾向于將白領工人視為一個獨立的社會中間等級。?
3.對白領雇員工作性質的再考察
隨著研究的推進,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意識到,必須對白領雇員的社會生存狀態做更為細致與全面的考察,而不是將其外在的社會特征強行嵌套進已有的理論模型之中。據此,一些學者開始重新探討白領職業勞動過程的性質。
美國學者拉爾森(Magali Larson)在其研究中提出,與傳統無產階級化歷程相比,白領工人的無產階級化歷程應當涵蓋四個觀察維度,即經濟地位的異化(Economic Dimension of Alienation)、組織化生產的異化(Organizational Alienation)、知識技能的異化(Technical Alienation)與政治(意識形態)的異化(Political Alienation)。?拉爾森在工程師、教師等白領從業者身上發現,與傳統產業工人相比,他們的無產階級化方式呈現出以下獨特之處:一方面,體力工人所經歷的經濟異化、組織異化及政治意識形態異化現象在白領勞工身上均有所體現,這表明后者在生產過程中同樣深受資本專制力量的宰制;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白領工人自身所擁有的專業技能是商品價值生產鏈上的重要一環,因而他們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會被“去技術化”。據此,拉爾森認為,白領工人的無產階級化應當被表述為勞動者部分享有技能自主權的特殊異化狀態。?
類似的看法也出現在德伯 (Charles Derber)的研究中。德伯指出,與后現代理論的預期不同,白領工人在生產目的上確實經歷了“意識形態無產階級化”;不過,這種特殊的無產階級化狀態又沒有馬克思主義學者想象的那么徹底,因為他們對生產過程還保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決策權。這一狀態表面上減輕了白領工人的被異化程度,然而實際上卻使得他們認同了資本的剩余價值分配法則。[21]
及至20世紀下半葉,隨著新自由主義國際貿易秩序的建立,跨國資本得以在全球范圍內追逐超額利潤,以往只存在于發達國家中的高科技產業也開始迅速向世界其它地區轉移。受此波知識轉移浪潮的影響,很多發展中國家已經建立起了規模龐大的科技密集型產業,當地白領勞動者的人數自然也蔚為可觀。與發達國家同類工人相比,發展中國家中的這批白領技術工人雖然也生長于市場環境中,卻是跨國貿易和國家政策主動塑造的產物。在此背景下,以勞資二元關系范式為主的既往分析范式已無力回應當下的發展趨勢,如何找到新的理論透鏡來觀察發展中國家的白領勞工群體,成為下一階段白領研究的重要任務。
二、范式轉換:生產政治理論與發展中國家白領勞工政治研究
當人們意識到對發展中國家白領工人的考察嚴重滯后之時,一種新的研究范式開始受到廣泛關注,那便是從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發展而來的生產政治理論。
生產政治理論是由美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邁克爾·布洛維(Michael Burawoy)所提出來的統攝性分析框架,主要用來探討勞資雙方在生產過程中所結成的結構性關系,以及國家力量對這種關系形態的主動干預。在布洛維看來,為了緩解資本與雇傭工人之間的緊張關系,國家會主動從兩方面入手規制勞資關系:一方面,國家會建立一套社會保障制度,幫助工人不再完全依靠工資性收入來維持自身的勞動力再生產,進而降低他們對資本的依附;另一方面,國家通過實施一系列勞動法規來阻止生產過程中資本對工人的無限度剝削,維護工人的正當權益。[22]考慮到國家所扮演的這種重要角色,布洛維指出,馬克思意義上的上層建筑不僅存在于政治生活領域,也存在于經濟生產領域,其具體形態便是工廠中由國家干預生成的政治性規訓機構,簡稱“生產政體”。[23]質言之,生產政治詳細地展示了微觀生產關系的政治性構建過程。
生產政治理論的成熟,標志著當代勞工研究開始有意識地將國家作為獨立變量引入階級分析框架中來。在其指引下,學者們發現了專制、霸權以及霸權專制等產生于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國家內部的生產政體形態,加深了人們對勞工階級生產處境及市場地位的了解。
美國學者麥凱運用生產政治理論視角,詳細考察了菲律賓國內高科技產業中跨國公司的勞動體制。在其著作中,他提出了兩個重要問題:高科技產業的生產政體會是何種形態?菲律賓政府在生產政體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對此,麥凱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在當地不同規模的跨國企業中,盛行著一種獨特的生產政體,他將其命名為“靈活積累型”政體。[24]在其治下,跨國資本對技術工人的高壓管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與配合,由此在生產領域和勞動力市場中出現了一個組織力量弱小、內部競爭激烈的青年技術工人大軍。具體而言,國家對生產政體的塑造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為了提高生產能力,國家有意識地放松對跨國企業生產管理過程的監督,并建立偏向于資本方的勞動仲裁體系,以此削弱白領工人的組織化談判能力;其二,為了吸引投資,菲律賓各級政府主動幫助跨國資本在全國范圍內招募年輕、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提供規模龐大的勞動力后備軍,從而削弱了技術工人的市場談判能力。[25]如此一來,跨國資本得以在國家的“保護”下既放心地攫取剩余價值,又保證工人對生產政體的消極服從。
除了考察生產過程,麥凱還將視野擴展到了當地的勞動力市場。他發現,由于高科技產業需要大量具備較高知識技能的勞動力,這使得發展中國家在迎合資本、壓制勞工的同時,還必須在短時間內利用職業教育及社會保障等各類制度創造出一批中高端白領工人群體。[26]由此看來,無論是在生產領域還是在社會生活領域,白領工人無不受國家相關政策及制度的影響。
項飆在對印度IT勞工的研究中采取了類似的分析視角。項飆向人們揭示了印度國內一個龐大而不為人重視的非正式部門——“獵身”業務,并認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印度IT業才得以在全球信息產業鏈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所謂獵身,即是指兼具勞務派遣與技能培訓功能的印度本土勞力行利用自身擁有的各類關系網絡,在國內招募大量廉價技術工人,然后將其派往本土或海外的正式公司,并從中賺取工人勞動價值的復雜業務。在該體系中,正規公司并不與工人發生法律意義上的雇傭關系,而是由勞力行代表雇主直接管理那些被派遣工人,并為其辦理擔保、簽證、支付報酬等多項事務。[27]這樣一來,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公司能夠根據市場形勢隨時招募或裁退工人,從而大幅降低企業運作成本。至于那些工人,等待他們的卻往往不是海外公司豐厚的報酬,而是高度彈性化勞動力市場中變幻莫測的工作前景及市場處境。
獵身業務的存在,實際上使得那些大企業成功地避開了民族國家的勞動權益保障體制,并強化了他們剝削技術工人的能力。不僅如此,它還向工人灌輸了一套以個人能力為中心的市場觀念——在此觀念下,每個人的市場地位均被視為自身能力與價值的自然體現,而勞資關系的公正與否則變得無關緊要。這一市場意識形態的普及,最終徹底瓦解了工人群體的內部凝聚力。[28]
對比第一階段的研究成果,當前的白領研究無論是在問題意識上還是理論視角上均有明顯進步。
首先,學者們不再簡單復述前人有關白領工人階級地位的問題意識,而是積極向外拓寬白領研究的問題域。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同一主題,即國家怎樣干涉及塑造白領勞工與跨國資本之間的關系?不同類型的干涉會對白領勞工的生產地位及市場處境帶來何種影響?在該主題的指引下,人們開始拋棄過去那種靜態化的勞資二元關系理論范式,不再將國家視為獨立于勞資關系之外的力量。生產政治理論正好為研究者們提供了一個更具穿透力的分析工具。
其次,相比于先前基本以西方發達國家作為討論背景的研究格局,對全球化進程下發展中國家白領工人及高科技產業的考察日益成為主流的學術興趣。這一趨勢表明,學者們一致認同,在當今特殊的國際經濟秩序下,發展中國家與資本及勞動之間的復雜關系將會是今后理論創新的重要源泉。
三、新視角的引入:生產政治與中國白領雇員政治研究
市場化改革至今,中國已成為全世界吸納跨國投資最多的國家。數據顯示,在全球產業轉移潮流的影響下,中國的信息、金融、電子商務等各類高科技產業近年來發展速度驚人。[29]與這一趨勢相對應的是,一支日益擴張的白領勞動力大軍日漸壯大。他們身處勞動力市場的中高端,通常被人們稱作都市白領。
值得肯定的是,研究者對這一新興社群有著濃厚的學術興趣,并做出了諸多有益的嘗試。然而另一方面,當我們近距離地觀察已有成果時會發現,它們當中絕大多數都在探討這一人群的社會地位與社會功能,而疏于考察他們在生產過程中所遇到的結構性力量。
當前對我國白領群體最感興趣的當屬社會分層學者。在他們看來,與普通勞動者相比,白領在收入水平、社會地位與教育水平上均屬于中高等層次,因而是社會中產階級的核心代表。[30]在此認識論的基礎上,中國白領研究被理論界等同為中產階級研究。現有研究主要關注兩大議題:其一,致力于通過社會調查與社會統計的方法來論證白領階層在當代中國社會結構中的“新中產階級”地位,并從社會聲望或消費習慣維度挖掘他們的階級特征、歷史來源及自我身份認同。例如,李路路和李升認為,當代中國存在兩類性格特征完全不同的中產階級,其中所謂的“外生中產階級”便是指市場經濟部門中的管理及技術白領雇員。相較于“內源中產階級”,白領的中產階級身份顯然源自他們的市場能力與市場地位。[31]李培林等人在2006年對全國中產階級規模進行測量時,更加明確地將“職業”作為界定中產階級的標準之一,因而白領雇員群體自然就被視為新興中產階級。[32]其二,繼承西方理論家對中產階級社會功能的探討,考察中國白領階層的政治認同與集體行動傾向。李友梅用“強政治取向”和“弱政治參與”[33]這兩對概念來總結該群體的主流行為方式;李春玲在研究中也認為他們對政府政策和現實政治體制基本持肯定的態度,因而是促進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34]
上述學者均發現了中國白領群體在意識傾向或社會流動上所表現出的獨特之處。李友梅在考察上海白領的群體發展階段與社會心態時便指出:這一群體在社會經歷、價值分享上,以及在行為規則、公共知識體系與價值認同上存在缺失,使得他們至今無法形成真正相對一致的利益行動以及對群體身份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從這個意義上來分析,該群體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和功能都存在著眾多不確定性,因而并不能簡單地用西方白領理論來推論他們的階級歸屬。[35]李春玲也承認,當代中國白領雖然在總體上承認國家權威,希望政治秩序的穩定,但其中的很多人又對現實政治環境和自身市場處境表達出強烈的不滿。[36]張宛麗在對比歷年中國中產階級的規模后則指出,近年來中國中產階級內部的幾類人群在社會地位上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向下流動。[37]
雖然上述研究并沒有在這些現象的基礎上提出進一步的理論命題,但其發現仍然令人深思。為什么被人們普遍視作市場化進程受益者的白領反而并不認同自己的中產階級身份呢?他們的市場地位與社會政治權利遭到了哪些力量的制約甚至侵犯?筆者認為,要想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超越當前以生活方式或消費方式為主要考察對象的社會分層視角,轉而從生產過程及勞資關系的角度來探索白領作為雇員同國家、資本形成的結構性關系。
以國家為中心的分析視角,可以揭示國家行為對工人社會地位及意識傾向的重要影響,這一分析范式對當代中國白領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當代中國白領研究要想繼續向前推進,就必須在現有的基礎上實現兩個轉變:首先在理論范式上,從以往著眼于討論該人群宏觀社會特征的社會分層范式轉向側重于關注勞動過程的生產政治理論范式。既有研究大多將中國白領的身份限定在社會生活領域或消費領域,卻沒有意識到他們作為雇傭勞動者同樣要面對資本的宰制;其次在研究策略上,不宜再將白領的社會地位及市場處境視為個人能力的簡單對應物,而應當深入考察國家在高科技產業中所推行的發展戰略及勞動體制,進而在國家、資本與白領勞工三者力量對比的結構性分析框架中建立一種對應于產業工人的中國白領勞工政治學。
注釋:
①②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郭大力、王亞南譯,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第299-300頁;第665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2頁。
④ Randy Hodson,"Working in ‘High-Tech’:Research Issu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dustrial Sociologist",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Vol.26,No.3,1985,pp.351-364.
⑤⑥⑦哈里·布雷弗曼:《勞動與壟斷資本:二十世紀中勞動的退化》,方生等譯,張伯健校,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371頁;第372-373頁;第363頁。
⑧R.Crompton and G.Jones,White Collar Proletariat:deskilling and gender in clerical work,London:Macmillan,1984.
⑨Barbara Garson,The Electronic Sweatshop:How Computers are Transforming the Office of the Future into the Factory of the Past,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8.
⑩?理查·塞尼特:《職場啟示錄:走出新資本主義的迷惘》,黃維玲譯,時報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60頁;第169頁。
?埃里克·歐林·賴特:《階級》,劉磊、呂梁山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4-58頁。
??Erik Olin Wright and Joachim Singelmann,"Proletarianization in the Changing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8,1982,pp.182-183;pp.198-202.
?C.萊特·米爾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周曉虹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35頁。
?Steven P.Vallas,"White-Collar Proletarian?The Structure of Clerical Work and Levels of Class Consciousness",The Sociology Quarterly,Vol.28,No.4,1987,p.535.
?David.Lockwood,The Blackcoated Work:A Study in Class Consciousnes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轉引自李強:《社會分層十講》,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23-128頁。
?Duncan Gallie,"New Technology and the Class Structure:the Blur-collar/White-collar Divide Revisited",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7,No.3(Sep.1996),p.471.
??Magali Sarfatti Larson,"Proletarianization and Educated Labor",Theory and Society,Vol.9,1980,pp.139-140;p.170.
[21]Charles Derber,"Managing Professionals:Ideological Proletarianization and Post-Industrial Labor",Theory and Society,Vol.12,No.3(May,1983),p.335.
[22]Michael Burawoy,"Between the Labor Process and the State:The Changing Face of Factory Regimes under Advanced Capitalis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48,No.5.(Oct.,1983),p.589.
[23]Michael Burawoy,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London:Verso,1985,pp.123-128.
[24][25][26]Steven C.McKay,Satanic Mills or Silicon Islands?:The Politics of High-Tech Production in the Philippine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p.216;pp.218-219;p.16.
[27][28]項飆:《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的技術勞工》,王迪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60頁;第14頁。
[29]安德魯·羅斯:《當產業都外移中國之后》,高仁君、奚修君譯,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5頁。
[30]夏建中、姚志杰:《白領群體生活方式的一項實證研究》,《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1期,第144頁。
[31]李路路、李升:《“殊途同歸”:當代中國城鎮中產階級的類型化分析》,《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7期,第15-37頁。
[32]李培林、張翼:《中國中產階級的規模、認同和社會態度》,《社會》2008年第2期,第1-19頁。
[33][35]李友梅:《社會結構中的“白領”及其社會功能——以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上海為例》,《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6期,第105頁;第107頁。
[34][36]李春玲:《中國中產階級的增長及其現狀》,載于李春玲主編:《比較視野下的中產階級形成:過程、影響以及社會經濟后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45頁;第134頁。
[37]張宛麗:《對現階段中國中堅階層的初步研究》,《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第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