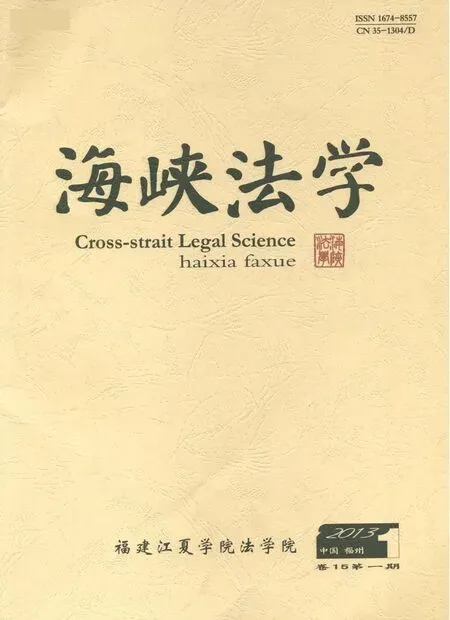我國遺囑見證制度之重構
引言
一份遺囑的制作,除了立遺囑人外,根據遺囑形式的不同,還有遺囑的參與人,這些參與人又可細分為遺囑制作人(書寫人)、見證人和在場人。因為有效遺囑須具備相應的要件,而且遺囑又只能在立遺囑人死亡后方生效,為此,大陸法系國家一般通過規定見證人的欠格要件來排除不適格的見證人,通過確立合格見證人的方式確認死后生效的遺囑為立遺囑人的真實意思表示,達到保障死者終意得以實現的遺囑原則。我國《繼承法》第18條明文規定了遺囑見證的欠格者范圍為“(一)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二)繼承人、受遺贈人;(三)與繼承人、受遺贈人有利害關系的人”。1985年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繼承法司法解釋》)第36條將第3項解釋為“繼承人、受遺贈人的債權人、債務人、共同經營的合伙人,也應當視為與繼承人、受遺贈人有利害關系,不能作為遺囑的見證人”,這些規定將利害關系人的范圍界定的較為寬泛,不利于真正保障遺囑人終意的實現。筆者擬從比較法的角度,考察遺囑見證欠格者范圍之立法和判例的界定以及見證程序要件的規定,進而探討我國《繼承法》有關遺囑見證制度重構問題,以期為《繼承法》之完善盡綿薄之力。
一、我國遺囑見證制度存在的問題
在近現代各國民法中,遺囑見證人是證明遺囑真實性的第三人,因其親自參與遺囑的制作,其證明作用直接關系遺囑的效力。遺囑見證人不僅需要客觀、公正,還需要完成見證任務。我國學者將遺囑見證人的任務概括為:(1)證明遺囑人立遺囑時的心神狀況;(2)證明立遺囑時的情況,主要為立遺囑人是否自愿、有無不當影響。在特別遺囑情況下還須證明立遺囑人所處的非常情況;(3)記錄遺囑內容。[1]259明確遺囑見證人的任務,對明確遺囑見證人的資格、程序等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上述不同因素影響著立法對不同形式下的見證人范圍的界定。對比上述理論和大陸法系以及英國有關遺囑見證的規定,可以發現我國的遺囑見證制度存在以下問題。
(一)第17條存在的問題:遺囑見證人人數不能滿足證明力之要求
我國《繼承法》第17條規定的五種形式的遺囑,除自書遺囑以外,其他形式遺囑的制作都有參與人:公證遺囑要求辦理時原則上為2名公證員,特殊情況下1名公證員時,另1名可由見證人代替。顯然,公證遺囑原則上是不需見證人的。①代書遺囑需2名以上的見證人,但代書人可為見證人;錄音遺囑和口頭遺囑都只規定有2個以上見證人,錄音和記錄均可由見證人實施。
從比較法角度看,《德國民法》將遺囑分為普通形式和特殊形式。普通形式的遺囑有公證遺囑和自書遺囑(《德國民法》第2231條),在辦理遺囑公證時,“應當事人的要求,公證人在公證時必須請二位證人或一位第二公證人在場,此情況應在筆錄中注明。證人或第二公證人應在筆錄上簽名”(德國《聯邦證書法》第29條)。顯然,公證遺囑中的見證人不是強制性的,但申請人為無閱讀能力的聾啞人、無書寫能力者時,必須“請一位證人或者第二公證人在場”(德國《聯邦證書法》第24條第3款、第25條);②特殊形式的緊急遺囑的訂立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在市鎮長或代理其行使職責的人面前(《德國民法》第2249條),二是在3個證人面前(《德國民法》第2250、2251條)。《德國民法》第2249條明文規定了該市鎮長行的是公證人之職責,并明文規定市鎮長必須為做成證書邀請2名見證人。③《日本民法》也將遺囑分為普通方式和特別方式,和德國法律規定相比,普通方式的遺囑除了公證遺囑和自書遺囑外,還有密封遺囑。公證遺囑和密封遺囑都需公證員和2名見證人,日本不承認代書遺囑,但密封遺囑可以代書;特別方式有危急時遺囑和隔絕地遺囑兩種,其中危急時遺囑包括死亡危急時遺囑和海難時遺囑兩種,隔絕地遺囑又包括傳染病隔離時遺囑和在船時遺囑。危急時遺囑由其中1名證人記錄,但死亡危急時遺囑需有3名見證人(《日本民法》第976條),而海難時遺囑可以是口頭的,需2名見證人,由見證人記錄(《日本民法》第979條)。隔絕地遺囑中傳染病隔離時只需1名見證人,但需警察1名(《日本民法》第977條);在船時遺囑除需2名見證人,還需船長或者事務員1名(《日本民法》第978條)。④日本法繼受了法國法,因此,日本法有關遺囑形式的規定和法國法基本相同,但法國對公證遺囑中的見證人數的要求沒有日本嚴格,可由2名公證員作成,也可由1名公證員和2名見證人協助作成(《法國民法典》第971條)。⑤英國的遺囑繼承要求遺囑必須是書面的且需至少3名證人證明。[2]27
可見,各國對普通遺囑中的見證人人數要求都在2名以上,德國、法國的公證遺囑除外。而在特殊遺囑中,日本學者認為,隔絕地遺囑中規定的“警察”、“船長或者事務員”并不僅僅是目擊遺囑訂立之在場人,而是代行公證員職務之人。[3]700而我國《繼承法》中的代書遺囑的代書人可以兼任見證人,這實際導致對代書遺囑的見證只有1人。我國臺灣地區承認代書遺囑,但要求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臺灣地區民法”第1194條)。筆者認為,在遺囑制作過程中,不同的身份在遺囑訂立中擔負著不同的任務,起著不同的作用,見證人的重要職責在于證明立遺囑和參與立遺囑的過程,如代書、記錄之人兼任見證人,則難以滿足證據規則所要求的2名以上的證人人數,其證明力顯然是欠缺的。
(二)第18條存在的問題:對遺囑見證欠格者范圍的確定不嚴謹
1.第1項存在的問題:對遺囑見證人能力要求不完善
遺囑見證人的資格,也即遺囑見證人的能力,是法律規定遺囑見證人為遺囑見證時應具備的資格。我國《繼承法》第18條第1項對遺囑見證人的能力欠格者范圍規定為無行為能力人和限制行為能力人,即,適格的遺囑見證人須為有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德國《聯邦證書法》第26條第2款第2、3項規定,“未成年人”、“精神病患者或癡呆者”不得為公證時的證人。法國規定在場的見證人須“懂法語并且已成年”,會簽字并且享有民事權利(《法國民法典》第980條)。《日本民法》第974條第1項也規定未成年人為欠格遺囑見證人。⑥因此,要完成遺囑見證任務,見證人須為完全行為能力人是毋庸置疑的。
但并非完全行為能力人就都能完成見證任務,對見證人生理、文化能力等是否還應該有所限制?我國《繼承法》對此沒有規定,但有學者主張,盲人、文盲不宜擔任遺囑代書人或見證人。具有閱讀和書寫能力的聾啞人一般可充當書面遺囑的見證人,但一般不為代書人;聾啞人均不得為口頭遺囑、錄音遺囑的見證人。[4]355德國《聯邦證書法》規定,“無聽、說或看的能力者”、“無書寫能力者”不得為見證人(第26條第2款第4、5項),不懂德語之人亦不得為見證人(第26條第2款第6項)。《日本民法》對此均無明確限制,但日本最高裁在昭和55年(1980年)12月4日的立遺囑盲人侄子能否成為公證遺囑中的見證人的判例中認為,見證人在公證遺囑中的作用是“見證立遺囑人系本人;確認立遺囑人是處于正常的精神狀態;基于自己的意思表示向公證員口述遺囑內容;證明公證員依法忠實記錄并宣讀給立遺囑人聽,從而確保立遺囑人的真意,防止日后為遺囑產生糾紛”,因此對照立遺囑人的口述和公證員宣讀的內容,確認兩者之間是否有出入,不是通過“看”來對比筆錄的正確與否的,故該盲人侄子并非不能履行見證人的職責,盲人非民法第974條規定的證人欠格者,為此維持了二審認定公證遺囑有效的判決。⑦但從本案也可以看出,如果見證需要閱讀能力,則盲人以及不識字之人,包括不通曉立遺囑人所用語言之人確實無法完成見證任務。同樣,耳聾之人也因其無法聽到立遺囑人之口述,故不能成為代書遺囑、口頭遺囑中的見證人。另一不可忽視的因素是日本不承認代書遺囑,上述案例的背景是公證遺囑。英國的判例否認盲人為遺囑見證人。[2]4法國的判例否認癡呆、盲人、聾啞人為遺囑見證人。[4]357,360
2.第2項存在的問題:受益人范圍包含了非受益人
見證制度的公正性、客觀性還要求見證人與見證事項沒有關聯性。法律為保障遺囑的真實性、客觀性,都對遺囑見證人的資格予以限制。因此,各國確立遺囑見證人的資格,多遵循遺囑見證人應具有民事行為能力并且與繼承人、受贈人沒有利害關系這兩大原則。[5]977利害關系通常是指與遺囑的指定有著某種利益關聯。考察我國《繼承法》第18條第2、3項可見,前者的范圍是遺囑受益人,后者的范圍是利害關系人。
我國《繼承法》第18條第2項明確將繼承人、受遺贈人規定為欠格見證人,因繼承人和受遺贈人為繼承中的受益人,其在場見證會對立遺囑人的意思表示有著重大的影響,無法保證遺囑的意思表示為真實的。我國《繼承法》中規定的“繼承人”系法定繼承人,但并非法定繼承人一定是遺囑之受益人,比如第二順序繼承人。生活中,被繼承人將遺產給自己的孩子或配偶,多請自己的兄弟姐妹作為見證人,實務中有的法院會將此情形認定為無效;⑧但也有法院認定為有效。⑨中國自古就有舅舅為大的習俗,繼承人因父母去世發生繼承糾紛時,也多請舅舅、叔伯出面調解,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為尊,了解情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對其之信任。但被繼承人的兄弟姐妹為我國《繼承法》規定的法定繼承人,屬于第18條第2項規定的欠格見證人,而從受益人的角度分析考察卻可見,在遺囑人將遺產給自己的子女和配偶時,被繼承人的兄弟姐妹是無法直接受益的,只有將遺產給父母時,被繼承人的兄弟姐妹在法定繼承的情況下才可以受益,并且不是必然的間接受益人,這樣的間接受益人是利害關系人。
從比較法的角度考察可見,《英國遺囑法》在第15條規定,受益人及其配偶不得為證人。[6]280德國《聯邦證書法》對涉及遺囑利益的見證欠格者范圍規定為將從意思表示公證書中獲取合法利益的遺囑或繼承契約中的遺產繼承人或指定的遺囑執行人(第27條、第26條第1款第2項),即對繼承人是有限定條件的,要求其有遺囑利益。《法國民法》規定為遺囑的受贈人(《法國民法》第975條),《日本民法》對見證欠格者范圍明確規定為“推定繼承人和受遺贈人”(《日本民法》第974條第2項)。所謂推定繼承人是指如果現在發生繼承,則立刻成為繼承人之人,也即在法定繼承人中最優先順位之人。有先順位繼承人時,后順位繼承人以及喪失繼承權或者被繼承人申請廢除繼承權者,不是推定繼承人。[7]650因日本法規定被繼承人的配偶為常態繼承人,則被繼承人的配偶肯定為推定繼承人。⑩顯然,上述國家立法規定的欠格見證人的共同標準都是遺囑的受益人。
3.第3項存在的問題:司法解釋中的遺囑利害關系人并無利害關系
《繼承法》第18條第3項將“與繼承人、受遺贈人有利害關系的人”規定為欠格見證人,其具體包含哪些人較為不明;《繼承法司法解釋》第36條則將第3項解釋為“繼承人、受遺贈人的債權人、債務人,共同經營的合伙人,”,認為上述人員“視為與繼承人、受遺贈人有利害關系,不能作為遺囑的見證人”。如學者所言,“《說文解字》:‘擬,度也’,有比照、模擬、設計的意思;‘制,裁也,從道從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斷,一曰止也。’‘擬’、‘制’合在一起,便有決斷性虛構的意思”。[8]139既是虛構,乃法律的假定,是為了實現法律背后的制度目的而作出的一種不容辯駁的決斷性的虛構。換言之,上述人員事實上無利害關系,但法律擬制其有利害關系。上述人員見證的遺囑繼承,是導致這些利害關系人獲利抑或受損,繼承可以導致債務得以清償或免除,合伙業務得以擴大或縮小嗎?答案顯然是否定,誠如《英國遺囑法》第16條所規定,不動產遺產抵押的債權人及其配偶可以作為遺囑的見證人。[9]310可見,我國《繼承法司法解釋》對此的解釋采擬制構造顯然是不嚴謹的,將無利害關系人確定為利害關系人。筆者尚未發現實務中有上述人員作為見證人的案例,但有繼承人的好友作為見證人被確認與其具有明顯利害關系,不符合見證人主體資格條件的案例。?筆者認為,利害關系人的范圍是否包含好友、好友的認定標準是什么,都是難以掌握的。如前所述,除自書遺囑,其他遺囑的制作都須有遺囑參與人的參與,則立遺囑人和遺囑參與人的關系,理論上應該是立遺囑人選任代書人及見證人等遺囑參與人,但實踐中,也常有遺囑受益之人,如遺囑指定的繼承人或受贈人挑選遺囑見證人和代書人。
日本法對利害關系人則明確規定為推定繼承人、受遺贈人的配偶和直系血親,法國法規定受贈人,包括第四親等在內的血親或姻親不得為見證人(第975條)、夫妻不得為同一遺囑的見證人(第980條)。顯然,都是和遺囑受益人有婚姻或血緣關系才可能成為間接受益之人的。筆者認為,修法時,一方面可借鑒我國臺灣地區的立法,規定遺囑見證人由被繼承人指定,從而保證立遺囑人意思表示之自愿、真實;另一方面,明確見證利害關系人之范圍。是故,上述國家的立法規定都對我國的修法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三)程序存在的問題:對遺囑見證程序無明確、具體的規定
1.未明確見證人之見證環節
遺囑見證人不同于訴訟中的證人,其主要區別在于遺囑見證人具有可選擇性,見證人證明的內容不僅包括實體性事實還包括程序性事實。我國《繼承法》中僅有遺囑方式的規定,并無對見證程序的具體規定,司法實踐對于見證過程的要求一般為全程見證。代書遺囑的重要環節在于見證立遺囑人的口述,見證立遺囑人予以確認并簽名,最后由見證人當場簽字。對于缺少上述見證環節的案件,法院多認定為無效。?
《日本民法》不承認代書遺囑,但對公證遺囑(《日本民法》第969條)和密封遺囑(《日本民法》第970條)則詳細規定了程序順序,要求見證人見證所有程序。?日本司法實踐對于公證遺囑中見證人程序要件的審查經歷了由嚴格到緩和的過程。首先在日本最高裁昭和52年(1977年)6月14日的判例中,1名見證人因遲到未聽到立遺囑人口述過程,僅聽到公證員讀筆錄、遺囑人點頭,該公證遺囑被認定無效。?此后,日本的下級法院對于公證遺囑制作過程中口述、記錄階段只有1名見證人或無見證人的案件多認定公證遺囑無效。?但日本最高裁在平成10年(1998年)3月13日的判決中維持了一、二審判決判定一個見證過程有瑕疵的公證遺囑有效的判決。該案中的2名見證人都見證了立遺囑的全過程,瑕疵在于立遺囑人最后蓋章時有1名見證人因故不在場,公證員隨后告知了在會見室的該見證人有關蓋章的事宜。日本最高裁認定該遺囑有效,理由是鑒于立遺囑人“并沒有推翻蓋章前的想法,再者,本案的遺囑公證沒有違反遺囑人的意思”,是故無理由否認上述公證遺囑的效力。日本學者落合福司指出,緩和見證人要件的背景在于公證實務的做法,因公證遺囑的制作需要事先的準備,交付公證書當日則會簡化手續,使得見證人的見證流于形式。[10]213對于見證程序順序的緩和還體現在另一死亡危急時遺囑的判例中。本案危急遺囑的制作過程沒有遵守《日本民法》第976條第1款規定的程序,沒有當場制作而是事先根據立遺囑人的意思擬定好后讓其確認的。一審法院為此認定無效,但二審法院認為,盡管如此,不能僅僅因為形式的欠缺就否定該遺囑的有效性,由本案查明的事實可以認定,本案危急遺囑的內容確系立遺囑人真實意思的表示。
從日本判例的變化可見,以制定法的形式詳細規定遺囑的制作順序,恰恰導致與實踐之背離,得不到司法實務的認可。《英國遺囑法》明確要求遺囑人簽字時,2名以上的見證人必須同時在場見證,但見證人的簽字不需要相互見證。[9]309為此,我國在修法時,應規定2個遺囑見證人同時見證遺囑人的口述、確認、并當場簽字這一程序為重要的、不可缺的環節,而不宜如日本法那般規定地太細。
2.沒有對遺囑欠格見證者在場的回避規定
我國《繼承法》僅對見證人人數有規定,但如果達到最低2名見證人后,另有欠格證人在場時對遺囑效力是否有影響,則無明確規定。我國有學者認為,“如果參加遺囑的見證人在三人以上,除去不具有見證資格的人以外還有兩個合格的見證人的話,則無論該遺囑是否有其他不合格的見證人參加,也應當認為有效”。[4]353日本對此亦無立法規定,日本最高裁在平成13年(2001年)3月27日的判例中認為,“由于受遺贈人長女的在場不能左右本案遺囑的內容,沒有妨礙遺囑人基于真實的意思立遺囑”,故該公證遺囑有效。該案還有兩名合格見證人在場。但學說認為,在本案立遺囑時有3名證人在場,其中1名為欠格證人,則遺囑當為無效。[11]78筆者認為應該區別欠格見證人在場的遺囑的效力,與遺囑有利害關系的欠格見證人應當回避,因為這樣的欠格證人的在場對立遺囑人真實地表示自己的意思還是有影響的;而無法勝任見證職責的欠格見證人,如無行為能力人等的在場,對立遺囑人真實意思的表示沒有影響,則其在場不影響遺囑的效力。
二、我國遺囑見證制度之重構
結合上述存在的問題,建議從以下方面重構我國的遺囑見證制度。
(一)完善繼承法第17條規定,增加遺囑見證人之人數
如上所述,在我國,代書人和見證人同為一人時,對代書行為的見證只有一人,不符合見證的一般要件,故建議增加1名見證人。同理,口頭遺囑和錄音遺囑都應予以增加,以防止錄音人和記錄人同為見證人。故修法時,在完善遺囑形式規定的同時應將我國《繼承法》第17條中規定的見證人人數由2人提高至3人。
(二)完善繼承法第18條規定,明確見證欠格者范圍
首先,將現行《繼承法》第18條第1項的“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擴大至“需要閱讀時的盲人及需要聽說時的聾啞人以及文盲”。
其次,如上所述,現行法律將見證人范圍擴大到所有繼承人則范圍太廣,若今后《繼承法》的修改再增加第三順序繼承人,則欠格見證人范圍更廣,可能導致我國一些農村地區的相互有親屬關系的村莊中有資格做見證的人變少。為此,筆者認為,可將現行《繼承法》第18條第2項中的“繼承人”變更為“遺囑指定的法定繼承人”。如果遺囑未指定法定繼承人為見證人,不論第一順序還是第二順序,意味著該遺囑是對其不利的,但其還愿意做見證人見證對自己不利的遺囑,則該證明的可信性是毋庸置疑的,故當允許遺囑未指定的法定繼承人為見證人;若其事先不愿或在立遺囑人去世后反悔,前者情形是該人的權利,后者情形則為立遺囑人選任見證人之風險,并且可能發生在任何見證人的身上,不能成為立法或修法時之禁止其作證的理由。而之所以不建議采用日本法規定的“推定繼承人”一詞,概因使用“推定繼承人”一詞,意味著 “繼承開始前推定繼承人法律上之地位,為將來繼承開始時得為繼承之希望的地位”,[12]92乃系與繼承期待權相應的專業用語,為理論上對繼承權含義之解釋,不為普通百姓所能理解。
最后,將第18條第3項的利害關系人明確為遺囑指定的繼承人、受遺贈人的配偶及直系血親。以現行《繼承法》為例,如果立遺囑人指定其父母為遺囑繼承人,即逆繼承,則法定第二順序的繼承人,即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兄弟姐妹均系遺囑指定的繼承人的直系血親,乃利害關系人,故不得為見證人;但如果立遺囑人指定其子女、配偶為遺囑繼承人,即順繼承,則法定第二順序中的兄弟姐妹既非遺囑指定繼承人的配偶,亦非直系血親,故為無利害關系之人,完全可以做見證人,這也符合了我國的民間習俗。特別是,生活中遺囑的順繼承遠遠多于逆繼承。
綜上,將現行《繼承法》第18條修改為:“(一)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需要閱讀時的盲人及需要聽說時的聾啞人以及文盲;(二)遺囑指定的繼承人、受遺贈人、(三)遺囑指定的繼承人、受遺贈人的配偶及直系血親”。
(三)增加有關見證程序的規定
鑒于上述有關見證程序的論述探討,建議在第18條增加2款規定,第2款為“訂立遺囑時,前款第二、第三項欠格見證人在場的遺囑無效”。第3款為:“遺囑見證人由立遺囑人指定,須同時見證立遺囑人的口述、確認、簽字過程,見證人亦須當場簽字。”
三、結束語
遺囑見證,涉及到遺囑的真實性、有效性,至關重要,因此,合理、嚴謹地制定欠格見證人的范圍,方能保障立遺囑人終意的實現;另一方面,由于是繼承法涉及千家萬戶、每一個人,比起抽象模糊地使用專業術語“利害關系人”,法律更應該明確規定利害關系人的范圍,以便于立遺囑人注意避免選任欠格見證人,合法制定遺囑,安心處分自己的財產。
注釋:
① 2000年7月1日施行的《公證遺囑細則》第6條規定“遺囑公證應當由兩名公證人員共同辦理,由其中一名公證員在公證書上署名。因特殊情況由一名公證員辦理時,應當有一名見證人在場,見證人應當在遺囑和筆錄上簽名。見證人、遺囑代書人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十八條的規定”。
② 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證書法》,資料出自于于司法部律師公證工作指導司編:《中外公證法律制度資料匯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03-704頁。
③ 參見《德國民法典》,資料出自于陳衛佐譯注:《德國民法典(3版)》,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608-611頁。
④ 有關日本遺囑形式要件的規定,詳細參見拙文:《論我國遺囑形式要件的認定及完善---中日比較法的視野》,載于《北方法學》,2012(5):87-95。
⑤ 本文中有關德國民法典的內容,參見羅結珍譯:《法國民法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72頁。
⑥日本民法第3條規定的成年年齡為20歲,但未成年人結婚后則視為成年(第753條),而日本法規定的最低婚齡為男18歲、女16歲(第731條)。近年,修改成年年齡為18歲的呼聲較高。
⑦ 參見[日]民事判例集.34(7):835。
⑧ 參見:遺囑糾紛,娘舅作證無效[EB/OL].[2012-7-11]http://news.cnool.net。
⑨ 參見:王玉峰等與曲秀英遺囑繼承糾紛上訴案,山東省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2011)青民五終字第233號民事判決書.[EB/OL],[2012-7-11]北大法寶。該案的四個見證人系被繼承人的姐妹,遺囑將財產給再婚的妻子。
⑩ 日本的繼承人順序,第一為子女(日本民法第887條);第二為父母;第三為兄弟姐妹(《日本民法》第889條);配偶是常態繼承人(《日本民法》第890條),即有第一順序繼承人時,配偶為第一順序,繼承份額均等;無第一順序、有第二順序繼承人時,配偶為第二順序,但繼承份額為三分之二;無第二順序、有第三順序繼承人時,配偶為第三順序,但繼承份額為四分之三。
[1]張玉敏.繼承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英]Andrew.Iwobi.Essential Succession(2.影印版)[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3][日]加藤永一.言作成程と人/立會人の役割[J].法學(東北大學法學會),50(5).
[4]劉春茂.中國民法學·財產繼承[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
[5]佟柔.中華法學大辭典(民法學卷)[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5.
[6]陳碰有.英國遺囑繼承制度研究[J].廈門大學法律評論,2001(2).
[7][日]金子宏,等.法律學小辭典(3版)[M].東京:有斐閣,2000.
[8]盧鵬.法律擬制正名[J].比較法研究,2005(1).
[9]陳葦.外國繼承法比較與中國民法典繼承編制定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10][日]落合福司.公言が人立會いに瑕疵があってもではないとした事例[J].新大學要5,2000年.
[11][日]本 美智子.要 言判例100[M].日本:學 房,2010.
[12]史尚寬.繼承法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