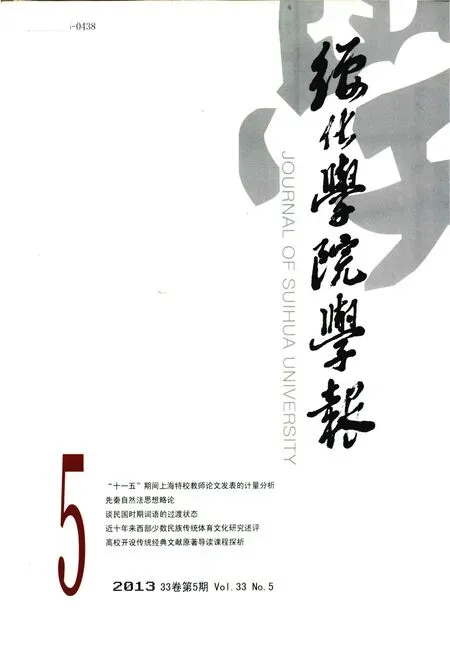尋夢于神性世界:論沈從文的生命哲學與理性文學思想
李修元
(銅陵職業技術學院 安徽銅陵 244000)
沈從文是現代文學史上獨具一格的“這一個”,又是一個尋夢于神性世界的理性存在。沈從文從荒蠻、偏僻的湘西走進了都市,卻始終沒有真正進入都市文化圈。因此,他便立足于湘西世界,用一種“鄉下人”的眼光審視著都市世界。從藝術創作的角度來看,沈從文天生就是一個贊美人性、詠唱抒情牧歌的詩人,以詩意來展示湘西神奇優美的民俗風情畫卷而在文壇上奠定了不朽的地位。“沈從文湘西題材的文學創作本身具有比較鮮明的原始主義傾向,沈從文夢回湘西,營造了一個審美烏托邦世界,把湘西文化作為中華民族復興的文化資源之一,這是沈從文的藝術審美思想在現代文學史上獨樹一幟的關鍵”。[1]可以說,沈從文在尋夢于神性世界的心靈深處隱含著一種獨特的生命哲學,體現為一種自我的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理性人格。這或許是進一步深入探討作家思想的復雜性與矛盾性的一把鑰匙,同時,研究沈從文生命哲學的理性文學思想對當代文學的發展方向也極富啟示意義。
一、生命哲學:人性與神性
沈從文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明確提出“美在生命”這一人生命題。他在《水云》中說過:“我是個對一切無信仰的人,卻只信仰‘生命’。”由作家的“生命信仰”再延伸到他對人性的理性思考。在沈從文看來,人生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必須自我超脫的“生活形式”,即人的生存及生理需求;另一種是人生的精神境界即“生命形式”,它不僅表現著自然人的“本性”,還蘊含著不同于現實世界的充滿愛與美的生命形式的“神性”即人生理想。在沈從文看來,神性與人性的自然融合,是人生追求之最高理想標準,特別是在文學藝術創造上更應完美體現。因此,沈從文在繁華的都市世界中尋夢于自己曾經生活過的故鄉——湘西世界,以犀利的秉性反抗并批判國人對現代物質主義傾向的同時,追尋超越世俗的人生價值。沈從文從自己熟悉的鄉村文化記憶中,從那些尚保持原始經濟生活方式的人情美、人性美里,構筑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沈從文以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在文學上創造了理想的生命哲學,以愛和美喚起國民“人性”中的“神性”。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便是一個典型的令人神往的“神性”世界,是用“愛”和“美”構筑的一個世外桃源。因此可以看出,沈從文崇尚的生命哲學是尋夢于以人性為內涵的神性世界。
二、文學追求:批判與重造
民族靈魂的重鑄和深掘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命題,動蕩的時代和現代人性墮落的現實促使沈從文極力尋求“民族品德重造”的途徑,他對文學追求的強大動力正是源于對民族品德消失的清醒認識以及對民族和人類命運的深深憂患。他執著于文學創造來張揚理想的生命形態,以實現文化的變革與民族人格的重構,他傾注于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捕捉與思考,體現出極其敏銳的洞察力,由此可見,沈從文的文學追求賦寓深沉的現代性品格。實際上,沈從文倡導的民眾和民族的文化改造,在本質上不同于20世紀30年代主流文學提出的社會革命,但在“人性的解放”,“精神重造”及改造“國民靈魂”的基本主題上又與“五四”啟蒙思潮是一脈相承的。當然因受現代性與局限性的雙重影響,使他的文化思想難免帶有理想化色彩,也因此而形成了風格獨特而內蘊豐富的“沈從文現象”,彰顯了作家的創作理想和藝術品位。
沈從文筆下的城鄉呈現著鮮明的二元對立模式,道德與審美視角,烏托邦式的理想,民族重造的希望,病態人性的批判及現實生存的困境等,構成了二元框架里五彩繽紛的內容。以沈從文為代表的京派文學明顯呈現著兩極形態:鄉村的美麗、靜穆與城市的墮落、混沌。這也是他們在多重文化沖突中作出的文化選擇。正如凌宇所說:“沈從文是從社會文明的進步與道德的退步,即歷史主義與倫理主義二律背反的角度透視都市病態的。這類作品主要有《蕭蕭》、《柏子》等。汪曾祺說過:“《邊城》是一個懷舊的作品,一種帶著痛惜情緒的懷舊”。當然,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對過去純真美好童年的迷戀,是與現實中丑惡虛偽作對比。所以有論者說:“它有文化批判的傾向,是用‘夢’與‘真’構成的文學圖景,同文本外的現實丑陋的相比照,讓人們從這樣的圖景中去認識‘這個民族過去偉大處與目前的墮落處”,[3]沈從文企圖以生命的強力來滋養文明侵蝕下的人性的枯萎,抗拒人性的扭曲和病態,當然也不乏對鄉下人現代生存方式和不健全人性的反思。沈從文希望回復“童心”,以重新煥發中華民族的青春活力。
三、創作風格:詩化與神蘊
沈從文創作的小說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以湘西生活為題材的,一類是以都市生活為題材的。而其在文學上的主要貢獻是用小說和散文建構了他特異的“湘西世界”,描寫了湘西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贊頌了人性美。“在他成熟的時期,他對幾種不同文體的運用,可以說已到隨心所欲的境界,計有玲瓏剔透牧歌式的文體,里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這是沈從文最拿手的文體,而《邊城》是最完善的代表作。”[4]在《邊城》中,作者以恬靜悠遠的風格,用溫潤柔和的筆調,借詩詞曲賦的意境,描繪出了湘西邊城的美麗風光,刻畫了一群性格鮮活而又可愛的人物形象,它既是湘西邊城山村生活的牧歌,也是一曲真摯、熱烈的愛情頌歌。在《邊城》這座“希臘小廟”里,作者同時還供奉著自己的文學理想。作品打破了傳統的寫作手法,不僅創造了獨特的藝術境界,而且創造出了自己的理想文體:詩化抒情小說。作品用散文的筆調和詩歌的意境淡淡寫來,沒有激烈的矛盾沖突,沒有人與人之間的你爭我奪,只有微妙的暗示,細膩的心理刻畫,情不自禁的感情流動。現實與夢幻,人生和自然,天衣無縫的融合在一起,融合在“水”做的背景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畫”,也是“詩”。
沈從文的鄉土題材小說藝術上最大的特色,就是很詩意地講述他年輕時節經歷見識過的人和事,將生命掙扎的粗獷同生存泥涂的險惡,皆用小說形態作詩意的抒寫。在短篇小說《柏子》中,沈從文寫到湘西,寫到他記憶中的河流及水上岸邊風物,寫到他熟悉且關懷的那些在社會底層頑強掙扎的人物命運,他的筆好像具有了一種魔力,字里行間便充滿溫情的緬想和悲憫的情緒,那些山光水色,平常人事,只要輕輕點染勾勒,便發出一種美的光輝
對湘西完美人性的思考與表現,是沈從文小說在思想上的又一個顯著的特色。《蕭蕭》就是作家最富有寫實意味的作品之一。作品以小說聯結著風俗散文與愛情歌謠,自由結構使小說融入豐富的散文和詩的因素。
除了小說,沈從文的散文創作成就也很高。司馬長風說過:“沈從文的筆是彩筆,寫出來的文章像畫出來的畫。畫的是寫意畫,只幾筆就點出韻味和神髓、輕妙而空靈。……沈從文的散文,則像順流而下的船,不著一點氣力,‘舟已過萬重山’”。[5]其散文那種詩化的文體與詩意的抒情帶有牧歌的特征,他常常將湘西的人生方式,通過景物印象與人事哀樂娓娓道來,真切而富有歷史感,飽蘊作者的故鄉情思與現實思考。在《鴨窠圍的夜》中,作者從水手與妓女的纏綿相戀中進行著愛欲即為生命、生命契全自然的人性的哲理思考,這種違背傳統道德與倫理的思考,表現了沈從文獨特的、原始主義的人性理想。地域性、民族性及人性仍是沈從文散文著力表現的主要方面。
在文體結構上沈從文善于追求千變萬化,形態各異,在他的短篇小說中幾乎不找不出兩篇結構完全雷同的作品來,堪稱可貴。如《八駿圖》是橘瓣綻開式結構;《大小阮》是雙線結構;《月下小景》是連環套式結構等等。
四、獨立品格:自覺與理性
沈從文從藝術創作、文學理想及自身生活實踐對文化人政治與人格的理性自覺與自省進行了全方位的深刻反思。鑒于政治、商業文化對知識分子人格的奴役與侵蝕的社會環境,對于文化人獨立自由人格的堅守,沈從文始終保持一種本能的警惕。
首先表現的是現代的懺悔精神與理性的深沉反思。對于人格奴化的警醒,沈從文通過實踐進行了深刻的探索和思考,他認為作為一名作家應該具有獨立的個性人格和獨特的創作思想,所有藝術創作都需要有個性,都必須滲透作家的人格、感情和思想。想達到這個目的,寫作時要獨斷,要徹底地獨斷。由此可見沈從文作為一個鄉下人如何從現實學習,而終于仿佛與現實脫節的深一層意義和原因,這“深一層意義”就是沈從文現代的懺悔精神與理性的深沉反思的最好體現。
其次是高揚學術本位與理性的審美精神。他的許多朋友加入了黨派,而他自己卻從未加入何類政黨,這是他自覺意識的理性表現。沈從文認為,文學家應高于政治家,這便是他理性的批判精神的突出體現。他倡導要把文學“從商場和官場解放出來,再度成為學術一部門”,“使文學作品價值,從普通宣傳品而變為民族百年立國的經典”。[6]他主張政治與文學之間應該建立一種較為理性的關系,可見,對于作家主體的自我塑造來說,宣揚本位與理性的審美精神是很有必要的。坦誠和正直是沈從文作為中國現代文化人的獨立品格,沈從文一直反對文學被淪為金錢的娼妓,更不贊成新文學被政治看重,卻是始終如一堅持文學家的人格和藝術至上的創作觀點。身在大都市,商業宣傳與活動難免時有發生,但沈從文一貫保持警醒的頭腦,以免喪失文化人獨有的個性品格而陷入低級趣味,如若那樣,所謂的作家,也只能創作出敷衍、世俗的“白相文學”,相對于學術本位而言,那就是一種藝術墮落。他在批評左翼文藝運動時說過:“并不在文藝的政治傾向性和宣傳革命的政治觀點,而是集中在一部分作家只要‘思想’,不要藝術,空有血和淚,而無實在深入的人生描寫,以至宣傳思想而不注重藝術所導致的概念化、公式化、傾向化”。“大多數青年作家的文章,卻‘差不多’,文章的內容差不多,所表現的觀念也差不多……因為缺少獨立見識,只知道追求時髦,結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7]沈從文的審美思維具有理性精神,而其人性品格則是充滿浪漫主義色彩,惟其是理性的,他對生命哲學的追求才凸現了永恒的理想主義情懷;惟其是浪漫的,他的文學思想才蘊含著堅韌不撥的理性主義光輝。
[1]何小平.沈從文創作初期的人類學詩學創作[J].吉首大學學報(社科版),2012(1):46-50.
[2]沈從文.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沈從文文集[C].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11):45.
[3]錢理群,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79.
[4]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家史[M].臺北:傳記文學雜志社,1985:11.
[5]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中)[M].香港: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
[6]沈從文.文學運動的重造[J].文藝先鋒,1942(2).
[7]凌宇.從邊城走向世界[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