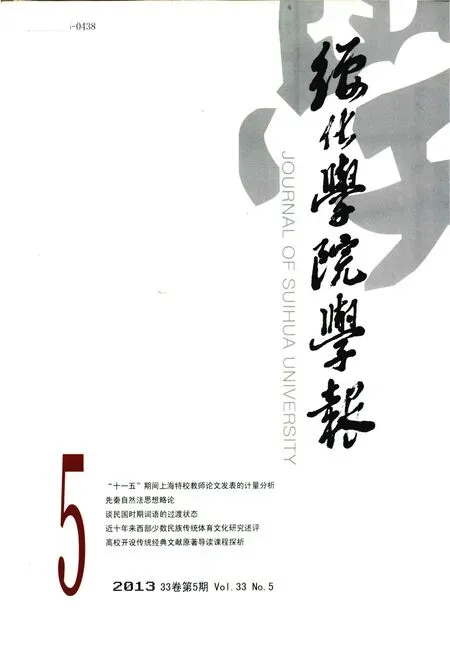論阿諾德·柏林特環境美學思想的局限
馬 草
(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 山東濟南 250014)
阿諾德·柏林特是西方環境美學的代表人物之一,與艾倫·卡爾松被譽為當代環境美學的“雙子星座”。柏林特的環境美學思想迥異與其他環境美學體系,他以環境為邏輯起點,以審美體驗為基礎,以審美參與為核心,以一元化美學為目標,建構了其獨樹一幟的環境美學體系,他自己和研究者稱之為“參與美學”或“介入美學”。柏林特提出了許多富有原創性和啟發性的觀點,對于突破傳統美學的局限,拓展美學的視野和深度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然而柏林特的環境美學思想并非完美無缺,而是存在著許多漏洞與缺陷,本文將就這些問題進行一些探討。
一、環境與環境美的混淆
自然美一直是美學中的難點,長久以來困擾著美學界。環境美學是以自然美的發現與研究為起點的,因而對這一問題十分關心。柏林特認為,在西方傳統美學界有一個傾向,那就是以藝術美來衡量和看待自然美,即“如畫”模式。“如畫”模式在欣賞自然時將其看做一幅風景畫,關注自然界符合繪畫的顏色、線條等形式方面的審美特征。在柏林特看來,傳統美學對自然之所以美的解釋是自然體現了藝術的某些特征與規律,是自然美恰好印證了藝術美。柏林特非常反對這種觀點,認為這不僅不能揭示自然美,反而是對其的遮蔽,對待自然的正確方式是將自然如其當作自然。也就是說,他認為自然之所以美就是因為它是自然,而不是其他的事物。自然有其不同于其他事物的本質特征,而自然美就是根植于這種特征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認識自然,領略自然美。
正是在對傳統美學關于自然美問題批判的基礎上,柏林特對自然與自然美進行了擴展,提出了環境與環境美,建構起了自己的環境美學體系。但在這一過程中,柏林特并沒有解決自然為何美,進而也就無法解決環境為何美的問題。他論證環境為何美時的思路很簡單,他認為:“對環境的審美,雖然始終沒有離開知覺領域,但觀者參與其中的意識會被強化與集中。有意地關注于知覺的品質是審美發生的重要標志。”“在此,感性的體驗扮演著重要角色,它不是單獨接受外來的刺激的被動者,而是一個整合的感覺中樞,同樣能接受和塑造感覺品質。感性體驗不僅是神經或心理現象,而且讓身體意識作為環境復合體的一部分作當下、直接的參與。這正是環境美學中審美的發生地。 ”[1](P16)“審美最本質的特征就是當下、集中全部注意力的感知投入”。[1](P12)柏林特認為環境之所以美是因為環境感知,當人們處于對環境的感知中時,環境也就是美的。正是在此意義上,感知成為柏林特環境美學的中心,他甚至直接宣稱:“環境感知在本質上就是審美的”。[2]即感知就是審美,或審美就是感知。在此可以明顯地看出,柏林特不僅將感知與美感混為一談,而且還將感知與審美混淆。感知作為人的意識不一定就是審美或美的,中間還有一系列的轉化程序,而柏林特卻忽視了中間過程,將二者等同了起來。
問題還在于柏林特對環境與感知二者關系的認識,他認為“環境是:一系列感官意識的混合、意蘊(包括意識到和潛意識的)、地理位置、身體在場,個人時間及持續運動。……它是當下對現存情況的集中感受和投入,包含豐富的直感和意蘊。”“環境具有整體的屬性,沒有什么表層、深層,內與外之分,它成為體驗發生的前提,同時也是體驗的內容本身。 ”[1](P33)在柏林特看來,環境就包括環境感知,感知就是環境的一部分。原來的環境→感知→環境美的思路轉換成環境→環境美。柏林特認為環境本身就已包含了環境美,二者是統一的,當我們進入環境時就已經是在感知,也就是審美。在這里柏林特把環境與環境美混淆,直接等同起來。但是二者有著本質性的區別,環境是一個實在之物,即使像柏林特所界定的那樣,它仍然只是一個實體對象;而環境美則是人類對環境的價值判斷或情感判斷,二者根本不屬于同一領域。葉朗先生對此也指出:“自然物是‘物’,而自然美則是‘意象’,這是根本性質不同的兩個東西,而這些環境美學的學者把他們混為一談了”[3](P183)。
由此可以看出,在自然美和環境美的問題上,柏林特并沒有真正解決,反而將其混淆,這就給其理論體系帶來了動搖。我們甚至可以說,柏林特雖然意識到了自然美和環境美,但沒有解決自然與環境為何美。傳統美學對自然為何美的解釋雖有片面之處,但卻將自然與自然美區分開來;柏林特卻將二者混淆,對此的解釋也是缺乏說服力的。
二、審美超越的缺失
柏林特對康德的無功利的審美靜觀說一直持批評態度,他認為這不是正確的審美方式,真正且正確的方式是審美體驗。柏林特所說的體驗并不是傳統美學只強調視、聽兩種感官,而是身體全部感官的調動與投入,全方位地感受環境,進而形成一個持續性和一體化的體驗模式,即審美參與。“它調動了所有感知器官,不光要看、聽、嗅和觸,而且用手、腳去感受它們,在呼吸中品嘗它們,甚至改變姿勢以平衡身體去適應地勢的起伏和土質的變化。”[1](P28)“環境體驗作為包含一切的感覺體系,包括類似于空間、質量、體積、時間、運動、色彩、光線、氣味、聲音、觸感、運動感、模式、秩序和意義這些要素。環境體驗不一定完全是視覺的,它是綜合的,包括了所有的感覺形式,它讓參與者產生強烈的感知。”[4](P25)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環境感知也就成為美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感知是美學的中心術語”[1](P40),“體驗是感知的并且是審美的中心特征”[1](P141)。
柏林特一方面注意到了環境所擁有的多方面的感知特征;另一方面又注意到并充分發掘了主體全方面的感知能力,并將二者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他最著名的觀點——審美參與。審美參與強調身體全部感官的投入,全方位地體驗、感知環境。這是傳統美學所忽視和缺失的,也正是柏林特最大的貢獻與成功之處。但是也隱藏著某種危機,那就是:體驗之后是什么?柏林特對體驗的闡釋是以身體為中介的,強調的是身體感官的參與。但身體的感知首先是一種生理快感,它只是審美中最基礎的一部分,并不是審美的全部,除此之外審美還有著更高的層次與追求。而對于更高審美層次和境界的追求恰恰是柏林特所忽視的,也就是說柏林特的環境美學缺乏審美提升的環節。缺乏審美提升就有可能將審美沉浸于感官的愉悅中,從而失掉美學的反思與超越品格,最終導致美學只是快感的描述,人類也因此喪失反思能力與超越能力而淪為身體的奴隸。
柏林特不是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例如“沉思和冥想在描述美學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傳達感受的過程中,描述總帶有與觀摩者自身相關的意義”[1](P27)。他在對迪斯尼公園進行分析時認為,“主題公園既是商業文化的升華物同時也是一種失去升華機制的崇高。”[4](P41)在論述環境的神圣性時,他認為“在神圣性中,既沒有脅迫也沒有恐懼而只有一種被擴展被升華的感覺,一種通過神圣性的光輝而變得珍貴的感覺。 ”[4](P134)但是出于對康德非功利審美靜觀說的批判,柏林特認為“鑒賞性的體驗仍然是審美描述的中心。”[1](P24)甚至于他對于審美提升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審美超越持懷疑與批評態度:“自然是否像藝術一樣具有超越性?……通過與自然交流達到超驗的感覺,像藝術一樣,但這樣做有可能放棄體驗中的美感,而傾向于一種神秘的超越感。不管是何種超越感,都存在一種危險,即把藝術或自然僅僅看作獲得某種狀態的工具,并且這將可能拋棄審美的內在特征和構成欣賞情境必要成分的自然或藝術的連續性。”[1](P156)由于過分珍視環境體驗的獨特性,柏林特對形而上的審美提升與審美超越持拒斥態度,這就使得他走向極端。柏林特更愿意沉浸于獨特的環境感知中,而不愿意去追尋在這之后的審美境界。我們不否認獨特的審美感知或審美快感的重要意義,但是感知的獨特性及其快感并不足以使環境美學自立自足,反而存在著取消環境美學的可能。因為只沉浸于生理性的快感,或者審美只是感官愉悅,那么美感也就成為了快感,審美也就成為身體感知。如果美學只是對身體快感的描述,那么它將與生物學或生理學無異,從而使環境美學乃至美學面臨著被取消的危險。
審美不僅僅是在物質領域獲得的感官愉悅,它還有著自己更高層次的追求,即探尋物質、現實背后更深遠的層次和境界。這就是審美超越,這才是審美得以自立、自律的根本。對于審美活動來說,超越意味著對有限性的擺脫,對無限的追求;意味著對自我的突破,是對意義的探尋,是對自由的渴望。審美超越使得人類能夠擺脫物質、現實的束縛,從而進入一個全新的領域與境界,而這正是人類在現實中無法獲得的。也只有審美超越才能真正地使審美區別于其他人類活動,從而獲得一種獨特的品格與價值。喪失掉審美超越,審美體驗只能沉淪于感性的肉欲中,審美也將最終消亡。柏林特的審美體驗對超越環節的忽視,無疑是其環境美學思想的一大缺憾。
三、一元化美學的困境
柏林特認為美學的研究領域可以分為兩類:自然與藝術,而傳統的美學是無法同時兼容二者的。柏林特的目標并非只是提出一種專門適用于自然的美學,而是試圖建構一門能夠涵蓋自然、藝術兩種形態的美學,即 “一種普遍的美學”[1](P147),艾倫·卡爾松稱之為“一元化美學”。柏林特認為“自然的美學可以作為欣賞藝術的模式”[1](P155),這是因為二者有著相同的體驗方式,而這恰好是建構一元化美學的基礎。在柏林特看來,“連續性和感知的融合在藝術體驗和自然體驗中都會發生”“兩者都能通過感知方式被體驗;兩者都能被審美地欣賞;并且更獨特的地方是,兩者都能起到與欣賞者相互交流的作用,引導參與者進入一種整體地感知情境中。 ”[1](P155)基于此,柏林特自信地認為,以審美體驗為基礎的參與美學正是能夠解決自然與藝術不能同時兼容的方案,并且宣稱“它做到了任何一種理論所應該做的——解決更多的問題而非產生更多的問題。 ”[1](P157)他所說的參與美學正是環境美學,而這就是他追求的一元化美學。
我們可以看出柏林特的論證思路:因為自然和藝術可以讓欣賞者產生相同的審美體驗,因此二者可以用一種美學理論予以解釋。但這種思路存在著一個漏洞,那就是過分關注欣賞者,而忽視自然與藝術本身的特點。眾所周知,自然與藝術有著本質性的區別,我們很難用一種標準來衡量。在存在方式上,自然作為自在之物,是宇宙萬物進化的結果;而藝術作為人類創造之物,體現的更多的是人類的自我力量。在欣賞方式上,自然有著立體的、多方面的感知特性,而藝術就未必有這樣的特色,它多是偏重于一種感官。在體驗類型上,自然審美的體驗是基于身體立體感知的,其想象空間十分有限;而藝術審美的體驗更多的是想象式的,它為人類提供了一個廣闊無垠的想象空間。在審美境界上,人們從二者中獲得的意蘊也可能完全不同。因此要想以自然審美模式來統一自然和藝術是極其困難的,很容易導致主體性的泛濫。自然審美模式必須滿足兩個特點,即審美對象的多方面感知特征和審美主體的全方位的感知能力,然而藝術本身并不具備多方面的感知特征。當用自然審美模式來欣賞藝術時,柏林特就把重點放到了審美主體身上。因此當審美對象不具備多方面的感知特征時,柏林特更多地是依賴主體的審美經驗來達到審美參與。主體的審美經驗成為達到審美參與的唯一途徑,審美主體的主動性得到了放大。那么在自然審美中也很可能會出現過度地依賴主體來達到審美參與的情況,這就會導致人們對審美參與的適用性和客觀性的動搖,并進一步產生對自然審美的合理性質疑。因此卡爾松在對參與美學進行研究時也注意到了這個情況:“究其本質而言,自然的美學欣賞是否根本上還是一種瑣碎的、主觀的臆斷”[5](P8)。 柏林特忽視了這一點,這就造成他以自然審美模式來欣賞藝術時會產生重重的矛盾。
柏林特在其環境美學體系中,是否成功做到了用審美參與來分析藝術美呢?答案是否定的。在具體分析時,柏林特更多的是用自然、建筑來做例證,而幾乎不涉及傳統的文學、繪畫等門類。即使是在分析擁有大量傳統藝術的博物館時,柏林特也僅僅是著眼于展品布置方式而產生的體驗感,而非藝術作品本身。而著眼于展品布置方式恰恰說明了柏林特不是通過客體,而是依賴主體的主觀性來達到審美參與的。聯系到柏林特是出于對傳統非功利的審美靜觀說不適用于自然審美的情況才提出審美參與模式的,那么基于自然審美而提出的審美參與模式也未必適用于藝術審美。這是因為審美參與是基于自然審美的特點而建立的,在創立之初沒有考慮到藝術審美。審美參與是全方位的身體感知,藝術則是偏重于一兩種感知,而且是精神性的。
對于藝術鑒賞來說,傳統的靜觀方式仍然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很可能是無法替代的。但這將會導致柏林特最不愿意看到結果出現:自然與藝術會各自擁有一套審美模式,建立一元化美學的目標也將不復存在。而同樣身為環境美學家的艾倫·卡爾松則與柏林特相反,他認為自然欣賞與藝術欣賞不同,可以存在兩種不同的模式,“在環境與藝術作品之間存在著一種非常重要的不可類比性。它典型地包括這樣的事實,即藝術作品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點完成的。……可是與之相比,在自然環境完成的過程中時間上根本不存在任何特定點。 ”[6](P80)“如果對藝術進行審美欣賞,我們必須具有藝術傳統和藝術風格這些相關知識,而對自然進行審美欣賞時,則必須知曉不同自然環境類型的性質、體系和構成要素這些相關知識。”[5](P34)因此,卡爾松認為藝術審美是靜觀,自然審美是參與。相對柏林特的主張,卡爾松的主張顯然更為務實,也更具有合理性。而柏林特的主張則比較激進,存在著很大的缺陷。彭鋒先生也指出:“柏林特的這個主張顯然過于魯莽,因為某些場合的藝術審美明顯是分離式的,比如在音樂廳里安靜地欣賞古典音樂或在畫廊里欣賞繪畫作品……想象一幅繪畫作品中的花香跟在大自然中聞到真正的花香是截然有別的,由此不難明白想象的介入與真正的介入是不同混為一談的。 ”[7](P213)由此可見,要想找到兼容自然與藝術同時又不喪失各自特點的美學模式,柏林特的一元化美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1]阿諾德·柏林特.張敏,周雨譯.環境美學[M].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
[2]阿諾德·柏林特.程相占譯.審美生態學與城市環境[J].學術月刊,2008(40):21—26.
[3]葉朗,美學原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4]阿諾德·柏林特.陳盼譯.生活在景觀中——走向一種環境美學[M].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
[5]艾倫·卡爾松.陳李波譯.自然與景觀[M].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
[6]阿諾德·柏林特.劉悅笛等譯.環境與藝術:環境美學的多維視角[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
[7]彭鋒.美學導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