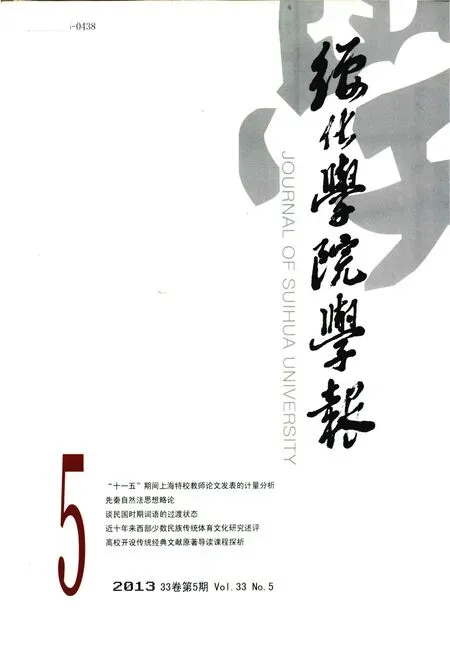“死亡”敘寫中的三種關系——《生死百年》與《活著》比較
羅興國
(寧夏大學人文學院 寧夏銀川 750021)
《生死百年》是2011年出版的閔良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活著》是1993年出版的余華在小說創作轉型期中的長篇力作。從小說創作時間上來看,雖然兩部小說大致相差十七八年的時間,但從小說的內容上來看,兩部小說卻十分相近。可以說兩部小說講的都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中關于死亡的故事。《生死百年》講閔家族人及與其有關的人在歷史莫測的長河中艱難的掙扎,終一個個地死去。《活著》講徐富貴的親人在苦澀的歷史中,在艱難的生存困境中,一個個地死去。“死亡”是貫穿兩部小說的主線、主題,也是兩部小說中人物的終極命運,死去的人已經死去,而活著的人也終將死去。當面對死亡時,由最初情感的劇烈震蕩,到最終情感的平淡、釋然。在小說中刻意去遮蔽、隱去這種情感也好,釋放、表現這種情感也好,“死亡”對人們情感的沖擊永遠是最犀利而深透的。《生死百年》與《活著》就是圍繞以下三種關系,對“死亡”進行冷靜而透徹的敘寫的。
一、人與歷史
在這兩部小說中,都寫了在中國曲折歷史中人不斷死去的命運。很顯然,在人與歷史之間,歷史對人的決定性是更大的、更有力的、更普遍的。兩部小說共同涉及到的歷史背景有土改、大躍進、三年饑荒災害、文革,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經歷著共同的歷史和不同的命運,有人生存下來,有人死去。《生死百年》中的閔少卿和《活著》中的富貴就是兩個這樣的人物。在土改的歷史浪潮中,他們的經歷有許多相似之處,兩個人曾經都是地主,都是靠剝削貧下中農過自己好日子的人,而他們又都不務正業、游手好閑、嗜賭如命。閔少卿在賭場中把家底輸個凈光,富貴也把百畝田地、家中宅子等家財都輸給了龍二,結果兩人都因輸光家產而由地主落為了貧農,而特殊的歷史卻給予了他們非常態的命運。土改中,他們因為是貧農不但得以活命,而且還受到了一定的照顧。反而是那些不肯交出錢財的、贏了錢的人一命嗚呼了。所以在兩部小說中,同樣的歷史賦予了他們同樣戲劇化的命運,而最終他們的命運卻又是不同的。在土改的浪潮中,閔少卿雖然輸了家產,順風順水地活了下來,但到了大饑荒的年代,歷史就沒有再次眷顧這個曾被認為是舉人灣最幸運的人,在自己和家人被饑餓重壓得奄奄一息的時候,他在夜晚偷偷去打漁時命喪青衣江。而他自己也并沒有為自己的生命做最后的掙扎,在岸上兩個兒子默默的注視中消逝于江霧中。歷史決定了他的饑餓,他沒有能力去反抗歷史,但他有權利反抗饑餓,即使付出生命的代價。再看《活著》中的富貴,他和閔少卿在土前土改中都有著同樣的命運,但在大饑荒時期兩個人的命運就分道而各異了。富貴也是因輸光家產,使得贏了他的錢的龍兒替他去死了,他在土改中得以活命,可以說他也是幸運的。如果說在土改中這是他的幸運,那么他在大饑荒年代得以繼續存活下去,那就是他生命的韌勁了。在一家人的共同忍受與扶持下他們度過了大饑荒年代,使生命得以繼續向前艱難延續。在他個體弱小的生命與歷史大饑荒的對抗中,他勝利了,他仍然活著。所以可以看出,如果說閔少卿和富貴輸光家產而在土改中的得以活下來是一種歷史的不經意偶然的話,那么在歷史的下一道溝壑——大饑荒當中閔少卿因饑餓而死去,富貴經歷饑餓仍然活著,這就是歷史的必然。因為在歷史對生命的嚴酷考驗下無非兩種結果,一是死亡,一是活著。歷史在冥冥中注定了一些人的命運,無論你如何掙扎你都不能逃脫,在歷史面前絕大多數人永遠是卑微的弱者,無意識的消亡者。
在人與歷史這一層面,從兩部小說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兩部小說雖然同寫歷史、同寫歷史中人的命運,但最終的落腳點卻不同,《生死百年》寫一個家族在中國百年歷史中的生生死死,而其最終的落腳點是“百年”,即百年中國歷史,而“死亡”只是構成這歷史苦澀風景的色彩之一。如作者所說:“所以,我從故鄉的小山寫起,一路尋找百年中國之足跡,述之為文,與大家分享我在這種尋找中的感動與思索,也算為這段澎湃的歷史作個小注。”而《活著》寫以富貴為中心的一家人在近半個世紀歷史風雨里的生死,其最后的落腳點是“活著”。所以在人與歷史這一層面,《生死百年》更注重的是歷史,寫死亡也是為了歷史,而《活著》更注重的是人,寫死亡時為了活著。也因此,《生死百年》中對于歷史的涵蓋,包括其所涉及的人物都要比《活著》豐富些。那么從反面來說,越是著力于歷史與人物的豐富性、涵蓋的廣泛性上,那么相對一般其深入性與穿透性就薄弱些。而其薄弱處正在《活著》中得到較為完美的彌補。即《活著》中對于歷史的苦難、對于人的苦難的超越性。“我決定寫下一篇這樣的小說,就是這篇《活著》······寫作的過程讓我明白,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我感到自己寫下了高尚的作品。”[1]人活著只為活著本身的存在,而不是為了歷史或為了苦難或是為了自己等其他事物。這是《活著》最真實的力量。
二、人與人
無論在任何歷史境況下,歷史對人的命運的決定性都是不容否定的,當然這命運中也包含著人的生死。而在大的客觀歷史下,對人的命運具有一定程度的決定性的,還有另一因素,那就是人。與歷史對人的絕對客觀影響不同,人對人的命運的影響與決定多是帶有主觀刻意性的,當然也有些是主觀無意識的。但人對人的命運的決定性無疑是存在的。這其中當然也包含著對生死的決定。尤其是在特殊歷史時期相對立的兩種人之間。在兩部小說中,在共同的死亡的命運下,人與人之間簡單而直接的關系卻體現出完全相反的結果。在《生死百年》中兩個革命小將來到舉人灣,在天龍寺中打砸燒毀“封建余孽”,而寺中的兩個和尚延均和延平在一旁平靜地為革命小將端茶倒水,沒有絲毫傷心和異樣,結果,兩位革命小將門牙黑了一半,被兩個和尚給毒死。顯然在那個歷史背景下,在這個事情中,革命小將是批判者,是強者,兩位和尚是被批判的對象,是弱者,革命小將“理應”去掃除他們眼中的“封建欲孽”,而兩位和尚“理應”檢討自己,承認過錯。但結果卻是兩個和尚在兩位革命小將不知不覺中,把他們毒死。兩位革命小將死于非命,而兩位和尚繼續生活下去。而《活著》中文革時期春生被打為走資派,被紅衛兵抓去批斗,掛牌游街,大喊毛主席萬歲,又被紅衛兵罵,“這是你喊的嗎?他娘的走資派”[2]之后被打倒在地,腦袋被踢得咚的一聲響,之后整個人趴倒在地。一個多月后春生便上吊死了。革命衛士們在斗爭中勝利了,他們的批判讓“敵人”最終一敗涂地,自殺認罪。作為被批判對象的春生則在斗爭中默然死去。春生的死在他們來看是罪有應得。紅衛兵繼續以他們狂熱的生命來不斷沖擊那些的將被打垮的生命,而春生生命的消逝只是對紅衛兵們的批斗的一個沒人在意的“正確”的回應而已。、
所以可見在兩部小說中,同樣是寫文革時期的兩種人的關系,即批判者紅衛兵與被批判者兩個和尚及春生的關系,他們的關系都是單向對立的,即紅衛兵把他們看成對立的批判的對象,而他們卻不得而知這是為什么。但這相同的關系最終的結果卻完全不同,在《生死百年》中這種人與人之間單向對立關系的最終結果是主動的批判者、相對的強者的紅衛兵的死亡。而在《活著》則是被動的被批判者,弱者的春生的死亡。所以可以看出兩部小說中的這兩種不同的結果實際是一種相互的補充。它們共同構成了一種完整的生命形態,展現了生命的兩種必然——生或死!這是這兩部小說在共同的“死亡”的主題下,所展現出人與人之間,決定與被決定的偶然與宿命。
另外,在另一個層面,如果將小說的作者與小說中的人物也視為作品中的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系的話,那么在《生死百年》與《活著》中作者與小說中人物的關系也是既有相同又有差異。在《生死百年》中作者閔良與小說中的人物的距離拉開的比較大,其關系比較疏遠。而在《活著》中余華與小說中人物的距離實際是很近的,其關系也是比較近切的。所以從直觀感覺上看兩部作品,《生死百年》中閔良寫人物的死亡與種種艱難命運,他始終是保持了客觀的、旁觀的、冷靜的創作者的身份的。而《活著》中余華寫人物的死亡與困苦命運,他表面雖然也是冷靜、客觀、旁觀,但其實際對作品中的人物投注了太多的主觀情感,其內心中對作品中的人物有著一種無法言說又難以回避、難以割舍的悲憫思緒與情感。“不論善惡,他都要保持一種理解后的超然,并由之產生一種悲憫心,這也導致了他進入90年代之后在《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中的風格轉變:這些小說在描寫底層生活的血淚時仍保持了冷靜的筆觸,但更為明顯地加入了別天憫人的因素。”[3]這就使得作品在對極端生命形態冷靜抒寫的同時呈現出了一種默默的溫情。“重視寫作的余華自然要將‘為內心寫作’當作自己最高的藝術原則,《活著》出版后,人們從活著中讀出了種種意義,余華卻只認同‘讓內心真實作主’的說法,不是毫無道理。”[4]這回答了《活著》中溫情來自哪里,即來自內心。
三、人與自身
在各種復雜的關系中,人與自身的關系應該是最近的,但也是自己最容易在無意識中忽略掉的。對人的命運、對人的生死的決定,除了歷史因素、其他人的因素之外,自身因素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人對自己的生命具有一定的決定權,這種決定就必然會包含不平衡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生,一方面是死。而不平衡則是人不一定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生,但人絕對有權利決定自己的死。當然這其中還包含了一層無意識的、偶然的因素,使得自己的生死具有了一種不可測的、冥冥注定的色彩。在《生死百年》與《活著》中都有人選擇以自殺的方式走向死亡。而這種自殺也既是可以與歷史因素有關的,也可以是與歷史因素無關的。《生死百年》中四爺爺投水自殺,《活著》中春生上吊自殺。他們都已自己決定自己的方式選擇死亡。但明顯《活著》中春生的自殺是帶有直接的歷史因素的,而《生死百年》中四爺爺的自殺其歷史因素很為淡薄。主要是傳統文化心理的扭曲而導致的四爺爺自殺。但從另一方面說春生完全可以選擇活下去,雖然這種存活是非常態的,是艱難的、屈辱的。但最終他仍然選擇自我了解。這其中的原因何在?就在于他自身對他的阻擋,他無法越過;自身給他的重壓感,他無法繼續負擔;他自身給他帶來的絕望,他無法回避、更無法超越現實自身悲苦的存在。所以春生選擇自殺,結束自己難以承受的生命之悲苦。而四爺爺戒男女之禮,一輩子未娶,一心只讀他那幾本圣賢書,三次跳水都被人救下,沒死。第四次終于如愿,淹死于犀牛塘。其實四爺爺也可以選擇繼續安靜地活下去,其自殺看來好像沒有什么特殊的緣由,但最終四爺爺選擇自殺,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他對自己生命的一種厭棄、一種孤獨的冷漠、一種偏執的解脫。其深層原因還是在于四爺爺被自身所圍困,而且這種自身的圍困越縮越緊,四爺爺無法掙脫,終選擇一了百了的方式,使這自身的圍困與自己的生命同時消盡。所以小說中兩人共同的選擇自殺,雖然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外在因素的影響但其背后其實都是自己與自身之間裂變卻又難以維持或調和這種裂變的結果。
有些時候,有些人的“死亡”呈現出一種自身的無意識狀態。即他并不是要刻意自殺、也根本沒想自殺,而結果卻又自己殺死了自己。在無意識的狀態下,人與自身之間突然的接近,近到無法看清自身;是一種人對自身異常的清醒,清醒到完全忽略了自身;是一種對于自身太想生存,以至于最終死亡的至極而反的關系。《生死百年》中的黑豆和《活著》中的苦根就是如此。他們兩個人的命運可以說是幾乎完全相同,《生死百年》中黑豆的父親汪武上山挖洋芋時,摔斷腿,被凍死在山上。母親在江邊洗衣服時,掉進青衣江淹死。只剩下黑豆繼續活著,而最后黑豆卻吃了太多生肉而把自己撐死了。《活著》中苦根的父親二喜干搬運時被兩塊水泥板夾死,母親鳳霞在生產后大出血而死。只剩下苦根跟著富貴,但最終苦根卻吃豆子把自己撐死了。兩個孩子都以自己的雙手把自己送上死亡之路。而這一切對于他們自己卻又是無意識的。他們的想法很純粹、很簡單,在本能的驅使下,他們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一次無懈可擊的對自身的謀殺。這種“死亡”所呈現出來的是一種人在不經意中笑著擁抱自身時用力過大而把自身勒死的悲劇。這種悲劇的呈現使得小說中的“死亡”在帶上了一層荒誕色彩的同時,也顯得更為單純、深沉。“從普通人的類乎災難的經歷和內心中,發現生活的簡單而完整的理由”[4]。這是這兩部小說在文本背后要表達的中心內涵。
上述《生死百年》與《活著》中的關于“死亡”敘寫之中的三種關系,人與自身的關系其實也是包含在人與人的關系之中的,只是它更近切、本真些。而人與人的關系也是包含在大的人與歷史的關系中的,只是它更具體些。所以總歸兩部小說寫的都是人與歷史,更具體的說是苦難的歷史與苦難的人生,而這些苦難的歷史與苦難的人生終歸是該有個結果的,對于一些人,這個結果就是死亡!這種死亡在小說中是冰冷的,但穿過死亡之后卻是溫暖的。
[1]閔良.生死百年[M].銀川:陽光出版社,2011.
[2]余華.活著[M].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
[3]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4]王達敏.余華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