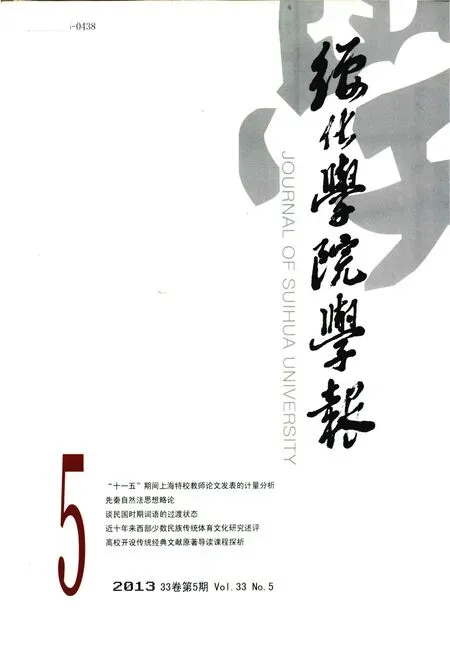小說與電影的裂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女性身體解讀
陳香玉
(綏化學院 黑龍江綏化 152000)
在文學敘事中,身體亦即刻錄故事的地方,身體成為一個意義的集結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女性身體被符號化而蘊含了豐富的能指和所指,承擔起言說哲思的重要使命。正如劉小楓指出的,“昆德拉編織了與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的故事相似的關于一個男人與兩個女人的身體的故事。”[1]《生》中,女性身體意象無處不在,被成功編織進哲學話語和兩性話語的宏大敘事中。《生》被成功搬上了銀屏,更名為《布拉格之戀》。盡管導演考夫曼以其卓越的電影才華完成了從小說到電影的藝術轉換,但從小說到電影的敘事轉換過程中,身體經歷了從文字符號到影像符號的藝術形式的復雜轉換,兩種異質敘事媒介呈現的身體必然存在不可縫合的裂隙。本文將電影與小說視為兩種平等的藝術表現形式,盡量避免傳統的小說文本中心主義思想,從兩個角度探討改編過程中的轉化機制。
一、性別視域下的身體符號
“身體是權力紛爭的核心場所。”[2]在男性權力處于統治地位的父權制社會文化中,女性身體必然臣服于父權制權力,不可避免地淪為父性權力規訓與懲罰的對象與客體。《生》中,男性權力通過對女性身體的操控達到損毀女性主體地位與自我意識的目的。特蕾莎的母親成為九個男人爭奪的對象。其中一個男人通過侵犯她生育權利與自由的卑鄙手段永久性地占有了她。哪里有權力哪里就有反抗。特蕾莎的母親采取了一種消極反抗的人生姿態——輕賤和鄙棄自己。她甚至在客人面前講述自己的隱私,毫不羞澀。特蕾莎少女的天真使得她對女性的處境抱有幻想。然而,特蕾莎的身體也沒有因其愛人的身份而獲得不同的待遇與評價具。特蕾莎下意識地對身體的不公正待遇進行了反抗——以身體的出軌來對抗托馬斯身體的不忠與放蕩。但特蕾莎已經內化了男性權力的身體倫理價值觀,最終以高度監控自己身體的囚犯的自律意識結束了身體的反抗與背叛,她重新接納了托馬斯,包括他不忠的身體。
如果說特蕾莎及其母親徹底喪失了自己身體的宗主權,主體意識遭到父性權力的壓制與踐踏,那么薩賓娜則是有意識地嘲弄男性權力對女性身體的不恭。薩賓娜并非女性主義者,在她看來,對生來是女人這一事實進行反抗,與以之為榮耀一樣是荒唐的。但她對女性及其身體的處境有清醒的認識。薩賓娜是唯一能夠掌握自己身體的宗主權,保持獨立完整主體人格的女性,她的身體不屈從與任何一個男人,她是自己身體真正的主人。
小說中,昆德拉對女性的態度是復雜的,既不是厭女癥患者,也不是女性主義者,他主要是將女性作為弱勢群體進行關懷與體認的。女性的身體內涵是多元而復雜的。電影《布拉格之戀》中的女性身體與小說有著不可彌合的裂隙,無法成功傳達小說文本中身體符號的全部含義,電影以其獨特的影像敘事方式賦予身體別樣的內涵。從小說到電影的身體符號轉換過程中,身體在不同藝術形式的互文與互動過程中承載了更多意義。
“視覺迷戀的對象是女人的身體,觀看本身就是高度性別化的。”[3]電影作為高度視覺化的藝術形式,必然建構一個女性身體淪為窺視目標的視域空間。《布》片中,女主人公的出場迎合了男性觀眾的窺探欲。小說中,托馬斯與特蕾莎的第一次見面是在小旅館的酒吧里,而電影卻將兩人的初次邂逅安排在酒吧游泳池里。這樣以來,電影中的特蕾莎就不用像小說里那樣穿上粗陋難看的女侍者服,而是身著一襲神秘黑色泳衣,活力四射地在水中暢游,水花四濺,托馬斯被其曼妙的身體及其散發出的火熱生命力深深吸引,情不自禁地緊緊尾隨。鏡頭給了托馬斯一個特寫鏡頭,他的雙眼熱情燃燒著情欲的火焰。在凝視中,觀眾分享了男主人公對特蕾莎的欲望觀看,認同了托馬斯的獵艷行動和窺視目光。女主人公的出場顯示了考夫曼藝術手法的高妙,一方面,女主人公為男性觀眾的觀看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其出場推動了敘事線索的發展——男女主人公第一次相遇。
電影作為觀看的藝術,必然被打上父權制的印記,著名電影理論家穆維爾指出,“主流商業電影設定的凝視主體無疑是男性……觀眾認同男主人公的行動和目光,分享對女主人公的欲望觀看。”[4]《布》中,占據視點鏡頭的權力主體通常是男性,女性身體處于被凝視的客體位置。影片中有一處場景最能體現這種看與被看的性別權力關系:托馬斯與薩賓娜鏡前調情。托馬斯衣冠楚楚坐在一旁觀看薩賓娜身穿黑色蕾絲內衣在鏡前搔首弄姿,一個特寫鏡頭突顯出男主人公審視與品味女性身體的雙眼,緊接著切換到近景鏡頭,薩賓娜觀看自己鏡中的身體,又切換到托馬斯凝視女性身體的鏡頭。流暢的剪輯暗示了影像藝術的父權文化邏輯:女性身體不僅是鏡頭前觀眾窺視的欲望客體,還是男性角色凝視的他者。
二、哲學視域下的身體符號
《生》堪稱現代哲理小說的典范,昆德拉借助不同性別角色的身體表現了自己獨特的身體哲學。在柏拉圖的二元論傳統中,身體與靈魂是二元對立的,身體是被靈魂主宰的奴隸,在哲學領域處于卑賤的弱勢地位,而靈魂則高高在上,與真理與道德常相隨而顯得不可企及。然而,從17世紀開始,身體的地位有所提升:身體不再受哲學的譴責,但依然因其反智性被理性放逐。幾個世紀后,尼采提出“我完完全全是身體,此外無有,靈魂不過是身體上某物的稱呼”,[2]徹底顛覆了身體對靈魂漫長的哲學屈從地位。被解放的身體終于可以和靈魂平起平坐了。在這樣的身體哲學背景下,昆德拉在《生》中傳達出這樣的身體哲學:作為無思維之肉體的身體是獨立于靈魂的自然客體,有著自己的靈魂,身體既可以與靈魂分道揚鑣,亦可與之相互找尋。靈魂與肉身相互找尋使得生命變得沉重,如果它們不再互相找尋,生命就變得輕盈。
小說中,特蕾莎與薩賓娜的身體符號承擔了不同的哲學能指功能,代表了兩種不同身體態度與哲學,而托馬斯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身體哲學之間艱難徘徊,生命也在輕與重之間彷徨選擇。特蕾莎堅持身體上靈與肉的不可分割性,要求身體必然服從靈魂的倫理法則,身體應承擔靈魂的重負與辛勞。因此,她認為表征肉體的性與表征靈魂的愛應當是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她無法理解托馬斯身體的背叛與靈魂的專一。特蕾莎追求靈與肉彼此找尋的沉重愛情,她的堅持讓托馬斯感到了生命的沉重。而薩賓娜則恰恰相反,她堅守身體的自主性,認為身體的自然欲望與靈魂有著平等的權利,身體只為了身體的快樂而快樂,不必受靈魂的倫理牽絆與束縛。托馬斯在她那里體驗到生命的輕盈,而在特蕾莎那里卻感到沉重的幸福。托馬斯的矛盾與選擇暗示了昆德拉的哲學選擇:在享受了身體與靈魂分離的生命之輕之后,托馬斯意識到身體與靈魂彼此找尋的痛苦,最終選擇了特蕾莎身體的沉重而非薩賓娜身體的輕盈。
那么,電影如何轉述小說中深刻的身體哲思呢?導演考夫曼費盡心思。本文將選擇幾個代表性的場景來探討兩種藝術形式之間的轉換機制與得失。場景一:特蕾莎第一次踏進托馬斯的家門時,靈魂正沉浸在愛情的激情與浪漫里,而她的肚子卻咕嘟咕嘟地叫個不停。小說中是這樣議論的:“產生特蕾莎的這一情景,粗暴地顯示了肉體與靈魂之間不可調和的兩重性——這一人類根本的體驗”,敘事者調侃道,“瘋狂地愛和聽到肚子咕咕叫,這兩者足以使靈魂和肉體的同一性——科學時代的激情幻想——在頃刻間化為烏有。”這一生活細節顯然是小說的刻意安排,其用意十分明顯,無非是昆德拉借以傳達關于身體具有獨立于靈魂的自主性的藝術手段。導演考夫曼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細節傳達出的哲學思考,在影片中沒有遺漏對這一生活細節的藝術表達,只是在藝術傳達方式上做了些許改動:影片中,特蕾莎踏進托馬斯家門時肚子沒有咕嚕咕嚕叫,而是忍不住打了一個響亮的噴嚏。影視藝術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導演不可能讓演員表演肚子發出咕嚕咕嚕的響聲,如果勉強表演配上虛擬聲音又難免失真而顯得刻意、做作,導演只好讓演員打噴嚏來代替肚子響。然而打噴嚏并沒有傳達肚子響所暗示的哲學思考,沒能使觀眾嚴肅思考。只是使電影的喜劇元素得到增加,讓觀眾輕松一笑。因為打噴嚏傳達的信息和含義是有限的:一是女主人公在關鍵時刻感冒了,二是女主人公在關鍵時刻有失優雅,暗示了影片愛情的現實主義特征。堂吉訶德說得好,饑餓是愛情的大敵,但沒有說過感冒是愛情的大敵。在談情說愛時肚子響這一悖論正體現了肉體與靈魂的悖論與分裂。因此,盡管導演有非凡的藝術才華,影片依然難以窮盡小說的深刻哲學思辨,而這正是影視藝術的局限性所決定的。
場景二:特蕾莎與工程師發生一夜情,借以體驗身體對靈魂的背叛。小說中,作者用文字精細地描述她身體與靈魂的分裂過程:“她把自己的身體趕得遠遠的,她不想為它負一點責任……她的靈魂想以此表明,在根本不贊成正在發生的事情的同時,她選擇保持中立。”特蕾莎努力讓身體擺脫靈魂的控制,試圖體驗身體獨立自主的快樂。電影中,女演員朱麗葉·比諾什的表演十分到位。一個中景鏡頭中,男演員背對攝影機,比諾什半躺在攝影機前,她拒絕凝視對方的臉,而是將視線投向空中,眼中充滿了迷惑與期待。比諾什用身體語言與表情語言精準地傳達出小說的意圖:特蕾莎困惑托馬斯身體的背叛,期待嘗試并檢驗身體對靈魂的背叛,她想體驗所愛的人所體驗的一切。但是,電影鏡頭是有性別傾向的。在畫面構圖中,特蕾莎始終占據次要位置,她的身體語言顯示了女性的被動與客體地位,這與小說中特蕾莎主動嘗試身體的背叛是背道而馳的。
總得說來,小說中女性身體的處境隱喻了女性在社會文化中的性別位置,具有傳達作者關懷弱勢群體的言說功能與符號意義。而電影中,女性身體的深度被平面的景觀身體取代了,淪為男性人物及觀眾觀看的欲望對象。這種裂隙并不能證明電影藝術的劣勢,而只能說明小說與電影藝術之間存在不可彌合的裂縫,這一裂縫主要體現在對女性身體的表達上。
[1]劉小楓.沉重的肉身[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80
[2]汪民安,陳永國.后身體文化、權力和生命政治學[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9,10
[3](美)彼得·布魯克斯.身體活——現代敘述中的欲望對象[M].朱生堅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06
[4]戴錦華.電影理論與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