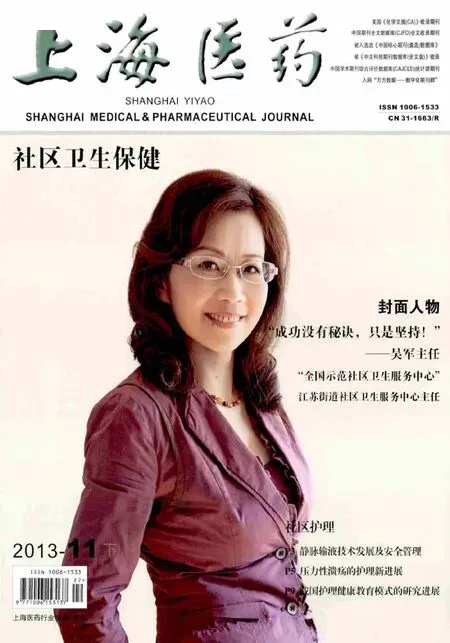壓力性潰瘍的護理新進展
吳唯勤 李曉靜
(1. 上海第八人民醫院胃腸外科 上海 200233;2.上海國際醫學中心 上海 201318)
壓瘡即壓力性潰瘍(pressure ulcer, PU),臨床上俗稱為“褥瘡”,祖國醫學稱之為“席瘡”。1989年美國全國壓力性潰瘍顧問小組(National Pressure Ulcer Advisory Panel, NPUAP)對壓力性潰瘍定義為:由于局部組織長期受壓,引起血液循環障礙,組織營養缺乏,致使皮膚失去正常功能而引起的組織破損和壞死。2007年NPUAP重新定義為:是皮膚或皮下組織由于壓力、剪切力或摩擦力而導致的皮膚、肌肉和皮下組織的局限性損傷[1]。有研究表明,住院期間壓力性潰瘍的發生率為3%~10%,髖關節骨折后壓瘡的發生率為10%,臥床不起的老年人家中壓瘡的發生率為50%[2]。做好壓瘡的預防和護理是社區衛生服務的重要內容之一。
1 病因和危險因素
1.1 外在因素
1.1.1 壓力
壓瘡的發生與皮膚壓力暴露的增加、活動受限或感知受損有關。這些危險因素降低了患者通過改變體位來減少壓力的能力,高危因素包括:脊髓損傷、腦卒中、多發性硬化、外傷(如骨折)、肥胖、糖尿病、認知缺損、藥物的使用(鎮靜、催眠和止痛藥)、手術等。
1.1.2 剪切力
剪切力是施加于相鄰物體的表面,引起相反方向的進行性平行滑動的力量。剪切力作用于皮膚深層,引起組織的相對位移,能切斷較大區域小血管的血液供應,導致組織氧張力下降,因此它比垂直方面的壓力更具危害。它與體位密切相關,患者半坐臥位時身體下滑、肌肉、骨骼下滑,而皮膚及皮下組織由于床的摩擦力而無法移動或移動受限,這樣就產生了剪切力。
1.1.3 摩擦力
摩擦力是兩個物體表面互相移動產生的機械力。當個體不能自主抬起身體并且在此狀況下移動時,將有發生摩擦傷的高度危險。摩擦會破壞皮膚角質層的屏障功能引起淺層組織損傷。
1.1.4 潮濕
潮濕引起的皮膚浸漬改變了上皮對外部壓力的回彈力,尤其是處于長期浸泡狀態時。兩便失禁、傷口滲液和汗液均能導致潮濕。某些潮濕類型,尤其是大便失禁,由于皮膚暴露于細菌和消化酶中使其pH值提高,從而增加了發生壓瘡的風險。
1.2 內在因素
內因是通過影響皮膚的支撐結構,血管系統和淋巴系統來降低其耐受性。
1.2.1 年齡
年齡是壓瘡風險最有關的人口學特征,65歲以上患者發生壓瘡的風險增加,75歲以上風險更大。
1.2.2 組織灌注
影響組織灌注、氧氣運輸、感知障礙等疾病會增加壓瘡的風險。例如脊髓損傷慢性期的患者,既往的深靜脈血栓、下肢骨折和肺炎病史都是發生壓瘡的高危因素[3]。
1.2.3 營養
營養不良和脫水都是壓力性損傷的內因,包括近期體重減輕、營養不良、蛋白質或能量攝入不足。營養不良和缺水與皮膚干燥和腫脹有關,增加了壓力性損傷的風險。
2 壓瘡的分期
1989年NPUAP將壓瘡分為4期:Ⅰ期:淤血紅潤期;Ⅱ期:炎性浸潤期;Ⅲ期:淺度潰瘍期;Ⅳ期:深度潰瘍期。
在臨床評估中發現有些患者雖然皮膚完整,但深部組織出現損傷。另外,如果傷口覆蓋焦痂或壞死組織,傷口則無法分期,深色皮膚患者很難判斷是否存在I期壓瘡。因此,NPUAP于2007年對壓瘡重新進行分期,在原有4期基礎上,增加了可疑深部組織損傷及不可分期階段。
懷疑深層組織損傷的描述:由于潛在的軟組織壓力和(或)剪切力損傷,局部區域為紫色或暗紫色或顏色改變或血皰形成。與臨近的組織相比,這些受損區域的軟組織可能有疼痛、硬塊、有黏糊狀的滲出、潮濕、發熱或冰涼;在深膚色人群中深部組織損傷可能很難發現;創面的進展過程中可能會有深色的水皰出現。壓瘡可進一步發展并被薄的焦痂所覆蓋,即便使用最佳的治療方法,病變也仍會迅速發展,暴露多層皮下組織。
不可分期的描述:全層組織缺損,其基底被腐爛組織(黃、褐色、灰色、綠色或棕色)和(或)焦痂(褐色、棕色或黑色)所覆蓋;只有腐爛組織或焦痂充分去除,才能暴露壓力性損傷的基底和其真正的深度,因此分期無法確定,足跟的焦痂是穩定的(干燥、黏附牢固、且無發紅或波動),可以作為身體自然的屏障,不應去除。
3 壓瘡評估工具的使用
現在臨床上愈來愈重視早期識別壓瘡高危患者以便盡早進行干預,運用的評估工具包括:Barden量表、Norton量表、Barden評分,還有一些用于評估特殊人群的量表,包括用于重癥監護患者的Glasgow量表、Cubbin量表和Jackson量表。一項研究對成人壓力性損傷評估工具的信度和效度的評價,結果顯示Barden、Norton量表均有良好的評分者間信度。但臨床實際使用過程中要根據具體情況選擇不同的評估工具。
4 壓瘡疼痛的評估與管理
對于壓瘡引起疼痛的研究逐漸在開展,壓瘡相關性疼痛的發生率約為37%~66%。使用驗證評估工具的研究,其報告壓瘡相關性疼痛的發生率高于非驗證評估工具的研究[4]。壓瘡患者的嚴重性或分期與其疼痛相關,疼痛隨壓力性損傷嚴重性增加而增加[5]。Gorecki等[5]報道,壓瘡越嚴重的患者(III期和IV期)更有可能主訴疼痛,且疼痛更加頻繁和劇烈。盡管疼痛增加的水平與更換敷料無直接相關[4],但這些時間疼痛的經歷更常見[5]。患者的疼痛還與傷口的受壓、傷口清洗技術、敷料的覆蓋和去除等有關[5]。
疼痛評估應當包括對肢體語言和非語言的線索的觀察,特別是對那些有認知障礙的患者和兒童。在評估工具的使用上,以下疼痛評估工具已被驗證可用于評估成人壓力性損傷相關性疼痛:視覺模擬評分法(VAS)、Wong-Baker表情疼痛評定量表(FRS)、McGill疼痛問卷(MPQ)。
5 促進壓瘡愈合的措施
5.1 營養支持
熱量不足將影響蛋白質在傷口愈合中發揮作用。蛋白質也是傷口愈合所必需的營養,目前一致認為壓瘡患者對蛋白質的需求增加[6]。每天至少30~35 kcal/kg的熱量;每天1.25~1.5 g/kg的蛋白質;每天1 ml/kcal的液體,臥床患者因活動力降低,肌肉萎縮,所需能量需減少,截癱患者每天需要(29.8±1.2) kcal/kg的能量支持;癱瘓患者每天需要(24.3±1.1) kcal/kg的能量支持。
5.2 體位
常規的體位改變是壓瘡護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因其不僅可以對界面壓力重新進行分配,而且可以增加患者的舒適性、尊嚴感和功能,使患者有條件進行基礎護理,能夠進行常規的皮膚評估。雖然已經認識到改變體位的重要性,但是還沒有高質量的證據證明其應用于壓瘡患者干預措施的有效性。
5.3 感染的治療
大部分慢性傷口都被細菌污染,但并非所有傷口都是感染傷口。壓力性損傷傷口發生局部感染的征象包括:傷口出現新的破潰和(或)面積增加、傷口周圍發紅、滲液量增多、滲液黏稠度增加或變為膿性、疼痛加劇、傷口周圍組織腫脹、傷口周圍溫度升高、惡臭、形成竇道、橋接、袋狀或可探至骨頭。
5.4 碘劑的應用
Vermeulen[7]在2010年報道了3項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研究,碘制劑在促進傷口愈合方面(表現為用不同處理方法后傷口面積的減小)有顯著統計學意義。
5.5 局部醫用蜂蜜
蜂蜜是一種含有葡萄糖、果糖、蔗糖和水分高度復雜的糖類過飽和混合物。蜂蜜用于傷口治療已經有幾個世紀的時間[8]。蜂蜜被認為可以通過滲透作用吸收傷口的水分到傷口表面,促進產生濕性愈合環境和降低傷口pH值,這些有助于傷口自溶清創而促進傷口愈合[9]。
5.6 負壓傷口治療
負壓傷口治療(negative pressure wound therapy,NPWT)是一項傷口處理技術,應用密閉敷料和負壓吸引保持傷口的真空狀態。有報道負壓傷口治療可以通過減少水腫、增加局部營養和氧氣輸送、清除傷口滲出液、促進肉芽組織形成,并且增加生長因子。該療法主要是用于減小傷口體積,也可用于皮瓣縫合手術的傷口床準備。將泡沫敷料或紗布填塞傷口,外層用透明薄膜敷料密封,其中插入引流管連接真空負壓機器。負壓傷口治療已經廣泛應用于各種復雜、難愈性傷口,國內文獻有非常多的報道。
5.7 傷口敷料的選擇
傷口敷料的應用是為了避免傷口污染、損傷,吸收多余滲液,填塞死腔,減輕水腫,以促進愈合環境的優化。傷口的愈合是建立在濕性愈合的基礎上,即通過選擇封閉或半封閉敷料,以保持創面合適濕度,為傷口床做好準備[10]。影響傷口敷料選擇的因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周圍皮膚情況、方便使用和移除、維持濕度平衡的能力、吸收滲出液和氣味的能力、更換敷料時的疼痛、感染的控制和維持細菌平衡的能力、傷口隱蔽效果、專業人員的技術和知識、可獲得性和成本效益、敷料與傷口是否貼合、舒適性。
6 健康教育
對患者及其照顧者進行相關知識的教育是成功實施壓瘡管理的重要部分,也是在實施預防性策略中能夠與患者及家人很好合作的重要保證。患者及其家人應該清楚的理解壓力性損傷的影響及其預防的重要性,壓瘡的風險因素及可以減少或避免其發生的方法和策略。這點對于居家護理及即將出院的患者很重要。
直到現在,很多人依然認為,只要護理得當,就不會發生壓瘡。實際上因為基礎疾病的因素,有些患者不管有無預防措施均會發生壓瘡。要充分運用各類評估工具,及早識別壓瘡高危人群,盡早進行干預,采取適當的措施,使用適合的敷料,使壓瘡對患者的影響降到最低。
參考文獻
[1]胡愛玲, 鄭美春, 李偉娟, 等. 現代傷口與腸造口臨床護理實踐[M]. 北京: 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 2010: 150-170.
[2]楊桂華, 楊海新. 護理人員對預防病人難免性壓瘡的真實體驗[J]. 中國護理管理, 2008, 8(8): 68-70.
[3]Gelis A, Dupeyron A, Legros P,et al. Pressure ulcer risk factors in person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part 2: the chronic stage[J]. Spinal Cord, 2009, 47(9): 651-661.
[4]Girouard K, Harrison MB, VanDenKerkof E. The symptom of pain with pressure ulcer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Ostomy Wound Manage, 2008, 54(5): 30-40, 42.
[5]Gorecki C, Closs SJ, Nixon, J,et al. Patient-reported pressure ulcer pain: A mixed-methods systematic review[J]. J Pain Symptom Manage, 2011, 42(3): 443-459.
[6]Stockton L, Gebhardt KS, Clark M. Seating and pressure ulcers: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J]. J Tissue Viability, 2009,18(4): 98-108.
[7]Vermeulen H, Westerbos SJ, Ubbink DT. Benefit and harm of iodine in wound care: A systematic review[J]. J Hosp Infect,2010, 76(3): 191-199.
[8]Jull AB, Rodgers A, Walker N. Honey as a topical treatment for wounds[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08, 8(4):CD005083.
[9]Gethin G, Cowman S. Manuka honey vs. hydrogel-a prospective, open label, multicentre,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to compare desloughing efficacy and healing outcomes in venous ulcers[J]. J Clin Nurs, 2009, 18(3): 466-474.
[10]Meaume S, Ourabah Z, Cartier H,et al. Evaluation of a lipidocolloid wound dressing in the local management of leg ulcers[J]. J Wound Care, 2005, 14(7): 329-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