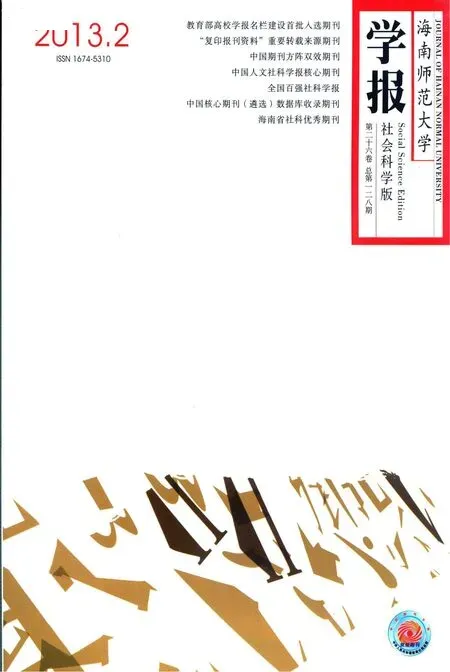“社會主義文學”作為“遺產”是否可能?
張均,等
(中山大學中文系,廣東廣州510275)
一
張均(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社會主義文學”是個寬泛的概念,主要指1942年到1976年間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影響的主流文學。這個時代的文學深深地打上了毛澤東個人思想和意志的痕跡。作為教學“共識”,我們普遍認為它的“文學性”比較可疑。但作為學術研究,看待問題的方式會有所變化。數年前,錢理群老師表示,最近20年知識界最大的失誤就是沒有認真清理和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并明確表示“社會主義遺產是我們今天面對現實可以繼承、借鑒和考慮的一個遺產和資源”。但眾所周知,對此學界分歧很大。北大的一批學者如陳曉明、李楊、韓毓海等,包括上海的蔡翔,肯定的意見較多,而南京、上海的王彬彬、丁帆、陳思和、郜元寶等偏“右”的學者的評價就比較低,甚至是激烈否定。兩方面也“爆發”了一些爭論。這給我們廣州的學者留下了很好的話題:究竟“社會主義文學”能否作為“遺產”?如果不能,根據在哪里?如果能,又是在什么意義上能,又有哪些方面可以作為“資源”?無疑,這是充滿文學史張力和現實糾葛的復雜話題。我們可以先從右翼學者的觀點談起。王彬彬老師有一篇文章,叫《〈紅旗譜〉每一頁都是虛假的和拙劣的》,徹底否定“社會主義文學”,但行文中不乏學術的表達,譬如認為“十七年文學”“漠視個人情感和命運”、“缺乏獨立精神的、沒有批判意識”,等等。陳思和老師的看法相對平和,認為“十七年文學”的主要價值在于民間立場。這其實是從“社會主義”之上剝離出一些異質性,并在操作的意義上構成了對前者更深刻的拋棄。
吳敏(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這個話題是錢理群先生在2002年“當代文學與大眾文化市場”學術研討會上提出來的。錢理群老師說的“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包含很多方面: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思潮、社會理念、文學藝術以及與之相關的諸種實踐方式。我們今天聚焦的問題是“社會主義遺產”,這個“遺產”不是像魯迅《拿來主義》里所說的“大宅子”,我們可以要,也可以不要;面對“社會主義遺產”,我們沒有可能選擇“不要”,它不是外在于我們,而是內在于我們的。我們今天走到了21世紀,就是從1942年、從1930年代的左翼甚至更早的時期走過來的,我們就是社會主義文學的兒孫,我們現在流著的文化血脈中有一部分就是從這里承傳下來的,它是集體記憶或者集體無意識,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支配、控制我們。不能說社會主義遺產“是否可能”,我們其實沒有選擇的余地,盡管我們時時在反抗,在調整,不斷地做著精神上、文化上的弒父,但其實我們很難擺脫它,而且我們也不能擺脫它。社會主義思潮距離我們太近,我們是近親遺傳,也許要過很多年,這些遺傳才會有根本性的形變和質變。
黃燈(《天涯》雜志編輯、廣東金融學院副教授):我個人也在研究“文革”時期的連環畫。其實就我個人而言,我還是很喜歡看。盡管王堯老師一再提醒我不能把它詩意化、理想化,但是我就是喜歡看。而且我的小孩都喜歡看,他才5歲啊!以前把它說得一塌糊涂,當時它發行十幾億冊肯定是有它的理由的。它應該是有超越時空的力量的,不能這么短的時間下一個結論。
申霞艷(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教授):“十七年小說”至少在塑造人物上還是值得今天的作家學習的。很多先鋒小說,比如說馬原的,對文學經驗確實提供很大貢獻,但他沒有一個人物立得住。當我們談馬原的時候,只能談他的敘事技巧,而談不出一個人物。但我們一談《紅樓夢》,就說賈寶玉如何如何,林黛玉如何如何。文學的感染力很大程度是建立在人物形象身上的。我們當代文學的老師講馬原都覺得很困難,但如果講一個具體的人物就好很多。
郭冰茹(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我一直強調做當代文學研究應該注意幾個時間點:故事講述的年代、講述故事的年代,和讀者讀故事的年代。討論“十七年文學”也不能剝離當時的語境。在當時語境中,評判文學的標準是什么呢?就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倘若按照當時的標準,絕大多數的“十七年文學”是成功的。現在以藝術標準第一來衡量,當然覺得它們跟政治結合得太緊密了,藝術上太乏味了。所以我一直覺得討論“十七年文學”,與其討論它的審美價值,還不如討論它的社會文獻價值,討論作家在迎合主流意識形態與追求藝術自覺之間所做的努力,討論這些文本所存在的張力元素。這些被譽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書寫帶著一種理想主義色彩來回應當時具體的現實,但是它也留存了其他任何社會歷史文獻中都無法彰顯出來的異質性因素。這恰恰是“十七年文學”在被抽離出當時的語境后留給后人的價值。
如果再追溯一下,“十七年文學”當然離不開從1930年代以來一直推行的“文藝大眾化”運動,這場歷時久遠的運動強調如何來看待舊形式,如何進行民族形式的再創造。“十七年”時期的文藝政策就是強調要老百姓喜聞樂見、要大眾化。而且當時的主流作家幾乎都出自解放區,他們受到的文學教育大多來自《三國》、《水滸》。與此同時,西方(主要是現代主義)的影響基本是隔絕的。可以想象,如果要創作長篇小說,章回小說可說是當時惟一的可供借鑒的傳統的舊形式。我后來發現“十七年”的長篇小說的確在很多層面上都對古代章回小說有借鑒。比如說人物塑造,章回小說比較強調人物的出場,以前講《紅樓夢》都講王熙鳳怎么出場,實際上“十七年”小說也很講究人物的出場,比方說林道靜的出場,梁生寶的出場,都很詩意化。另外還有人物性格的相互映襯,比如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提到《林海雪原》中的“五虎將”模式。當然人物塑造并不是古代章回小說的核心目的,章回小說脫胎于話本,其核心是為了講故事,因此在情節設計上花費的心思遠大于人物塑造。“十七年”小說很多情節設置是借鑒章回小說的,比如說“峰巒疊起”,比如因果關系造就的敘事動力等。從這個角度來講,先鋒文學的“向后轉”,可能就是在敘事技巧上的革新已經無計可施的時候,重新再退回到最傳統的人物、故事上來,比如格非、莫言、蘇童的轉向。“十七年文學”在汲取傳統方面做得相當不錯。它在滿足既定的政治要求的同時也能夠刻畫幾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像楊子榮、像江姐,同時也能講幾個好聽的故事。按照當時的審美價值或者評判價值,或者說喜聞樂見這個要求來講,它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如果一定要讓現在的讀者喜歡當時的東西我覺得有點強人所難。《紅旗譜》是因為塑造了朱老忠這個兼具革命性和民族性的英雄人物,因為描述出了農民從單打獨斗走上無產階級革命的成長史而被譽為“經典”,而并不是因為其卓越的藝術成就。所以我覺得《紅旗譜》并非像王彬彬老師說得那樣毫無價值。
張均:既然“社會主義文學”內在于我們的血液,無法排除,那么陳思和、王彬彬等學者否定性的觀點與立論方法是否存在一些可以討論的問題呢?其實哪個作品沒有“謊言”的成分呢?魯迅寫閏土,說他被兵、匪、旱、災尤其是愚蠢的文化折磨得貧窮而麻木,實際上閏土的貧窮主要因為他在婚外戀中的經濟賠償所致。這個材料在周作人的回憶中有記載,但并不能因此說《故鄉》就是謊言。單單責怪《紅旗譜》和“十七年文學”,在立論上是不那么服人的。
吳敏:王彬彬文章最后說:每當聽到或者看到有人歌頌“文革”,他就覺得是一件非常驚恐的事情。我認為他的批評是在審視我們曾經走過的歪路、邪路、教訓、血與痛的經驗,而這些文化反思,現在我們做得還非常不夠,包括“文革”不能談,“文革”博物館不能建,給中國人帶來這么大的悲痛和災難的事情現在還是話語禁區。在這一點上,我同意王彬彬。但是我不太同意他的判斷。王彬彬將“十七年文學”比喻為一只“爛蘋果”。在他的理解里,《三家巷》、《創業史》“是觀念先行的產物,是在圖解某種政治理念”,“展現的是臆想的歷史和臆想的現實,卻又對讀者產生著可怕的影響”,是一只“爛蘋果”;“十七年”有些作家,如周立波、柳青、趙樹理、歐陽山等,是富有文學才華的,他們的作品有一些風景描寫、風俗敘述、場面刻畫等,但這些是“枝節性的東西,不足以影響對整部作品的評價”。我想追問的是,“十七年文學”難道就只有“風景、風俗、場面”這些“文學性”么?這些元素難道只是判斷文學作品價值的“枝節”?《山鄉巨變》、《李雙雙》、《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紅豆》等作品難道都是政治化的“爛蘋果”?這些作品里傳達出來的民情、鄉情、性情、喜怒哀樂,能夠用“政治理念”全部囊括嗎?還有,讀者對文學作品的閱讀和接受有他們自己的選擇性,他們可能恰恰對那些“政治理念”不敏感或者有意過濾,打動他們的可能就是那些情愫、場景甚至與思想主題關聯不大的家長里短、怦動人心的某些片段。譬如,莫言說自己讀《林海雪原》字字不能忘記的是其中《白茹的心》那一章;陳忠實認為自己走上文學道路,受趙樹理、柳青的影響最大,他初讀《創業史》并不能完全理解,但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小說對農村生活的理解認識以及藝術描寫,卻深刻地影響了他。當然,莫言、陳忠實這些作家的藝術成就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十七年文學”是滋養他們的一種肥料,而且不是“爛蘋果”式的肥料。所以,應該允許學生喜愛《三家巷》的理由是“小說寫了乞巧節”。我們不應該用“文學史”的思路來規定、控制讀者的自主評價,而且“文學史”的評價也不能是一錘定音的。另外,如果僅僅具有文獻學的價值,我認為也不是真正的好作品,文學創作還是要從文學的立場說話。我不贊成整體性的謾罵或歌頌,還是需要更多的具體分析。
張均:的確,王彬彬的背后存在民族良知。他要通過文學研究說他想說的話,至于文學本身怎樣還來不及計較得那么清楚。這樣的立場可以理解,但需要反思。程光煒老師經常提到,我們今天實際上是用現代文學的標準評價當代文學,用啟蒙的標準判斷革命。這中間存在錯位。50年代初的時候,我們曾用當代判斷現代,用新民主主義權衡“五四”,把“五四”搞得面目全非,那么現在我們反過來用“五四”的眼光來判斷共產黨的文化,也把共產黨文化弄得面目全非。
吳敏:這里涉及到的核心問題是評判文學的標準。我們的標準設在哪里比較合適?如果單單從“五四”啟蒙主義的文學價值觀來立論,就會覺得“十七年文學”幾乎一無是處;但剛才郭冰茹和申霞艷的具體分析我覺得特別好,分析章回小說與“十七年文學”的關系,人物形象在“十七年”小說中的成功,采用的標準是藝術形式、形象塑造。或許,我們的文學觀念還應該拓寬。
羅嗣亮(哲學博士后、中山大學社會科學教育學院講師):我也在想到底應該是怎樣的標準。80年代后我們老講主體性,但更多強調的是個體的主體性。實際上“社會主義文學”里還有對“群體主體性”的關注,幾億農民需要一個表達,你可以說代替他們表達不夠真實,但是無論如何這可以說是文學史上第一次代表這樣一個群體去表達。當然“代表”就意味著農民不是做真正的主體,因此這里面是一個打著引號的群體主體性,或者說在努力地塑造一種弱者群體的主體性。我來自農村,我總覺得魯迅和沈從文寫的農民不太像農民。真實的農民既不是翠翠也不是閏土更不是祥林嫂,“十七年文學”里面有一些我倒覺得挺像。農民不止是懦弱的一面或者純潔無暇的一面,他們本身是多元的形象。
羅成(文學博士,中山大學中文系講師):你講的我特別有感受,真正的湖南妹子哪里會是翠翠這個樣子?沈從文的寫作是他離開了這個地方以后寄托了某種人文理想而打造出來的。王曉明曾用“鄉下人與土士紳”這個說法精彩詮釋過沈的兩種心態交織:沈躋身于京派文人群體,那是一個留學英美的學生群體,自身有深深的自卑感,因此想要營造出一種不同于城里人的氛圍,論證鄉土文化是比墮落的城市文明更好的,所以這是他想象出來的。如果你是湖南人,你就會發現翠翠的形象離生活真的很遠。比較起來,趙樹理筆下的很多女性形象更有味道,更生活更真實。無論是《小二黑結婚》還是《三里灣》,那些年輕女孩的形象既有某種理想性又有很強的生活性,比如挑選男朋友、做農活、發明創新等等。那種狡黠的生活智慧,跟父母的對抗,我不喜歡就是不喜歡,就真的有北方姑娘的味道。這些形象能讓我強烈感受到趙樹理筆下的生活感。不管社會主義文學是否可能,我關注的是文學本身應該是怎么樣的。吳敏的觀點很重要,首先今天的討論是意識形態很強的一個話題,但是今天我們能不能回到文學本身呢?如果文學僅僅是文獻的、歷史的材料,那真的沒那么重要或者我們也可以像王彬彬那樣不用去看它了。但它可能是個多元的對象,有生活經驗的層面,有審美感受的層面,也有意識形態的影響。
張均:那個時期文學的生活感、經驗感和審美性非常豐富,但現在的研究無法呈現,顯然是我們的標準出了些問題。這中間除了用現代代替當代、以啟蒙代替革命之外,還有一點就是用知識分子觀念代替下層民眾的觀念。剛才嗣亮提到社會主義文學有對群體主體性的關注,對弱者的關注。這是共產黨文學最核心的地方。王彬彬等學者講的人性、啟蒙、自由更多是知識分子的自由和主體,而不是農民的。不同的人的生活需要不同,對人性內涵的理解也完全不同。知識分子重在于自由表達,在于對抗權力,但下層民眾首先要吃飽,對獨立思考、自由言論就沒有那么深的感受。這表明知識分子用來評價文學的標準——自由、獨立等概念——在中國的土地上比較飄渺。這方面,恐怕右翼學者的立場也有錯位。
吳敏:與其說是對“弱者”的關注,不如換一個詞叫“平民”。雖然“平民文學”的觀念周作人早在“五四”時期就提出了,但我覺得“平民”真正成為文學作品的主角,而且作家真的把自己的感情融入普通百姓,把普通百姓的悲歡納入自己的情懷,是在《講話》之后。當然,《講話》的“為工農兵服務”、“群眾化”有很多遮蔽,遮蔽了傳統農民封建性的東西,啟蒙沒有完成,這些我們應該反省批判,但另一面,普通百姓成了文學作品里的主人公,有了自己的喜怒哀樂,有了自己做主人公的陽光的一面,這種文學傾向非常寶貴,貫穿在“十七年”文學創作中,但沒有被評論界重視。譬如趙樹理描繪的二諸葛形象讓人感到特別親切,他因為愛自己的兒子才會去反對小二黑和小芹的婚姻,作者的筆觸帶著嘲笑又帶著寬容,帶著批判也帶著溫情,而二諸葛這樣的人其實就是我們的爹、我們的爺爺,讓我們覺得特別可親。人們可以批評有些作品里的農民形象塑造得不好,但他們一定不是閏土,甚至不是阿Q,不是那些黑暗的、思想麻木的、處于被啟蒙位置的農民。《講話》之后到“十七年”,甚至到樣板戲時期,平民就是普通人,與普通讀者有親近的情感上的交流。我覺得思想啟蒙、從西方來的一些觀念常常被當作最高的價值標準,而平民的價值觀念常常被知識分子忽略,普通民眾自信的、陽光的、務實的、凡俗的、包括宿命的一面,比較少被肯定。
二
張均:汪暉有一個看法,認為來自下層的那種尊嚴感、主體感的初步確立,是20世紀很大的成就,但這樣的成就在圈內基本上是失語的。其實陳思和老師說得非常明白,他判斷文學的標準就是知識分子的獨立意識。但很長一段時間文學追求的是下層的情感、主體、欲望,而非知識分子品質的東西。我們用知識分子眼光去判斷社會主義,那它肯定沒什么價值。這不太合理,引起了左翼學者的反彈。所謂“新左派”比較承認社會主義文學經驗。他們有兩種進路,一是從民族國家想象入手,一是從“反現代的現代性”入后,后者說社會主義在追求一種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方式的現代性。唐小兵在《再解讀》里、李楊在《抗爭宿命之路》里,都談到這個問題。李楊受竹內好啟示,認為西方侵略中國來了,中國國家內部必須組織出一個主體性來對抗西方,而這個主體性的組織方法,就是毛澤東說的建構“我們”和“他們”。“我們”是肯定性的,“他們”則被否定。這類分析和右翼很不一樣。郜元寶因此很不滿,說他們難道忘記了當時像路翎這樣的知識分子被整得發瘋?這也有道理。那么,左翼學者的優缺點又在哪里呢?
吳敏:社會主義文學有它的兩面性。《講話》以后強調關注“民間”,戲曲里的農民改變了以前做丑角的固定模式,很多變成了正面的、昂首挺胸、笑容滿面的形象,還有諸種民間藝術,像秧歌、剪紙、年畫、民間歌舞啊等等,都被賦予了特殊價值。五六十年代特別了不起的事情是做了很多民間文化的整理和改造工作,《梁祝》、《白蛇傳》、《天仙配》、《阿詩瑪》、《劉三姐》、《追魚》等,很多民間戲曲拍成了電影,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做得真是太棒了。當然時間是太短了,范圍也太窄了。中國在相對自給自足的文化環境、在自覺地對抗資本主義文化的思想前提下,提倡和展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化,一方面,它出色地、鮮亮地發展著“我們的文藝”,另一方面,它又是在非常閉塞、對于現實西方無所知、或者知之甚少的情況下發展。丁玲1937年在延安寫過一首詩《七月的延安》,說延安是個“樂園”,“街衢清潔,植滿桑槐;/沒有乞丐,沒有賣笑的女郎;/不見煙館,找不到賭場”等,在1932年,丁玲還有一篇《五月》,寫江邊大廈飄著各種外國旗、殖民地都市的酒吧、舞廳、脂粉、香水、鴉片嗎啡的販賣者、銀行家,白色黃色的資本家買辦、碼頭上的苦力、災區的難民等,作品對于西方的印象完全是一個沒到過西方的人的馬克思主義文字式的想象,把西方妖魔化了,也把中國效仿西方文明的都市簡單化妖魔化了,帶有明顯的封閉性、閉塞性、片面性。這種在不了解西方基礎上評價西方文化的觀點在《講話》里更明確。《講話》里說,馬列主義“決定地”、“應該徹底地”破壞“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的、頹廢的、悲觀的情緒,這些“創作情緒”很多就是指資本主義藝術觀念。從延安到五六十年代,中國相對封閉,所謂“反西方”是比較愚昧的“反西方”,因此,社會主義文藝的自足發展一面開掘了民間文化的寶藏,一面又夜郎自大地拒絕借鑒外來文化,這兩種非常極端的形式扭結在一起。
郭冰茹:我并不覺得李楊是新“左”的代表,他強調用知識考古學的方法來討論“十七年文學”,他可能盡量不做價值上的評判,而是在考量“十七年文學”為什么“現代”,何以“現代”,或者說怎樣“現代”。他說“沒有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何來新時期文學”,這個立論的前提是早期的新時期文學表達出來的那種樂觀主義精神、理想主義態度和英雄主義基調以及敵我對抗的思維模式在“十七年文學”中特別多見。他同時也強調新時期伊始的那批主要作家,包括知青作家、以王蒙為代表的“歸來者”,他們主要的文學資源來源于“十七年文學”,所以他們當時的文學創作有非常深的“十七年”印記。其實“十七年文學”本身并不是一個很科學的概念。因為它用時間段來概括當時出現的所有文學作品,難免削足適履。這段時間出現的文學作品當然有共性,但個性也很明顯,像《暴風驟雨》和《山鄉巨變》都出自周立波,但個中差異實在非常巨大。還有,建國初與1957、1958的作品、與1962年前后的作品都有很大不同,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具體文本具體分析。
另外,李楊的《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中也詳細討論了《紅旗譜》。他把《紅旗譜》解釋為成長小說。按照成長小說的定義,應該是一個主人公在經歷了很多事情之后,他的性格得到了發展和完善,但我們基本看不到朱老忠的性格發展過程。不過李楊認為他的性格特點正好處在民間好漢跟無產階級英雄的中間過渡階段,雖然是定格的,但他表現出來的正是中國農民在成長過程中承前啟后的性格特征。《紅旗譜》不僅是朱老忠個人的成長史,也展現出整個農民階層的成長路線。借用巴赫金的理論,李楊認為《青春之歌》和《紅旗譜》是中國現代小說真正擺脫傳統,走向現代的開始。這兩部小說彰顯了“十七年文學”的現代性。我認為還有一點也可以說明這種現代性。浦安迪討論中國四大奇書時認為,傳統章回小說的結構實際上與古人的宇宙觀、世界觀相契合,古人認為這個世界是循環往復的,而不是直線型的。所以奇書體里面不管《紅樓夢》也好,《水滸傳》也好,其實到了七八十回時已經大團圓了,大家都上梁山了,三國都三足鼎立了,但是在后面三四十回的時候作家分別將它們拆解了。浦安迪認為這就是中國古人看待世界的方法。但是“十七年”的小說在借鑒章回體小說結構的時候卻避免了這種循環往復的宇宙觀,代之而起的是非常現代的線性時間觀,這些小說都有頭有尾,但這個尾絕對是一個新的起點,而不可能像《紅樓夢》或者《水滸傳》把以前的圓滿的結局重新拆散開。“十七年文學”表達的整個是現代人的時間觀。
王敦(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語言與文化系博士、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我與郭冰茹有同感。是的,從完全不同時期的中國敘事里,確實能體察到共通性。跳出階段性局部研究,才有可能從更為廣闊的時間性前因后果里面有所發現。如果把中國敘事文學的歷史切成一段段的,滿足于就事論事地局部分析,反而不一定能把局部看透。從大處著眼,中國的敘事性文學形態主要被兩種內在的時間性框架所支配,一個是延綿在古代敘事里面的盛衰、治亂等交替的循環性框架,一個是晚清以來的關于個人和社會歷史曲折向前發展的線性敘事框架。海外漢學家浦安迪、王德威,國內的陳平原等都從各自的研究角度,以各自的方式提醒過我們。這兩種時間性框架,在晚清之后也一直并存,只不過后者在更多的時候是顯性的,前者是隱性的;兩者之間,在不同的階段,形成各種潛在的張力。這在社會主義文學里面也是如此。我認為,與其糾結于探討社會主義階段意識形態的特殊性及其這種特殊性造就了怎樣的敘事,倒不如把社會主義階段意識形態看作是現代史觀的一種展現,看看“十七年”時期小說話語是怎樣體現出敘事的現代性,并與隱性的敘事傳統發生怎樣的關系。
其實從近現代以來,不管晚清的革命黨、改良派還是民國后的共產黨、國民黨,盡管具體意識形態主張大相徑庭,但被忽視的是,它們是具備強烈的同構性的,即都遵循線性的發展史觀。它們相互之間不可調和的爭奪,實則是在如何發展上產生了不可調和的分野。于是,被不同意識形態所主導的現當代小說敘事,在敘事形態上也是具有強烈的共性的。以晚清、民初為例。不同觀念的人,比如革命的作者或者是改良的作者,在進行敘事的時候,面臨著同樣的表征層面的挑戰,比如如何將一直生活在傳統時間里的國人帶入現代的線性發展時間,如何來展現在落后的目前狀況下展示還并不存在的社會愿景?這樣一種大的同構框架,對于現當代文學研究應該說是相當重要的,卻往往被輕輕放過。意識形態的逐鹿,使得棲居于其中的中國人,每每在與敘事的同構性相遇的時候,迷失于意識形態的標簽和圍欄中……這個問題在當代文學研究里要比在現代文學研究里更嚴重……如何走出意識形態的畛域來面對真正的敘事問題,面對中國敘事百年來的敘事現代性實驗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實驗,這本身成為遲遲得不到正視的問題。
羅嗣亮:可以把社會主義文學看做是現代性的實驗,但要說它真正能夠有多大的成功,真的是很難,畢竟它的時間也不是很長。作家本身的資質跟現代作家相比也要差一些。而且整個文學的要求,也根本就不是以產生經典作品作為方向和目的,所以我覺得,如果這樣去談,會不會是有一點對那個時代的苛求?我自己近期也比較關注“新左派”,不過他們思想大于學術,更多地是從社會政治角度關注這個問題。
張均:左翼研究的缺陷就是未能有效地解釋民族國家和人的關系。其實建立國家的最終目的還是人的自由。當我們把文學看成政治的工具的時候,其實這種工具又起著爭取人的尊嚴的作用。為工農兵服務無非是為了讓工農兵過得更好,而不是把工農兵給殺了。左翼學者這方面比較欠缺,沒有在國家和人之間建立有效關系。單講國家,對強調“人”的學者來說,確實難以接受。當然社會主義文學里的人,主要指下層,不太包括上層。
羅嗣亮:我比較贊同自由主義的文學批評說社會主義文藝比較缺少人的維度,尤其是個人關懷的這種維度。但我覺得,雖然“新左派”沒有很好解釋社會主義文學所達到的成就,但至少他們比較好地說明了,我們為什么要弄出這樣一種文學來,對歷史作了一種同情式的理解。當然這種理解可能是比較思想性的,在某些時候會經不起一些自由主義者在細節上的攻擊。我觀察到各個領域都有“新左派”,惟獨歷史學領域沒有“新左派”。但這并不能影響我對“新左派”的一些肯定性的評價。我們為什么要以這樣一種反西方的現代性的方式去塑造這樣一種文學,“新左派”比較好地說明了歷史的緣由。
王敦:我們討論社會主義文學的時候,其實往往在討論社會主義政治。這時,文學變成了政治的借代修辭。我承認,借代性修辭往往存在于語言使用的潛意識里并且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有沒有可能,我們暫時離開這個關于文學的借代性修辭,嘗試暫時回到文學文本的結構形態層面來思考問題,不帶入意識形態這個干擾因素呢?我也讀過在“十七年文學”的同時,“戡亂”時期的臺灣的某些作品,比如宣揚金門炮戰時期國民黨士兵同仇敵愾的小說。我發現,盡管兩岸同時期的意識形態完全敵對,但兩岸相同題材文學文本的結構形態卻驚人地相似:同樣地顯示出來戰友之間的情誼,弘揚集體主義的高尚,并弘揚一種抵御敵對勢力的英雄主義,顯示理想主義的信念。我發現,意識形態完全相反的文本,在很多方面,在表征手段、修辭手段上,可以是同構的。所以我想:將意識形態懸置起來,進入文學形態研究本身,確實很有必要。只有跳出具體意識形態所帶來的具體價值判斷要求,我們才能真正科學地去思考中國敘事的階段性問題。否則的話,我發現,論者很快就會把各自的意識形態立場給借代進去,很快就會變成當下“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論爭,而沒有文學什么事了。……所以我建議:何不正視這個“癥候”,何不痛痛快快地把腦子進行“分區”,一半專門負責來說用文學借代的政治,另一半專門負責說文學形態本身。這樣可以自覺地與政治修辭保持距離,避免用價值判斷來代替形式研究,免得忽略和詆毀任何作家在敘事形式上的辛勤勞動,包括避免忽略“十七年文學”的文學形式探索本身。
三
張均:自由主義認為“社會主義文學”無“遺產”可談,“新左派”則持相反意見。那么,我們怎么看?當然,直接的感受是負面“遺產”比較多。但它有沒有一點正面的遺產?我自己覺得,看社會主義必須要分階段。現在不少人把延安文學都看作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它“統治”誰呢?解放區那巴掌大的一塊很窮的,隨時可能被政府軍消滅。那時它不是統治者的文學,而是“少數者”的文學。1949年后反抗者變成了統治者,文學又面臨內在的轉換,轉到了國家認同的生產。現在很多紅色電視劇,《錢學森》啊,《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啊,其實都是那個年代集體認同的再現。這種功能很健康,也很正常,尤其那個時代我們民族處在100多年來第一次作為一個真正的民族在世界上發言的時期。這兩個層面都是值得繼承的。當然還有一個非常不能繼承的“遺產”,就是統治工具。它講一個合法的神話,一個歷史的神話或一個恐懼的故事,來統攝民眾,樹立黨的權威。這使它的“遺產”問題變得復雜而糾結。
吳敏:我更愿意用平民、群眾、民眾、百姓這樣的術語,涵義更寬泛,指各式各類的普通人,各種各樣的民眾生活形態,包括民間習俗儀式、民間的倫理觀念和好惡情感、民間藝術的模型程式等等。陳思和老師分析樣板戲中的民間文化隱形結構,分析《沙家浜》中民間戲曲式的人物關系模型,分析阿慶嫂的“江湖女人”特征,分析《紅燈記》中的“道魔斗法”,講得特別好,可以參看他在《中國新文學整體觀》里的第五章《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民間文化形態》。
羅成:吳敏講的其實很有拓展空間,周作人在《平民文學》中講了兩個標準,第一個是普遍與否,第二個是真摯與否。一個方面是要反映一個普遍的人生,而且是普遍的平民的人生,過去的文學講的都是才子佳人帝王將相,而現在要講普通人的人生故事;另外一個是有沒有真摯的情感,作品一看上去就能夠打動你,周作人提出真摯的標準是“以真為主,美在其中”。所以我覺得平民文學可能稍微比“少數者文學”更貼切一些。當張均說“少數者”的時候,我們會覺得這是一個很獨特的概念,是不是《講話》之后才有的?而用平民文學,就可以把“五四”和《講話》聯系起來。剛才吳老師一開場講我們都是毛澤東的兒孫,但是毛澤東可能本身就是“五四”的兒孫,這一點很多人不愿意承認。但很明顯的是,國民黨到了臺灣以后大力宣傳傳統文化,其實是“五四”反對的那一套東西。反過來看,社會主義文學繼承下來的東西,難道沒有“五四”主張的精神?那么張均講到每個當代文學研究者,面對比如胡風問題,會覺得有點難堪。我覺得這還是由于我們現在對于“文革”或者是社會主義這樣一段歷史沒有形成一個客觀討論。如果有可能的話,先在政治思想上把這個問題研究透徹了,當代文學本身的探討應該會有一些更重要的進展,比如說“新左派”支持的可能不是那個籠統的社會主義文學,而是帶有理想性的比較積極的健康的關注人民大眾生活的這樣一個方面,這個方面和50年代后期尤其是1962年以后發展起來的那樣一套走極端的“毛主義”可能是分開的。但這種區別完全放在文學中間沒辦法說清楚,需要站在更高的政治哲學的高度來反思。當代文學大有可為,因為我們的對象足夠復雜,它既有積極的東西,但是也有很多負面的,正是這樣一個對象才值得我們真正深入去研究。其實可以有一個“漫長的當代文學”,它從1942年一直到今天,像先鋒小說、《白鹿原》、莫言等,為什么那樣寫,其實也是要反抗或者說要拆解之前的那樣一個文學的狀態。
吳敏:如果要更具體地談“社會主義文學遺產”,我還是要再強調一下“群眾”的概念。“群眾”是毛澤東《講話》里的核心表述,1949年前后主要改稱“人民”,所謂“新的人民的文藝”。群眾、人民、民間、老百姓、工農兵這些近義詞,是從延安到“十七年”到“文革”的系列核心語匯,正是這些核心語匯及其相關的文化活動引發了很多知識分子的認同心理,成為文學發生轉折的樞紐,使得國民黨、蔣介石認為他們最大的憂患不是“外攘”的日本而是“安內”的、以“群眾”為中心的共產黨,所以,我認為這是特別重要的一組概念。當然,這些概念后來被變形,被變成“陽謀”,被拿來當做整治知識分子的思想工具,實施愚民政策的借口,被異變。但是,這些概念及其相關文化活動的正面性和反面性、穩定性和易變性、陰謀性和陽謀性、理論性和實踐性,特別值得人們關注研究。
張均:用“少數者”或者“平民”的概念的區分,在于文學曾經有過的事實狀態與我們希望文學達到的狀態,兩者不太一樣。革命文學確實是站在下層立場上來談問題的,它里面既有人性的溫暖,也有殘酷的東西,并非全民的,不面向所有人。所以林崗老師說,《暴風驟雨》這種小說是冷漠的,沒有人性,但事實上,它對下層農民很有人性關懷,對地主則很欠缺。所以說這類文學是“少數的”主要是就事實而言,但我們可以期望文學有更好的理想狀態。
羅嗣亮:我覺得用“人民文學”來概括從1942年到1976年的文學更合適,因為那個時候,說是平民的話,也不太可能。平民的概念在于它包括知識分子,但是工農兵可能又會更加偏激一點。
吳敏:“人民文學”在1949年前后是被用得最多的詞,所以吳組緗說,如果是人民好了,那么多人好了,我們知識分子寧愿吃一點苦也可以,但是,“人民”又是一個陰謀和陽謀……
羅嗣亮:我對遺產的看法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精神的遺產”,因為從藝術性的角度講可能不是很好。那么這種精神,一方面是作家的精神。無論是作家也好,共產黨也好,其實都處在轉型過程中,因為這些人本身都是從傳統中走過來的,所以自然有些不現代的地方,但這一代作家的價值之所在,主要是提供兩種精神,一種是獨特的公共精神,這跟我們現在談的批判性的公共精神還不一樣,他們是一種擔當社會責任的自覺,對國家命運的自覺。我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美國學者列文森研究明代畫家董其昌的一個結論,他講,董其昌畫畫得很好,但又自認為畫畫不過是雕蟲小技。古代文人是把藝術當做一種非常小的東西、不足以安身立命,但是“毛時代”的作家,即使把文學作為某種工具也好,畢竟是通過這樣使文學有了一種擔當的公共精神。后面的作家在這一點上對他們有繼承,傷痕文學也好,改革文學也好,都繼承了一種公共的精神。第二種精神,就是他們對社會生活有一種審美的自覺。我曾經讀到近代作家在報紙上發表啟事去尋找“創作”材料,這說明作家的生活視野實在太狹窄。應當承認,“毛時代”的作家對生活的視野,一定是比傳統作家更廣。另一方面是作品的精神,作品現在雖然否認得很多,但得承認它們在道德、信仰上的力量。同時,這個時代的作品透露的草根美學趣味,我覺得還是應該承認的,也是為后來的作家所繼承的。
吳敏:從延安到新中國成立的“十七年文學”,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歷史演變的一環,很多作品在歷史的長河中會逐漸消失,然而,它們卻是新時期文學發展的鋪墊,是很多文學家成長的基石和土壤,譬如莫言、陳忠實等眾多當代作家就是踩在趙樹理、踩在《創業史》的基石上成長的,后來的很多作家清洗、吸收、消化、改造了社會主義文學中的若干元素,開辟了更為廣闊的創作道路。沒有延安、“十七年文學”階段的土壤,就可能沒有后來的許多文學大家,當然也可能會出現另種類型的文學家。也許過若干年以后,這個時期的創作就是某種新文學的“引子”或“前言”,然而,這終究是一個新的開始。啟蒙型的知識分子,如果沒有認知、情感的轉型,寫民眾時有時的確很難擺脫高高在上的潛意識,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里富農家的女孩就是漂亮,農民家里就是臟,(笑),周揚的感覺是很敏銳的……但在趙樹理那里,這些人就可能是自己的親人,當然也可能是仇家,但應該是關系很近的仇家;到了莫言這里,就是“我爺爺”、“我奶奶”、“我父親”,普通民眾以及與之相關的民間藝術真正走進了作家的審美視野,盡管其中裹雜了諸多落后文化的內容,但這種創作方向的轉變是根本性的,是魯迅的時代很難做到的。在我看來,這正是我們今天談論“社會主義文學遺產”的主要用意之一。
(錄音整理由中山大學中文系研究生張楠、鄭甜甜兩位同學承擔,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