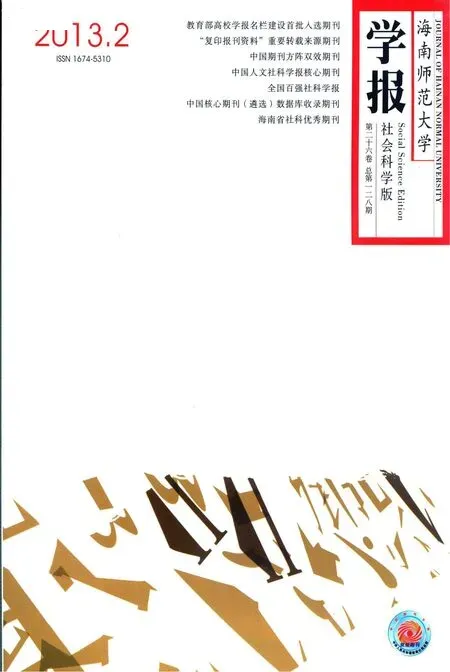反思傳統與悼念青春的孤本書寫——評房偉長篇小說《英雄時代》
王金勝 段曉琳
(青島大學文學院,山東青島266071)
當下文壇,房偉具有批評家、詩人、小說家的多重身份。他以其銳利、勁健、思辨和突出的問題意識,成為很有特色的“70后”文學批評家。相比之下,在《英雄時代》出版之后,作為小說家的房偉,也開始建構起一個清晰的個性化文學形象。《英雄時代》是一部在戲謔與油滑中,飽含真情地反思傳統與悼念青春的“孤本小說”。彌漫于整部小說的情感基調,是一種解不開的青春情懷與抹不去的英雄情結。小說讀來,樸實中有奇崛,讀后細細回味,卻滿心蒼涼。
一 反思傳統與文化批判
《英雄時代》首先吸引讀者的,恐怕是故事中套故事、雙線齊頭并進的交叉/對比敘事模式。小說在肉聯廠的快意恩仇里,穿插著一個武松和潘金蓮的傳奇故事,前者是充斥著肉腥氣的庸常現實,后者是滿含感傷情懷的英雄幻想。兩個故事在主題上是一致的,在精神氣質上也具內在貫通性,英雄武松與俠女金蓮,既是建民與王梅的情感寄托與理想化身,又是建民與王梅的庸常現實在浪漫想象中的映照,有時《打虎記》的情節進展則更像是建民與王梅的情緒與情懷的慣性延伸。另外,兩個文本在敘事上都帶有傳奇與荒誕的色彩,更重要的是,兩個文本都是在批判傳統的基礎上思考自由、青春、激情與夢想,在荒誕又真實的體驗里去緬懷曾經的英雄時代。
《英雄時代》以審美的方式質疑著人們對俗常世界及其歷史—文化邏輯的認同:“我固執地認為,有關自由、青春、激情和夢想,一定要以對文化傳統的批判為基礎。這并不是說我們的傳統不好,而是這些傳統在接受的過程中,總存在著被簡化為道德符號的危險,而成為‘瞞和騙’的伎倆、‘借尸還魂’的工具。我們對傳統的選擇,不應是捍衛,而是要以‘當下’作為檢驗。對中國傳統中高蹈流走的風致,自由奔放的精神世界,自當向往之、推崇之。”[1]作者在批判傳統的基礎上,緬懷著那個久已逝去的英雄時代。一方面,小說追溯歷史,對文學發達、風采天下、繁華無比的宋王朝進行了深情的追憶與緬懷,通過重構大宋燦爛輝煌的文化場景,呼喚著理想的強大的文化和文明,并從中求得文化再造的偉力。這一部分寄寓著作者的理想、青春、希望和熱情,呈現出一個充實飽滿、熱情真誠、激情充沛的作者形象。但作者最終的目的并非在此,他所要做的是從歷史和現實的隱蔽聯系中尋找真實的惡性遺傳因子,將現實生活與大宋王朝故事在某種程度上相互參照、印證,作為我們對自己置身其中的文化空間的精神事實的鏡像,由此引發人們對現實的重新反思。
《英雄時代》隱含著諸多文化母題。首先,看客/庸眾意象。在《英雄時代》中,出現了三次大的看客場景:虎肆看客、武松決戰西門慶時的看客和金蓮之死時的看客。
一只落寞而又孤獨的瘦虎因落難于虎肆,成為各色無聊看客的消遣。在這一場看客的表演里,庸眾的無聊、鄙俗與矯情躍然紙上。對那些無聊看客來說,“看”這樣一只皮毛像破地毯一樣的瘦虎本身是無聊的。那么如何才能讓“看”變得有聊呢?那便是矯情。通過矯情地夸張、矯情地表演,看客在看虎與表演看虎間獲得精神的自娛和對自身的肯定。沒有人真正關心這只瘦虎,更沒人關注過它的尊嚴與靈魂。孤獨而落寞的王者,變成了被咀嚼在看客口中的渣滓。只有與它一樣落寞而又無路可走的邊緣人——武松,才可以靠近它,理解它,看到它內心的尊嚴與力量的強大。也只有這虎與武松才真正明白這些看客的“無聊”與“矯情”,“淺薄”與“鄙俗”。
看客/庸眾的胃口是永難滿足的,這一點在武松決戰西門慶時得到了極致的體現。這場本來四個回合就可以了結的打擂,卻因為看客的不滿硬生生地拖了十個回合。為了滿足看客鑒賞暴力之需,武松先后把西門大官人打倒了十次卻不殺他。后者每摔倒一次,大家都會發出一陣或大或小的哄笑,一些同情弱小的婦女們還自告奮勇地給西門慶送水、擦汗,鼓勵他繼續上陣。最后,西門慶不堪眾辱,一頭撞上槍頭,用噴涌的鮮血結束了這場冗長的決斗。但如此死法,不僅不能得到陽谷縣民的諒解,反而引起了他們的不滿:“這樣自己送死算是嘛玩意兒呀!”這一段關于看客的描寫,庶幾近乎阿Q之赴刑場。無聊與麻木,不滿與抱怨,“哄笑”與“同情”,是看客們麻木、殘酷和對生命的冷漠的見證。
與武松不同,風塵俠女潘金蓮以自己的特立獨行、潑辣任性,挑戰、耍弄了這幫無聊鄙俗的看客/庸眾。正如魯迅《復仇》里持刀對立于曠野的裸體男女,她總是不愿給那些無聊的看客以痛快——無論是“擁抱”抑或“殺戮”。在羅生門般的金蓮之死中,她的每一種死法,都沒給那些焦渴的看客們以滿足。庸眾們盼望她在受盡折磨后問斬,可她偏偏等不得秋后,就先收拾干凈了自己,拿褲腰帶裸體上吊了;庸眾們盼望她在騎木驢的時候經受百般折磨,痛不欲生,可她偏偏就掙扎了一下,就大出血而死,讓庸眾們看了個不過癮;庸眾們盼望著她能從獅子樓上一躍而下,摔成肉餅與血漿,可她偏偏穿上飛行器,在眾目睽睽之下化作大鳥飛走,把一群人晾在擂臺前發傻。無聊的庸眾被給予了無聊,這是對無聊庸眾的最大的嘲弄與報復。
其次,阿Q精神與國民劣根性。《英雄時代》中最阿Q的莫過于武大。在西門慶狂熱追求潘金蓮,全陽谷縣都知道武大要戴綠帽子時,武大卻以詭異的邏輯安慰自己:“武大是個有理性的人,金蓮只和他上過一次床,原來是弟弟的相好,要說戴綠帽子,那也只能是他先給弟弟戴綠帽子,西門慶再給他戴綠帽子,自己也并不吃虧。”但與阿Q相比,小說中的武大更為聰明和狡黠。他不但擅長自欺,也擅長制造輿論。他像一個喜劇版祥林嫂,向那些中老年婦女訴苦,用深情款款而又苦大仇深的語氣作開場白:“這些年的事情,不說也罷……”于是武大開始了為自己的辯護,儼然他是一個有涵養有道德,卻馴妻不成反受盡委屈的典型好男人。但庸眾們更關心的是他與金蓮的房事,于是武大便聰明地忸怩著紅著臉說:“你壞!老問人家的隱私。”于是婦女們歡笑了,“街上充滿了快活的空氣。”無聊的庸眾碰上同樣無聊而又甘為笑柄的訴主,那剩下的就只有“快活的空氣”了。武大可謂小說中最為粗鄙的人物。他既是可以和老寡婦泄泄火的猥瑣小市民,又是不愿獨自贍養老人的小心眼;他既是不會發火只會發牢騷的娘娘腔,又是用大煙殼子水做炊餅的無良小販;他既是偷窺金蓮的齷齪奸尸犯,又是愛貪便宜、仗勢欺人的無恥之徒,還是利用武松之名發橫財的奸商。就是這樣一個無恥自私的侏儒,在潘金蓮裸體雙刀大戰西門慶時,不僅不敢跟欺負自己妻子的西門慶叫板,卻指責孤立無援的金蓮為“淫婦”,儼然一個道德衛士與中華大丈夫。此外,小說直指中國文化與千百年來國民性的積習之處頗多。比如,大宋朝也有愛“揩油”的路士,有喜歡“瞞和騙”的梁山泊,有“愛面子”的大宋皇帝。
再次,偽道德與假正經。肉聯廠的王梅與《打虎記》的金蓮,都曾遭遇過道德輿論里的“被空氣化”與“臭帶魚”效應。庸眾是很聰明的,庸眾的道德更加聰明,他們不能直接傷害你,卻可以突然“糊涂”起來,裝聾作啞,裝腔作勢。中國的道德往往呈現為一種社會輿論而非信仰而存在。它不能阻止一個人做壞事,也不能促進一個人做好事,但它能改變一個人做事的環境。就連妓女也成了高尚的道德衛士。小說中的張大戶自稱是傳統理學的信徒,卻以用理學把辣妹們改造成溫順的大嫂為己任,是個“具有守成主義思想的文化衛士”。他沉醉在這一道德拯救的幻覺中,甚至想立即寫信給汴梁的理學大師們,向他們介紹心得體會。張大戶可以看作是中國偽道德家的典型代表,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道德模樣的假模假式,一旦過頭就成了矯情。比如王梅,口中談著墮落,手上卻又裝模作樣地扶了扶副廠長送她的鉆石耳釘。來肉聯廠視察的省領導,個個假模假式的正經體面,酒席上卻是葷段子不斷,手底下不安生。就連武松當上都頭之后,也變得有些假模假式了,平時叫金蓮“小阿蓮”,現在叫人家“大嫂”,還故意為了避嫌去送花石綱。最可笑的是宋江,打著“替天行道”的旗號,燒殺搶掠,活活淹死十萬宋兵與五百梁山義軍,讓戰斗變成了屠殺。
二 反抗“被安置”與英雄存在的可能
當現實以龐大而堅固的異己面目和敵對力量出現時,個體自我的微不足道感便油然而生。在這種現實、環境、氛圍中,個人無法擺脫那種強烈的“被安置感”。盡管小說只是在最后一章里提出了關于“安置”的人生命題,但無可否認的是整個文本都在表達著強烈的“被安置”的生存/生命狀態,以及作家對“被安置”命運的抵抗。
王小波曾說:“對生活作種種設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設置動物,也設置自己”,[2]129“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置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2]131在中國傳統的道德認知系統里,武松被安置了“打虎英雄”稱號,活在眾人的膜拜里;金蓮被安置成了“淫婦”,活在歷史的罵名里。處于現實生活和權力關系中的人,總難以擺脫“被安置”的命運。王小波之所以一直懷念那只“特立獨行的豬”,不也是因為在40年的人生歲月中“除了這只豬,還沒有見過誰敢于如此無視對生活的設置”。人遲早是要被安置的,不同的是,有的人被安置了就忘了是被安置的,“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素”。[2]131而另外有些人,卻懷有清醒的記憶,發出痛苦的呻吟。武松是不是英雄?放眼中國歷史,英雄大多為用刀劍殺人者,用道德殺人者,用仁義殺人者,殺男人,殺女人,殺潘巧云、殺閻婆惜、殺潘金蓮。但房偉的武松不是這樣的英雄,這個武松有異族血統。他喜歡發明,他可以裸奔,可以呼嘯心中的躁動。作為梁山好漢,他不粗野,甚至有些郁達夫式的文人感傷氣質,論其性情,也并不像他的外表那樣強悍。這個武松更像是個行走在路上的邊緣英雄。他想習文,卻被汴梁的附庸風雅倒了胃口;他賣牛雜,卻不會搔首弄姿地“叫先”;他想進禁軍,卻被高衙內的潑皮朋友頂了名;他進了柴府,卻因為沒有后臺推薦而只混了個三級武師;他斗殺了西門慶,卻落得個刺配滄州;他上了梁山,卻最終成了招人恨的“欠揍派”,為各大集團所不容;最后又在梁山一個歡慶勝利的晚上,他神秘地失蹤了,他的去向就像潘金蓮一樣成了“羅生門”。武松似乎總在碰壁,總面臨無路可走的人生困境。他與虎肆中的猛虎,像一對同病相憐的老友,一樣的遍體鱗傷,一樣的苦悶彷徨。這英雄武松,正如作者所說:“不是以道德殺人的黑社會分子”,也不是“打手”與“大哥”,而是“一個浪漫多情的武林高手,一個善良而不走運的民間英雄,一個游離于體制之外的個人主義英雄,一個不甘束縛、不相信謊言的人格高貴的騎士,一個向往自由與冒險的行吟詩人”。
房偉的金蓮,也一反傳統道德的“淫婦”設置。她敢愛敢恨又重情重義,率直坦蕩又獨立特行。她是個風姿綽約且身手不凡的俠女、英雄。她有傳奇般的經歷。在幼年坎坷遭遇之后,她成了名震京師的女撲手。遇到武松之后,她陷入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戀,若不是因為重情義,也不會落入張大戶的手中。可金蓮畢竟是金蓮,她就是不給張大戶痛快,也不給武大痛快,她開豆腐店,實現了經濟獨立。武松歸來,她不是投懷落淚,卻只將鴛鴦刀劈頭而來,不言不語,卻勝千言萬語。當“打虎英雄”武松當了都頭也有點“假模假式”之后,她又氣又恨。面對著西門慶的處心積慮,金蓮并沒有半推半就,而是雙刀戰雙刀來了個裸體對決。她踢殘了王婆,又狀告西門慶殺人,卻成了道德輿論的犧牲品。在武松斗殺西門慶時,金蓮悄無聲息地消失了。恰恰拒絕“被安置”的武松金蓮,才是有著真性情的真人,他們身上有著理想的人性與理想的性格。
在小說的現實敘事部分,這種對“被安置”命運的抵抗,寫得更觸目驚心。劉建民,一個熱愛文學的工科大學生,被安置到冷硬、機械、充滿血腥的屠宰車間,從事與自己所學和興趣毫不相干的工作。理想、激情被殘酷的現實無情地放逐。王梅,大學外語系的畢業生,一個漂亮雅致,自視甚高,遺世獨立的林黛玉式的女子,也不得不整日面對鮮血淋漓、皮肉飛濺的殘酷現實。為擺脫“一地豬毛”的工作,她屈從于權力的淫威,委身于副廠長。不僅是他們,瘋瘋癲癲的“至尊寶”、懷才不遇立志考北大研究生的老崔、“公共汽車”二妞、風騷辣妹徐姐,同樣無法逃脫“被安置”的困境。
在與中國底層現實的切身搏斗中,房偉切膚地感受和認識到這種生存/文化現實的影響和牽制力量。正統文化觀念的巨大惰性力量,無孔不入的權力控制,無所不在的利益交換,隨處可見的勾心斗角,構成了環環相扣的現實鎖鏈,一種難以掙脫、更難變更的強大現實力量。主體與外在的現實客體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使青春、激情、詩性、浪漫、理想統統遭到了無情嘲諷和殘酷打擊。面對這種現實,劉建民或在冥想和幻化的世界中得到解脫,或通過玩世不恭的言行得以宣泄,或通過小說寫作釋放自由奔放的生命……他始終未屈膝于副廠長和嚴書記的權威,始終有對自身命運和尊嚴的掌握。他恪守著自己的生命原則和信念。但最終王梅成了自暴自棄的婦人,劉建民離開工廠做了個體屠宰戶,起早貪黑地忙活,向工商稅務部門小頭頭行賄。就連那本承載青春記憶的《打虎記》也被燒成了一團黑色的灰燼。
“歷史上的偉大作家大多是文化上的異端。”[3]真正的文學是一種對抗性的實踐。它要對自己置身其中的歷史文化空間說不,要反抗社會禁忌和一切不人道的異己力量,無論它是政治觀念、意識形態,是市場、利潤、商業意識形態,還是當下風行的身體、欲望、日常意識形態。唯有反抗總體性話語,文學才能獲得自身生長的力量,才能突破自身被異己力量同化的命運,并最終獲得自己在人類精神生活中存在的合法性。對現實的懷疑、介入和批判,是衡量一位作家文學素養和文學抱負的基本尺度。在略薩看來,“重要的是對現實生活的拒絕和批評應該堅決、徹底和深入,永遠保持這樣的行動熱情——如同堂·吉訶德那樣挺起長矛沖向風車,即用敏銳和短暫的虛構天地通過幻想的方式來代替這個經過生活體驗的具體和客觀的世界。”[4]當虛無主義、相對主義、功利主義、享樂主義成為了我們的生活信念和生活原則的情勢下,將自我從日常化寫作的囚籠中解放出來,還給他廣闊的精神視野和責任倫理的承擔,是何等的必要。
《英雄時代》就彰顯了這樣一種極可寶貴的精神力量。房偉小說在對自我及其價值、歸宿的審視和尋找及其表達上,有自己的獨特之處。房偉對自我價值的尋找和審視,既非外在于自我,從外部現實中尋得自身價值的皈依,也非僅從個體得失的角度來權衡。他是在歷史與現實、傳統與當下的糾纏、交錯中,在個體與歷史、文化的深刻聯系中,尋找自我的位置和價值的。這其中有質疑,有悲嘆,有思考,有孤寂,有冷嘲熱諷,有游戲幻化,有現實與人心的陰暗,也有生命的沉潛與躍動,有痛苦的絕叫,也有詩意和想象力的飛揚。
從深層看,小說這種混雜的敘事風格關聯1990年代以來知識精英啟蒙理想的困境,其癥候之一便是“英雄”的末路窮途。1980年代,在“新啟蒙”浪潮的沖擊下,革命文藝“英雄”形象轟然倒塌。在經歷了“傷痕”、“反思”、“改革”文學對“英雄”祛神圣化的人性化演繹后,1980年代中期開始,顛覆“英雄”神話與解構“史詩”成為文學敘事的主潮之一。作家們紛紛從民族、國家、人民、階級立場回撤到私人立場,宏大敘事分解為“小敘事”,崇高、莊重的敘事風格就此瓦解。1990年代,現代性時間觀徹底被后現代性空間觀取代。失去了由總體性統攝的現代性/時間,“英雄”也就失去了生長和存在的可能。由此,由個體生命意志對抗群體權力而產生的強烈悲劇意識被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世俗、卑微的個體,日常還原,零度寫作,是自由意志的消歇、反諷策略的興起,是“人”的解構。需要指出的是,房偉的生活和閱讀閱歷,使他既難以完全認同1990年代以來的犬儒化敘事,也難以完全接受魯迅那樣韌性決絕的啟蒙精英話語。在一個“準個體”時代,1980年代那種穿越歷史時空和一切文化藩籬的“英雄”,就像印家厚們一樣,不會是房偉寄托情志的對象。經歷了現實無情的抽打和磨難,他不愿跪伏于磨難與挫敗之下,做一個渾噩唯諾度日的人,但也難以做一個徹底與悲劇性人生做決斗的人。在“小人物”、“順民”和“異見者”、“英雄”之間,他在探討第三種可能,于是就有了劉建民這樣將頑童的游戲心態、青春的熱烈激情、多愁善感的憂郁情結、中年的滄桑孤獨融為一體的形象,有了這樣一個想象力飛揚、世俗粗鄙而充滿活力的小說世界。《英雄時代》最動人的地方,也許就在于一種存在于英雄與凡俗、崇高與世俗、游戲與莊重之間的張力。
作家是從自我與外在的現實與人生的關聯中,以質疑/否定外部現實和人生的形式,執著于詩意/希望的找尋。小說中充滿了對庸常現實與人生的呈現——灰色的生活,物質的渴望,欲望的景觀,尤其是在劉建民、王梅“反成長”的成長故事中更讓我們看到了心靈的隔膜、靈魂的破敗和生命的衰朽。這本是一種1990年代以來小說中最常見的敘事經驗之一,但房偉在講述這一些故事時,是懷著一顆溫暖的、詩意的心——它曾被視為軟弱的、無力的,甚至是過時的。但恰是這樣的“心”才最有力量。這顆“心”有沉重的體驗、絕大的悲哀,有著屬于作家自己的歷史和現實的境遇。作家通過這顆“心”建構了他與歷史和現實的關系。生命內覺的被觸發,誕生了《英雄時代》的奇幻景觀。
三 堅硬的現實與強勁的想像
在價值荒蕪的時代,曾經熱血充盈的青春之軀,在現實日復一日的踐踏蹂躪下日益剝落銷蝕。靈魂也漸趨粗糙、荒涼、冷硬而孤寂。但富有血性和激情的心靈,也在頑強地向詩意最深處掘進。如果說,反思傳統與文化批判的部分集中體現在《打虎記》里,那么《英雄時代》里關于肉聯廠的主線敘述則更多地承載了作者的青春記憶,那是一種帶著點意識流的,帶著點肉腥氣的,陽光燦爛的記憶,又是一種抹不去的,悵惘的,帶著血和淚的青春情懷。青春,總是承受著躁動的迷惘與灼人的痛楚。《打虎記》用春夏秋冬四個季節寫了武松情欲的躁動與愛情的萌發。當他在那個煩躁多雨的夏天,憂郁地感慨“他很怕失去金蓮,因為他把握不住金蓮,正如他把握不住那個多變的夏天”時,當金蓮與武松在冬至那天夜里,爬上古槐盟誓后,金蓮凝望著宇宙蒼穹,想“那些不是星星,而是雪的眼淚,是女人梳頭時散落的新羅玉珠,是漫天被凍結的五顏六色的山盟海誓時最美麗的語言”時,記憶中那最深處的溫柔與感傷被無意間觸動,激蕩起曾經的青春年代里碧色的漣漪。但當青春夢醒時,激情變作滄桑,自由不過是短暫的自欺欺人,現實仍舊是庸常的瑣碎與平凡。劉建民與王梅并沒有獲得自由,而是為了生存也選擇了他們曾經不以為然的手段。
盡管青春的記憶里總有蒼涼的底子,可到底還是懷著英雄幻想去追求自由、激情與夢想。青春的喜與狂、傷與痛,都在最灼人的痛感里,如此真切地證明“活著”的真實。在《英雄時代》這部看似游戲的小說里,在油滑與戲謔之下,是作者悼念青春的全部真情。這種激情在小說結尾處的“老虎”意象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也許,這世上本就沒什么英雄,在我甜美的夢中,武松逃離了紀律森嚴的城堡,正像一只強壯的老虎,奔向那無限廣闊、無限美麗的森林原野。武松要去找他心愛的女人金蓮,他永遠在快樂地奔走,他永遠在路上。”
關于青春的記憶和敘述,需要的是一種奇譎瑰麗的想象和精準的語言。惟此,才能使最難以傳達的最真實的青春體驗窮形盡相。相對于主題、內容而言,小說中奇譎的想象與精準的言說所帶來的直接閱讀快感,讓人有更深切和久遠的體驗。小說一開篇即借助想象對食品廠進行了神采飛揚的頗具油畫風的皴染,骯臟淋漓的工廠在“我”的想象中成為了“莊嚴、肅穆,充滿了神秘的氣息”的中世紀歐洲城堡。運送活豬活牛的車“都是些英俊的高頭大馬,神情高傲突兀,披著厚厚的黑色馬甲,只露出兩個馬眼看清楚敵人和前方的路”。而作為肉食加工車間工人的“我”則化身為“歡送他們的號手,為他們吹響滿懷信心的出征號角”。當騎士們滿載牛羊和女人而歸時,“我滿懷崇敬地守在城堡門口,雙手舉向天空,向勇敢的騎士們歡呼,并以上帝的名義祝福他們。”于是,在這個中世紀的歐洲城堡中,在浪漫瑰麗的騎士傳奇里,一場場青春的快意恩仇上演了。不管是屠宰廠里的大起大落,還是“燕麥小子”的浪漫幻想,不管是武松金蓮的愛情新寫,還是梁山故事的現代重構,作者在現實與想象的交叉敘事中,飛揚著叛逆與反思的翅膀。
除此之外,作者的想象力還在屠宰廠里的快意恩仇與武松金蓮的歷史傳奇中多有體現。這些部分往往寫得瀟灑自信而又有著恢宏瑰麗的氣度,有著魯迅所極度贊賞的唐傳奇之風。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有言:“傳奇者流,源蓋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故所成就乃特異。其間雖亦或托諷喻以紓牢愁,談禍福以寓懲勸,而大歸則究在文采與意想,與昔之傳鬼神明因果而外無他意者,甚異其趣矣。”[5]魯迅所激賞的,正是唐傳奇的“文采與意想”和“想象”,這正是它與其他以道德勸誡為目的的小說的不同。且不提老鄉與工人們械斗的跌宕起伏,也不提二妞事件里“豬戰群雄”的大氣精彩,且不說“翡翠綠青蛙”事件的詼諧諷刺,也不說武松與史進“茅廁面條戰”的幽默犀利,單單是“金蓮裸體大戰西門慶”這一節,其壯觀程度,惟金蓮雙刀戰武松與武松斗殺西門慶可與媲美。關于金蓮之死先后有四種說法,且一種比一種生動傳奇。先是說金蓮被挑斷了手腳筋入了女牢,判了斬立決,在當了“小凳子”與被“鹽水灌腸”的折磨后,未等及秋后問斬,就脫盡污穢,干凈體面地全裸自縊身亡;第二種說法是金蓮因是“淫婦”而被當街騎木驢大出血而亡;第三種說是金蓮在與官兵的包圍戰中,被砍四十多刀,成了肉醬,后隨大雨沖走化作了春泥;第四種則更加傳奇,說金蓮穿了武松發明的飛行器,“化作大鳥”高飛不見。在這里,“文采與意想”,“想象”構成了小說的本體質素,被放在了敘事作品的價值高端,成為作家展現文學追求和人生理想的重要方式,是文學對抗庸常現實的重要方式,充滿了智慧的快樂和創造的喜悅。
與這奇譎瑰麗的房式想象相一致的,便是獨具特色的房式語言。在《英雄時代》中,作家展現出了他令人驚嘆的語言駕馭能力,精確而形象,生動而犀利。只有對生活的質感有著最敏感的體驗與捕捉的人,才會流淌出如此具有藝術個性的語言。在這里,姑且將《英雄時代》最具有房氏個性氣質的語言,稱之為“屠式語言”。這是一個發生在屠宰廠里的“英雄故事”,于是小說敘事也采取了屠戶式的視角與敘述語言。有些詞句相當精彩。比如“我蹲的姿勢很古怪,幾乎就要坐到地上了,屁股和地面的距離就差橫放一條小火腿腸的寬度。”(第3頁)①本文正文中標注頁碼均見房偉:《英雄時代》,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王梅則‘砰’一聲倒下,像一袋子豬肉倒在了案板上,很快發出粗重的鼾聲。”(第6頁)“(嚴書記)他一直閑得發慌,本就肥胖的身體日益豐滿,陷在寬大的藤椅里,活像絞肉機卡住了半噸豬肉。”(第38頁)“這些風憲官就像六個月的小公豬一樣無法無天。”(第68頁)“那個‘微笑’就會像豬尿泡一樣迅速發酵、膨脹,直到最后在空中撐破,發出一連串低沉而羞澀的聲音,好像一把殺豬刀砍在了豬的大腿骨上。”(第116頁)這些語言,在房偉的筆下流出,是這樣的自然,在屠宰廠的英雄傳奇里又是多么的和諧。這樣的在屠戶視角下流淌出來的屠式敘事語言,是《英雄時代》最突出的語言風格,幽默風趣而又機智準確,獨成一體。
除卻“屠式語言”,房偉還在《英雄時代》中展現出了他獨特的藝術敏感,并用最為質化的語言,準確地表達出來,在這些精準的語言之下,飽含著一個作家最生動的生命體驗與最深刻的青春記憶。比如“我曾看到冷凍車間的臨時工大老李,偷偷從冷庫順出一只豬腿,豬腿上閃爍著青冷幽光,仿佛我的小說中武松使用的雁翎刀,寒光閃閃,照亮了多年后睡夢中我甜美的笑容。”(第6頁)“如血的夕陽像漫天的紅汞壓迫在每一個帝國公民的心上。”(第31頁)“馬蹄鐵敲擊在石子路面,發出好聽的音樂聲,像是空中飄滿了快樂的冰糖。”(第50頁)“熟睡的栗色戰馬,并肩而立,月光劃過它們光滑的脊背,如同騎士鋒利的劍劃過湖水,是那么美麗而迷人。”(第63頁)這些最能抓住讀者心中最敏感的溫柔的語句,是作者對于生活最具個性的體驗與對個人記憶最精準的表達。
[1] 房偉.后記[M]//英雄時代.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282.
[2] 王小波.一只特立獨行的豬[M]//王小波全集:第一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3] 余虹.文學知識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67.
[4]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給青年小說家的信[M].趙德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67.
[5]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