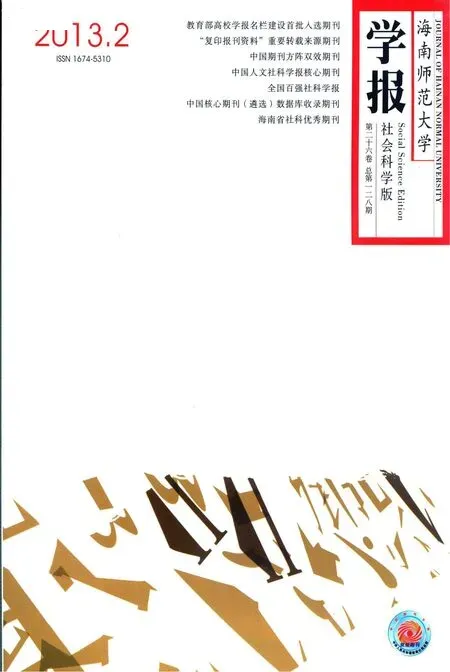對中國鄉村的“小歷史”敘事——讀畢星星的《堅銳的往事》
傅書華
(太原師范學院文學院,山西太原030012)
畢星星在《堅銳的往事》的《自序》中說:“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宣布:他要把非虛構文體打磨成一種利器,為人類書寫記憶的權利而戰。紀實,成了一個全球性的文學現象。2001年,也是‘諾獎’設獎百年紀念,瑞典文學院以‘見證的文學’為題召開了一個研討會,各路巨匠提出,希望文學起到為歷史見證的作用,作家應該記錄歷史的真切感受,用自己的語言對抗以意識形態來敘述的歷史和政治謊言。”畢星星說他因此“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暗暗堅定了自己的選擇”。[1]
我不能判定紀實是否成了一個全球性的文學現象,但我卻分明地能夠感覺到,1990年代之后,中國的思想標高、精神深度,是通過民間性的“小歷史”對歷史的紀實性思想性文字來體現的。所謂的“小歷史”與“大歷史”,是西方新歷史主義的一對概念。西方新歷史主義認為,歷史化的文本有兩種,一種是單數的大寫的歷史,一種是復數的小寫的歷史。譬如說,占統治地位的正史屬于“大歷史”,集中的統一的對歷史的闡釋屬于“大歷史”,基于某種觀念形態下對歷史的闡釋屬于“大歷史”;各種野史稗說屬于“小歷史”,分散、零碎的對歷史的闡釋屬于“小歷史”,私人性經驗性的對歷史的敘說屬于“小歷史”。之所以說1990年代之后,中國的思想標高、精神深度,是通過民間性的“小歷史”對歷史的紀實性思想性文字來體現的,從遠里說,是因為中國有著久遠的歷史文學不分的傳統,如《史記》等等;從近里說,是因為面對今天的價值失范,自覺地或不自覺地需要通過憶舊來尋求新的價值資源以支持自己失衡的價值天平,這就是今天憶舊得以盛行的主要原因——無論是紅色文化的再度出場,還是對歷史真相的重新打撈,抑或對舊聞舊事的興趣,或是百姓、坊間普遍的懷舊情結等等。而民間性“小歷史”對歷史的紀實性思想性文字之所以在這其中能夠獨占鰲頭,一是因為時代性的原有價值大廈崩塌之后的普遍的不信任、懷疑而導致的重新認知事實真相的沖動、需求;一是因為作為單數的“大歷史”對歷史的敘說無以滿足上述的沖動、需求之時,“民間”作為復數的“小歷史”對歷史的敘說就得以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地“浮出歷史地表”。于是,我們看到了種種“非虛構寫作”的盛行,于是,我們看到了種種“一個人的歷史敘事”倍受讀者的歡迎。
一
畢星星的《堅銳的往事》就是這其中的一份努力,就是這其中的一項碩果。它偏重于對中國鄉村歷史真相的重新打撈,而在這種打撈時,又因為作者親身體驗的真切,加上作者理性認知的深刻,從而修正、重建著我們的鄉村記憶,讓我們有了“去蔽”之后得以“澄明”的快意。
說起來,像我這樣的即將進入花甲之年的一代人,我們對中國鄉村的記憶,最初是通過那些寫土地革命、土改、合作化運動、農村階級斗爭的小說而得以完成的。我們對這些“文本的歷史”曾經深信不疑,而沒有看到這些“文本”的書寫,是為“權力”所“制約”,是“歷史的文本”。直到我們下鄉插隊,面對真實的中國鄉村時,我們也還在時時懷疑自己真實的所見所聞,這樣的認知“病癥”,在原本就在鄉間生活的農村青年身上體現得更為突出,他們寧愿相信“文本”而不相信自己親歷的真實。倒是不怎么識字的作為我們上一代的鄉間老農,他們只立足于自己私人性的切身的生存利益,從而能夠“本能”地去除“文本”對“真相”的“遮蔽”,說出類如《皇帝的新裝》中小孩子所說出的真話來,并因此每每讓我們這些被“文本”“遮蔽”了雙眼、不相信自己雙眼的人,大吃一驚,目瞪口呆。直到多少年后的今天,當我們知道了“懸擱一切價值判斷”“直觀事物本身”時,當我們知道了一切歷史都是“文本的歷史”而“文本”又因為“權力”的“制約”而是“歷史的文本”時,當我們知道了“修改教科書”能夠修改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歷史記憶時,我們才深切地體會到,我們作為有“文化”的“知識青年”,我們應該有責任重新回望我們的鄉村歷程,我們應該有責任重新書寫我們的鄉村記憶。因此,我們愿意伴隨畢星星,重新開始我們對中國鄉村的回望與反思。
或許是因為畢星星是文化人的緣故,或許是因為文化是鄉村變革的最為深刻的標志,總之,畢星星的這本《堅銳的往事》主要是以文化特別是以文化的直接載體——文化人為主線,寫在“權力”的規訓下,寫在城鄉文化的沖突中,鄉村文化的種種表現形態,進而來揭示中國鄉村的歷史真相。
《特級教師南巖之死》被多家選本選入,并曾獲冰心散文獎、趙樹理文學獎,在畢星星的作品中,最受文壇好評。在幾十年的農村政治革命中,原有的自然經濟基礎上形成的鄉村民間文化及文化人最受摧殘、蔑視,被傷害、改造的程度最重,即使是在“十七年小說”這種被規訓了的“歷史的文本”中,我們也時時可以看到這樣的印痕:譬如這些小說中的一個主題范型就是,作為新的政治文化載體的青年農民與作為原有的鄉村民間文化載體的老一代農民的沖突。但鄉村的文化人卻在這種劫難、坎坷、磨難中,默默地執著地堅守著自己的位置,從而使鄉村文化的長河得以在田野的大地上延伸、流淌。鄉村教師是鄉村文化人的典型,在新的政治性的教育體制內,鄉村教師的社會身份、文化身份,最難以歸屬:一方面,他們在名義上是現行體制中人,是現行體制認可的文化形態的承傳者,另一方面,在實際的生活中,他們又沿襲著傳統鄉村文化人的社會角色,在實際的教學生涯中,又通過自己的生活方式,通過自己的言傳身教,在隱形層面上,傳承著鄉村的固有文化。南巖作為特級教師,就是他們的典型,他們的代表。畢星星的這篇文字,寫了南巖由于參加革命的父親與在鄉間的母親的離異而得不到父系家族的認可,那其實就是政治文化與鄉間文化的斷裂而給南巖帶來的身份歸屬的無著,是上述鄉村教師身份歸屬的隱喻,這種無著使南巖一生飽經困苦、坎坷、屈辱,但南巖卻在這樣的境遇中,因了自己在語文教育中的突出貢獻而成為省級著名的特級教師。作者在講述南巖的一生時,借助自己與南巖的親屬身份,使全文字里行間充滿了濃濃的親情,充滿了感染人打動人的情感的力量,使我們不由得不沉浸其中,在對鄉村教師的深刻理解時,深受感動。
《特級教師南巖之死》確實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優秀的紀實文字,但在畢星星的紀實文字中,它卻遠遠不是最好的一篇,如在這本《堅銳的往事》中,比它勝出一籌的文字隨手就可以舉出幾例來。我猜想,《特級教師南巖之死》之所以被多家選本選入并獲散文界、山西文學界大獎,多半是因為這篇紀實文字中情感的動人力量,還因為南巖的教師的社會身份——而又是從一般的重視教育的這一層面上對教師這一職業的認可。在獲取殊榮這一層面上,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仍然可以把《特級教師南巖之死》視為一個“歷史的文本”,只是導致其成為“歷史的文本”的“權力”,來自于文學界的判定能力。于此,我們不能不感嘆于文學界判定能力的歷史局限性——它們還更多地生存于“大歷史”的陰影之中。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奇妙的錯位:文本的“小歷史”敘述與對這“小歷史”敘述文本的“大歷史”的判定。這樣的一種奇妙的錯位,或許也是民間性“小歷史”對歷史的紀實性思想性寫作潮流在其發展中,所應該受到重視的一個問題吧。
話題似乎有些扯遠了。回過頭來我們接著來談畢星星的這本《堅銳的往事》。
在我看來,《最后的鄉紳》是一篇要遠遠高于《特級教師南巖之死》的杰作。誠如作者所說:“在封建時代以至民國,鄉紳都是鄉村社會一個重要的階層。‘紳為一邑之望,士為四民之首’……鄉紳成為基層政權和底層民眾聯系的中介,決定了它在村落視野里的鄉土權威地位。”但“自民國以后,鄉紳的社會地位日漸滑落。土改一舉將原來的鄉村精英請下了歷史舞臺……由于鄉村干部中文盲半文盲居多,對讀書人心懷一種天然的文化歧視,鄉紳日益成為零畸者和多余人”。然而,“經歷了幾十年的曲折,我們的鄉村終于又開始向自治回歸。一旦少了自上而下的權力干預和強制,這些鄉村知識分子的作用立刻突顯出來了。”可惜的是,歷史沒有給《最后的鄉紳》中的主人公“師傅”這樣的一個機會,他“生不逢時,在鄉里制度的承襲變革過程之中錯了位”,只能成為一個上述的“零畸者和多余人”。讀《最后的鄉紳》,在主人公“師傅”“受盡奚落和嘲笑”的種種可悲、可笑、可嘆的言行舉止中,我們時時都可以看到魯迅小說《孔乙己》中孔乙己的面影,他們都是作為某種文明的承載者,卻生活在這種文明的沒落時代,從而成為一個時代的“零畸者和多余人”。這里有著個體生命在歷史長河中的偶在的無奈、悲涼,也有著在歷史長河中必然的言說不盡的豐富的時代與社會的內涵。魯迅多次說過,《孔乙己》是他寫得最為滿意的最好的小說,《最后的鄉紳》也可以說是畢星星目前寫得最好的紀實性文字。與《最后的鄉紳》相類似的,還有畢星星對已然被今天這個影視時代所淹沒的鄉村戲曲蒲州梆子的敘寫,還有對鄉村戲曲傳人《劇壇怪才墨遺萍》的敘寫。
二
《誰還知道李希文》、《毀譽參半說浩然》也是兩篇意蘊厚重的紀實文字。
這兩篇文字都寫了在一個時代權力規訓下的鄉村文化人及通過他們而體現出的鄉村文化的呈現形態。李希文是代表一個時代文化風尚的農民快板詩人,他曾經紅極一時,如郭沫若所說:“我是郭老八,陜西有個王老九,你就是李老十。”但誠如作者所說:“李希文其實并不是一個農業從業者……他應該是一個游民無產者。這個成分的因子浸透在血脈里,他的成功失敗,和這個職業贈與的心性息息相關。游民的革命性和游移性、投機性潛伏著,氣候合適一定要萌發的。山西好多農民領袖,在這一點上都和李希文相似。”其實,并不僅僅是山西,中國的農民領袖也大多是如此。中國的革命文化中也多有這種基因潛伏其中。早在中國革命的農民運動興起的時候,毛澤東就在其經典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對此以“痞子運動”有著精彩的描寫與論說,當然,毛澤東是從“好得很”的對此的贊揚來批駁對方對此“糟得很”的指責的。不能否認的是,類似李希文的這種游民性,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存在。在革命的初起之時,他們的言行也是代表著被壓迫的貧苦農民的真正利益的,因為在革命初起之時,如畢星星所說“道地的農民沒有能力代表農民”,而類似李希文這樣的人的身上“有農民式的淳樸,也有游民式的狡黠”。這樣的一種復雜的格局、構成,在孫犁、趙樹理的小說中,都有著十分深刻與精彩的揭示。孫犁、趙樹理的文學創作之所以先后成為文壇主流的代表,又先后退出時代的文學主流,與這種游民性及對其的評價的歷史浮沉關系甚大,這是個用許多專論也難以說清的問題,是一個直到現在也還沒有說清的問題,我在這里自然不能給以展開,但我們也因此能夠感受到畢星星寫了李希文這樣一個“典型”及這一“典型”被我們今天所遺忘的歷史的沉重性。再多說一句的是,李希文退出歷史舞臺與其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明星,作為一個時代話題,有著同樣的深刻與沉重,誠如畢星星所說:“一個農民廁身于國家的政治博弈里,該是多么危險的賭局和游戲。”李希文這一代游民的民間性、底層性及其所曾代表的農民利益與政治規訓的脫節,是造成他們悲劇的根本原因。
浩然則可以作為李希文之后的一個時代文化的標志性人物,是李希文之后的一代在政治規訓下的農民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身上流淌著李希文的血液,但在這一文化譜系的成長中,已然更多地脫離了民間、底層與農民本身,而更多地符合了規訓的標準。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他也仍然還是被規訓的對象而不是規訓者本身,對規訓迎合的真誠,在被規訓時本身所自然帶有的民間、底層、農民群體的風貌,都讓后人對此一言難盡。如此,我們也就會明白,畢星星為什么會在說浩然時,會“毀譽參半”了。這個“斯芬克斯之謎”不是畢星星一個人所能破解得了的,它需要時間和更多的人對此的努力以及新的價值資源的引入。畢星星能夠深入地參與、豐富這一論說,已經是非常地難能可貴了。我對此還非常贊賞的是,畢星星更多地是從歷史的角度、層面,對此給以揭示、論說,而不再局限于我們所習見的從人格、道德倫理的角度來臧否人物,這樣的一種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原則、尺度,在我們回望一個歷史時代的風云人物時,特別是政治人物時,是非常必要與及時的。
三
當然,我說我們在回望一個歷史時代的風云人物時,要更多地從歷史的角度、層面而不再局限于我們所習見的從人格、道德倫理的角度來臧否人物,并不意味著我們放棄對人物人格及道德品格的評價。當我在批判政治規訓給民間文化帶來的負作用時,也并不是就對民間文化有著一種完全的肯定。事實上,由于傳統的老中國是以群體性的道德倫理作為社會價值本位的,特別是在民間,道德倫理的力量往往是作為統治性的力量存在的,所以,在今天這樣一個傳統與現代斷裂的時代,如果我們不是從一個特定的具有歷史內涵的尺度上,而是從一個一般的具有普泛意義的尺度上使用“規訓”這個概念,那么,如何評價、用什么去規訓傳統的鄉村的民間的道德倫理,如何重建新的民間的道德倫理,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緊迫的時代性的社會問題。正因此,畢星星的《大匠野史》頗值得文壇給以更多的關注與重視。
這篇作品的主人公是一個鄉村建筑匠人的領袖,因之,被稱為“大匠”。“大匠”帶領著自己的鄉村建筑隊征戰南北,功績赫赫,但卻引起了自己養母之子即自己堂弟的妒嫉之心,而這位堂弟“在村子里就是有名的惹不起,慣以死纏爛打制勝”。于是,他的這位堂弟以莫須有的對自己的母親不孝為長期攻擊“大匠”的利器,終于使“大匠”心氣郁結,積郁成疾,絕癥致死。畢星星說:“大匠的死,是一個非常耐人解讀的現代人死亡文本。”下面,我試著來解讀一下,是什么導致了這個“現代人死亡”?
大匠之死,首先死于“純粹的惡”。畢星星對此分析說:“堂弟謀害大匠,并不希圖自己得到什么。他沒有利己的動機,純粹為了害人。與必要的惡相比,這是一種純粹的惡,惡意的破壞屬于沒有意義的破壞。他一般針對對象的優勢地位,如榮譽、社會地位甚至審美方面的優勢評價等。”這樣的一種“純粹的惡”,是社會差別對人性扭曲之后的人性的“惡疾”,這種“惡疾”在底層在民間普遍存在且歷史悠久,其破壞性的能量駭人聽聞。十年浩劫之所以能夠形成,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種“純粹的惡”在起作用。漢娜·阿倫特在論述西方的德國極權主義之所以能夠形成時,將“平庸的惡”歸結為其中的一個原因,那么,我要說,中國的十年浩劫能夠形成的一個原因,則來自于這種“純粹的惡”。
大匠的死,還死于民眾對這種“純粹的惡”的軟弱與無力,還死于民眾缺乏公眾意識公德意識:“當初堂弟挑起事端,狂熱地攻擊大匠的數年,小城一直把它當作一件私事。”說到底,是因為民眾沒有看到這種“純粹的惡”對自己利益所帶來的傷害因而袖手旁觀。這樣的一種作為“國民劣根性”的“冷漠”,在魯迅的筆下,我們可以時時看到。這樣的一種“冷漠”所帶來的實則對“純粹的惡”的鼓勵與放縱,也是十年浩劫能夠持續的一個重要原因。可喜的是,當市場經濟讓民眾對個人的利益有了自覺的維護意識之后,民眾終于“如夢方醒……他們開始失悔,在大戰膠著的時候,在大匠遭遇滅頂之災的時候,小城沒有出手助戰,小城沒有救護自己的功臣”。也許這種“失悔”,正是魯迅筆下的“庸眾”在今天開始覺醒并建立自己的現代公眾意識公德意識的開端吧。
大匠的死,還死于如何看取傳統的民間的道德倫理。事實上,“純粹的惡”,往往也是假傳統的民間的道德倫理或這種道德倫理的“革命化”外衣而大行其道的。這個問題又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如何看取傳統的民間的道德傳統,這在“五四”之后本已經不成問題,但在今天這樣一個以批判“五四”以弘揚傳統為盛事的時代,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又一次擺在了我們的面前。因之,畢星星在《大匠野史》中所堅守的啟蒙立場,就顯得難能可貴。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確如畢星星在文中所引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所一再主張的:中國人應“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正因為我們是一個有著悠久的以傳統的道德倫理作為社會價值本位的國度,所以,“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對于我們就格外重要,否則,永遠如畢星星所說:“玩‘技術’的耍不過玩‘道德’的”,“大匠的慘敗慘死,無疑是現代生活中道德又一次戰勝技術的可悲的范本”。所以,畢星星大聲疾呼:“社會對人的技能評價和道德評價要區分”。
“大匠當然也要為自己的死負責任。他的愚忠愚孝,使得他仿佛還生活在兩百年前。”在大匠身上,我們分明可以看到中國鄉村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重負與曲折。畢星星呼吁:“這種小人的挾嫌進攻還能遇到,巨人們,先放下包袱,輕裝上陣才是。”這可以視為現代之聲對傳統鄉村的呼喚。這種呼喚,在“反思現代性”的時潮中,如果我們立足于中國的現實大地,特別是不要忽視中國的不發達地區的現實實際,我們對這種呼喚,就會倍感親切。
《大匠野史》之所以稱為“野史”,是因為上述大匠之死的真正原因,在對大匠的“正史”中,只字未提。大匠之死的真正原因“私下議論是可以的,形成一種公開書寫,那是斷不可行的”。“推測紀念碑的碑文,正面呢,肯定是永垂不朽、鞠躬盡瘁、功高蓋世、能工巧匠之類,陰面呢,簡略介紹生平,比方全國優秀企業家啦,世界杰出人士啦,榮獲魯班獎啦等等。”畢星星為此悲憤地說:“有人制造了大匠的死,我們又樂于修改大匠的死,大匠便只能這樣死去。”這樣悲憤的聲音,我們在魯迅的《為了忘卻的紀念》中曾經聽到,在魯迅悼亡體的《傷逝》中也曾經聽到。正是不滿足于大匠“這樣死去”,有了畢星星的這篇《大匠野史》,也讓我們由此看到“野史”高于“正史”的價值,看到了當今民間性的“小歷史”對歷史紀實的價值。
四
從傳統走向現代,從鄉村走向都市,是百余年來中國的民族期待,也是這一群體中每個個體的個體期待。這種期待,在實現這一期待的歷程中的坎坷,在剛剛開始實現這一期待之后的對鄉村失落的失落感及對鄉村的親情憶念,還有那對現代對都市的不滿與反思等等,所有這些,都生動地通過畢星星的個體性的人生記憶的《走出鄉村》而得到了生動而又深刻地體現。
這種體現是通過畢星星寫自己家族從其爺爺開始到其子女一代共四代人才走出鄉村的家族軌跡來完成的。
畢星星的家族聚居在山西的晉南地區,也稱為河東地區,那里是中國傳統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在歷史的轉折處,傳統文明的成熟之地率先走向現代文明,也是歷史的必然,如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所認為的,當一種歷史形態成熟之后,它就會在自身孕育出一種埋葬自身的對新的歷史形態的渴望與期待。如是,我們看到了畢星星的爺爺在科舉中成為秀才之后,又順理成章地循著歷史的腳步,成為北京國立法政大學的學生,而畢星星的爺爺不明原因的死亡而導致的畢氏家族在走出鄉村的歷程中的受挫,簡直就猶如中國的現代化之所以一波三折的眾說紛紜不明就里的一個隱喻。畢星星的父親沒有走出鄉村,就像畢星星所說,是從鄉村走向都市的一個“頓歇”;畢星星的大哥一代,在民國時期,通過讀書、參加革命而伴隨新的政權進入城市;畢星星的姐姐一代,在“文革”前通過讀書進入城市;畢星星本人在“文革”初中斷學業,又通過參軍提干而走出鄉村;畢星星的兒女一代,在新時期隨父母入城讀書而進入城市:一個家族走出鄉村的歷程,真真是猶如我們民族從鄉村走向都市的一個縮影。從這樣的“小歷史”中,或許我們可以借此來窺探“大歷史”的某種真實,進而窺探真實的歷史本身。
在這其中,我們看到了畢星星的父輩在“整天餓得前心貼后心”的三年困難時期,也仍然不惜拆房來支撐兒女通過讀書來走出鄉村的苦撐苦熬。這個走出鄉村的夢想“是那樣誘人,以至于后人累斷筋骨,受盡艱難,那個夢想也能夠支持他們付出最慘烈的犧牲”。這是一個鄉間家族的夢想,從文化形態上來說,這也是我們民族的夢想,以致我們不惜犧牲鄉村成就都市,犧牲農業成就工業,犧牲百姓的日常的物質人生而成就原子彈那燦爛的蘑菇云。
在這其中,我們也看到了城鄉之間的巨大差異。于是,有了中國特色的城鄉分治的戶籍分隔制度,有了城市戶口的優越性、優越感,有了農村戶口轉入城市戶口的“難于上青天”的艱難,有了畢星星在城鄉之間像“搬運工”一樣,年年將城市的物品“從大米、掛面,水果糖,到肥皂,火柴,堿面,作業本,圓珠筆”周轉、搬運到鄉下的家中。
在這其中,我們還通過那諸多的豐富細節,看到了畢星星在從鄉村走向都市的途中,對都市近于偏執的敵對情感,對于鄉村近于偏執的懷戀。諸如作者在寫到自己扣上門鎖告別家鄉時的感受:“我對準門扣,搭上鎖身,按上鎖簧。拇指和四指一合。啪嗒……我所在的鬧市,日日夜夜鋪排著聲音的盛宴,混合成震耳欲聾的巨響。他們厚顏無恥地展示著自己的速朽,倒是那一聲‘啪嗒’成為永恒。每當‘啪嗒’一聲,我的心就感到刺痛,也感到溫甜,它指示我,這才是真正觸動靈魂的聲音。”畢星星還寫道:“由鄉村到城市的道路上,數不清的腳印,帶著各色的泥土,密密麻麻踩到了城市的水泥地面……這一支迷失了家園的隊伍里,也彌漫著我們一家無可奈何的惆悵和蒼涼。漂泊,是現代人永遠的宿命。鄉村,卻是我們烙印終生的胎記。”聽到畢星星這樣的中國的現代知識分子也從內心深處發出這樣真情的感嘆,我就不由得要說,我們民族其實從實質上并沒有“走出鄉村”,我們民族“走出鄉村”的路還十分十分地漫長,還要經歷非常非常的曲折與坎坷,中國學界當今對現代性的反思,也還是移植的、平面的、膚淺的。或許,我們在對鄉村的回望與反思時,還需要重新確立我們的價值立足點。這,或許也是今天民間的“小歷史”對歷史進行敘說時所應該有所警惕的吧?
《堅銳的往事》值得評說之處還有很多,引發的問題也還有很多,諸如那一時代鄉間的民謠,那是比那一時代主流詩歌更為真實的對歷史的記憶;諸如那一時代鄉村婚姻生活與性生活的民間的個人性記憶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樣的記憶等等。總的說來,畢星星這種基于民間的“小歷史”的對鄉村歷史的回望與反思,對于喚醒、修正我們對中國鄉村的記憶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時的,因為誠如作者在本書前言中所說:“數十年間,國人的集體記憶也早已經損毀得不成樣子……1949年以后的生活,歷史已經書寫涂改又書寫幾經輪回。走過的日子,穿越的事件,翻開書,大驚失色,白紙黑字早已不是你經歷的記載。”無論對于歷史“民間眼光與精英判斷”怎樣地“竟然如此互相抵牾,互相哂笑”,但“一個完整的記錄”畢竟“有待各色各樣的記錄去豐富補充”。《堅銳的往事》就是這樣的一個非常及時的現實性極強的豐富與補充。
[1] 畢星星.自序·堅銳的往事[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