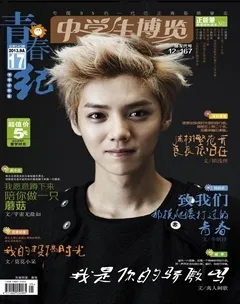輕舟已過萬重山
匯博這個巴掌大的學校,到了最后也沒榨出幾毛錢來,于是中考前一個星期我們默默無言地自掏腰包交了車費35元大洋,由學校派大客拉我們奔赴考場。最后一場生物結束以后,從大客車上下來時我死命抱住小A,配上滿臉的悲痛心酸唱腔道:“此去一別,不知又要何時相見~此去經年,需是良辰美景虛設,縱有千種風情,更與誰人說啊。”只是小A一記出神入化的廬山升龍霸成功讓我纏綿悱惻的尾音轉變成高頻率抑揚頓挫的尖叫,所謂凄神寒骨余音繞梁,大概就是這么個樣。
只是可憐我們聚會策劃人剛解放第一天就不得不去超市東轉轉西摸摸準備聚會必需品,我露齒對不耐煩的售貨員小姐一笑,聳聳肩放下手中看了至少十分鐘的請柬,心想明明掛眼科是窮人的權利,但卻沒想到真正在畢業典禮那天聽韓大班長在上面致畢業敬辭的時候,心里沒由來地矯情了一把。
三年的回憶像羽毛,風一吹就盈盈飄起。
初一初二的時候的確夠青澀,也就是在這段時間里,經過歲月這把殺豬刀的整形之后,完成了從生嫩二貨到文藝小清新的華麗轉身。體育課,操場上一群鶯鶯燕燕歪七八扭地跑過揚起身后大片灰塵成為當時校園里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停電時,諸位女同胞不亞于唱“阿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的尖叫聲寂寞地劃過墻邊后,凄美地落在推門而入的年級主任腳邊;最后一晚,教室電腦早被電教部撤回,只好清唱的我們明明集體跑調,還是堅持唱滿十分鐘。那些零碎的記憶都展現出無比清晰的姿態,許許多多的細節就這樣毫不掩飾地呈現出來。
初三的時候,洪水猛獸般的試題撲面而來,每天晚上到凌晨宿舍里還是明晃晃的一大片手電筒燈光,宿舍管理員大娘嘆口氣過來敲敲門說快睡吧。總分共100計入中考的體育考試、微機測試和實驗操作捎帶上一輪驗收急匆匆地攔路。實驗操作抽到生物里比較簡單的洋蔥上皮細胞觀察,在實驗室忐忑地把調好的顯微鏡給監考老師看,聽他說一句“嗯,很不錯”時心一下子高興地要飛起來。最后中考那幾天中午午休老師們輪流巡查不準背書,初一初二放學較晚回宿舍吵吵鬧鬧,每個樓梯拐角處都站著一個老師把食指按在嘴唇上默默地對學生說安靜。一下子就不舍起來,不管三年里和他們有多少摩擦,最后全都抹掉,只留滿心的感動。
但就像席慕容的《祈禱詞》里寫的一樣“我知道這世界不是絕對的好,我也知道它有離別有衰老”。當初我們如何如何期待畢業討論畢業照在哪拍好,操場的楊樹旁?宿舍門前的梧桐下?小花壇前?可到頭來我們還不是默默地聽從學校的安排,中規中矩地穿好校服排成梯形站在高高的階梯上,仰起臉來時清晨太陽明晃晃的光一下子擠進視線,不習慣地瞇起了眼,站在支架相機旁邊的拍攝人員立刻嚷嚷起來第幾排靠左數第幾個同學麻煩把眼睜一下。
就這樣畢業了。
最后幾個月,教室干燥的空氣中一張張面無表情嘴唇不斷蠕動背書的臉,夜晚,手電筒暗淡燈光下濃重的黑眼圈,全都變得模糊并且在記憶里以3×10^8m/s的光速向后退去,我突然就明白了李白《早發白帝城》里那句“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畢業成了一條河,蜿蜒地流過我們的生活。如果以后有人問我,你是在哪所中學畢業的?我就會回答說匯博中學,“匯”是初三有一次物理考試寫凸透鏡的會聚作用我寫成了匯聚作用還差點被薄女士揍的那個“匯”,至于“博”嘛,就是匯博的那個很偉大很陣勢很氣魄的“博”。
編輯/張春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