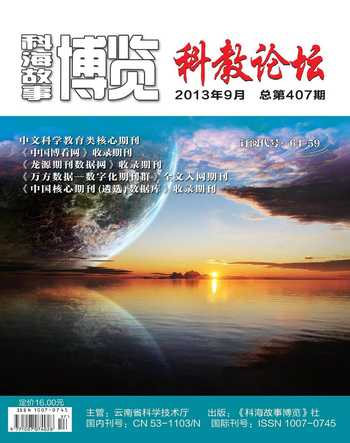淺論翻譯研究的“語言學途徑”、“文化學途徑”及“泛文化”
摘要:翻譯與語言和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其應該同時注重文化學途徑和語言學途徑的結合,使譯文在回歸文化本性的同時能夠體現語言關聯性。本文分別闡述了翻譯的文化學途徑和語言學途徑,并對現今存在的翻譯“泛文化”現象提出幾點思考。
關鍵詞:翻譯 語言學途徑 文化學途徑 泛文化
引言
翻譯,就筆者作為一個語言教學的學習者身份來看,其就是運用語言這個載體來進行不同文化信息交流的一門學科,語言是工具,文化是內容;而且翻譯也能為語言的教與學提供一個溝通的橋梁。注重語言的流暢還是文化內容的轉化與保持?眾說紛紛,但可以知道二者應該相互權衡,缺一不可。那么,當我們用語言來表達文化信息的時候,應該怎樣把握它的語言學途徑和文化學途徑,讓翻譯學----這門從語言學中獨立出來的學科,能夠忠于其功能本質,服務于語言文化的交流(這里說的“服務”可能過于牽強,但是我們終觀翻譯的研究,就可以得到一些解釋和啟迪)。翻譯是一個跨語言與文化交流的過程,它通過目的語“再現”
的方式把源語言的信息表達出來,幫助目的語讀者了解原作者意欲表達的信息內容并獲得與原作者和源語言讀者感同身受的思想體驗,翻譯的目的實質是為了幫助那些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們可以進行信息與情感的交流;翻譯在某種程度上講也是一個“思維再創造”的過程,但“創造”不代表無規則,在翻譯的過程中, 譯者必須遵守一定的標準與原則。忠實和通順是兩項最基本的要求(賈文波,2004)。那么這里的“忠實”和“通順”該作何解釋?就筆者看來,“忠實”,顧名思義就是要忠于原文的文化內涵、忠于原文的本性;“通順”,其就是要譯者注重原文在翻譯過程中表達方式的語言學途徑,即語言的關聯性。那么,顯然,在翻譯過程中,語言學途徑與文化學途徑應該是互相結合的。
一、翻譯的“語言學途徑”
最近十多年來, 國外出版了不少用功能語言學(這里所說的“大功能”與N.Chomsky的形式主義相對而言,包括語篇分析、話語分析、社會語言學、認知語義學、語用學、認知功能學等)作指導的研究翻譯問題的文章和專著(黃國文,2004:16),即用語言學這門學科來指導翻譯學科的進行。而奈達也認為翻譯研究有四種途徑:1、語文學途徑(philological approach);2、語言學途徑( linguistic approach );3、交際學途徑(communicative approach );4、社會符號學途徑( sociosemiotic approach )。關于翻譯的語言學途徑的理解,首先,我們要知道語言學是研究語言的一門科學,而翻譯學不單單是研究翻譯的科學,筆者認為它更是一門藝術,因為科學講求實際與關聯,而藝術講求表達的美感,比較藝術與科學,只有藝術才會用“雅”來闡述與修飾。對此,筆者查閱資料時也發現,奈達曾在《翻譯科學探索》中認為“翻譯是一門科學”,并試圖將語言學、符號邏輯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學科融于翻譯學科。但在后期的論文中,其改變了立場:認為“研究翻譯理論是科學,而翻譯本身是一門藝術、技巧,不是科學”。這種解釋似乎對他早期的翻譯語言學途徑進行了否定。但這是不是就說明語言學途徑完全沒有優勢呢?其實不然,強調翻譯的語言學途徑,不但可以表達出連貫語言之美感,也可以在一些結構復雜的句式中幫助譯者理清思緒,以便譯出通順流暢的譯文,讓目的語讀者感受到語言之美。翻譯的語言學途徑主要是關于兩種語言的對比,即原文與譯文的句式、詞法、形式、篇章等的對比,以便加強譯文語言的關聯性。就筆者涉及過的英譯漢或者是漢譯英的方法和技巧都是以英漢兩種語言的對比為基礎的。國內學者鄧巧玉也同樣認為:對于英漢翻譯實踐來說,對比英漢兩種語言的異同, 尤其是相異之處,從而掌握它們的特點是十分重要的。通過對比,掌握兩種語言的特點,在翻譯時就可以自如地運用這些特點,還可以使我們重視一切難譯的地方,認真研究同一思想內容如何用不同語言形式來表達的問題(鄧巧玉,1999:61)。可見重視翻譯的語言學途徑為我們得到結構嚴謹的譯文是大有益處的。
二、翻譯的“文化學途徑”
關于翻譯的文化學途徑,筆者認為應先理解什么是文化。而“文化”這個概念極為抽象和復雜,國內外的學者已先后對它下過近200種定義,但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見。在這里,筆者選取蔡榮壽學者的定義,即文化是一個復雜的總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人類在社會里所得的一切能力與習慣(蔡榮壽,朱要霞,2009)。筆者認為,文化的內容是一個復雜的但又不失完整的真實的表述,不能曲解,不能會錯源文化的思想內涵,因此任何翻譯都要考慮文化的差異性、普同性、社會性、發展性及功能性,翻譯才可能達到讓讀者理解的同時也不失原文的文化本性的目的。我們可以通過以下兩個例子(蔡榮壽,朱要霞,2009)來說明:
1.“亞洲四小龍”
誤譯:the four dragons of Asia
正譯:the four tigers of Asia
分析:因為在漢語中“龍”多表達的是褒義,如“龍鳳呈祥”、“龍馬精神”、“龍騰虎躍“等。而“龍”在英語里對應的詞是“dragon”,在英美文化中,“dragon“代表兇殘的怪獸,是邪惡的象征。所以“亞洲四小龍”譯為英語的時候不應該用“dragon”,而用“tiger”代替。那為什么這里要用“tiger”來代替“dragon”呢?筆者通過維基百科查閱到:在大多數的西方國家及說英語的非西方國家中,比如印度和孟加拉國,“tiger”代表著耐心、專注、堅定、警覺、深思熟慮的品質,而且在一些亞洲國家,比如中國、韓國,“老虎”也有著“王”的象征意義,即對應英文的“king”。據全球唯一一個以動物為主角的電視頻道:Animal Planet(動物星球)通過超過50000名來自73個國家的觀眾投票調查獲知(維基百科):老虎以微弱的優勢擊敗了狗,被評為世界上最受歡迎的動物,老虎獲得了21%的選票,狗20%,海豚、獅子、馬分別是10% 、13%、 9%,蛇8%,這里有一個文化的共性在里面,所以這樣才能讓英語語言的讀者真正理解“亞洲四小龍”的含義,也不會曲解了我們中國的“龍”的含義,否則就會因為文化差異而產生誤解。像這樣的中西文化差異的詞語還有很多,比如:“紅色”、“六”、“collectivism”、“capitalism“等。
2.Hawkes把《紅樓夢》中的“阿彌陀佛”譯為“God bless
my soul.”用上帝來代替佛教的壽佛。這可能讓西方人誤以為我們中國人也信上帝。這樣的譯文就會大大削減中國的文化內涵。
通過上面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知道,翻譯需要考慮雙語的文化鏈接、共性和差異,并相應“采取歸化或異化的翻譯策略”。美國著名的翻譯理論家奈達認為“文化之間的差異比語言結構之間的差異給譯者帶來更多更嚴重的復雜情況。因為詞語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義。”筆者發現,很多人常把翻譯這門藝術比喻成“帶著鐐銬跳舞”,以強調翻譯所受的文化約束。因此,在我們翻譯是時候,了解并熟悉目的語及源語言的文化是必然的,這樣做出來的譯文才能夠得到大家的認可,也才會到達交流及共鳴的作用。但是過多強調文化途徑是否就是上上策呢?其實不然。蔡榮壽認為,翻譯之所以如此艱難,是因為語言反映文化,承載著豐厚的文化內涵, 并受文化的制約(蔡榮壽,朱要霞,2009)。但是如果我們對這個“文化”因素給予過多的考慮是不是就是權宜之策呢?周曉梅認為,對于外部因素的過度關注就會造成翻譯研究中的泛文化傾向,這導致了研究的分散性和無深度性(周曉梅,2012)。顯然,如果過度地重視翻譯的文化學途徑而忽略了翻譯的語言學途徑,那么所得到的譯文必定會給人一盤散沙的感覺,沒有嚴謹的結構的文章不叫文章,最多是句子的拼湊罷了,這對于翻譯實踐來說注定是失敗的。據此,要想得到一篇成功的譯文著作,同時兼顧翻譯的“語言學途徑”和“文化學途徑”這條原則是譯者必須堅持的。
三、翻譯的“泛文化”現象
現如今,全球化加快了跨文化交際的發展,我國翻譯學研究必然也會受到影響,即發生了令人矚目的“文化轉向”,它改變了傳統翻譯學的研究“路徑”與方法。據此,筆者查閱文獻發現研究者將之前的關注點由文本內部語言結構因素轉向了外部文化渲染因素,這不僅為翻譯研究注入了新內容、新視野,也擴大了寬度,增加了深度,讓人們感受到翻譯活動的豐富多彩,意識到翻譯的多方延展,發人深思。但是,在此過程中也出現了負面情況———很多研究漸漸偏離了翻譯學本性,出現了“泛文化”的傾向。所謂翻譯的泛文化現象,是指在翻譯學研究中,不將翻譯活動作為實際考察的對象,而把從其他學科(如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中借用來的概念、術語、命題等作為研究內容,進行闡釋和討論(周曉梅,2012)。筆者發現,在我們譯注的過程中,將兩種語言進行轉換,為了滿足目的語的文化需求,就會違背本土語言的文化內涵,可到最后也無法完全將目的語的文化內涵融入到譯文中去,同時也失去源語言的文化本性,于是乎,兩者兼失。根據周曉梅學者的研究,筆者總結發現,泛文化現象影響下的翻譯研究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1.翻譯理論無根基性;2.翻譯研究無系統性;3.深度研究的“平面化”;4.翻譯文化的誤讀誤用。那么針對這些問題,我們怎樣克服泛文化現象及其引起的這些問題呢?筆者認為:1.應該回歸本體的翻譯研究根基;2.堅持翻譯的初衷:忠實與通順;3.不能胡亂添加任何無關聯的成分4.不能夠生搬套用其他學科的內容。翻譯研究中對文化的關注本來是為了在翻譯中更好地保留“異文化”信息,以達到平等交流的目的。但是周曉梅認為,翻譯學研究者對于這方面的關注顯然是不夠的,一方面,他們沒有認真消化吸收其他學科的概念、術語,更沒有將其內化為翻譯學本身的原則和方法;另一方面,在翻譯學學科擴大的同時,學科邊界被模糊了,或者說整個學科也被泛化了。在一些人主張一切都是翻譯時,翻譯學與其他學科的界限被消彌,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也混雜不清,讓人無法認識翻譯活動的本質與特征(周曉梅,2012)。如果是這樣,那么“翻譯”這門學科就會失去其本性了。在全球文化大融合的這個時代,如何保持翻譯不被“泛化”是值得翻譯研究者共同努力的。
四、結語
翻譯中需要對等的綜合性關系。對于現如今多元文化視角下的翻譯研究,它的走向必然是語言分析與文化判別的結合,我們應該好好審視翻譯的本位研究,給予其正確的定位,樹立正確的翻譯語言觀和文化觀,并正確對待其間的關系,運用語言學的科學理論去處理翻譯文本的結構,然后有效運用翻譯的文化觀保留譯作的本土文化,并同時融合目的語的文化知識,注意學科間的相關性,在維護文化多樣性的同時不能偏離文化的主體,克制泛文化現象,并依靠藝術的眼光、語言素養和文化修養,全面細微地考慮各方面因素以期得到一部優秀的譯作。
參考文獻:
1. 賈文波.應用翻譯功能論[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4.
2. 黃國文.翻譯的功能語言學途徑[J].中國翻譯,
2004,(5):15-19.
3. 鄧巧玉.翻譯的語言學途徑[J].中國保險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9,(1):61-62.
4. 蔡榮壽,朱要霞.翻譯理論與實踐教程[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9.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Tiger_worship
6. 周曉梅.對翻譯學研究中泛文化現象的反思與批判[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2,(5):72-75.
7. 張艷豐.再論奈達早期翻譯理論中的語言學途徑,http://www.cnki.net.
8. 許鈞.翻譯研究與翻譯文化觀[J].南京大學學報,
2002,(3):219-226.
作者簡介:胡啟琴,女,貴州貴定人,中南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語言磨蝕,語言教師發展,語言翻譯與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