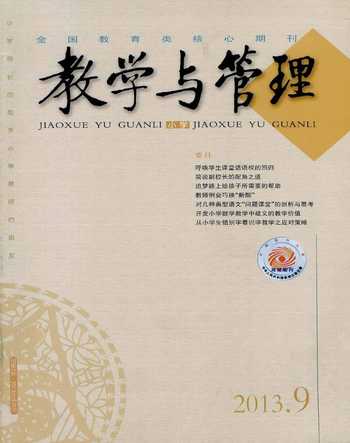看到集體,也要看到個體
莊華濤
那年期末考試,班級成績非常理想,均分在學區排名第一,我心情自然格外好。
謄寫成績單時,我意外發現小玉居然只考了六十來分,有點不太相信。這孩子,平時考試沒低過八十五分,怎么這次考成這樣了?本來想去查分,但想想還是算了,第一是查分手續非常復雜,第二是班級均分已經第一了,再查也沒多大意義。
一份份成績單發下,一張張笑臉綻開。孩子們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嘰嘰喳喳興奮地相互比較著成績。只有一個孩子例外,那就是小玉。
她沉默地坐在那兒,不說話,也不搭理同學,只是將自己的成績單早早地收了起來。可以看出,她對自己的成績非常不滿意。不想去再與她說什么,我想她能做到自己不滿意就行了,也相信她以后會努力的。
交待完必要事項,孩子們便回家了,我留下來參加學校的會議。誰知,會剛開了一半,小玉的母親就找來了,說是小玉一直在家哭,讓我幫著查一下試卷,好讓孩子能夠平靜下來。
我以試卷在中心校,不方便為借口拒絕了。但她再三請求著,最終我只好打了個電話到中心學校,求領導幫著查看了一下。卷面分沒出現錯誤,真的是六十來分。
聽我這樣說,她也就不再好說什么,只得無奈地回家了。
下午又接到了小玉母親的電話。
“沒事,您就放心吧,她沒影響班級的整體排名。要考慮的不是現在考了多少分,還是多教育孩子以后要細心點。”我耐心與孩子母親交流道。但小玉母親表達了自己想看到試卷的意愿。
根據小玉的編號我很快便找著那張試卷了。但看到試卷時我愣住了——雖然是密封著的,但我一眼可以看出這張試卷的筆跡明顯不對——小玉是班級寫字最好的,字跡向來工工整整。我以為是翻錯了頁,再細心地從頭往后翻了一遍,對應編號的試卷還是這一張!
征求領導意見后,我拆開了試卷密封線,果然試卷不是小玉的,她的試卷與另一個孩子的試卷裝混了。應該是監考教師收卷時大意了。
重新檢查孩子的試卷,分數的確相差很多,她考了91分。復印了一份后,我糾結了半天。既想告訴她真實的情況,又怕她知道最終結果后會抱怨學校。最終,我還是打了這個電話,因為權衡再三,我認為還是讓孩子知道實情更好。
小玉母親出現在我面前時,沒有一絲怨言,只是一個勁兒地表示感謝、表示歉意:“太麻煩您了,老師。要不是看到孩子這么難過,我也不會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麻煩您的。也請您原諒,您關注的是一個班的孩子,而我可能太關注自己孩子了。”
事情就這樣過去了,我的內心在為有這樣執著且通情達理的家長而感動的同時,也不由地思考著孩子母親的那番話。是的,作為教師的我,關注的是整個班集體的狀況,但自問一下,我有沒有關注到集體背后那一個個孩子?我也曾自詡將學生都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看待,但我真的做到了嗎?如果做到了,眼中所看到的應該是一個個具體而明確的“孩子”,而非籠統而模糊的“集體”!
那天,我想了很久、很多,也想得很深、很投入。最終我明白了,作為教師,我的眼中不應該僅僅只有“集體”,更應該有“人”——一個個具體的孩子。教好每一個具體的孩子,育好每一個細小的心靈,才是我最值得關注的。
因著這樣的經歷,在以后的日子里,每每遇到類似情況時我首先想到的是“人”,是個體的孩子。當孩子考試失利時,我想到的是如何安慰孩子而非對班級整體成績的影響;當孩子生病時,我想到的是及時帶孩子去就醫而非等著家長來處理;當孩子情緒不穩定時,我想到的是怎么去輔導而非怎么去教訓……
在這樣的工作思維下,我感覺到自己與孩子的心理距離越來越近了。
因著這件事,我樹立了一個最基本的觀點——任何集體都是由一個個的人組成的,而每一個班集體也都是由一個個學生組成的。那么,要想真的使班集體能夠有所發展,教師看到的就應該不單單是整體狀況,更應該有某一個或某一些學生的個體狀況。這樣,才能讓全部學生都能受到應有的重視,都能身心健康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