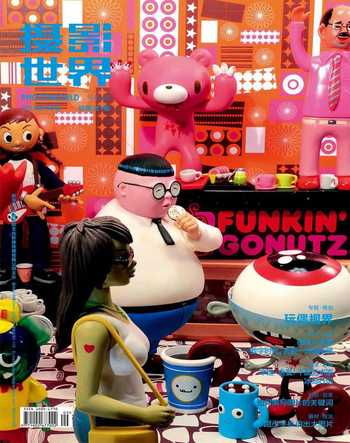戰火中的玩具攝影
羅雪揮


即使在最壞的時刻,他知道,孩子們也需要在沖突中找到力量生存下來,茁壯成長。這恰恰是布賴恩堅持拍攝“戰爭—玩具”項目的理由。
“卡桑火箭炮總在他們的腦海中,孩子們對血腥的戰爭場面高度警覺。”(編者注:卡桑火箭炮是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集團所自主研制的軍事武器)這是美國攝影師布賴恩·麥卡蒂(Brian McCarty)寫在博客上的一句話。他的作品緊緊圍繞著戰爭與和平的主題,以戰亂地區作為背景,卻拋開紀實手法,以玩具作為拍攝主體,用一種與眾不同的手法反映了自己對戰爭的理解。這些影像也作為藝術治療的手法之一,幫助因戰亂而經歷創傷的孩子。
戰爭給無辜的兒童們帶來了太多心靈上的沖擊與傷害,在這些飽受戰亂之苦的孩子們的繪畫中,恐怖的卡桑火箭炮總是布滿了天空。布賴恩受到這些繪畫的啟發,用玩具作為攝影道具,模擬了這類戰爭場景:你可以看到一棟粉紫相間的玩具屋頭頂,炮彈像下雨般傾瀉,兩個玩偶跑出屋外,手足無措;你還能看到可愛的灰姑娘茫然地站在焦土之上,密集的炮彈正如蝗蟲般向她飛來。
孩子眼中的戰爭
2010年,布賴恩開始實施一個名為“戰爭—玩具”的項目,靈感源于他多年前在薩格勒布(Zagreb,克羅地亞首都)參觀的一個展覽,時值克羅地亞戰爭結束不久(編者注:克羅地亞戰爭指的是1990年到1995年之間,克羅地亞從南斯拉夫獨立出來時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之間因民族對立引發的戰爭)。自那以后,布賴恩開始對玩具攝影與戰地攝影相結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意識到可以將玩具作為一種文化載體,乃至一種觀察工具來剖析戰爭本身。在以色列、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的人道主義組織幫助下,這個瘋狂的想法最終成形。布賴恩開始運用自己獨特的玩具攝影經驗,試圖按照藝術療法的原則,治療孩子們因戰爭而遭受的心理創傷(編者注:藝術療法是心理治療的一種,主要以提供藝術素材、活動經驗等作為治療的方式)。
在當地看護人和具有專業藝術治療經驗的志愿者陪伴下,布賴恩通常先和孩子們做游戲聊天,而后要求孩子們畫一幅畫,或者寫一封信,把他們看到、聽到、感受到的戰爭表達出來。這些工作有時在教室中進行,有時在社區中心,有時干脆就在防空洞里。因為受到年齡和語言發展程度的局限,孩子們通常很難表達自己內心所受到的傷害,但是用繪畫的方式宣泄,就要容易得多。在孩子們的畫中,有無休無止的炮彈從天而降,有躺倒的尸體,有成片的鮮血,有野蠻的入侵,也有激烈的對抗。
根據孩子們描述的畫面,布賴恩去尋找合適的玩具,然后將其擺放在真實的戰地環境中,用玩具模擬孩子們眼中的戰爭場景。拍攝的位置通常位于沖突地區,非常危險,所以他不會帶孩子們一起去,而是事后將拍好的照片帶給他們,聽取反饋。有一次,一個小女孩看到照片后很失望,因為布賴恩沒有選一個穆斯林布娃娃做她的替身,而是用了一個沒有戴頭巾的玩偶。
孩子們把自己投射到照片中的現場,對于他們來說,這也是一種真實的還原。這樣的還原對孩子的心理,可以起到疏導作用。而對于布賴恩來說,拍攝戰爭玩具的意義就是重建孩子們的未來。倘若不是自身具有強大的抗壓能力,在戰爭環境下,孩子們很容易對人性失去信心。但令布賴恩欣慰的是,在正確的治療和引導下,這些孩子們看起來仍然保存著童真。
通過玩具還原現實
戰爭從來沒有遠離過兒童這個群體。在布賴恩的“戰爭—玩具”項目中,他列入拍攝計劃的地區有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以色列、阿富汗、蘇丹以及哥倫比亞。在地球廣袤的土地上,有太多的沖突與殺戮正在逐日上演。布賴恩希望能夠藉此項目,通過全球視角,借助兒童的眼睛,來反映戰爭給孩子們帶來的心靈重傷。他要用自己的攝影作品,用玩具來彰顯人性,哪怕是暴露了人性之惡。
在布賴恩手中,玩具不再是游戲的道具。一切玩具都是殘酷戰爭的翻版。布賴恩用照相機和想象力,抓住了令孩子們無比恐懼的瞬間。灰姑娘不再是童話里穿水晶鞋的人,在加沙的炮火中,她依然是那個孤苦伶仃的無助的窮孩子,活著還是死去,都仰仗命運的安排。當象征和平、帶有倫敦奧運標志的玩具船在水面上行駛時,荷槍實彈的士兵瞄準了船,緊張的對峙一觸即發。這同樣是他在加沙實地拍攝的一張照片。在約旦河西岸,士兵們還在狙擊,玩偶男孩面朝下匍匐在地,與殷紅鮮血一起流失的,是他脆弱的生命。
當下,布賴恩把關注的重點放在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兒童身上。這是不幸的一代人,從未曾享受過沒有火箭炮襲擊、沒有空襲、沒有槍炮聲、沒有敵人的和平生活。在布賴恩的畫面中,你常常能看到畫面中危機四伏,死神總在附近徘徊。聯想到這是出自一個兒童的真實視角,更會讓人不寒而栗。
對孩子們來說,戰爭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之一,對攝影師也是如此。要在戰爭肆虐之地還原戰爭,即使是通過玩具拍攝,也驚險無比。布賴恩回憶,他在約旦河西岸拍攝的作品《沿墻射擊》(圖06),也是孩子們用畫描繪的一個真實事件。拍攝那天恰好趕上一次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當他擺好了“士兵”和“男孩”,布置好拍攝用的假血時,聽見遠處有人對他大喊大叫,激動的巴勒斯坦青年朝布賴恩投擲石塊,大批的新聞記者將鏡頭對準了布賴恩。失去耐心的以色列軍人開始向騷動的人群發射催淚瓦斯。在人們尖叫著四下逃散時,布賴恩按下了快門。
比這更危險的是2012年底,加沙地帶戰火重燃。布賴恩第一次和戰爭離得如此之近,感受到了孩子們經歷過的恐懼。他最終通過一個偶然的機會逃離了加沙。那之后的一個禮拜,加沙地帶多處遭以色列國防軍飛機轟炸,作為報復,哈馬斯則引爆了1000多枚火箭彈和炮彈(編者注:哈馬斯即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主張用武力消滅巴土地上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反對同以色列和平共處,主張建立一個以耶路撒冷為首都的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布賴恩躲在耶路撒冷的酒店里為孩子們祈禱,為這個世界對孩子們帶來的傷害而感到歉疚。
用影像帶去陽光
在布賴恩看來,攝影的本質是非常個人的感受。促使每個攝影師拿起相機的動力不同,但目的都是要通過一個獨特的角度去記錄世界。布賴恩坦言,他受到很多優秀紀實攝影師的影響,但是他之所以進行戰爭玩具的攝影創作,追根溯源,是因為從小對玩具的熱愛。
布賴恩說,在他的內心深處,住著一個小孩。他被玩具深深吸引,習慣于通過玩具來觀察、思考這個世界,并與之互動,包括用玩具來記錄真實生活。對于布賴恩來說,一張好的玩具攝影作品,遠不僅僅是用玩具充當道具那樣簡單,而是要能夠揭示生命瞬間的真實本質。比如在“戰爭—玩具”項目中,玩具模擬的場景其實是孩子們真實生活的投射,布賴恩在其間扮演的角色,是參與者,也是記錄者。
他的下一個目的地是阿富汗。作為戰地攝影師和玩具攝影師,布賴恩的背包最重的時候達到27公斤。雖然他一直盡力精簡裝備,但有些特殊的拍攝道具還是必須攜帶的,比如一個定制的、經常使用的相機支架。用于拍攝的玩具體積都比較小,很多時候需要貼近地面拍攝,這個支架可以幫助布賴恩在高出地面哪怕是幾毫米的地方拍攝。在拍攝中,玩偶和道具很容易被風甚至被路過的行人弄倒,而漫天撒落的“火箭彈”,則需要用纖巧的工具固定,攝影師需要時時注意這些工具不能出現在畫面中,以免穿幫。
布賴恩喜歡使用本地能夠買到,或者本地孩子制做的玩具。如果恰好在貧民區,就買便宜的玩具,以盡可能地通過玩具來反映當地的文化環境和經濟發展水準,這是“戰爭—玩具”項目希望傳遞的另一層信息。
布賴恩從沒有放棄過希望,一如他在孩子們身上看到的那種希望。他曾經拍攝過一幅作品,陽光照耀著廢墟,一個穿著紅鞋的小女孩在快活地舞蹈。這并不是來源于一張具體畫作,而是布賴恩與孩子們的心靈感應。即使在最壞的時刻,他知道,孩子們也需要在沖突中找到力量生存下來,茁壯成長。這恰恰是布賴恩堅持拍攝“戰爭—玩具”項目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