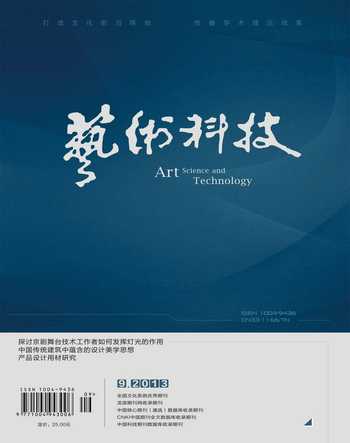淺析線描藝術的感知與表達
李靜靜
摘要:線描藝術,嬗變而有秩序,簡潔而豐富,體現了“以一治萬,由萬歸一”的多樣、統一法則。其表現語言介乎具象與抽象,狀物與寫心之間,是一種有既定目的又能在隨機過程中發揮潛能的手段,更是一種超以象外不為物役的精神暢想。本文從圖式形態、精神內涵、中西藝術對比、視覺表現形式、創作理念等方面,論述了傳統藝術中線描的感知與表達。
關鍵詞:線描;感知;表達;精神內涵
線,在幾何學上,它是一個看不見的實體,它是點在移動中留下的軌跡,因此,線是運動產生的。在藝術創作中,線是點這一基本繪畫元素相繼的結果,是藝術活動的開端,是高度概括提煉的產物,同時也具有抽象的特性。當人類開始認知客觀世界和明白其中奧秘之時,不難得知在自然界里,線條本不存在,或者說它不具有實質上的獨立意義,之所以“看”到線條,卻是由于人的視覺局限所致,當人們從特定角度觀察某個事物時,只能看到局部,由此產生的邊緣就是線的形態,由線聯想到體,具有意象與非理性因素,這也是線的藝術魅力之所在。
線描就是通過簡練的線條,將復雜的自然現象作程式化、圖案化的概括。線作為最直接、最原始的繪畫表達形式,在傳統繪畫的歷史衍變進程中,集聚、濃縮著畫家的主觀情感和審美情趣。如何在簡單與復雜、對稱與非對稱、單線與多線之間充分挖掘線描的審美價值與精神內涵,卻是個循序漸進、邊畫邊悟的思維過程。在豐富的線描圖式里,有真實記錄,有間接傳達,有意向表現,猶豫或自信,無畏或膽怯,一切心理和想法都能通過線條表露無遺,正是在這種重復的隨性勾劃與反復涂繪中,勾勒出了一個個鮮活的藝術生命和逐漸明晰的主觀意圖。線描在繪畫過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一種藝術表現形式,通過控制筆端的運行軌跡,將筆跡流淌之處變為心中期待的創作意圖和靈感途徑。從藝術表現形式的直觀性與便捷性來看,線條是最簡潔的;從傳達創作者的藝術思想和交流溝通方面來看,線條是最貼切和最易于發散人們想象力的。這就是為什么當觀者欣賞藝術大師達芬奇的手稿時,能夠在如癡如醉的狀態中與藝術大師的精神產生“共鳴”,線條能借助其高度抽象概括的特性,激發出人們豐富的想象力,反過來,情緒的變化又會影響到對于線條藝術語言的視覺體驗。
縱觀中國幾千年的藝術發展歷程,線條始終占據極其重要的位置,并且線條本身也被賦予了獨特的欣賞價值,千變萬化、登峰造極,有時甚至忽略其所構架的內容。中國人迷戀線條的一個最極致的例子,就是創造了世上獨一無二的書法藝術,實用、豐富的內涵信息與審美的象形符號渾然一體,充分發揮了漢字的結構特性,使中國書法成為了一個獨立的藝術門類。中國的書法和繪畫藝術有著密切的關聯,由筆法帶動了線條程式的發展,“書畫用筆同法”(張彥遠)是對中國傳統繪畫用線和書法用線之關系的高度概括。
從世界繪畫發展史來看,自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素描、線描從作為草圖、油畫底稿的附屬地位,逐漸演變為有獨立藝術欣賞價值的繪畫門類,其中主要用線條為表現形式的繪畫大師數不勝數,例如西方有達芬奇、安格爾、荷爾拜因、門采爾等。而線描作為中國繪畫藝術的一種主要造型手段,也為歷代畫家所重視,并逐漸完善成一種獨立的藝術形式。古代畫家顧愷之、閻立本、吳道子、張萱,周昉、顧閎中、張擇端、李公麟等的經典之作及范本至今廣為流傳。用宗白華的話概括比較恰當:“中西線畫之關照物象與表現物象的方式、技法,有著歷史上傳統的差別:西畫線條是撫摸著內體,顯露著凹凸、體貼輪廓以把握堅固的實體感覺,中國畫則以飄灑流暢的線紋,筆酣墨飽,自由組織,暗示物象的骨路、氣勢與動向。” [1]
康定斯基將線的視覺表現形式分為兩種[2],一方面,是“張力”,線是在工具性能局限之中,從其短處中生發出特長來。它是用寫實派繪畫所忌諱的平面眼光去看世界,以二維空間概念作為形象思維的基礎,削弱透視變化關系,像是將三維空間“壓扁”后貼在一個平面上,從而有效地擴展了形象在畫面中所占據的平面面積,由于線本身具有張力的性質,因而線能以其最簡潔的形式來表現運動軌跡的無限可能性,同時也增強了平面化的裝飾效果。張力是指元素的內在力量,這僅僅表現為它是總的“運動”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就是“方向”,這也是運動決定的。由于人眼生理上的局限,造成視覺上的差異性,導致人眼的運動在觀察事物時不可能看得全面,因此必然造成一定的視錯覺,在這種情況下就能碰到線的獨特面貌——它有形成面的能力,將空間進行合乎視覺流動的舒適感的占有。這實際上就是一種自覺的意識,突顯出傳統線描對于表達對象高度和主動的表現性。只需對客觀事物有直覺的把握,然后根據造型需要進行自覺重組和再創造。
線條在表現上有三種功能:塑形、顯質和表現生命運動,如果對表現對象不體察、不研磨是難以把握的。在線描課堂實踐中,學生們經常無意識地就跟著對象“跑”,看到什么就畫什么,或是走向另一個極端,斷章取義的秉持著“將錯就錯”的繪畫理念。這些想法都是盲目的,不可取的。拜讀藝術大師的作品后不難發現,他們都借鑒過客觀原型,并能超越客體本身達到與其精神層面的一致,也就是說,他們并沒有主觀臆造物象,而是對于每一個細節,每一處局部都做了反復的技術推敲和足夠的主觀意義上的專注理解。這一點上與中國傳統繪畫中“意在筆先”的創作思想如出一轍。經過分析可以發現,大師觀察對象是透徹的,分解的。比如速寫人體,畫家能夠很輕松地越過實際上看得不是那么真切的解剖結構,而分解重構出客體自律的結構。通過簡潔而富有變化的線條,隨性的勾勒下來,這種參照客體的表現,在物我關照中,反映出對象確有的一種需靈性呼喚才能隱現的真實存在。[3]顯現這個“存在”是存在本身隱秘性使然。畫家只是追隨它做應該如此表現的自然而然的選擇。
線條的任何表達形式都不是千古不變、可機械地套用的。程式化固然是藝術完美的標志,但正因其完美,往往會形成模式,模式被不加觀察地濫用便造成了定向思維,這樣反過來成為扼殺創造力的桎梏。黃賓虹指出:“描法的發明,非畫家憑空杜撰,乃古代畫家在寫生中了解物狀與性質后概括出來的。”無論是創造新線型還是創造性地運用舊線型,生活都是它的源泉和依據,線的程式從生活中來,又回歸去表現生活,從而形成藝術美的創造,延續著線條的精神內涵。
總之,線描藝術,如同藝術活動中抽絲剝繭的轉化過程,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字或是繪畫都是由線條編織成了最初的模樣。當刪除掉表層的一些“虛飾”,便能明晰地分辨出這種語言的內在的聲音,給予藝術以最簡潔和最準確的表現,純粹的形式服務于豐富、生動的內涵。
參考文獻:
[1] 宗白華.藝境[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193.
[2] 康定斯基.康定斯基論點線面[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64.
[3] 徐勇民.徐勇民線描[M].湖北美術出版社,20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