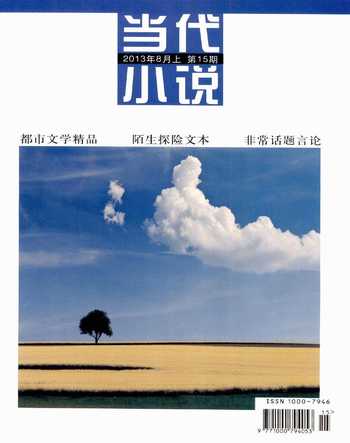火車穿過槐花鎮
湯成難
1
一條河就把小鎮撇開在繁鬧之外。河的這邊是槐花鎮,河的對岸是縣城。河繞著小鎮安安靜靜地流淌了一圈,在西北角的地方朝著淮河方向去了。這條河叫槐花河,上世紀四十年代開挖的,是抵御日本鬼子還是向淮河引水,鎮上已經沒有幾個老人能說出個道道來。河上沒有橋,只有一個擺渡,擺渡的船是槐木的,周身長滿青苔,沒有掌舵,一根繩子聯系著兩岸,人坐上船,從水里撈起繩子就可以自己渡過去了。
渡口在槐花鎮的西邊,穿過一片棉花地,爬上一個大堤就到了。鎮上的人很少擺渡到對面的縣城,去干什么呢?好像槐花鎮的人都不喜歡熱鬧似的。槐花鎮并不大,按照地域大小和人口結構還夠不上“鎮”,但它確實是一個鎮,并且有了鎮的模樣。從南門街到北門街,有超市,醫院,幼兒園,集貿市場,還有一個不大的公園,好像這些足以讓槐花鎮的人安居樂業了。
擺渡的人少,渡口常年都是冷清的狀態,船被淹沒在長勢迅猛的水草之中。但每個月的幾個日子里,水草會被人擄到一邊去,小船又在槐花河上悠悠蕩蕩起來。船上的人總是會哼著小曲兒,或者看著遠處的云朵快樂地想著心思。冰涼的水順繩子流向胳膊,這些絲毫不會削減他們的愉悅。這些人不外是槐花鎮在縣城讀書的孩子,有時是那個從縣城嫁到槐花鎮的女人,有時,是我的父親。
2
四月的時候,槐樹開花了,油菜也開花了,白色,黃色,一串一串的滿世界都是。夜里剛下了雨,泥土呈現出浸潤后的松軟。天還沒亮,一雙腳就從北門街走到南門街了,地上濕漉漉的,褲管上已經染了金色,腳尖上也沾滿槐花,這雙腳要穿過槐樹林,穿過棉花地,再爬過一個大堤。這是楊廠長拉著板車去渡口,他要把板車上幾大包毛絨玩具擺渡到對岸的縣城,再從縣城運往一個叫做毛里求斯的地方。當然,后半部分的內容不需要他做。
玩具是玩具廠生產的,這是槐花鎮上年代最久的一家工廠,廠里的活兒似乎永遠做不完,半個鎮的婦女都和這些活兒有著關系。
楊廠長的工作又和這些婦女有著關系,他是副廠長,分管倉庫和人事,楊廠長的事情并不多,大多時候他會伏在一張油漆斑駁的桌子上寫寫畫畫,記記出勤或算算工資表什么的。有時也去車間轉轉,在女工面前停下,看看活兒,然后叮囑一句,針腳要細。
活兒也是可以帶回去干的,下班時分,一些婦女的自行車后座上馱著一大包玩具零件,小白兔的耳朵或眼睛什么的,她們會在次日的白天跑到自家地里侍弄侍弄,待到晚上坐在日光燈下再將小白兔的耳朵侍弄侍弄。
所以,當楊廠長經過這片棉花地的時候,總會看見一兩個身影,四周霧靄濃濃,即便如此,他也能分辨出身影的主人。楊廠長朝清冽冽的空氣里咳嗽一聲,對著身影喊道,李家的,明天要把耳朵交到倉庫啊。
喊聲得到回應后,拉板車的手變得更加有力,到了渡口,他把玩具搬上小船,然后揪一把草,將鞋下的泥巴擦掉,擇一個位置坐好,并不著急過河,而是點上一支煙,仰著腦袋,對著墨黑的天空輕吐煙霧。這一刻,楊廠長是滿足的。
楊廠長就是我的父親。
我從來沒有和父親一起經過渡口,至少在我的記憶里沒有過。我也常常從這里擺渡到對面的縣城,或者從縣城擺渡到槐花鎮。我在縣城讀書,師范,每個月都回槐花鎮。
但我已經很久沒有回去了,上次離開還是春節過后,現在已經四月了,槐花應該開得滿山坡都是,一樹一樹的,像雪一樣綴滿枝頭,我開始想念那些淡淡的香氣,想念家鄉的槐花餅。
上個禮拜母親來看我了,鋁制飯盒里裝滿了槐花餅,她坐在床頭看著我吃,半天都不說話,臨走時突然冒出一句:“還是回去吧——”
我沒有因為母親的話立即回去。她依然每個月來看我,把吃的送來,囑咐我早點回去,然后再回一趟娘家。
她就是那個從縣城嫁到槐花鎮的女人。她的娘家我去過很多次,尤其是現在。那是在縣城的老街,一個三合院,鋪著青磚,紫藤從墻角伸出來,把一面墻爬得滿滿溢溢的。外公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陽光使得他半瞇著眼睛,我問他當初怎么舍得把惟一的一個女兒嫁到槐花鎮呢?外公也不睜開眼,臉上看不出一絲表情,停半天才說:“他們自由戀愛。”
外公口中的他們即是我的母親顧如萍和我的父親楊建設。父親那時也像現在這樣,要把幾大包的毛絨玩具送到車站托運處,只是那時還不是廠長,而是跟在廠長楊瘸子后面的倉庫員,母親是托運站的收貨員,幾次之后,父親便喜歡上了這個扎著麻花辮的小姑娘,她手腳麻利,頭腦機靈,最令他著迷的是那雙眼睛,總有著千言萬語似的。父親開始給母親寫信,那些信既深情款款又熱力四射,他堅信這個叫顧如萍的小姑娘將會成為他的妻子。那些信后來我也看過,文采很好,字遒勁有力,現在還堆在家里的柜子底下,平鋪下來的長度足以使我母親從縣城走到槐花鎮。
這是我父親這輩子值得驕傲的一件事,用我們這兒的話說,就是挺長臉的。二十歲那年,楊建設就和顧如萍結婚了,如果人的下半輩子從結婚開始算起,那父親的下半輩子長臉的事情還有幾件,比如他在楊瘸子的手下很快從一個保管員升到副廠長;再比如他的女兒——楊小白考取了縣城的學校——這些足以讓父親和楊瘸子坐在槐樹底下喝好幾回酒了。
現在父親和楊瘸子喝酒的理由又多了一條——他們開始以親家的身份坐在傍晚的老槐樹底下了,而且還挺像那么回事。
3
春天過后,我還是回到了槐花鎮,父親執意把我的畢業推薦表和一堆材料送到了槐花小學——我將在這里實習,幾個月后,還要在這里工作。父親做這些的時候很開心,母親說他一整天都沒回來,與校長和教導主任打了招呼,也順便打了一宿麻將。
到槐花小學教書,無非又將成為父親長臉的一件事,教師曾是他的夢想,楊建設多么希望把他的漂亮有勁的字用粉筆認真地書寫在黑板上。但這些并不是我的夢想,或許曾經是,這半年來我已經建立了新的人生觀,有了新的打算,我想留在縣城。要不是去槐花小學也是母親的意愿,我一定會和楊建設反抗到底。
去學校報到那天,遇到了楊加林,他正在走廊上和學生說話,看見我突然停下來,我想他并不是奇怪我的出現,我實習的事他父親楊瘸子肯定對他說過。我沒有搭理他,不屑地走過去了,他咬了咬唇,習慣性的,然后繼續和學生說話。
如果按照楊建設和楊瘸子的意思,我和楊加林將于明年春節舉行婚禮,楊建設說,多好的一對,兩小無猜,青梅竹馬。這話讓我聽起來很惡心。
在沒有這個婚約之前,我不討厭楊加林,當然我們也不像楊建設形容的那樣兩小無猜,我和加林從來不在一起玩,他大我五歲,小學的時候經常路過我家,用自行車帶過我一學期,僅此而已。
后來我在縣城讀書,加林也偶爾去縣城,代表青年教師參加培訓,我們在渡口遇到過一次。那天快天黑了,四周的風綿軟無力。加林彎腰把兩邊的水草擄開,從水里撈出繩子。做這些的時候,我們一直沒有說話,可能是因為突然長成人的緣故,水中龐大的倒影可以證明。小船行到河中間的時候,我和他一起拉了一段,也算是兩人齊心協力做了一件事。到岸后,他把船小心地系在一棵槐樹上,動作很仔細,也很緩慢。然后我們一起爬過大堤,穿過一片菜地,各自回家。
現在我經常想起那天——“齊心協力”地過河。我還希望我和楊加林再齊心協力地完成一件事——一起反對那場荒謬的婚約。但是沒有。約定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和他的父親拎了幾大包東西到我家來了,他們一起在老槐樹下喝酒,楊建設和楊瘸子都喝多了,大著舌頭暢想了美好未來。
就這件事,我一直想和父親好好談談,但是對方很不屑,楊建設不喜歡談話這種方式,他喜歡命令。這是他幾十年的職業毛病。那天也是這樣,他們又坐在老槐樹下喝酒,楊加林在一旁斟酒,姿勢畢恭畢敬。這一點很討父親喜歡,他喜歡這種態度,因為他身上沒有,他女兒身上也沒有,我們有的只是倔強和叛逆,這些共同特性,是我們父女之間惟一的聯系。
這場酒從傍晚一直喝到半夜,楊建設打開老槐樹下的一盞白熾燈泡,焦躁的光芒映在幾張臉上,路上只要有人經過,楊建設就會抬起手臂向對方打招呼,這個時候,他是興奮的,是激動的——槐花鎮最大玩具廠的正副廠長坐在一起喝酒,這種局面不亞于兩國領導人會晤。但我鄙視,對楊瘸子和楊加林熟視無睹,這使楊建設很惱火。當我把楊建設寫給母親的信像武器一樣搬到他面前的時候,他臉上的五官徹底亂透了。我說你和我媽還自由戀愛呢,憑什么給我包辦婚姻?
楊建設吼起來:“憑什么,憑我是你老子。”
這就是楊建設,總喜歡在別人面前彰顯威風,而我最受不了的正是這點。我說:“你把工作干得太投入了吧,我又不是你員工,你在廠里處理員工的人事關系,回到家來處理我的婚姻關系。老子怎么了,老子就有這權利了!?”我停了停,倔強的目光在楊建設和楊瘸子之間來回擺動,我想楊建設已經猜到我將要說什么,他不會讓那些話跑出來,更不會讓那些話在楊瘸子面前跑出來的。所以,在我將要張口的時候,一記耳光呼嘯而至。
就在這個時候,我開始憎恨楊加林的,像憎恨楊建設一樣。
4
這一年槐花鎮的春天我錯過了,聽說槐花和油菜花開得比哪一年都瘋,槐花結的槐米,還有油菜籽兒都飽滿結實。鎮上的榨油廠每天都飄著淡淡的油香,這種氣味漫不經心地,籠罩了整個小鎮,讓人心里覺得充實和飽脹,暖暖的,也蠢蠢欲動的。
這個春天應該不同于尋常,很多事情就在這樣一個季節里悄然發生著。回槐花鎮后,我也聽說了一些。比如一條鐵路將要穿過槐花鎮;比如我的父親楊建設和寡婦李蘭的事。前者是楊建設說的,他說這條鐵路將從縣城延伸而來,穿過小鎮,一直到達東邊的縣城。他說槐花河上會架一座鐵路橋,當然,這都是紅頭文件上說的。楊建設說這些的時候顯得了如指掌,好像他看過那份紅頭文件似的。至于后一件事,不是楊建設說的,他不會和我說這些。只有二愣子會和我說這些。
我一直覺得疑惑,每個鎮上都有一個傻子或者二愣子這樣的人物。槐花鎮也不例外。二愣子比我小好幾歲,三年級讀三年,四年級讀四年,現在十五歲了,還繼續著四年級。我是在去渡口的路上遇到二愣子的,他正在放羊,看見我就大喊了一聲:“不許動,放下武器——”
我說:“二愣子,過完暑假你就在我班上了,到時看我怎么收拾你。”二愣子嘿嘿笑了,放下樹枝朝我走來。大概是為了討好我,黑臉笑盈盈的,喊一聲“楊老師”。然后又神秘兮兮地說楊老師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
“你能知道什么秘密?”我停下腳步。
“大秘密,”他說,“楊廠長和李寡婦的,晚上,他們在油菜花地——”
“他們在油菜花地干嘛?你看見什么了?”我很警覺。
“走路唄,一前一后地走路。”二愣子死勁回憶。
我說:“呸,這也叫秘密,一起走路的人多了去了。”
二愣子嘟著嘴,有些失望。我把他吆開,一個人向著渡口走去。我不能說我的內心還是平靜的——楊建設和李寡婦一起走路,油菜地,晚上——我突然感到天空變得黑暗,腳步也沉重起來。我聽說過張大橋和李寡婦的事,聽說過胡二和李寡婦的事,但怎么可能是楊建設和李寡婦?楊建設怎么會喜歡李寡婦,楊建設應該喜歡母親才對,喜歡顧如萍才對,他們是自由戀愛的,他們是一見鐘情的,楊建設還寫過那么多的情書,現在還煞有介事地堆在房間的柜子下面。
我不知道鎮上還有誰知道這件事?母親知道不知道?她去縣城了,是不是因為這件事呢?
我躺在小船上,云層從頭頂壓下來。
我用手機撥通母親的號碼,電話里的聲音很平靜,“媽媽,你為什么去外公家?”我感到自己的聲音在顫抖。
“哦,外公生病了,我陪陪他。”母親回答我。
“那你什么時候回來呢?”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小白?”母親輕聲問道,然后告訴我過幾天就回去。
“可是,媽媽,”我幾乎說不出話來,我把手機貼在臉龐,過了很久才哽咽著說,“可是,我想你了媽媽——”
我不知道我在船上躺了多久,頭頂的那朵云早已變成了雨絲落在臉上。我好像睡了一覺,做了一個夢,又像是沒有睡著,只是陷在回憶里罷了。夢里我又聽見了那個聲音,隔壁房間父親母親木床的聲音,常常在半夜吱吱呀呀的,我已經明白那種聲音的意義,它是和諧的象征。待我長大后,木床被換掉了,換了嶄新的席夢思,我并不喜歡那床,因為再也聽不到吱吱呀呀的聲音了,它綿軟而厚實,仿佛能吞噬所有的快樂。
雨滴越來越大,頃刻間直泄下來,我急忙起身,這才發現船離開了岸邊,繩索已經松開了,船上沒有竹篙,沒有槳,船繼續往河中央飄去,我突然感到驚慌。
我朝著岸邊喊著,雨水把整個世界填滿了,大堤上有個黑影在奔跑,二愣子,我扯開嗓門喊著:“二愣子,二愣子——”
黑影停下了,朝我這邊跑來。
“二愣子,快幫幫我,船靠不了岸了。”
“看看船上有沒有繩子,卷起來,把一頭扔向我這邊,我拉你靠岸。”黑影回答我。
說話的人并不是二愣子,我不認識,管他呢,我只想盡快上岸。我用他說的方法試了幾次,十分失望,由于力氣太小,繩子總是落在水中。岸上的人說還是他來扔給我吧,讓我等一下,他去工地找根繩子——
他向大堤飛奔而去,剛跑出一壟地的長度又折回來,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要挾么?講價么?去工地——顯然他不是槐花鎮的人。
他回到岸邊,不由分說脫下鞋扎進河里,我嚇了一跳,還沒反應過來,一只腦袋已經從船尾冒出來了。他把繩子一頭系在船上,一頭隨他游向岸邊。
一番折騰后,渾身上下都濕透了,雨也逐漸停止,我一邊絞干衣服,一邊感謝他。
“你叫什么名字?”我問。
他低頭穿鞋,沒有回答我的意思,然后趕時間似的迅速向大堤跑去,老遠才轉過身,朝我狡黠地笑,說:“二愣子吧,叫我二愣子——”
5
對于陸飛做好事不留名的雷鋒精神,我還是心存感激的。但陸飛會說他很感謝那場雨,因為那場雨認識了我。
陸飛就是跟著鐵路建筑隊一起來到槐花鎮的。那時槐花正盛開著,白色花簇云一樣凝聚在枝頭。陸飛小我三歲,盡管如此,他短暫的前半生可以用顛沛流離來形容——出生在西藏,被養父母抱到黑龍江生長,七歲隨家人去了新疆,十二歲又回到東北農村,十五歲在遼寧勉強讀了一所技校,十八歲開始背井離鄉……我喜歡聽他的故事,盡管每一階段的生活都糟糕透頂。陸飛常帶著酒氣對我說話,他說他很孤獨,他說他沒有家鄉。良久又問我這是夢境嗎?怎么認識了你?怎么會有這樣一個奇妙的小鎮?
整整一個春天,只要一有時間,陸飛就會躺在鎮西的槐樹林里,那時他還不認識我。認識之后,陪他躺在槐花林的就多了楊小白和一本詩集。陸飛告訴我第一次來到槐花鎮的感覺,他說從沒有看過這么多的槐樹,從沒看到過盛開得如此濃烈的槐花,使人訝異和欣喜,像走進了一個夢境似的。他說北方很少看到槐樹,有的只是松樹和樺樹,筆直筆直的,長得一點兒詩意都沒有。陸飛喜歡寫詩,這也是讓我感到訝異和欣喜的,他的詩我也讀過一些,像描述的另一個自己:
我要準備一把傘和行囊
去遠方
一個很遠很遠的遠方
很長的路
我會穿過森林,河流,雪山和草原
我用露珠洗臉
我會一直走,從不停下
在某一個山口
你會看見我
我穿著灰色長衫
傘和行囊搭在肩上
路上,會有一位老人為我指路
路上,會有一位牧羊的姑娘羞澀地看我
路上,會有野狗,松鼠,狼和烏鴉
路上,我會一邊走一邊歌唱
我或許會在半路死去
在一株不知名的野花旁
于是,那兒就叫遠方
“這里就是遠方。”說完陸飛用兩片槐葉把雙眼蓋住,他說現在就想死去,在這片槐樹林,和一個女人身旁——
我不知道陸飛喜歡槐花鎮的理由是否和母親一樣,母親也喜歡坐在門前的那棵槐樹下,槐花悠悠地飄落下來,落在她的肩頭和老縫紉機上。老縫紉機是母親的嫁妝,二十多年了,聲音依然清脆。天氣好的時候,楊建設幫母親把縫紉機搬到老槐樹下,傍晚的時候再搬回去,遇上楊建設忙碌了,這些活兒就由楊加林代勞。
但母親已經很久沒有坐在老槐樹下了,縫紉機呆在臥室的角落里,偶爾也會咯呼噔噔響幾聲,但聲音都顯得局促和沉悶。母親不再坐在老槐樹下了,這使人很難過,我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對于楊建設和寡婦李蘭的事,我沒有再問二愣子,因為傳言已經像花一樣在槐花鎮上盛開了。我看不出母親是否知道這事,也看不出父親和母親之間的異樣,楊建設依然每天早出晚歸,出門前喝一碗母親熬的粥,晚上照樣享受母親為他打來的洗腳水。他把雙腳浸泡在熱水中,讓雙臂舒展在沙發扶手上,他告訴母親,明天又要去縣城送貨了。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明天他將比任何一天起得都早,天還沒有亮,他就要穿過一片棉花地,穿過大堤——我突然想起二愣子說的話。
楊建設一直保持著二十年前倉庫保管員的工作職責,堅持親自檢貨送貨,這一點深得楊瘸子的贊賞。楊建設說人際關系比工作能力更重要,所以他從一個徒有虛名的副廠長到擁有兩成股份,不能否認他良好的人際關系。
楊建設比以往更忙碌了。鐵路建筑隊來到槐花鎮之前,楊建設就被選為拆遷動員小組的組長,勘探測量出的鐵軌路線將把小鎮一截為二,一些房屋和農田需要退讓出來。拆遷的任務順利完成后,楊建設已經和這支建筑隊混得相當熟了,他經常走進白色工棚和技術人員聊天,甚至看到了施工藍圖,看到了鐵軌的明確路線。當他得知這條鐵路只是穿過槐花鎮,而不會為這個小鎮做片刻停留的時候,楊建設開始了新的任務,他又認真地伏在了那張辦公桌上,將鋼筆汲滿墨水,他要給縣里寫信,給省里寫信,給他從沒去過的中央寫信。
6
寡婦李蘭到玩具廠上班了,作為感謝她給楊建設送來了兩雙自己納的布鞋。母親竟然收下了,并和氣地把她送到門外。那個下午,我第一次看到母親和李蘭站在一起,陽光下李蘭棗紅色的卷發那么恣意,而母親卻像頂著一頭的槐花。母親老了,如果沒有李蘭的出現,我不會意識到這一點。
李蘭走后,我陪著母親坐在縫紉機旁,陽光越發無力,黑暗侵襲過來。我的話題故意圍繞著寡婦李蘭,但母親并不愛聽,幾次打斷我。她弓著背,身體前傾,大概光線昏暗的緣故,她的眼睛覷在縫紉機前。在我有記憶的時候,就看到母親這樣的姿勢,她坐在槐樹下面,但是脊背沒有這么彎曲。可是,現在,這個姿勢刺傷了我,它讓我無法控制——
“鎮上人都在說楊建設和李蘭的事——”話剛出口就后悔了,我看到母親的手在黑暗中顫抖了一下,我不敢往下說,似乎要等待什么,母親沒有理睬,繼續踩著縫紉機踏板,好像根本沒有聽。我們都忘了開燈,黑暗把縫紉機的聲音變得無比巨大,半晌,母親才停下來:“我不相信謠言,你父親不是那樣的人,除非——”她停頓了很久,“——除非,誰親眼看見了——”
很多年以后。我再去思考母親的話,我想我當時一定理解錯了,母親說只要你父親和寡婦李蘭的事沒有被人撞個正著,她都不會相信。他們一起走在菜花地里,并不能說明什么,她相信父親,她相信李蘭到玩具廠上班僅出于父親的善良和同情,后者只是行使了一個副廠長的職責而已。母親憎恨謠言,我也憎恨謠言,它讓原本就孤僻的母親很少再走出屋外。
我終究錯誤地理解了母親的意思,從那之后,我開始尋找某種“真相”,尋找的意義仿佛就是向母親證明她是錯的。
那天晚上,當楊建設又在沙發前享受母親端來的洗腳水時,我把寡婦李蘭的兩雙鞋放在他面前,我感到自己這一舉動的挑釁。楊建設愣了一下,好像早已知曉白天的事似的,我盯著他看,不放過任何一秒鐘,對方臉上每一種細微的變化都使我感到得意。
“李蘭送來的,給你的。”我對楊建設說,但他沒有搭理我的意思,依舊專注著電視節目。
“你為什么讓她到玩具廠上班?沒聽到鎮上人都在說你和她嗎。”我第一次用這種語氣和楊建設說話。母親直愣地看著我,很顯然被我嚇到了,她及時拉開我,阻止我繼續往下說。但晚了,遙控器已經被楊建設“砰”地摔在地上了,他怒吼道:“我廠里的事情你有什么資格說話。”
“我就是想不通,”我咬著嘴唇,“在謠言盛行的時候你讓那個女人到廠里干活——”
我知道楊建設不會給出一個回答,果然他用踹翻洗腳水的方式表示了不屑,“滾一邊去!”他向我喊,“滾到你的房間去。”
“你應該給我們一個解釋,你要給媽媽一個解釋。”我倔強著。
楊建設站起來踢了一腳沙發,然后憤憤甩門而出。
在我和楊建設爭吵的時候,母親在房里小聲地哭泣,這使我無心戀戰,就這件事,很多時候我真希望母親能像胡二家的或者鎮上那些剽悍的女人一樣,跟男人大吵一頓或者跑到寡婦李蘭跟前抽她兩記耳光。但沒有,我的母親不會這么做,她會認為一切事情都沒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一切僅是謠言而已。所以,次日早晨,楊建設離開后,母親竟然責備我昨晚的無理取鬧,“你父親不是那樣的人,”她反復那句話,“李蘭人品不好,但活兒不一定干不好,廠里用她也沒錯,她表示感激送鞋也沒錯。”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母親在安慰自己。最后,母親十分認真地對我說:“小白,你父親不是那樣的人,我不相信謠言,我也希望你不要相信謠言,你要相信你父親,尊重你父親。”
7
入冬以后,云朵每天更深一層。樹葉落光了,野草向大地交還了顏色。鐵軌的生長速度還是超過了人們的想象,幾個月的工夫,它已經像模像樣地躺在槐花鎮了。槐花鎮的人每天都會走上鐵軌看一看,那種神情像是察看莊稼的長勢一樣。只有楊建設的臉上沒有那種喜悅和滿足,寄往省里和中央的信陸陸續續被退了回來,有的干脆石沉大海,楊建設的眉頭鎖得更緊了,頭發也白了一些。但他沒有罷休,而是帶著那些信親自趕往省里。
小船又在槐花河上飄蕩起來了,水草知趣地跑向一旁。楊建設坐在船上,看向河的北邊,再過幾個月,那里將要架上一座鐵路橋,火車從上面呼嘯而過,帶著城市的氣息。楊建設不知道幻想了多少次,他踏上了那列火車,從槐花鎮上車,從縣城下車,或者在更遠更遠的地方下車。
楊加林往我家跑得更勤了,楊建設把這理解為婚約的作用,我卻認為楊加林只是在關心母親。春天過后,準確地說,在那個謠言盛開之后,楊加林幫母親干的活越來越多了,他儼然像我家的一個成員——像我哥哥——甚至有一天在學校的操場上將我攔住,很突兀地批評我,叫我多關心關心母親。加林的母親死于難產,一場災難剝奪了他叫媽媽的權利,他從小就叫我的母親姆媽,穿著母親為他縫制的衣服。坐在加林自行車后座上的那個學期,我們說的最多的話題便是母親,他總說羨慕我有一個全槐花鎮最好的母親。“我用我所有的一切跟你換吧——”他常常這樣調侃。“不換——”我也毫不猶豫地拒絕,那一刻,我終于體會到楊建設的那種長臉。
楊加林來的時候,我都會避開,要么將自己關進書房,要么去鎮西的槐樹林和陸飛約會。槐花鎮的黃昏總是十分悠長,陽光軟綿綿的,把人的身體一遍遍地撫摸透了,夜才開始盛大來臨。那些黃昏,我躺在槐樹林厚厚的枯葉上,閉著眼睛,接受陽光還有陸飛溫柔的輕吻和撫摸。我不再去想婚約的事情了,仿佛和我毫無關系。楊加林和母親從不和我提婚約的事,楊建設也很少提了,楊加林在我家的頻繁出現使他安心落意。那個日子好像安安靜靜地躺在遠方,躺在來年的春天,它和每個人都沒有關系。
我躺在陸飛的臂彎里,他的胸膛寬闊結實,手臂粗而壯,我曾看到這雙手彎曲過鋼筋,搬起過兩根枕木。陸飛說他曾干了兩年的操作工,現在已經升為資料員了。我常常把陸飛和楊加林進行比較,似乎每一處都略勝一籌,即使是同樣的愛咬嘴唇的習慣,陸飛的動作都那么有味道。
我想陸飛怎么就走進我的生活呢,那么及時,在我和楊建設為婚約較勁的時候。當然,楊建設并不知道我和陸飛的事,他更不會知道他的女兒和一個“鐵路上的”廝磨的那些黃昏。鐵路上的——楊建設習慣對鐵路建筑隊這樣叫。
陸飛的吻盤旋而來,像山風一樣,容不得我思緒的半點抽離。我愛你……我也愛你……分不清這幾個字是從誰的唇中飄出,我們就這樣一遍遍地吻著,呢喃著,直到筋疲力盡。我們常常一起躺在槐樹林里,或者躺在渡口的小船上,看太陽一點點地腫脹,再一點點地下墜,船早已離開渡口,和我們初遇那天不同的是,繩索是陸飛故意解開的,他要讓小船在槐花河上隨意飄蕩。然后我們并肩躺著,看著頭頂的星星一顆顆地清晰起來。
“如果每天都能這樣多好,”陸飛說。
我轉過臉看他:“我們幾乎每天都在一起的呀。”
“我是說每天——時時刻刻——一睜開眼——就能親到你。我每天都想你,想得快不行了,《黃帝內經》里說喜傷心,怒傷肝,思傷脾,所以你得對我的脾負責。”說完他拉起我的手放在胸前。陸飛說他病了,病得很重,是一種幸福的病,他要病死在我這里。
我用唇堵住他的胡言亂語。
“我們走吧,”他看著我,“我要帶你走——”
“去哪里?”
“西——藏——”
我坐起來。“你喜歡那里嗎?”陸飛認真地問。
“喜歡,”我也認真地回答,“雪山,藍天,白云,納木錯湖,雅魯藏布江,拉薩河……”我好像曾去過似的。
“對,我要帶你去西藏,我出生的地方,我的魂一直流放在那里,我的生身父母也在那里,盡管可能找不到他們,但我想回去。或許我早該回去了,但這么多年來,我好像一直在等待什么,現在終于知道了——”陸飛停下來看我,“等你,命運安排我到槐花鎮來等你。”
“跟我走吧,”陸飛在我耳邊輕輕說著。
“明年春天,”我回答他,“槐花盛開的時候,你帶我走——”
這個夜晚因為有了約定而感到美好和神圣。我們好像真的離開了槐花鎮,小船離渡口越來越遠,大堤模糊成倒影藏在水下。
當我們用竹篙把小船撐回渡口的時候,卻看見了楊加林,他站在對面,披一身夜色。如果沒有猜錯的話,他是從縣城開會回來的。他看到了我們并肩躺著,并把船飄向遠方,他過不了河,也沒有喊我們,而是安靜地從黃昏等到半夜。
到岸后,我拉著陸飛離開了,沒有和楊加林說話,甚至沒有絲毫歉意,說真的,我不喜歡他這樣。
幾天后的一個上午,楊建設突然沖到學校,將我從辦公室拎了出去,氣急敗壞地——我只能這么形容——向我叫嚷。他朝我指來的手顫抖得厲害,他說:“楊小白,你給我注意點,別給我搞什么花樣,鐵路上的那個,必須給我斷了。”
聽明白了怎么回事后,反而很坦然,我緩緩地對楊建設說:“我們是自由戀愛——”
“放屁,”楊建設手指往下甩去,“楊小白,你聽著,別給我生事,明年,明年春天,給我把婚結了。”
楊建設說這句的時候像是迫切安排廠里的事務似的——給他把婚結了,要不是明年春天我才夠到法定結婚年齡。
我不知道楊建設多久前定下的這門婚事?并為自己的決策得意了多久?他肯定把這也作為光宗耀祖的一部分——多好的一門親——楊加林姓楊,楊小白姓楊,生個孩子也姓楊,這個姓楊的孩子將要繼承兩家的一切,到那時誰還能說清楚玩具廠究竟是楊瘸子楊家的還是他楊建設楊家的。
楊建設離開后,我也把楊加林叫到走廊里,用一種無法控制的氣急敗壞的情緒說:“楊加林,你給我注意點。”我幾乎在模仿楊建設的語氣,“你最好別給我搞什么花樣。”我指的是向楊建設打小報告這件事。
楊加林一臉吃驚,表現無辜的樣子。我說:“你別這樣裝可憐。”
他咬起嘴唇沉默不語,似乎沒有向我解釋的必要。
幾個老師擠在窗口向外看,我轉身離開,走了幾步,看他還站著不動,又折回來,“求你了,”我用一種極其冷淡的語氣對楊加林說,“別咬嘴唇了,真的,你咬嘴唇的樣子,特難看。”
8
寒假時,母親回到了縣城,外公的身體一日不如一日了。臨走時母親反復叮囑我,“照顧好你父親”以及“不許和你父親頂嘴”等等。對于母親的擔憂我想是多余的,因為從她離開后,我便很少看到楊建設,他更加早出晚歸,甚至到了披星戴月的程度。
楊建設已經取消了在家吃早飯這一事項,直接在南門街的老李面館叫一碗陽春面。吃面的時候,太陽已經出來了,慷慨地照耀著楊建設沁出細汗的臉,是的,這個時候,他的臉上總是掛著一層汗珠。面館的老李會扯著嗓門喊道:“楊廠長啊,又去跑步啦。”
楊建設同樣用很大的聲音回答他:“是啊老李,跑步去的。”然后找一個敞亮的地方坐下。
跑步的習慣是在母親離開后才有的,每天早晨,天仍黑著,星星還沒散去,楊建設就起床了,他的動作很輕,但我還是醒了。門輕輕地打開了,又輕輕地關上了,他躡手躡腳地換鞋以及壓抑著咳嗽——我躺在被窩里,聽著這些細微的聲響,假想著楊建設跑步的路線:從后巷出去,經過鐵軌,沿著鐵軌到鎮西,穿過槐花林,再經過一片菜地——我被假想的路線嚇到了,身體在被窩里顫抖起來。好幾次,院門被輕聲關上的那一剎那,我也有掀開被子跑出去的沖動,但一次都沒有,我無法抗拒被窩的溫暖。
后來,在老李面館吃面的那個時間,楊建設開始談論跑步的事情,他會告訴一起吃面的人,鐵軌已經鋪到李四家的屋后了;槐花河上的鐵路橋已經架好了;從鎮東到鎮西竟然有兩千多根枕木呢……再后來,跑步的人增加了,有的人沿著鐵軌的方向從鎮東跑向鎮西,或者從鎮西跑向鎮東,至于有沒有經過槐樹林或者菜地,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跑步的人里還有寡婦李蘭。
母親不在家,我每天的大多數時間都是在床上度過,白天躺著一本接一本地看書,當然,也包括陸飛的情書。陸飛有時發信息來,問我正在干嘛?我也不回答,看著那幾個字傻笑著。傍晚我就會走出家門,迫不及待和情書的主人約會。
我們在街上胡亂填飽肚子后,再回到槐樹林。此時的槐樹林霧氣深重,月亮被緊鎖著,樹葉已經落光了,毫無保留地奉獻給大地,我們打著手電,追逐著彼此閃爍不定的影子。或許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那樣的夜晚,純凈得只想抱著一個人哭。夜越發深重,四周有風吹起,涼薄地貼在臉上,仿佛預示著一場沉重的雨即將落下。
回到家后,楊建設還沒回來,或者已經睡了,屋子里黑漆漆的。母親去縣城后,我和楊建設碰面的機會便更少了。即使知道對方的一些訊息,也是從鎮上人的口中得來的,比如他知道了我和陸飛仍然廝混著;比如我也聽說了他和寡婦李蘭更有眉眼的謠言。
那場雨果然在第二天的傍晚落下了,那時楊加林正在為蠶豆鋤草,雨不像是冬天的,撒潑著性子朝地上倒下來,楊加林躲在走廊下,斜風雨還是將他打濕了。這些日子,楊加林每天準時出現在我家的菜地里,他從家扛著鋤頭,或者提著水桶來,像他每天夾著講義從辦公室走向教室一樣,這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地上騰起一陣煙霧,外面很冷,我打開門,剛要喊他過來避一避雨,就看見楊建設從遠處回來了,我拿起一把傘,迅速沖了出去。我要在楊建設回來之前離開,決不給他阻止我和陸飛約會的機會。
那一夜我沒有回去,準確地說,沒能回去,院門被楊建設反鎖了。后來我知道那個傍晚楊加林被困在走廊下一直到雨停,我還知道那個傍晚楊建設沒有回家,而是追向了我。他沒有打傘,所以跑了一截就折回去了,回到家中,楊建設十分生氣,他憤憤地把門反鎖上,然后躺在床上聽著外面的動靜,楊建設多么希望能聽到我乞求的敲門聲,一遍一遍地,于是他在這個聲音里起床,開門,當然,也包括狠狠地訓斥我一頓。
可是,一直到下半夜,這個聲音都沒有出現,我沒有像他想象的那樣敲門,而只是用鑰匙輕輕捅了一陣,便和陸飛離開了。
我們在槐樹林里以擁抱打發時間,然后又在陸飛的工棚里看了一會兒書,直到那些建筑隊的人準備休息了,我們才回到鎮上。寒冷和黑暗追趕過來,緊隨著我們,在老李面館吃了一碗面后,才決定在對面的朝陽旅店住上一夜。
楊建設敲開門的時候,我們都被對方嚇到了,他只穿了一件單衣,被汗和雨水黏糊在身上。這一夜楊建設并沒有睡,敲門聲沒有在他意料之中出現,使他更加氣急敗壞,他跑到我們常去的槐樹林,又跑到渡口,幾乎跑遍了整個槐花鎮。這應該是他這些天來最有意義的一次跑步,他一刻都沒有停止,渾身疲乏,直到遇到面館的老李,才使他又鉚足了力氣。
楊建設已經氣得說不出話來了,指著陸飛的手在半空中晃了很久。
9
外公終究沒能熬到春天,柳樹還沒發芽的時候,外公走了。他的骨灰被母親帶到了槐花鎮,這是外公第一次來到這里。
母親是喜歡槐花鎮的,她說她看了第一眼就不想離開,她無法在外公活著的時候說動他,現在死了,她要將他安葬在自己身邊。我曾問過外公,為什么不喜歡槐花鎮呢,春天的時候到處都是潔白小花,一串一串的,那么好看。外公閉著眼睛半晌才回答我,說他這輩子最討厭的就是槐樹了,因為它通身長著刺兒。
楊建設依然把大多的時間花在寫信上,火車就要運行了,他像臨考前的考生似的,忘記了吃飯和睡覺,白天寫了厚厚的信有時被揉成一團,夜晚在日光燈下又重新鋪開信紙,他找出已經生銹的圓規和尺,在白紙上認真畫下槐花鎮的地形,標出地理位置,人口結構,交代了這個小鎮從八年抗戰時期到五年自然災害的困苦,但最終都挺過來了,他感慨萬千道,現在的槐花鎮,雖然工業不很發達,卻擁有了八千多畝種植地,連續八年都畝產豐收。槐花鎮還沒有一條像樣的與外界聯系的路,他多么希望火車能在這里做片刻停留,載上槐花鎮的人,載上那些要去縣城讀書的孩子們。
火車是一個月后開通的,像一年前的那個春天,鎮上的人擠在了鐵軌兩側,伸長脖子,等待火車通過,這些黢黑的臉,從火車出現的方向,轉向火車消失的方向,像向日葵。火車沒有為槐花鎮做片刻的停留,甚至沒有慢下腳步的意思。瘦小而貧瘠的槐花鎮還不具備挽留它的力量。它像一條巨龍,帶著城市的氣息和垃圾呼嘯而來,不知道它來自哪里,又去向何方,像一個匆忙的行者,桀驁不馴的,從槐花鎮疾馳而過。
建筑隊離開了,陸飛沒有走,作為資料員他要和另一個施工員再呆上一陣,等到工棚拆遷,他們才會調到下一個工地。
我和楊家林的婚期越來越近了,幾棵老槐樹已經被楊建設鋸下,正在讓木匠做一套像樣的家具,那些抽屜和柜門的雛形,一件件地擺在院子里,等著好天氣刷一遍油漆。
我依然隔三岔五地和陸飛在槐樹林約會,什么都阻擋不了我們,槐樹已經打苞了,過不了幾日槐花就會洋洋灑灑地開放。那個時候,當所有人為我的婚事張羅的時候,我已經和陸飛躺在西藏的藍天下了。還有什么比這更美妙的呢。
火車依舊每天碾過槐花鎮,車輪與鐵軌碰撞出的聲音,提醒著它的落后。鐵軌像一道疤痕,伏在槐花鎮瘦弱的脊背上,小鎮被割成了兩半,鐵軌以南,鐵軌以北。鎮上的人已經習慣了從南邊走向北邊,需要繞一條長長的橋洞。火車若無其事地經過,它的來去和槐花鎮從沒有任何關系。鐵軌交磨的聲音,總是在幾個時刻準點響起,強調著它的到來和離開。
半夜時,楊建設會突然驚醒,看著頭頂漆黑的屋梁,巨大的聲音使得身下的床板顫動起來,原本安靜的小鎮,無數房屋在黑夜里齊聲嗚咽。聲音消失的時候,槐花鎮又落進了靜謐之中,但楊建設再也無法睡去了,火車仿佛從身上碾過一樣,他感到從未有過的困苦和難受,他在床沿上坐了很久,然后索性披上衣服走出門去。
這個夜里,我也醒來了,是被一陣清香喚醒的——槐花開了,這是春天最自然樸素的香味,我從床上一躍而起,來不及洗漱就向著工棚飛奔,我要告訴陸飛槐花開了,我還要告訴他我要和他一起去西藏。記得去年冬天的時候,陸飛問我為什么要待到來年槐花開放?我無法告訴他一個明確的理由,我喜歡槐花,我喜歡槐花鎮的春天,那個瞬間,我仿佛突然理解了母親。
工棚的門緊閉著,敲了很久才打開,我問陸飛呢?陸飛怎么不來開門?快幫我喊他起床。
對方看著我愣了好一會兒,揉了揉眼睛說,走啦,陸飛前晚就走了——
10
楊建設寄出的信,沒能改變鐵軌的運行方向,卻改變了我的人生方向。他向中鐵第XX建筑部,鐵道部,以及公安機關寫信,檢舉了一個叫陸飛的人在槐花鎮鐵路建筑施工期間,對當地居民生活構成影響,并具有傷害婦女的違法犯罪行為。
上面下來調查的時候,竟沒有通知當事人筆錄,楊建設代替我匯報了情況,并用他良好的社會關系使陸飛在派出所蹲了十多天,作了口供,寫了檢查,然后由建筑隊的項目經理調職到一個南方工地。
從工棚回來,我感到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飽脹著憤怒,槐花的香氣使人喘不過氣來,我想起了楊建設伏在燈光下的那些夜晚,我都快原諒他了,他的脊背越發彎曲,頭發這一年也白了很多,我甚至想走上前和他說說話,像一個女兒和父親的對話一樣,但我怎么也不愿相信,那些夜晚,他竟然做著一件齷齪不堪的事情。
我推開院門,四肢仿佛失去控制,一腳踢壞了幾只新做的抽屜,一群麻雀從老槐樹上撲楞撲楞地飛走了。楊建設不在屋里,這才想起他早已出去了——
天還沒有亮,只有一些慘淡的藍色散落在黑暗之中,我爬上鐵軌,從鎮東跑向鎮西,我一刻也不想停,跑向槐樹林,跑向渡口,又穿過棉花地。突然,我停下腳步,感到心跳得厲害,楊建設沒有跑步,他究竟去了哪里?我想起那個傍晚母親和我的對話,母親說她不相信謠言,除非誰親自看見了——
幾個月來,一直感覺有件事等著我去做,原來,等著我的就是這件事情。二愣子趕著羊從身后經過,我幾乎沒有思考便喊住他,我說二愣子,楊老師帶你去看一個秘密,大秘密——
我們從大堤下來,向西北角的油菜地走去,春天真是一個可怕的季節,一切植物奮力地從泥土中鉆出來,試圖要遮蔽整個大地。在田垅盡頭,一片野草蓬勃的溝渠里,終于看見一個聳動的脊背。天暗得使人難受,我感到呼吸困難,雙腳像陷在泥土里一樣,一步也邁不動。二愣子突然興奮起來了,好像看到了從沒看過的精彩畫面,他沖到我的前面,向黑影跑去,又敏捷地將他們的衣服挑在一根樹枝上,然后咿咿呀呀地向槐花鎮狂奔。
我也返回身,是的,我要回家,我要告訴母親,我要親口告訴我的母親顧如萍,我看見了,看見了你相信的那個人,正在做著你不愿意相信的事。我還要告訴母親,你錯了,那些謠言才是事實。
我往家走,雙腿已經不聽使喚,好像完成的這件事,消耗了我全部的力量。二愣子已經到鎮上了,從南門街跑到北門街,他咿咿呀呀的聲音喚醒了這個早晨。是的,傳言比我的腳步還快,我追不上它們。
太陽躲在云層后面,遲遲不肯出來,這注定又是一個陰霾的日子,我想起槐花鎮的春天,似乎都是這樣的天氣。這段路我走了很久,好像走盡了我這一生。當我到達槐花鎮的時候,已經聽到母親死亡的消息。
母親死了——
趕在真相大白這一刻,她躺在鐵軌上,讓一列飛奔而來的火車將自己撕成碎片。
母親出事那天,楊加林哭得特別厲害,從小到大第一次看見他哭,他對我說姆媽早就知道謠言了,姆媽只是不愿接受,她怕一接受,就沒臉呆在槐花鎮了,她喜歡槐花鎮,她不想離開——
鎮上很多人都去看了,像二十多年前母親嫁到槐花鎮的那天。枕木被染紅了,衣服尸骨延綿在鐵軌上,母親的臉早已分辨不出來了。
加林沒有再去教書,因為每天火車經過時發出的聲音,都使他一陣哆嗦,他把白色粉筆塞進嘴里,塞得滿滿的,然后麻木地嚼著,直到粉末從嘴角溢出來,白得像槐花一樣。再后來,他就成了另一個二愣子,每天躺在大堤上,只要有人經過,就會跑上去抓住對方的衣角,說,告訴你們一個大秘密,大秘密——
鎮上的人還是會談起我的母親,那個曾經扎著麻花辮的姑娘,他們都沒有忘記母親從縣城嫁到槐花鎮的那年春天,槐花的白色像汁水一樣四處流淌——談論的人突然沉默了起來,好像不忍回憶母親短暫的一生,不知道誰感嘆一句,唉,就是死得慘哩,被火車撕得碎碎的,鐵軌上到處都是骨和肉哩——
是的,我的母親終究把自己留在了槐花鎮。
這一年,槐花又開瘋了,一樹一樹的,春雨過后,地上又是一寸深似一寸的白。
責任編輯: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