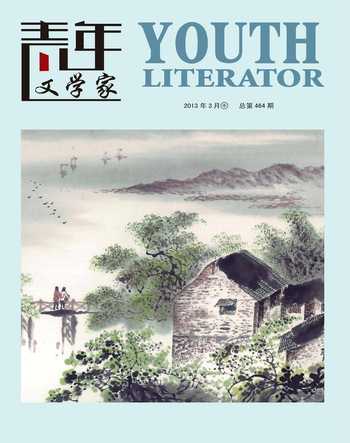兩個多余人形象的比較
摘 要:在俄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學史中,都出現了一系列“多余人”的形象。他們有著相似的基本特征,但也因為社會、文化、個人經歷等多方面的差異,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態度。本文從奧涅金及周萍兩個形象入手,嘗試對“多余人”同中有異的性格和經歷及其形成的原因作出比較分析。
關鍵詞:多余人;奧涅金;周萍;比較
作者簡介:起建飛,女,玉溪師范學院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外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的教學與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3)-8-0-02
在世界文學的人物長廊中,有一組人們熟悉的被稱作“多余人”的藝術形象。從奧涅金到畢巧林、奧勃洛摩夫、羅亭等一系列人物,他們有著共同的特點:都是出身于貴族地主階級的青年;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多少接受過啟蒙思想熏陶,有對自由人權的要求;在現實中都感到苦悶、壓抑、找不到出路;永遠不會站在腐朽政府一邊,也永遠不會站在人民一邊積極斗爭。他們孤芳自賞,高談闊論、碌碌無為,從來不會認真去做一件事,也從未想要認認真真去做完一件事。他們都出現在共同的歷史時期。十九世紀初,俄國社會各種矛盾都十分尖銳,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思想傳入俄國,喚起了部分年輕的知識分子的覺醒。但現存的任何思想都不足以提供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辦法。于是這些覺醒中的青年人找不到真正的出路,猶豫彷徨,既不甘心沉淪,也不能和民眾站到一起,由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成為社會的“多余人”。
大約一個世紀之后,在相似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的現代文學作品中也出現了一批相似的文學形象,如《沉淪》中的“他”,《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莎非女士的日記》中的莎非、《雷雨》中的周萍等。他們同樣誕生在一個舊時代最黑暗的時刻。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一批出生于舊時代的青年接受了“五四”前后引進的西方思潮的影響,有了初步的覺醒。然而辛亥革命的失敗,新時代的曙光一閃即逝,社會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不知道出路何在,感受了自由思想的青年們陷入了更大的苦悶和彷徨。他們苦悶卻懦弱,不甘心命運又只能自怨自艾而無所作為,也成為社會的“多余人”。
正如世上不會有兩片相同的葉子一樣,這些“多余人”形象也不盡相同。下面,就以周萍和奧涅金兩個人物來對“多余人”做一個粗淺的分析與比較。
周萍是曹禺先生的名作《雷雨》中一個重要的悲劇人物,在第一幕他剛出場時,作者對于他的形象、性格特點有一段全面深入的分析。他是“一個美麗的空形” ,“他不能克制自己,也不能有規律地終身做一件事。然而他明白自己的病,他在改,不,不如說是在悔,永遠地在悔恨自己過去由直覺鑄成的錯誤;因為當著一個新的沖動來說時,他的熱情,他的欲望,整個如潮水似地沖動起來,淹沒了他。”[1]
這讓我們很容易聯想起普希金筆下俄國文學史上的第一個“多余人”——奧涅金。奧涅金學過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懂一點兒拉丁文、詩歌、音樂,卻沒有一樣精通。他最大的本事是追逐愛情游戲、尋歡作樂,但就連對自己的這種“本事”,他也失去了熱情。“他已患上了一種病癥/…簡單說,俄國人的憂郁病/已經漸漸纏上他的身/…什么也不能打動他的心/什么也不能引起他的注意。”[2]厭倦了一切,尤其厭倦了大都市的無聊生活,也為了躲避債務,繼承遺產,才促使他來到了鄉下。和周萍一樣,他也悔恨:“誰真正生活過并且思考過,/誰就不能不藐視世人;/誰感受過,一去不返的日子的/幻影就不能不擾亂他的心:他已經不再迷戀生活,/回憶像毒蛇咬噬著他,/悔恨也日夜把他折磨。”[3]
但是和周萍一樣,盡管對以往悔恨,他們卻沒有辦法改變自己的生活。而這悔恨也成了他們痛苦的重要原因。四周是無盡的黑暗,眼前是無望的生活。但是他們既沒有勇氣打破黑暗,也不能忍受黑暗,更不能忍受自己對于生活的這種“忍受”。內心永遠要承擔自我的拷問。然而對自己懺悔要遠比對上帝懺悔困難得多,因為自我的否定是最殘酷最徹底的否定。既不能按自己的思想來行動,又不能按自己的行動來思考。永遠不能有真正的行動,只能有永遠的悔恨。這是一種徹底的“進退失據”。在這樣的心態之下,難免要陷入苦悶、彷徨、迷惑、痛苦之中。
為了擺脫苦悶,他們都選擇了“愛情”這種個人的方式來進行自我的救贖。周萍生長在令人窒息的家庭中,造成他苦悶的原因被具象化為陰沉的老宅院和在家中有無上權威的父親的壓抑。不滿而又懦弱的性格,對父親又恨又敬;恨父親,又缺乏勇氣來正面反抗,敬佩父親,又沒有同樣強大的性格來掌控自我的命運。為了使自己內心的矛盾得到平衡和宣泄,他與自己的后母——父親的妻子——發生了亂倫的關系。可是他不愛后母,知道亂倫的齷齪,更怕承擔私情敗露的后果。于是他又轉而去尋求侍女四鳳來擺脫自我的責難,不想對方竟又是自己同母異父的妹妹。從親緣的亂倫到血緣的亂倫,他一再想要擺脫心靈的壓抑,獲得平衡,卻使自己陷入更大的不平衡之中。一無所長的他當然不能承受真相的殘酷,只得以自殺毀滅自己早已沒有意義的生命。
和周萍不同,俄國的風氣給了奧涅金機會,他可以肆無忌憚的與上流社會的美人們周旋。多年沉溺于熱戀的游戲,毀滅了他的熱情。所以當達吉亞娜對他表白時,他不能接受。也許是因為出于生活習慣,使他不能相信對方的真心。如果他相信,就更加沒有勇氣接受了。以他“多余人”的性格怎么可能去認真面對一件事情?幾年后,他“愛”上了已嫁作他人婦的達吉亞娜,這不過是又一次的借著愛情的游戲來拯救自己苦悶的靈魂。達吉亞娜的拒絕破滅了他自我拯救的幻想,小說也在此戛然而止。留給世人的不過是對奧涅金這部“沒有讀完,/就突然放下,把它遺忘”[4]的“人生的小說”的一絲喟嘆。
不過,我們可以看出,周萍和奧涅金對待愛情、追逐愛情的心態是有著明顯的差異的。奧涅金早已不相信愛情的神話,他追逐愛情只是因為精于此道,別無他長。他不相信愛情,卻需要一次次的沉醉來暫時打發時日,消磨生命。愛情成了一次次的逢場作戲。他拒絕達吉亞娜的話倒也不全是冠冕堂皇的托詞,他確實已經不能夠正常的“生活”。拒絕達吉亞娜,意味著也拒絕了平常的生活。他是一個愛的懷疑主義者。“有誰值得愛?有誰能相信?/誰對我們永遠不變心?/…誰能寬容我們身上的缺點?/誰永遠不使我們感到煩悶?”[5]普希金插入的這段議論中的九個疑問,正是奧涅金懷疑一切的心態的寫照。但周萍是相信愛的,他只是不相信自己也還能付出同樣的感情,也不相信自己還有被救贖的可能。所以他會被四鳳的真情而感動,卻也只能覺得“不能不愛她”。四鳳身上的新鮮與生命力,是他自己所缺少的,少女特有的純潔和對愛的熱烈,暫時沖散了他心上壓抑、腐敗的死氣,所以他不能離開四鳳而活。他已經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四鳳新鮮的生命之上,茍延殘喘。當這個愿望被破滅時,即使四鳳不是他的妹妹,他也不可能再活下去了。
所謂“多余人”,都是腐朽社會與新思潮結合的早產兒,都有同樣頹廢的人生態度。但在相似的性格之下,周萍的悲劇多了一層文化批判的意義,而奧涅金的悲劇多了一層現實批判的意義。中華文化幾千年的傳承使每一個個人成為歷史鏈條上的一扣,而聯系各個環扣的規則是以宗法制為核心的各種壓抑個性的行為規范。每一個個體都將把繼承來的觀念繼續施加給下一代,就像《駱駝祥子》中的虎妞,《金鎖記》中的七巧一樣,周萍的父親周樸園變本加厲地把自己所受過的壓抑施加在了他人和后代身上。周萍“多余人”性格的形成和父親的重壓有著不可分的關系。所以周萍在看似輪回地重復著父親的行為的同時,把他的苦悶斗爭指向了父親,他最終選擇的個人斗爭的最大努力,不過是要逃開父親走出令人窒息的老宅子去。但是周萍不但沒有走出老宅,反而在老宅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象征。個人的微弱力量是不足以打破傳統的鎖鏈的。相反,個人想要脫離社會歷史鎖鏈的行為卻導致個人被社會歷史吞噬了。與其說周萍是自己“多余人”性格的犧牲品,不如說他是獻給沉重的文化傳統的一份祭品。
周萍要逃離的是象征傳統與文化壓抑的父親與老宅,奧涅金要逃離的則是令他窒息的上流社會的中心——彼得堡。這里充斥著舞會、表演、裝腔作勢的高談闊論、爾虞我詐的“愛情”、貌似體面的決斗。奧涅金厭惡這一切,但是自己也一直以這樣的方式生活,所以他不能不也厭惡自己。生活現狀的不可改變,自己的不能改變,加深了這種厭惡感。于是他由大都市來到鄉村,從國內到國外。不停的漫游反而加重了他的苦悶,整個歐洲不過是上演《欽差大臣》式的鬧劇的一個大舞臺,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真正新鮮的空氣。永遠身處其中,所以,奧涅金的漫游不可能是真正的逃離。一旦他的個人行為與社會的共同行為不一致時,懦弱的性格使他選擇了妥協。因此,盡管不情愿,他仍然參加了自己深惡痛絕的決斗,打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因此,他在一次次漫游之后回來,過的還是一樣虛空的生活。于是,奧涅金的苦悶指向了以彼得堡為核心的整個現實社會。如果這個社會不顛覆,奧涅金的苦悶永遠不可能有出路。然而就目前的情況而言,這又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愿望。于是,奧涅金被遺忘了,彼得堡的生活還在繼續。“現實”的這片烏云,也壓在了讀者的心上。
既然生就了“多余人”的性格,周萍與奧涅金的悲劇命運注定是不可避免的。只不過,周萍的命運宿命的意味更重些,而奧涅金就完全是一個時代命運的悲劇了。這和作品的體裁有一定關系。戲劇要求更強烈的沖突來加強舞臺效果,而小說有更充裕的空間來展現生活的細節。周萍的經歷確實太戲劇化了。他就像俄狄浦斯一樣,我們明知他會有怎樣的命運,他自己卻不知道。我們將眼看著他在自我救贖的努力中,使自己更加陷入了命運萬劫不復的深淵。在他的生命中,命運是一張你越想擺脫,越被它牢牢束縛的羅網。盡管他也是特定時代的產物,但不可能每一個同時代的人都有他這樣離奇的經歷。種下“惡因”的是父親周樸園,嘗到“惡果”的卻是周萍為代表的子女們。這是中國人觀念中典型的“父債子償”式的倫理懲戒,而且是最嚴厲的一種懲戒。換句話說,周萍既然是父親的兒子,就要為了父親的罪孽受到懲戒,這是命運的安排。他的悲劇可以一死了之,但是,還活著的周樸園才是那個真正被懲戒的罪人。
奧涅金就不一樣了。他所經歷的,是同時代的所有年輕人的共同經歷。他所面對的是特定時代解決不了的矛盾。他只是活得比較清醒,卻和別人過得沒有什么兩樣。他是整個時代的一個投影,是時代的共同命運決定了他的沉淪。
如今,創作《葉甫蓋尼·奧涅金》和《雷雨》的時代都已經遠去了。然而“多余人”卻還在我們的身邊潛伏著。從有人將《廢都》中的莊之蝶看作當代的又一個“多余人”之日起,包括一度流行的衛慧筆下的人物在內,又掀起了新一輪對“多余人”熱鬧的討論。這說明“多余人”也可能潛伏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靈魂深處。當一個個體在時代變遷的大逆轉中覺得彷徨無措時,都可能面對來自靈魂深處的相同拷問。但愿那時我們能知道該怎么辦。
注釋:
[1]、《雷雨》第一幕,《曹禺選集》46-4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年1月北京第1版。
[2]、《普希金作品選》341頁,馮春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9年11月第1版。
[3]、《普希金作品選》344-345,同上。
[4]、《普希金作品選》576-577頁,同上。
[5]、《普希金作品選》425頁,同上。
參考文獻:
1、《普希金作品選》 馮春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9年11月第1版。
2、《曹禺選集》 曹禺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年1月北京第1版。
3、《外國文學史》 朱維之、趙澧主編,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1月第2版。
4、《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 劉元樹主編,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5、《歐洲文學史》楊周翰等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6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