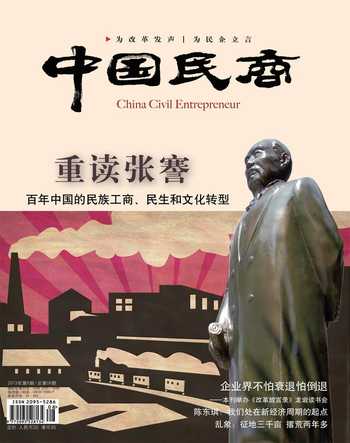慈善篇:“散盡家產以濟天下”
張光武
張謇曾言:“有錢人的焰勢實在難受,所以我非有錢不可。但那般有了錢的人是一毛不拔做守財奴,我可抱定有了錢非用掉不可”。至于他是如何用錢,他將錢用在何處何人之身,他的用錢理念又是如何?
張謇的回答是“國家之強,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實業教育,而彌縫其不及者,惟賴慈善。”
早在光緒二十二年,海門一帶,“自夏徂秋,霖潦漲溢,下沙災狀尤酷”。張詧、張謇即挺身而出,協同海門廳同知“霍邱王賓經理疏河”,張詧、張謇兄弟“散振平糴諸事,費出私財,不足則募,又不足則貸以繼之”。
張謇、張詧最早創辦的慈善機構是1906 年建成的育嬰堂,以收養棄嬰和赤貧家庭孩子為主,兩年后收養嬰兒多達1500 人。張謇和張詧還分別從育嬰堂認領男嬰,視為己出。張謇認領之兩名養子,取名為佑祖、襄祖。筆者祖父張詧所領養即為三伯父張敬安。余生也晚,未曾得見三伯父,然家中大人小孩凡提及之,必以敬稱,三伯長子讓武哥,在堂表兄弟姐妹中年齒居長,為人敦厚,亦極獲敬愛,了無隔閡,親情一片,全無嫡出、領養之別。
1907 年,南通地區江岸、海岸不斷坍塌,張詧乃動員地方資源成立南通保坍會,自任會長,穩定南通江岸海岸災情,每年賑救流離失所居民達幾十萬之眾。
從1912 年起,張氏弟兄創辦之慈善醫院、貧民工廠、濟良所、棲流所、殘廢院和戒毒所相繼建成。
1913 年,張詧發起,與張謇在南通城南創辦南通醫院(今附屬醫院)和兩所分院,一在唐閘,一在金沙。舉凡赤貧者看病均可免收醫藥費。
同年,張詧與張謇于南通城外辟地160 畝,建成義園(即今之公墓),歸葬者無論貧富,一視同仁。
1912 年,張謇六十壽辰,將宴客費用和親友饋金全部取出,創建南通第一家養老院。
1920 年,張詧用七十壽辰所得親友饋贈,在家鄉常樂鎮三廠鎮創辦南通第二養老院,該院常年費用7000 多銀元,亦全部由張詧私人承擔。
至1922 年,張謇七十壽辰,再度創辦南通第三養老院。
張謇、張詧弟兄創辦之養老院,前后收容孤寡老人500 余人。
談及自己和三哥創辦養老院初衷,張謇嘗自述心跡,謂:“夫養老,慈善事也,迷信者謂積陰功,沽名者謂博虛譽,鄙人卻無此意,不過自己安樂,便想人家困苦,雖個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濟,然救得一人,總覺心安一點。”此言對于后世不無啟迪。
1916 年張詧與張謇共同捐資,在南通西門外建成棲流所,收留乞丐并培養彼等習藝能力;又收留精神病患者,令其獲人道資助而不擾礙社會。
1912 年后,張謇著手規劃籌建殘廢院和盲啞學校。殘廢院建成后,張謇規定,凡殘廢者,無論年齡,無論籍貫住所,均可接納入院,且包辦吃飯穿衣。
1903 年,張謇赴日考察,專門考察日本的盲啞學校,回國后致信江蘇按察使,建議官方開設盲啞學校而未果,1911 年,張謇在赴北京之際,專程考察煙臺芝罘盲啞學校。1915 年,張謇終于一償夙愿,創辦狼山盲啞學校,是為中國人自己建立的第一座盲啞學校。
1922 年,張詧斥私資在崇明外沙(今啟東)大生二廠創辦大生醫院,救治缺醫少藥、罹患流行疾病之貧苦百姓。
凡抵南通參觀之中外人士,一致發現南通街頭竟無一乞丐、醉鬼和流浪漢!因為南通已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會,世人期頤大同,南通先行大同。
育嬰堂初成,張謇乃以賣字籌錢捐得款項為繼。其時計劃每季鬻字得500 兩,一年便有2000 兩收入,足夠收養一百多名嬰兒。至1922 年,大生集團經濟滑坡,張謇個人分紅和薪俸驟減,直接影響慈善事業,張謇乃再次登報鬻字籌措善款。持續兩年多,至1924 年張謇已屆71 歲高齡時方始停筆。
蓋張謇和張詧用于慈善機構之費用,盡為本人和親屬的捐贈。張謇曾言,南通之慈善事業全“系自動的,非被動的,上不依賴政府,下不依賴社會,全憑自己良心去做”。
僅慈善一端,張謇、張詧功在當時,澤惠千秋!
那么,至張謇逝世,張家實際經濟狀況到底如何?
1927 年北伐軍兵抵上海、南通,接舉報誣指筆者祖父張詧為“土豪劣紳”,乃舉家遠走大連避禍,至1931年風聲過后回上海,先于拉都路(今襄陽南路)永安別業,后于戈登路(今江寧路)363 弄覓舍而居,竟無力自置房產,所居均為租賃之屋,經濟窘狀可見一斑。
張詧之女、筆者三姑母張敬莊、五姑母張敬默均為普通教師,三姑母自五十年代起獨居任教之合肥醫學院教工宿舍,生活簡樸,筆者家庭及三伯父張敬安、四姑母張敬直和五姑母家生活狀況均與普通城市平民相若,五叔敬敷(希祖)早年留學,因二戰滯留美國,戰后與美裔五嬸白手起家,辛勤勞作,養家糊口,終老一生。
而筆者自記事起,家中生活亦極節儉,五十年代上海一般高級職員家庭給孩子訂份牛奶為尋常事,而筆者兄弟姐妹自小起從無月訂牛奶之享受,每日飯桌上,一小葷兩素一湯為家常便飯;偶食排骨,切成薄片,一人一片便為少有之樂事;偶進雞鴨,則雞腿鴨腿必是由母親先行撕下留給父親或大哥的,其余每人所食,僅為母親分在小碟里的一份。一年到頭,家中老小,從無食水果之享受。每年過年,家中小孩拿幾毛錢壓歲錢,看著別家孩子放煙火,我們唯一之享受便是買幾只小鞭炮,一只一只小心翼翼地放,放完了,滿地去找自家和別人放剩的啞炮,從中間掰開來,支上火頭,那中間便會冒出一串火星來, 也是一種樂趣。
筆者從小學至大學畢業長成前,唯一一次因考進大學由母親帶去南京西路凱司令吃西餐,那是從母親到筆者自己都是視作隆重的。
母親終年忙碌操勞,偶或抽紙煙,家中幾上常置,為價格在勞動牌和飛馬牌之間、2 毛7 分一包的東南牌。從小至大,常見母親徐姮由藏書閣樓取下外公徐積余生前所贈珍稀版本書去商賈處變賣貼補家用和接濟親友,其余金石、銅鏡、文物則全部捐贈國家。母親在文革中患腦血栓加長期營養不良,病中不敵一場尋常感冒病逝。
文革期間,紅衛兵喪心病狂,掘開四祖父張謇墓地,僅得一頂禮帽,一副眼鏡,一把折扇,一束胎發,一顆盡根牙耳,祖父母張詧夫婦遺骨幸賴當年家中老親陳叔夫婦(一為南通服務行業負責人、一為通棉一廠即大生一廠黨委書記)不顧安危冒雨搶救轉存泥壇中。
據筆者所知,四房即張謇直系后人生活狀況與我們三房亦伯仲之間,小異大同。現在想來,一切全不足怪,張家人用于事業就像用于家計,凡與民生、與民族整體利益息息相關之事業,則當機立斷,萬金不惜;用于家計又如用于事業,一分一厘從來都是精打細算緊著過的,利始而義終。如此行事,察古往今來,只怕不是一頂“商人”或“紳商”帽子可以蓋住。
古人有“散盡家產以濟天下”、“毀家興學”之說,張謇、張詧兄弟則以無私精神守護民生理想,追求實現民族整體利益,到了傾家蕩產地步,真正兌現了其人“家可毀,師范不可毀”的歷史承諾,張氏弟兄所為,俯仰上下,比肩者只怕是寥若晨星。
今天重提企業家的社會良心,不能繞開張謇和張詧,也繞不開張謇和張詧。張謇和張詧窮其一生,為世界留下一個嚴峻的現實話題:當人從窮人變成富人,當人創造了財富以后,他會把財富用在哪里?用在哪些人身上?或者說,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后,下一步會怎么樣?
張謇和張詧用短暫生命架起的,是一個重大社會和人生問題的答案:民生至大。富者無權輕視貧者,貧者無權輕視富者。
寫在后面
“謇無詧無以至其深,詧無謇無以至其大”。
張謇一生,踐履文化轉型,追求民族整體利益,唯民生為大,全不計個人之利害得失,自然曲高和寡。張謇對此十分自知,嘗言之,自己一生辦事做人,只有“獨來獨往、直起直落”8 個字,又謂:“我要去做東家,難有伙計,要做伙計,難有東家”。環視其一生,能始終信任他、理解他、支持他、伴隨他、且甘隱其后、為其后盾、自始至終、休戚與共、雖傾家蕩產仍在所不辭、七十余年如一日的,自非兄長張詧莫屬!
張謇、張詧一母同胞,七十余年始終互相扶持,共同創業,至死不渝。
“退庵無弟,則創之勢薄;嗇庵無兄,則助之力單。故蛩蟨相依,非他人兄弟可比”。
“這二三十年間, 我父創辦實業教育地方自治, 都是伯父贊助一切, 大概我父對外, 伯父對內,我父規劃一件事的大綱, 他就去執行; 或者我父主持大計, 他去料理小節。 所以我父三十年的聲名, 事業的成就, 伯父很有贊襄的功勞”。
張謇、張孝若父子上述感言,貼骨貼肉貼心,直道出中國近代第一城成功秘辛!此段牽動近代歷史之動人故事,極具醒世意義,足值今人記取。
歲值嗇公張謇誕辰160 周年,爰為此文,紀念四祖父嗇公張謇暨祖父退公張詧。
2013 年4 月 8 日19:49 一稿
2013 年5 月11 日13:53 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