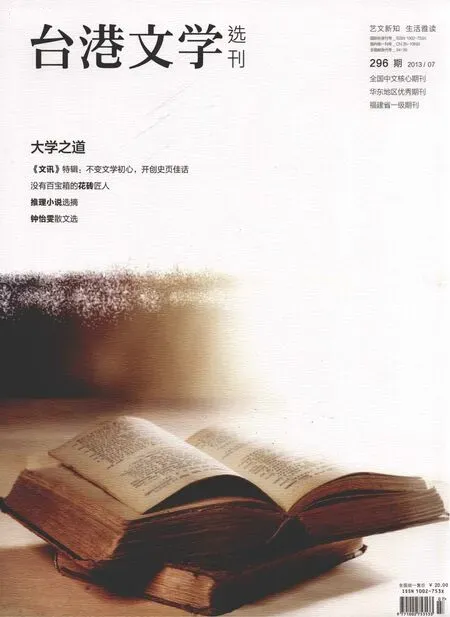鬼氣與仙筆
周芬伶(臺灣)
前言─馬華文學與女散文家
也許我們都來自陰暗復雜的女兒國,大家族重男輕女的舊遺毒,同樣是五個女兒一個弟弟,而且都曾經男裝想當男生。她像是我遺失在野半島的另一個妹妹,一見面就覺得格外熟悉,但引起我注意的是她身上飄著怪異之氣,初見面時她還是學生,眼睛化濃妝涂藍眼影,眼睛已夠大還特別強化有一絲妖異,那時女作家化濃妝的很少;第二次見面剪超短發無眼妝,圓咕嚕的眼珠如銀球古靈精怪,很像年輕時的沙岡,總之還是“怪”,然我與怪咖有緣。她說話又急又快,大驚小怪一堆,生活的小事都被她說大了,跟琦君一樣愛聊家常,而且話急得插不進,只能聽。
貓咪啊病痛,吃藥看醫生,還有能見陰暗之物……
穿得漂漂亮亮到東海一看到樹大叫:“我要爬樹!”我在一旁聽得直笑。
爬樹絕對是她生命中重要的事,那是她自己的位置,一個可以入世也可以超然的角度,“那是我跟世界的距離,跟家人的關系。一個旁觀者,住在她自己的島上。”令我想到寫《爬樹的女人》的樹冠生態學家羅曼教授,她是個另類樹冠學家,在澳洲用繩索爬樹,懷孕時利用采櫻桃的籃子登上尤加利樹,在非洲乘熱氣球俯視研究樹頂,又到美國麻州的溫帶林與貝里斯的熱帶雨林搭建樹冠步道,過著很具高度與難度的生活。她在樹上看到另一個世界,另一個自己。鐘怡雯的“異質”在于她的僑民與流放身份,在傳統與現代夾縫中的矛盾掙扎。
馬華文學與臺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鐘怡雯自己也很有使命感,我一直認為馬華文學在臺灣應有一個位置,它不是僑民文學,也不是本土文學,而是新移民(流放文學),也就是使用非母語在外地產生的文學,像哈金或高行健在西方,溫瑞安、李永平與黃錦樹在臺灣,他們的復雜性更豐富臺灣的文學。
臺灣是移民之島,舊移民長久定居而形成本土文學,新移民則有認同的焦慮與疏離感,在神州時代他們化為儒俠,練武舞劍,當中方娥真的散文最是令人驚艷,但其脫塵絕俗到底難入人心,鐘怡雯的文章能入人心,緣于她是激烈的豹走女子,與生活貼近,有著鮮明的個性與剛柔相濟的文風,令人樂于親近。
就像鐘怡雯強調馬華文學的浪漫精神,屬于她的浪漫是在不斷逾越與出走中,有種回不去的焦慮與掙扎,所以總在奔逃,進行中,動態的描寫特別出色,時而喃喃自語,大多是自問自答,獨特的鐘氏出品,像馬克白的獨白,像是懺悔,其實是上下求索的天問。
從北緯五度的野半島奔逃到北緯二十三度的福爾摩莎,她心魂未定,時常回望過去,有時對人事錯迕的現實感到迷亂。
在家庭中,她作為長女,背負著父親的沉默與威權,她選擇叛逃,逃離家門,越過國界,進入另一個傳統威權的學術圈,又進入婚姻,看似適應得不錯,但她還在驚魂不定,還在自問自答:我做對了嗎?哦,可能不對。這種自責感的催逼與母體脫離的分裂感,并非在地作家所能感受。
就像她愛引用的英文歌曲,也都是進行式與疑問句:
I hear her voice in the morning hours she calls me
Radio reminds me of my home far away
And driving down the road I get a feeling
That I shouldve been home yesterday
渦形回歸─流放的激進與退守精神相抗
作為僑民的后代,肩負著龐大的文化與家族的陰影,在種族語言多元,城市與雨林并置的馬來西亞,如果她選擇逃往西方,以英文書寫,那就很難掙脫湯婷婷與湯恩美一路的“混雜風”,或林玉玲書寫家族夢魘《月白的臉》,令人疑惑為何移民的家族圖象何以如此陰暗與壓抑,那讓人喘不過來的壓力,與凌亂破碎的心靈圖象有時令人不忍卒讀。
可能是漢文化越在邊緣地帶越保守威權,呈現歷史“停滯”的現象,儒教與父權的威力更顯巨大。
她選擇的臺灣,雖也是漢文化的孤島,卻是散文的樂園,起初她以中文系女子的典雅傳統崛起,與一般作家先從自傳散文出發再擴大之有所不同,她是倒著來的,先從其他枝枝節節寫起,像她的失眠(《垂釣睡眠》)、容易摔傷(《傷》)、常看病、貓咪(族繁不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于《瘀》,那有著過敏靈魂的年輕女子如何每晚與睡眠搏斗,寫得絲絲入扣:
不過兩三天的時間,我的身體變成了小麥町─大大小小的瘀傷深情而脆弱,一碰就呼痛,一如我極度敏感的神經。那些傷痛是出走的睡眠留給我的紀念,同時提醒我它的重要性。它用這種磨人脾性損人體膚的方式給我“顏色”好看,多像情人樂此不疲的傷害。然而情人分手有因,而我則莫名地被遺棄了。(《垂釣睡眠》)
就這樣她以生活的細節敘述,進入女散文家之列,她回避家族尤其是父祖的書寫,對于雨林生活也只有順便帶到,直到2002年出版《我和我豢養的宇宙》之后,她開始較有意識地省視自己來自的血緣,《今晨有雨》可能是個重要轉折,寫的是祖父的過世:
十八歲那年我離家,不,簡直是逃家,在你不知情的狀況下,走上不歸路。我慶幸自己走得遠遠的,徹底與你決裂,也一筆勾銷算不清的債。隔著南中國海,我開始寫作,卻無法書寫我們的關系。正確的說法是,跟血緣相關的一切,我根本拒絕去想。書寫是救贖。許多人這么說。我不相信,也不需要。何況,沒有沉淪,何需救贖?我寧愿沉默。(《陽光如此明媚》)
這時還是倔強地排斥書寫家族或愛情、婚姻,不能寫的事要不就是太親怕過于暴露,要不就是太瘋狂連自己都無法面對。2006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三少四壯專欄,后來結集而成的《野半島》就如火山噴發般,熱焰四射,還十分透明,語言是鐘氏出品但更急更快更雜,各種語言交雜,嗅覺味覺視覺并糅,尤其說及家族史,膽血都咳出來,果然是夠瘋狂而拒絕說出,難道她的拒絕與沉默都不需要了嗎?
感覺是擺脫小女生時期最后一次叛逆,但也是她正視自己的勇敢之舉,風格也有了改變,更鮮明,夠嗆辣!
我一直覺得傳統退守與激進嗆辣同時存在她身上,但她2006年之前是往傳統退守的方向走,之后是往激進嗆辣方向走,連她的馬華論述也進入左翼與雨林中,她更成熟自信,這對于她的創作顯然是一個跳躍。
因此她的作品可分為兩期,一是“小女生”時期,小女生是她的愛貓的名字,活了十年,也陪伴她來臺的第一個十年。2002年小女生過世,祖父過世幾乎同時發生,意味著她心中的小女生走了,大女生正在長大,以貓紀年,對于“無處不貓”的她想必不反對;2002年之后進入“野半島”時期,也即是把關愛回顧于她所來自的島,她與島的分離已近二十年,隔著時空與緯度看更顯永恒意義,“分離也是如此。必得被時間沉淀過才產生意義,此時,眼淚方會因不舍而流,綿綿的悲傷包裹起生活,你會發現,原來分離是一種浸泡記憶的福爾馬林,它讓記憶成為永遠”,以審美的眼光回望自己的家族與島,必須承認它在漢文化的邊陲,而禮失只能求諸野半島。
追溯鐘怡雯創作途徑是呈渦形回歸的,外面的圓是朝傳統中文典雅的方向前進,如《河宴》亦有寫及父祖家庭,仍不失懷舊散文溫柔敦厚之旨,再貼進自己的生活與內心作細節敘述,還有小物件的愛戀如《垂釣睡眠》、《我和我豢養的宇宙》,可謂世紀末的精美,再往記憶深處的野半島前進,那個島不是孤島而是比臺灣大好幾倍的半島,有意識的空間與離散書寫,像一張又一張充滿刺點的老照片,充滿后現代精神,這過程也是相互辯證的過程:
在另一個島,凝視我的島,凝視家人在我生命中的位置。疏離對創作者是好的,疏離是創作的必要條件,從前在馬來西亞視為理所當然的,那語言和人種混雜的世界,此刻都打上層疊的暗影,產生象征的意義。那個世界自有一種未被馴服的野氣。當我在這個島凝視三千里外的半島,從此刻回首過去,那空間和地理在時間的幽黯長廊里發生了變化。鏡頭一個接一個在我眼前跑過,我補捉,我書寫,很怕它們跑遠消失。我終于明白,為何沈從文要離開湘西鳳凰,才能寫他的《從文自傳》。(《北緯五度》)
不僅要離開,而且要離開得夠遠夠久,但太久也不行,久了就成一張張“月白的臉”,鐘怡雯描寫的臉一張張血色鮮艷,野性難馴。
鐘怡雯的人不能以美來界定,現在美女作家一堆只有更模糊她們的面目,她個子嬌小仙風道骨配上一張熱帶風情的狐臉,手心永遠冰冰涼涼,就像是筆記小說走出的狐仙。
鐘怡雯的文體交糅著現代與古典,現代如莒哈絲、蘇童的實驗精神,古典如魏晉人的瀟散不在名教之中,服食丹藥愛談玄虛則有何晏、劉伶、阮籍之風,筆法形影神問答如五柳先生。
這些文章幾乎可以將鐘怡雯定位為“鬼”作家了,詩人有“詩鬼”,散文當然也應有“文鬼”。但這只是鐘的一部分,她還有更陽光更多元的部分,屬于她神的一面,濕婆神,她是濕婆神的子民。
濕婆神的子民─北緯五度的熱帶憂郁
熱帶真的只能是憂郁的嗎?當溫度常年維持在高溫,一年只分涼季與熱季,涼季也在三十度上下,熱季比涼季長很多,陽光白熱化,那是干熱與濕熱交替,熱帶雨林帶來的豐沛雨量與野生巨獸橫走,在長期流汗與脫水中,我相信心情會受影響,鐘酷愛陽光,體質陰虛的她確實是具有向陽性。
她的憂郁與過敏、失眠體質還來自家族遺傳,長期游蕩在外與寫作研究,耗損精神,精氣神皆不足,她愛自己的辦法是勤看醫生愛吃藥。
過敏的人通常善感,善感易失眠,長期失眠引起憂郁,這是永無休止的惡性循環,但我要談的是本質的憂郁,熱帶的憂郁跟波德萊爾談的文明引發的憂郁不同。熱帶的憂郁較接近加謬的“異鄉人”的荒謬的憂郁,而致弒人/弒父,這是因為疏離與冷漠引發的憂郁成狂,如在《北緯五度》所寫的:
瘋狂的基因是鐘家的遺傳,從廣東南來的曾祖母吸鴉片屎,她本來就個性古怪,祖父和父親都得她幾分真傳;我的表叔從青年起便關在“紅毛丹”(瘋人院)關到現在,上回出來后把他老爸鋤死,沒人敢拿自己的命開玩笑再放他出來;三姑在我小學時住過精神療養院。大姑的獨生子,我那長得像混血兒的萬人迷表弟,二十歲出頭便住進了精神療養院,十幾年了時好時壞,大姑心疼惟一的兒子,千里迢迢把他送到澳洲醫治,兒子的病沒好轉,反倒是她在六十二歲之齡得了憂郁癥。二姑就別說了,一家四口簡直被下降頭一般。她三十歲左右出車禍之后精神狀況不穩定,五十歲郁郁而終。如今她的兒子也是,唉!
看來父系較嚴重,體質較像父系的鐘,難怪會有多愁多病身,書寫多少是種治療,父親原先也許不是那么沉默,當他從男子向父神靠攏就沉默地“像一首詩”了;又或者父親對他人不沉默,只對妻子與兒女沉默,讓沉默變成高墻。
她在叛逆的青春期選擇叛逃,與父祖絕裂,因此初來時甚少回家,她遺棄那個島,那島里有她瘋狂的血緣,然后她被那個島遺棄。應該說是“割裂”導致的“分裂”,而讓她愛恨交加,她用疏離與冷漠武裝自己,但是她對妹妹與母親的愛難以割舍,在日漸成熟后,又嫁給同鄉人,家鄉既是娘家也是夫家,她以迂回的方式重新拾起,并在其中找到平衡之道。她回怡保“我容易失眠。在怡保卻碰到枕頭就入眠,外加奢侈的午睡。有一次竟從半夜十二點賴到隔日十二點半,后面只隔十尺的地方在施工,夫家上下連同兩位同行的朋友七點多鐘就被吵起,惟有恒處睡眠不足的我創下奇跡。起床后從容梳妝打扮,赴遲到的餐會。餓了一晚胃口奇佳,早午餐一起吃可真是難得的美妙經驗”,吃飽睡足加上運動,純屬感官,她稱之為“狗日子”,感覺是享受也是幸福。再回家的感覺仿佛是心靈與身體的填補,過往的創傷與陰影,不再那么沉重。
女子在叛逃父家之后割斷臍帶,她想做她自己,這時也許是憂傷與憤怒交加,當父家變成娘家,就柔化為女兒之思,當夫家的生活是甜蜜的,從夫家回望娘家,變成具體的鄉愁。
她的鄉愁即她的寄脫與救贖,因此關于“野半島”的書寫多半是心靈回歸的神釋與超脫。
回憶與雷電交加─混雜風與重口味
從“小女生”到“野半島”時期,最大的改變除了回歸的生命圖像,在語言上多元交織,五味紛陳,題材統一,色彩鮮明,如寫怡保的吃讓人“飽死”,在復雜味覺上多著墨“我是南蠻,只愛南洋式的酸辣。搬離怡保后,在南部吃的多是馬來餐印度餐,熱心鄰居送來的料理徹底改造了我的胃。母親后來也做那種中馬印三種混合的菜,連糕餅也是。混血的胃讓剛來臺灣讀書的我十分不適應,很長一段時間處在‘餓死狀態,更加懷念‘飽死的日子”,還有各式糖水涼茶,寫出怡保人食“口野”的拼勁,更勝愛吃的臺灣人一籌;又寫異文化的混雜風情,既是后殖民也是后現代的,顏色十分刺激。
在語言上外表嗆辣,內里溫純,如寫印度人愛抓頭蝨《蝨》之篇,居然有張愛玲風的艷異之美:
我在油棕園度過童年的后半期和青春期,前后搬了四次家,搬來搬去,總與印度朋友為鄰,他們是善于利用美感征服貧乏的民族。即使住處那么狹小,屋前總也種滿繁茂的花草。餅干桶油桶牛奶罐子當花盆,栽出艷麗搶眼的花色。他們偏愛濃烈的花色,家家都有那么幾蓬大紅大紫的九重葛,花太重,以致不支垂地,很有散漫慵懶的情韻。花質厚重結實的雞冠花也是他們的最愛。不過那質地太過剛毅,顯得火辣辣的紅色有些殺氣。奇怪的是在油棕園住了那么久,很少看到有人捉頭蝨。花下捉蝨,應該有點怪誕的美感吧!
跟張不同的是,她直來直往不愛迂回,寫馬來西亞風土民情的作家不少,能寫其金玉其外,也能寫敗絮其中,又能得溫柔敦厚之詩旨的,鐘的散文堪稱一絕。她的混雜風與重口味形成她自己的特色,也表現移民作家的遺忘時間與雷電時間的并置。
相信讀者看完《野半島》,也有真相大白的感覺,但這是血與淚換來的,移民作家的痛苦如果不是逃就是困,作者選擇的先是逃,然后是困,最后是脫困。
結語
散文從文學性散文走向文化散文,似乎是世紀交替的重要轉變,文化散文涵蓋環保、飲食、旅游、運動、性別種種議題,有大散文與小品,品質有粗有細,大如余秋雨、楊牧;小如林文月、劉克襄,鐘在新移民與馬華散文這一塊自有她重要的位置,在臺灣散文中也是中生代的代表性作家。
散文家最怕被自己的風格所困,鐘能在盛年殺出一條血路,她還年輕,這表示她創作力旺盛,未來的路還很長,是可以被祝福與期待的。
(本輯系本刊特約稿)
責任編輯_楊際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