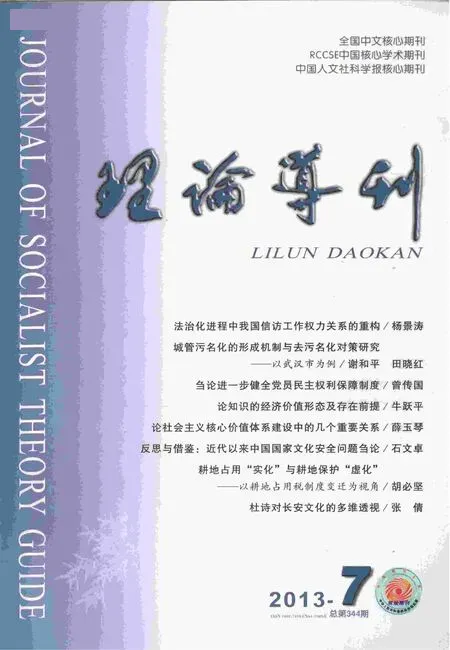網絡治理:政治價值與現實困境
李靜


摘 要:網絡治理是一種新的治理模式,它結合了第三方政府和協同政府的優點,強調在服務過程中公民應該擁有更多的選擇權。網絡治理強調主體由一元化轉向多元化,公共利益成為各個行動主體的共同追求,充分體現出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政治價值。但“理性經濟人”的存在不可避免會出現合作困境,“搭便車”效應也可能會導致參與困境,職責難以劃分會出現責任困境,而公民直接參與則會危及代議制政府、政府空心化從而出現合法性危機。
關鍵詞:網絡治理;政治價值;合法性;現實困境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3)07-0052-03
崇尚等級的官僚體制在20世紀是政府實現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的主要組織模式,強調層級化和權威化,處理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式都相對簡單和模式化。隨著社會日益復雜,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傳統的官僚體制已經顯得力不從心。如何應對21世紀更為復雜的挑戰,如何實現有效治理?公共管理和學界都在從不同的角度探討新的治理模式。
一、網絡治理:一種新的治理模式
網絡治理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逐步成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議題。網絡治理意味著政府在更大范圍內與私人公司、各種團體和非營利組織合作,以期實現公共目的,并提供各種公共服務。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認為網絡治理代表了四種發展趨勢的集合,它將第三方政府高水平的公私合作特性與協同政府充沛的網絡管理能力結合起來,然后再利用技術將網絡連接到一起,并在服務運行方案中給予公民更多的選擇權(如圖1)。[1]
因此,網絡治理實際上摒棄了傳統層級制政府自我封閉的管理模式及科層管理的縱向的權力運作模式,融合了第三方政府和協同政府的兩種治理模式的優點,構建政府與社會的各個領域的橫向聯系,并為公民提供更多選擇權以構成密切合作、相互依賴的網絡關系和治理模式。
陳振明(2003)認為網絡治理是“為了實現與增進公共利益,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私營部門、第三部門或公民個人)等眾多公共行動主體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環境中分享公共權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務的過程”。[2]這一界定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同,從中不難看出,網絡治理理論的主體是多元化的,包括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權力運作的模式是橫向的、合作的、分享式的,治理的目標是為了實現公共利益,而不是某一權力主體的私利。
網絡治理各主體間作用模型(如圖2)解析如下:
首先,網絡治理的主體構成發生了變化。網絡治理模式中,治理主體由單一趨向多元,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都是網絡治理的主體,非政府部門包括私營部門、公民和第三部門。
其次,網絡治理主體的角色重新劃分。傳統的科層制的治理模式中,政府是公共事務唯一的管理者,是單一的權力主體。在網絡治理模式中,政府從公共管理行為的唯一主體轉變為公共事務管理的參與者之一,是網絡治理各關系主體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樣受到網絡規則的控制。政府扮演著“元治理”的角色,是構建合作治理網絡的負責人,是保證合作治理網絡有效運行的管理者和協調人。非政府部門則通過網絡治理模式參與到公共管理中,平等地管理社會公共事務。
再次,網絡治理的權力作用模式發生變化。政府與非政府部門的關系是相互獨立的、平等的合作關系,權力的作用模式是依靠各個主體間的平等協商而產生的協議來實現公共管理的目的,以實現社會整體利益。因此,公共管理成為了政府和非政府部門共同參與而形成的公共行動體系。
二、網絡治理的價值體現
網絡治理無疑為公共管理領域的一場革命,代表的是等級式政府管理的官僚制的結束,取而代之的是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相互依存的公共管理新模式,適應了當代公共管理的環境變遷及其發展趨勢,治理主體多元、權力主體之間以合作為主要關系基調,社會自主自治成為公共管理的主要的模式追求,公共利益成為各個管理主題的共同目標,民主、平等和自由成為網絡治理的主要價值體現。
1. 民主:網絡治理的內在價值訴求。民主源于古希臘語,民主(democracy)由法語的demokratia演變而來,其基本含義是demas(人民)和kratos(統治)。亞里士多德是闡述古典民主最杰出的思想家,他強調“(公民)應享有平等的權利……(違反平等原則)的政體一定難以長久”。[3]7盧梭也強調積極參與的公民對于社會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全體公民應該結合在一起,決定對于共同體來說什么形式是最好的。赫爾德認為“民主需要這樣一種共同體,在這種共同體中,人民享有一定形式的政治平等”。 [4]2民主是全人類追求的終極價值,但這種價值是抽象的,對于民主的理解從古典民主到現代民主理解的角度并不相同,但作為一種價值導向,民主意味著人民對國家或地方的重大事務具有參與、決定的權利;作為一種工具導向,民主可以為解決社會問題、解決價值沖突提供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就是公共過程中的公開的積極參與。
不論從價值還是工具的角度來說,公民的政治參與都是民主的必需品。在民主實踐中,代議制民主成為各國民主實踐的首選,即使代議制政府給予了公民廣泛的政治參與權利,“不僅是發展自我認同感、個性和社會差別——及多元社會——的一種手段,并且其自身就是一個目的,即一種至關重要的民主秩序”。[4]144這樣民主就很容易淪落成為如熊彼特所言的“競爭性的精英主義的民主”。而網絡治理的出現不可避免地帶來一場民主的變革,公民參與的范圍將更加廣泛,并突破傳統的投票和選舉的主要方式,真正地參與進政府決策中,由治理對象轉變成為治理者,表達自己意愿及實現自身利益的機會將大大增加。因此構建個體化的社會成為可能,個體化的發展也將成為必然,實現公民民主權利不再是空談。
2.平等:網絡治理的外在價值體現。平等意味著相同或相等。古典政治學強調的平等理念是“人是平等的動物”,普通民眾在“人生而平等”的前提下,其生命在價值上是等同的。亞里士多德在探討平等觀念時認為,公民具有平等的投票能力,公民在原則上具有擔任官職的平等機會。民主的實現離不開自由,而自由的實現又離不開嚴格的政治平等。
作為現代政治學的一種價值核心,德沃金(Ronald Dworkin)要求人們“認真對待權利”,把平等稱為“至上的美德”,認為平等包括對生命的平等關懷、對公民自由的平等尊重、對經濟利益的平等分配。平等更多強調的是形式平等、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形式平等強調社會成員在權利和資格方面的平等,都擁有相同的從憲法和法律規定基礎上的各項權利。形式平等是實現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的基礎。實現形式上的平等可以為每個社會成員提供相同的進取機會,從而使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獲得基于個人奮斗而取得的成績。結果平等則是對每個生命個體的一種尊重,從賦予每個公民以生命的尊嚴出發,彌補因能力差別而致的結果不平等。所以形式平等應該是所有的平等類型中最具現實意義的部分。
盡管實現完全平等是一種奢望,在實踐中都應盡可能做到形式平等,盡量減少在平等的思辨性角度上的停留。網絡治理的出現為實現形式平等提供了更為完善的操作平臺。當公民個人成為治理主體一元之后,公民真正地變為權利主體,將人民這樣一個群體性的概念轉變為實在的個體,權利承載者開始具體化。公民、私營部門和第三部門同政府一樣成為規則的制定者,政府與以往角色的不同之處僅僅在于它還承擔著協調者的角色。社會政策的制定不能再忽視哪一方面的意見,絕對的服從將成為過去,合作成為社會治理的主要基調,正如羅爾斯所述,人類社會中,“每個人的幸福都依賴于一種合作體系,沒有這種合作,所有人都不會有一種滿意的生活。”[5]在合作過程中,不同的利益群體不可避免的要有一定的利益沖突,各個利益主體都想最大限度地獲得利益的最多分配,那么利益分配的原則是什么?在沖突協調的過程中不同的治理主體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因此利益分配的協商規則制定過程中各主體的權利分配便成為關鍵因素。這個時候最需要體現的就是平等價值。以平等為前提制定規則,實現合作共贏,這是網絡治理的外在價值體現。
3.自由:網絡治理的終極追求。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自由有兩個標準:一是“輪流統治和被統治”(ruling and being ruled in turn);二是按照個人選擇的方式生活(living as one chooses)。[4]7自由在現代西方社會被認為是最高的政治價值,是人類幸福及自我實現的前提和基礎。傳統自由主義的自由被稱為“消極自由”(negative),它強調以理性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眼光看看待人類,肯定個人具有充分的理智和自制能力,反對一切形式的強制;新自由主義強調的是“積極的自由”(positive),認為一個人的自由不是絕對的,而是有條件的,自由要受其他力量的制約。
自由還是個人達成自我實現和自我價值的前提條件,自由涵蓋著生命活動主體的自覺性、自愿性和自立性,這些都是自由的本質內涵。人作為人的存在,從其本質上來講是自由的,但自由不是絕對的,并不是可以無條件獲得的。正如馬克思所言“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6]從這些思想家的論述中可以看出,自由是有條件的,自由的實現不是脫離社會而孤立存在的,自由是人類追求的共同目標。在實踐網絡治理的過程中,以民主作為價值訴求,以平等作為外在的價值表現,歸根到底是要實現個體的最終自由與解放。平等是實現自由的前提和基礎,自由則是實現平等的最終結果。公民只有通過參與社會公共事務,與政府和其他非政府部門協商合作以完善公共服務,在實現治人以及治于人的過程中,與其他治理主體相互制約與合作,才能選擇相對自由的生活方式,從而實現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三、網絡治理的現實困境
任何一種理論的誕生,如果僅僅具有價值上的無可比擬性,并不能說明其實踐上的適應性,是否具有現實意義還需要經過充分的論證,網絡治理同樣如此。網絡治理強調各參與主體之間的相互依賴與共同合作,其現實困境也由此產生。
1.“理性經濟人”導致的合作困境。“理性經濟人”作為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即假定人都是利己的,而且在面臨兩種以上選擇時,總會選擇對自己更有利的方案。參與網絡治理的各個主體除了政府部門外,還有公民、第三部門和私營部門,而所有的非政府部門在客觀上都代表著特定的群體或者階層,網絡治理理論上要實現的目標是社會公共利益,現實中的治理主體在以平等的地位面對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的時候,如何能夠避免個人或組織以“理性經濟人”的身份追求自身而不是整體的最大利益?因為即使“理性經濟人”獲得最大收益,也不必然會導致整體收益最高。
另外,在面對治理對象的時候,是不是任何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都可以用合作方式加以解決?政府在處理某些公共問題上顯得力不從心,這些公共問題通過網絡治理就一定會奏效嗎?非政府部門之間如何處理競爭與合作的關系?因此,加強合作的時候應如何避免類似“囚徒困境”現象的出現將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2.“搭便車”效應導致的參與困境。“搭便車”行為是一種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的投機行為。因為團體利益共享,所以在一個共同利益體中,會有一些個體或組織自覺不自覺產生投機心理,產生即使自己不做,也會有別人去做的心理,而在集體行動中,單獨的個體或組織是否出力、出了多大的力,往往難以確定考證的標準。但結果卻是顯而易見的,“搭便車”的個體或組織增多,必然導致集體整體效率降低、集體利益受損。網絡治理恰恰需要全體社會成員及社會組織的積極參與以解決社會公共問題,那么應如何避免參與治理過程中的“搭便車”現象?
另外,一旦“搭便車”現象增多,參與公共問題的治理主體發現自己必須經過艱難的努力才能獲得社會地位與經濟效益而不勞而獲者卻大量存在,必定導致其參與治理的積極性受挫。
3.職責不清導致的責任困境。責任問題是網絡治理面臨的最難以解決的困境。政府是公認的公共權力的掌控者與行使者,掌握著非政府組織無可比擬的公共資源,在提供公共物品上具有規模效應與規模優勢的同時,也在滿足實現起點平等的政策傾斜的公正性要求。
網絡治理出現的背景是傳統的官僚制出現了問題,以一體化集中管理為特征的官僚制被公認為效率低下,扼殺人的創造性,降低人的滿意度,被認為是實現社會管理、政治管理的工具。但實際上,網絡治理又何嘗不是如此,只不過是以一種工具理性代替另一種工具理性而已。但傳統的官僚制的特點具有分工明確、責任明晰的特點,而網絡治理理論強調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相互合作,在合作當中公私部門要分享權力、分擔責任,這時必定會涉及到治理權力應如何分配及職能如何劃分等一系列的問題。職能不清會帶來治理主體行為受限、義務劃分不明、責任認定困難,難保不會出現相互推諉的結果。這種責任困境該如何擺脫?而且,由于非政府組織自身發展水平、管理模式及利益取向等原因,也決定著其參與社會治理水平的高低。
4.公民直接參與導致的代議民主的困境。公民直接參與可以理解為直接民主,而現代民主政治更多采取的是代議民主的形式,體現的是公民的間接參與。在民主問題上,羅伯特·達爾指出:“在公民參與問題上,兩種民主都同樣存在著不可克服的限制:在參與行為所需的時間和有資格參與的人數之間存在的相互作用,為雙方都設置了無法克服、無法繞開的限制。”[7]直接民主會導致決策效率降低,間接民主則有可能做出違背民意的決策。因此,網絡治理理論的出現似乎想解決這個兩難困境,促進公民社會發育,提高公民社會之于國家的自主性,從而實現民主的終極價值,實現“社會是由自己管理,并為自己而管理。所有的權力都歸社會所有”的美景。但合作網絡是否能與代議民主對抗并取而代之?代議民主該何去何從?
而且,在前面的幾個困境面前,網絡治理理論究竟能有多大作為,網絡治理能否提高決策效率?在民主與效率之間,究竟應該如何選擇?究竟哪一種民主形式更適合當代政治?這些都是政府官員和公共管理學者要思考的問題。
5.政府權力下移導致的合法性困境。合法性存在的前提是民眾的認同和服從。合法性危機也就是一種認同危機和服從危機。和平時期政府合法性源自于政府部門基于其掌握公共權力為公眾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基礎上。一旦網絡治理理論在實踐中得以踐行,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權威受到挑戰,則必然導致民眾對政治系統的認同減少,政府將如何發揮“元治理主體”的作用?是否還能有構建治理網絡的能力?原本屬于政府的合法性是否會由于其功能減少而轉移至非政府部門那里?
后續問題也會接踵而至,公民會不會因為政府減少承擔國家責任和減少履行國家義務而自動拒絕履行公民義務?當真如此,政治系統運行也有可能出現危機,政府在履行國家權力的時候必然會遇到阻礙。
結語
不可否認,網絡治理理論的出現畢竟為公共管理提供了一種新的治理模式,并在處理一些社會問題的時候也顯現了可行性和有效性;也為政治民主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視野和角度,必定會在社會動員和政治動員方面發揮大的作用,從而促進社會民主的發展。針對其可能面臨的困境,可以在明確治理主體間職責分工、建立并完善非政府部門參與制度與渠道、建立合作主體信任交流機制等方面加以緩解。
參考文獻:
[1][美]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D·埃格斯.網絡化治理[M].孫迎春,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18.
[2]姚引良,劉波,汪應洛.網絡治理理論在地方政府公共管理實踐中的運用及其對行政體制改革的啟示[J].人文雜志,2010,(1).
[3][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386.
[4] [英]戴維·赫爾德.民主的模式[M].燕繼榮,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5][美]約翰·羅爾斯. 正義論[M]. 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13.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7][美]羅伯特·達爾. 論民主[M]. 李伯光,林猛,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9:118.
[責任編輯:宇 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