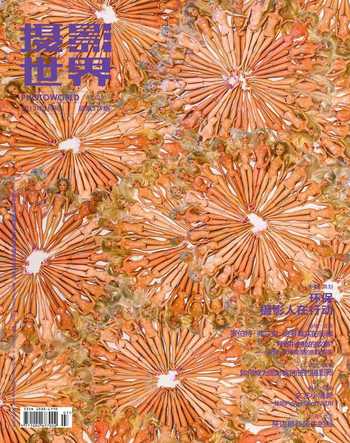西蒙·哈森特:冰山在融化



1963年,美國氣象學家愛德華·羅倫茲(Edward N.Lorentz,1917~2008)在一篇提交紐約科學院的論文中,提出“蝴蝶效應”(The Butterfly Effect)的概念—“蝴蝶效應”是指一種混沌現象:在一個動力系統中,初始條件下微小的變化,能帶動整個系統的長期、巨大的連鎖反應。而在攝影師西蒙·哈森特(下稱西蒙)看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蝴蝶效應”。
生于英格蘭艾爾斯伯里(Aylesbury)的西蒙自小就對攝影有濃厚的興趣。自沃特福德學院(Watford College)畢業后,西蒙給倫敦的頂尖攝影師作助手,延續自己的攝影熱情。1988年,西蒙跟隨他熱愛的切爾西足球俱樂部(Chelsea Football Club)來到澳大利亞,承接拍攝澳洲最有影響力的廣告,并多次獲獎。
1997年,西蒙來到紐約,在藝術攝影和商業攝影領域繼續他的事業。現在的西蒙,一半時間在紐約,一半時間在悉尼。西蒙于2009年展出個人作品《融化:冰山肖像》(下稱《融化》),以影像表達他對環境與人類關系的哲學及美學思考。
本刊編輯部特請著名的澳大利亞策展人阿拉斯戴爾·福斯特(Alasdair Foster),就本期專題及西蒙的創作,專訪了西蒙。
自述:11歲,踏上藝術人生“不歸路”
從我記事起,就對人的選擇,人對人生道路的決定方式感興趣。我們在任意時刻作出的選擇,都可能影響并決定我們未來部分的生命形態。每條路都通向其他的路,再通向更多的路,連綿不絕,選擇無盡。這些路也許相互交叉甚至指向同一終點;但也有一些路,永遠沒有回頭的可能。
我在11歲的時候,就踏上了一條不能回頭的道路—我決定畫一幅泰坦尼克號撞冰山的圖畫。我其實不是很明白為什么我會決定畫這樣一幅畫,或這個題材是怎么出現在我的小腦瓜里的,但3年過去了,我仍在畫。我已經深深沉迷在藝術和藝術史的世界里。我曾花數個小時邊畫邊研究知名藝術家的繪畫作品,其中很多今天仍是我的靈感源泉。
之后,我又踏上另一條路,作出另一個選擇—學作攝影師。我報名攝影課時,心里還想著這不過是一種記事的方式罷了,我還是更喜歡繪畫。但當我沖洗出第一張照片,當我看到影像逐漸變得清晰時,一切都改變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完全個人化的情緒激蕩著我。“視野”這個詞語獲得全新的含義。那時我確定了,攝影將是我一生的摯愛。
我經常回顧我決定畫冰山的那一刻,以及那個決定將我引上的道路。我毫不懷疑我現在的人生與我11歲時的決定相關。要不是它,這組題為《融化》的作品也無從存在。在我對泰坦尼克號災難的調查中,我發現大多數冰山要先從格陵蘭島西海岸冰山巷(Iceberg Alley)與冰川分離,通過巴芬灣(Baffin Bay),經漫長漂流后進入加拿大的紐芬蘭及拉布拉多省東海岸,才能進入輪船航道。
這組攝影作品的第一張就展現巨大的冰山從伊盧利薩特冰灣(ilulissat Icefjord)進入格陵蘭島的迪斯科灣(Disko Bay)的場景;最后一張描述的是紐芬蘭東海岸的冰山。這時,它們已經漂流了成百上千英里,身形也已支離破碎,與最初相比,就像是鬼影一般。當看到它們最初的宏大,以及后來要被海浪吞沒的樣子,我感到它們都是美麗而低調的:這樣的形變賦予了它們生命的過程,使每一座冰山都擁有獨特的個性,有只屬于自己的故事。
這個拍攝項目的初衷是非常個人化的,是一次個人的心靈之旅。但當后來再翻看這些作品時,卻不可能忽略我們正在面對的環境問題。正如我在年少時的選擇決定了我成為怎樣的一個人;我們作為人類這個種群正在作出的抉擇,也將決定我們的未來,以及我們所居住星球的未來。
對話:每座冰山都有自己的故事
福斯特:你是在哪里拍攝這些冰山的?
西蒙:最終的影像分別來自兩個地方的兩次拍攝之旅:加拿大紐芬蘭的圣約翰斯(St. Jones)附近海岸;格陵蘭島附近的伊盧利薩特冰灣;位于格陵蘭島的迪斯科灣。
這個項目的拍攝過程如何?
這個項目從想法產生到拍攝花了將近4年時間。當然不是4年都在思考這一件事—我是在工作之余規劃這個項目的。但是,這讓我有時間仔細計劃,認真思考它的每一步。我還花很多時間觀察美國藝術家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1903~1970)的繪畫作品,他使用色塊的方式分割畫布。于是,我也決定用相似的方法,用3種元素分割畫面:大海、天空和冰山。我了解我想以海平面的角度拍攝—也就是坐在船上。當這些關鍵因素都決定下來,項目就初具雛形了。
拍攝經歷了兩次旅行:先是去了紐芬蘭,第二次旅行去了格陵蘭島。在紐芬蘭時,我通過icebergfinder.com網站來跟蹤冰山,然后再發船尋找它們,真是很容易。
在格陵蘭,我找到人帶我去冰峽灣,那里的水面暗藏危險,冰山都是大塊的,隨時可能崩塌,帶來巨大海浪。而且,因為冰山在一刻不停的移動當中,我們回去的路隨時可能被冰山堵住。這些可是我從未預料的……
是什么吸引你拍攝冰山的?
最初我沒想過要拍攝冰山。我只想探索人們的選擇是如何決定他們未來道路的;一個人作出的決定性行動或選擇,是能夠改變他一生的軌跡的。
我經常猜想,如果我沒有在攝影事業發展上有所追求,那我現在在做什么。我回顧了指引我走向這條道路發生的所有事件,我的成就,我交過的朋友,和更深層次的—我兒子的出生。這些,都是我們作出的選擇,我們走上的道路,都是我們自己的“蝴蝶效應”。
“蝴蝶效應”這個具有哲學意味的概念,是如何啟發你拍攝冰山的?
改變我人生軌跡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在我11歲那年的某一天,我決定堅持繪畫—這本身就是個偶然。記得那是在我的出生地英格蘭,一個陰雨天,我的父親建議我讀一本書或者畫幅畫兒來打發時光。我選擇了畫畫,畫一幅泰坦尼克號撞上冰山后沉船的畫兒。
直到近日,我仍無從知道是什么讓我選擇這個題材的。我將作品展示給我的父親看,他非常喜歡。我可以看出來,他的激動是發自內心的。第二天,他就帶我到藝術品商店,給我買了些油畫筆和帆布畫板……就是這樣。我愛上畫畫了!這分熱愛至少持續了幾年時間,直到攝影出現在我的生活里。確實,是我的第一幅畫作,引領我走上今天的道路。
我開始思考我的人生中這一關鍵的時刻,思考它是如何催生出這組全新的攝影作品的。難道說泰坦尼克號是我人生之旅的一個暗喻?當我查找有關沉船的相關資料時,我無意中發現一個叫“冰山巷”的地方。據說,撞沉泰坦尼克號的冰山就來自這里。我開始對這個地方感興趣。說實話,我覺得這個“冰山巷”的名字也蠻有趣的,聽起來就像冰山都在這里排著隊,等著不知情的船像強盜一樣撞上它們。
就在那時,我確定了:其實不是泰坦尼克號,而是冰山!冰山,才是我人生之旅的暗喻。
隨著拍攝的進行,為什么你說自己逐漸沉迷在冰山的世界中?
冰山是易碎的,也是善變的。它們是無所不能的,同時也是脆弱的,周圍的環境時刻都在改變和重塑它們的形狀。冰山一直都處在被外界力量改變的過程中,其中有洋流和天氣系統。同時,它們還是神秘而誘人的;對我來說,它們如神話一般。我對拍攝一些專屬我自己的東西的想法非常感興趣。
當然,以后也會有人拍攝冰山,但都不是“我拍攝的”冰山,我的冰山早就不在了。每個冰山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它們從冰川中誕生,踏上自己的人生旅程,被外界改變,最終,融化回歸大海。展示冰山從誕生到消亡過程的想法,于我而言非常明確。這就像是我自己的人生軌跡,也終將走向死亡。
有趣的是,我在看這些照片時,這些本似靜物的冰山似乎都各有“性格”。
我開始想將冰山描繪成靜物的模樣,就像雕塑。我猜當你開始用一種獨特的方式展現一個靜物的時候,你就有賦予它某種性格的趨向了。這也是這個項目名稱的來歷《融化:冰山肖像》,最初的題目只是《融化》,標題的后半部分是我完成拍攝開始回顧成品時想到的。我覺得每座冰山都有自己的故事。每座冰山都有各自不同的形態,在旅途中擁有各自的傷疤,那只屬于它們自己的傷疤。
你從這個拍攝項目中學到了什么?
北極地區在過去的50年中改變巨大。冰川在以令人警覺的速度消融,我們需要即刻做些什么。我不知道國家確切的對策,但我們對自己的未來負有責任,我們應該盡一切可能結束全球變暖的危險。
這組作品改變了我—不論是作為一名攝影師,還是一個普通人。這個項目起初是非常個人化的作品—我相信這是我作為攝影師的首個“真正的”個人作品。我出于直覺創作,所有的一切都指引著我的創作,那么自然,那么流暢,就像是肌肉的條件反射。
這些照片,能起到改變世界的作用嗎?
很不幸,我不認為它們能改變世界。已經有環保意識的人們也許會欣賞這部作品,但我不認為這些照片能夠或有助于“改變”看法。人們似乎都掉入過度的物質消費陷阱中,根本沒有考慮氣候變化的真正威脅。
即使美國在2010~2011年相繼遭受颶風艾琳和颶風桑迪的襲擊,我們所做的也只是重建房屋,等待下次洪水的光臨。人們重新購置的豪華車、高檔玩具和奢侈品,更加劇了全球變暖。當你想想這些,真是覺得瘋狂:一直盲目地做自我毀滅的事情,簡直就是“愚昧”。
就環保題材,你拍攝過其他作品嗎?
我還有其他環保題材的作品,也是率性而為興之所至的。我曾在2010年颶風桑迪襲擊紐約州東海岸時,去到美國的長島瓊斯海灘(Jones Beach),拍攝過一系列照片。
我熱愛海洋,這種感情近乎癡迷。也許是因為我長大的地方離海太遠,大海總是讓我著迷。海洋代表了一種比人類更偉大的力量。我是無神論者,對我來說,真正的力量來自自然。
如果我在這組作品中傳達了某種信息的話,那就是,我們都應該與我們所居住的星球有一顆“同理心”(Empathy)。
你覺得我們每個人能對環境保護做些什么?
我覺得人類正處于困境之中。我們一直都在關心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卻沒有看到更大的險情!看著我們親手毀掉自己的未來,真是既奇怪又哀傷。這是一種懶惰。就像我們吃大量的垃圾食品毀壞身體,然后再吃藥物讓身體恢復正常一樣。看起來是個簡單的選擇,其實是在加大對自己身體的傷害。
因我們的行為而受罪的不是這個星球,而是我們的子孫后代,因為我們正將這個星座變得不適宜人類居住。星球最終不會毀滅,但人類會被我們親手毀滅。當我們將這個星球搞得一團糟時,自然就會行使它的權力。我想,我們需要研究長遠的預防措施,而不總是只做短期“修復”。
如果你能向掌權者發送一條環保消息,你想說什么?
趕緊收拾好這個爛攤子!如果我們連居住的星球都沒有,那人們所有一切都是無關緊要的。為值得的事情奮斗吧,不要再把金錢花費在追求虛假的夢想上了!消除全球變暖才是正事,快分清主次吧!
人類最兇惡的敵人就是人自己。人們經常都不能為自己作出最佳決定,還要讓政府告訴我們什么對我們是有益的,我希望我們的政府能像父母對待子女那樣對待它的居民。我們需要重視精神價值,而不僅僅是經濟發展!
俗話說,躺在墳墓里論窮富,是沒有意義的—難道,這就是我們的未來?!